思想空間編者按:
2010年2月1日,陳冠中與梁文道同時訪問台北,應《思想》雜誌之邀,進行了一場圍繞公共知識分子議題的對談。十餘年後的今日,我們與讀者們一起回首,再看當時對於香港、大陸及台灣三地思想狀況的探討與洞見;對照這十幾年來各地政局和知識分子境遇的改變,在驚異於兩人敏銳的洞察力與預見力之外,也反思於現今態勢之下,知識分子何為?民間何為?
香港反高鐵必須提高到一個視野,反對高鐵背後的意識型態,而這個反對訴求對於整個中國也非常有意義。——梁文道
一、香港:兩岸三地之間的觀察
陳冠中:
1949年後香港整個文化圈,受台灣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以我個人為例,中學時閱讀的《明報月刊》,當時就常刊登殷海光或談論知識分子的責任等言論,大一時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又走進了一間書店——「文藝書屋」,裡面大多都是台灣的書籍,像是《文星》、《皇冠》、白先勇、余光中、李敖、柏楊、張愛玲的著作。這些書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
1960-70年代,香港文化界老一輩人仍舊熱衷談論中國政治問題。1970年代初因為釣魚台等事件,興起了青年運動。當時有一本親北京的雜誌叫《七十年代》月刊,另一本完全由年輕人辦的叫《七〇》雙週刊,兩本完全不同取向的刊物。後者的許多成員之後都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或托洛斯基份子,前者的成員與讀者則很重視中國問題。當時大學生間有很多毛派與四人幫的支持者,也有反對毛派的左翼大學生,雖然兩派在大學仍屬少數,但算是大學生參與社會、關心國家的一個興盛時期。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毛派都消失了, 有些進入了外商公司、後來也都成為愛國人士。我在那時出版《號外》雜誌,剛開始也有批判性的西方式新左文章,但同時也有很多介紹波希米亞及雅皮文化生活的內容。在1980年代香港金融地產起飛,整個思想市場被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佔據後,文化氣氛也轉向世界城市的品味風格,批判的態度逐漸消失了。之後的不同時期我在台灣和大陸都經歷過類似的文化氛圍的轉向。
1990年代到了中國大陸之後,很多情況是不一樣的,他們知識界用的話語仍舊是香港1960-70年代的話語,像是知識分子責任、中國往何處去、革命還是告別革命等,仍要討論人文的商品化問題, 這是香港80年代後一度已經比較少談論的。我剛開始的時候不太參與,很多人希望我談中國大陸的問題,但我當時認為自己對中國的理解仍然不夠,不好意思過於介入。直到2005年錢永祥叫我為《思想》寫關於中國的問題時,我才好好思考如何去論述中國。雖然文章寫的不滿意,但透過寫作過程,我才慢慢整理我的思緒跟想法。大陸的問題意識與香港、台灣是有點不太相同的,要理解他們必須進入他們的語境中,這樣的態度也會對於我們理解香港、台灣本身有所幫助。後來我觀察到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就是梁文道, 他是真正engage,我從他身上學得很多觀察的視角。目前,大家很難脫離中國大陸的框架去思考問題,不參與其中也仍會受它的影響,而不參與將會很被動。現在不能再以隔岸觀火的態度去看待大陸,而是要真的參與它的公共事務、公共領域,但是需要盡量的理解大陸思想界的問題意識,作為知識分子,發出我們的聲音。
梁文道:
關於香港我有個想法,九七年後香港內部的問題是沒有把解殖或去殖作為真正的課題集中探討,更不用說作為政治、社會的變革日程表的一部分。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但解殖或去殖並不是宗主或主權誰屬的問題,而在於這個政治結構與社會肌理如何在殖民時代被組裝、被建構成一套體系,而這套體系在香港有沒有被更動的問題。
1997年前有一段「香港熱」,很多國際文化研究或後殖民研究都討論香港的問題,但我覺得遺憾的是它們並未觸及政治解殖的層面。這個問題不僅未被討論,而且被另一個問題給置換,也就是如何保持香港的平穩過渡,最關鍵的詞彙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這組詞彙是來自於中英雙方的角力,加上香港普遍表達對共產中國的恐懼,於是最終決定保持原來的樣子:北京政府必須保證香港如同之前一樣,用基本法的框架大致把它封存下來,而且保證保鮮期50年。結果香港進入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狀態,到現在為止香港等於冷凍、封存了英國的殖民體制。這是在中國、英國、香港三方都接受的情況下造成的。當時香港人並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但這樣的殖民地狀態我想在1997後矛盾就逐漸出現。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嚴重,在全世界經濟體的排名大概都在前三位。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存在一個特首,雖然我們都認為他是北京所派命的,不過程序上仍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這個選舉委員會是由八百人構成,分別由界別委員會選出,這些界別包括文化界、金融界等,當然他們被配置的票數比例不太等同。這些界別所扮演的是社會的功能性團體,這個運作方式像是義大利法西斯時期所形成的政治結構,亦即把社會分成各種界別,再分配政治權力,用一套體制將彼此組織起來。這些界別看起來都可以發揮功能,但事實上僅被少數的界別掌握。舉個例子,香港的幾個大財團便壟斷了這些界別。因此,八百個委員內,這些財團可以操控大約四、五百張票。因此,香港政治權力的分配同樣也是不平等,而且貧富差距與政治權力的不平等是重構的。因為,這個政治經濟結構確保了最有錢的人同時也是最有權力的人。這在港英時期就已經出現,香港當時的港督背後有個行政局,行政局內部有幾個當然的委員,例如匯豐銀行的主席,這代表的是英國金融體系如何在殖民地內部進行政治統治。這個體制延續下來,現在只是換成了選舉委員會與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但仍然確保商業與金融菁英壟斷社會與政治的地位。香港是最服膺於自由放任經濟學的經濟體,Milton Friedman曾讚譽香港是資本主義的天堂,香港人也很高興,但我們所付出的代價是在亞洲四小龍裡,是最晚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的地方。這與香港政府不願投入免費義務教育有關,因為一旦要投入公共支出勢必得增加稅收,而這是資本家所反對的。同樣地,亞洲四小龍裡,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小龍都經歷慘痛的產業升級,香港則無法走向第二階段工業化,因為一旦採行工業化,便需要政府大量的投入,香港商界是不會同意像台灣發展新竹科學園區的模式。
香港在這樣的內部矛盾下,2003年出現了50萬人的「七一遊行」,雖然這場遊行如今看來具有反動的性質,但至少開啟了一個社會運動的氣氛。之後也出現許多保運活動,像是文化古蹟保育, 許多青年與當地的居民結合,一起參與保護舊城區、歷史古蹟的運動。這個運動在我看來,出現了香港的解殖想像。保護歷史古蹟與解殖在香港產生了弔詭的關係,舉例來說,前年有群香港年輕人在保衛皇后碼頭,這個碼頭傳統上是英國港督就任或英國皇室成員來香港時上岸的碼頭。但政府規劃要拆除,供財團進行大型的商業計畫。香港年輕人的捍衛引來許多的批評,例如有些報章輿論認為他們是在迷戀殖民文化、在保衛英國殖民遺產。但在我看來這個保衛文化遺產的運動恰好是解殖的想像,因為首先,它並不否認殖民的歷史,也不試圖掩蓋;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在保衛殖民記憶, 也是在對抗香港城市發展的邏輯。香港城市發展的邏輯是我們有大概五成的土地是公園,其餘狹窄的土地才來建築、開發。這是政府炒作土地價格的作法,政府的稅收就是從這些土地增值而來。這種作法造成地租昂貴,也限制了香港人有多樣生活的想法。這個城市發展的模式正好是殖民時期主要的經濟命脈之一,而香港主流社會也完全接受以這種經濟增長的模式。今年的反高鐵運動,都是在這些脈絡下伸展開來。只是目前真正的反殖意識有多強仍不夠明確, 裡面的本土意識,在我看來並不是所謂的「港獨」運動,而是在進行解殖的工作。因為,這些民主與社會運動都是針對香港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的殖民地遺產進行的:一方面保護文化古蹟,另方面也要求民主參與、甚至釋放劉曉波;追求本土並不意味放棄對中國大陸政治的關懷,甚至可成為中國與香港彼此之間社會運動的結合。例如Twitter裡面有許多中國內地的朋友支持香港人反高鐵及爭取更多的民主參與。反高鐵運動的意義不僅止於香港,在中國近年來發展的許多高速鐵路,也犧牲了許多人民的生活、拆遷許多農村,香港反高鐵必須提高到一個視野,反對高鐵背後的意識型態,而這個反對訴求對於整個中國也非常有意義。
新左派與保守主義出現了緊密的結合。這種趨勢我覺得非常值得觀察,這也是我憂心的,中國是否會出現一套國家主義的論述。——梁文道
二、如何理解「盛世中國」?
陳冠中:
1992年我到中國後,感覺到中國正發生劇烈的變化;但2008年的變化更是巨大,那年中國發生西藏三一四事件、五一二地震、奧運、西方金融風暴等,中國政府華麗轉身,民眾覺得西方並沒有那麼好,而中國的發展使政府和民眾的自信心都高漲起來, 我感覺到中國人的盛世感在2008年逐漸浮現,我聽到更多的是年輕一代人這樣的想法。其實他們處在矛盾的狀態,一方面生活壓力非常大,很難進入好的大學、要靠關係找到好的工作、憂慮是否買得起房子;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特別忠黨愛國,容不得有人批評中國, 對他們的父輩一代對黨和政府的批評也不耐煩,他們相信現在是很好的時代,所以他們特別支持政府。國家所傳達的意識型態和歷史解釋,他們完全內在化了。由此我似乎觀察到下一輪中國的模樣, 時代提供一個故事給我,於是我寫成小說。2009年1月份之後我開始動筆,寫了半年完成。我把時間推延至2013年,事實上,是在寫2009 年;希望藉由時間的推延把2009年的情況更突顯出來。我想問的是: 如果這樣一個盛世真的出現,知識分子如何自處,幸福的意義是什麼?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崛起,這個21世紀的大國應該是怎麼樣的大國?
對於大國崛起的事實,中國內部的知識分子很多也是非常興奮的,願意因此忽略或漠視許多問題。譬如說,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是否屬於殖民主義,知識分子大都是不想也不能觸碰這種問題。要知道甚至一個民主的共和國也可以是實行、支持殖民主義的,法國第三共和就是法國殖民主義最盛的時期。
在近幾年中國對於異議的聲音採取更多樣的壓制方式,也就是說,面對這樣的盛世,體制內已經不存在糾錯的機制,每個有位置的人都在說官話,盡力附和政府,這種情況到這兩年特別嚴重。而因為中央政府近年稅收增加,非常富有,也提供了許多資源給予學者,導致學者為求做學問不願多批評政府,許多產官學菁英都在政府的資源挹注下,過著豐富多彩的生活。以致於知識分子雖然大都知道社會有問題,但不想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他們能夠做到「不說真話,但也不講假話」已經難能可貴了。
近年大陸思想界的分歧很厲害。我曾參加過一個座談會,與會者有自由派也有軍方鷹派,主題是討論中國的未來;鷹派的學者跟我說,他們支持中國的民主憲政,不過通往憲政的道路現在只能是軍政;他們與自由派都批評政府,但軍方鷹派對政府的批評主要是反對政府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指責政府對中國的未來缺乏強國應有的遠見與戰略。
反觀,台灣或香港其實在以上和其他許多話題層面都可以著力,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
梁文道:
台灣與香港兩地在談中國的時候都有用中國來談自己的傾向,就和中國人談論美國其實都是在談自己,美國只是個區分內部政治立場的座標一樣。同樣地,台灣與香港的大眾媒體每次在談論中國時,也都是在談論自身。在香港,談論中國只有兩種態度, 一種是典型的反共反華,他們對中國的評論都是制式的,譬如說山西要是又發生了礦難,這類評論就非常簡單,最後的結論就是一句話:因為共產黨不民主。為什麼奶粉裡會有三氯氰胺?答案也是因為它是獨裁國家。所以談中國談了半天,只是不斷地加深與固定原有的刻板印象,無法細膩而深入地讓大家看到更多東西。另外一種類型的評論是這樣的:他們會說中國很大、很複雜,不能用簡單的價值來判斷,例如劉曉波被抓,我認為言論自由是基本的底線,這樣的作法絕對是不對的。但有一些學者似乎只是模仿中國官員的講法,大談「凡是都要有個過程」之類的論調。這兩派言論表面上是在談論中國,但其實都只是在投射自我主觀的願望,或者在表達與中國的某些關係罷了。我在香港常聽到許多讚揚中國的聲音,譬如曾經有個富豪找我去吃飯,問我為什麼對中國常有意見,他認為中國目前非常好,要做什麼馬上就可以做、要蓋什麼馬上就蓋起來。香港許多人很羨慕中國,認為這樣才是魄力、效率、速度。然而, 這些速度或效率背後的真實面卻是很少被理解。他們這些意見只是反過來在批評香港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而已。
這兩種中國評論的類型,同樣也發生在台灣。台灣輿論在談論中國時也多是在談論自己。香港與台灣都把中國當成座標,作為自己內部人群區分的方式,而非把中國視為一個真實存在的對象。這是兩地今日要談論中國最大的問題。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課題,我觀察到的是中國目前存在著一種法西斯的傾向。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出現幾次的論辯,像是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區分,雙方都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有不同的判斷。最近幾年的論辯有著很巧妙的演變,除了新左派與自由派外,出現了另一組的立場,目前仍未有明確的名稱去定位它,但一般稱為保守主義者,或者國家主義者,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政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他們從事古典學研究, 目的在於陶養人格、培養政治領袖。國家主義者出現後,原有的新左派與自由派出現微妙的牽動。新左派過去批評英美的新自由主 義,並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劃上等號,然而,在經歷金融風暴後,之前一些新左派成員如今的論點,卻反過來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的。更有許多學者開始思考「中國模式」,全方位地從法學、政治、經濟、社會闡釋「中國模式」,例如有位中國法學的學者就不斷提出中國憲法有自身的特色,它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中國模式」具有吸引力之處,在於他們往往以挑戰西方霸權與主流論述標榜自 身,認為中國有自身的一套,不受西方宰制;他們預設了一個本體論上的中國,西方理論資源根本派不上用場。對外在西方的知識版圖上佔有一席之地,對內則對政府的作法提供了正當性。新左派與保守主義出現了緊密的結合。這種趨勢我覺得非常值得觀察,這也是我憂心的,中國是否會出現一套國家主義的論述。
只能透過直接觀察與寫作,才能釐清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否則僅是停留在對它片面的疑慮或不安。——陳冠中
三、兩岸三地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社會運動
陳冠中:
1970年代當我開始撰寫文化評論時,對於上一代香港知識分子掛在口邊的這個詞彙是比較偏向玩世不恭的嘲諷,到了中國後,我也並不把自己定位成中國知識分子。當近年來英美思想界越來越多使用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後,也轉而影響中文的語境,三地民間也逐漸較常用公共知識分子這說法,鼓動了讀書人、文化界重新肩負一些改革與批判的使命。一開始我參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評論時,我並沒有想被說成公共知識分子,只是希望能帶給大陸不同的想法,主要座標是北京、上海、粵港的城市與文化,或者觀察輿論中比較少人談論的面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像是大陸出現維權運動,我就介紹美國的社區運動、消費者運動的資訊。我當時並不直接評論中國時政,直到受梁文道等人的一些啟發,這三五年我才逐漸意識到我們不能把自己當成外人,或避免麻煩而不發言。我們對中國的認知只能透過直接觀察與寫作,才能釐清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否則僅是停留在對它片面的疑慮或不安。我想香港、台灣與海外都能夠提供一些思考角度給中國,不能只是旅遊、城市、飲食男女的文化書寫;而中國也必須存在公共知識分子,若沒有批判的聲音,那麼中國這個準超級大國盛世的發展將是可悲的。今天我想說的重點是:台灣、香港的知識分子群體必須努力在大陸發出聲音, 成為大陸公共知識分子話語的一部分,介入大陸本身的知識分子討論。
梁文道:
「中國模式」或國家主義論述的出現,相對於許多香港的學者,我是較不悲觀。我認為即便許多年輕一代的學生崇尚中國的盛世,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容易自動變成維權人士,原因在於像是廈門或廣州等地方,人民原本並不想主動參與政治,但由於地方政府和部分外資破壞了他們原有的生活、污染了家園,使他們的生命深受侵犯,這才有了主動抵抗的情況。去年更有趣的例子是,有一群網友他們平日只玩網路遊戲,像是「魔獸世界」,根本不討論時事,但文化部決定暫停這個遊戲,於是他們一夜之間都成了反對者;文化部決定封鎖的原因也不是要控制什麼,只是因為政府與企業變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體制,為了維繫自身部門的利益,主動去管控網路。這個體制會莫名其妙地干預其他領域,為自己創生了一些反對者。此外,媒體與律師也是天生的反對者,由於媒體本身就是要報導新聞,然而,中宣部時常干預新聞播報的選擇,在長久的干預與壓制下,媒體會自動的變成自由派。律師也是一樣,長年面對政治的濫權和司法的腐敗,他們不得不從骨子裹變成反對派。所以我認為這樣的體制只會製造自己的敵人。
對亞洲或第三世界國家像是非洲與拉丁美洲,中國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在做國情研究,然而,這些成果最後都上升到國家主義的層級,研究目的也轉化為如何回應西方的問題,缺乏自主的研究, 以及與第三世界的知識對話和連結。在國家調控下的研究會產生許多知識關懷的偏差,像是我曾和一位水利學者聊天,討論西南水利工程對東南亞的影響,在雅魯藏布江、金沙江這些地區的水壩建設, 已經導致湄公河的水位下降,整個中南半島的水稻生產都會深受影響,那該怎麼辦。學者的回應竟是:那也沒辦法,因為中國要發展。我覺得這樣的知識關懷很可怕。這反映出中國的世界觀是非常侷限的,區域問題、亞洲問題都不在他們的視野中。我覺得這個區域的許多知識與社運都應該要連結。不過有時很多知識或資訊的相互學習,其成果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我去廈門訪談一些朋友在PS廠的抗議活動,我很好奇他們如何組織,標語和口號是怎麼形成的,這種型態與風格的街頭運動又是怎麼出現的。很意外的是,原來有一部分是看台灣的電視學到的。台灣的街頭運動某程度上成為他們模仿的對象,像是他們也會高喊:「大家說對不對!」香港對廣東也有類似的間接影響。
關於知識分子的身份,我個人是堅持必須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聽起來像是廢話,不過我認為,雖然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一直存在,但它的意義可能會變成一種形容詞,像是榮譽或尊稱,有時會把知識分子等同於學者。譬如中國媒體常稱我是學者,我就回絕這樣的稱號,因為我不在學院教書;也有一些媒體人用知識分子這樣的榮譽稱謂來質疑我,認為我只不過是做媒體的為什麼自居知識分子,我就會反問:你做媒體怎麼能不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對我而言,「知識分子」像是個志業(vocation),它可以是任何職業,作家、媒體人或學者,相反地,你可以是教授但卻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因為若不如此,我就沒有責任可言。其次、我從不把自己當成外人,我在台灣出生,香港是我的家,我長期在中國工作,書寫的對象是中國。我常在想我是不是個人類學家,但人類學家很少把自己寫的東西給他田野所在地的人看。但我做的正好是這個,那我到底是算內人還是外人?我一直不把自己當成大陸的外人,但同時也意識到我處在其中有些區別。知識分子在任何社會中,都要將自己定位成既在內又在外:「內」的意思是在社會中承擔一份責任,這點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把自己當成內人就是承擔這份責任。我最好居住在那個社會中,有什麼風險盡量一起接受。但另一方面,「外」的意思是必須要有距離感,保持一種批判的(critical)的距離,關於批判論述我比較保守一點,認為它仍然是在距離感中產生的。這種身份的定位,我個人沒有答案,但卻是我每天在琢磨、衡量的課題。
(本文摘錄自《文化研究:游與疑(思想15)》)
閱讀推薦:

《思想》雜誌由聯經出版於1988年發刊,2006年重啟。時至今日累積出版逾40期,收錄的評論、專文、書評已經超過300篇。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超華、王智明、沈松僑、汪宏倫、林載爵、周保松、陳宜中、陳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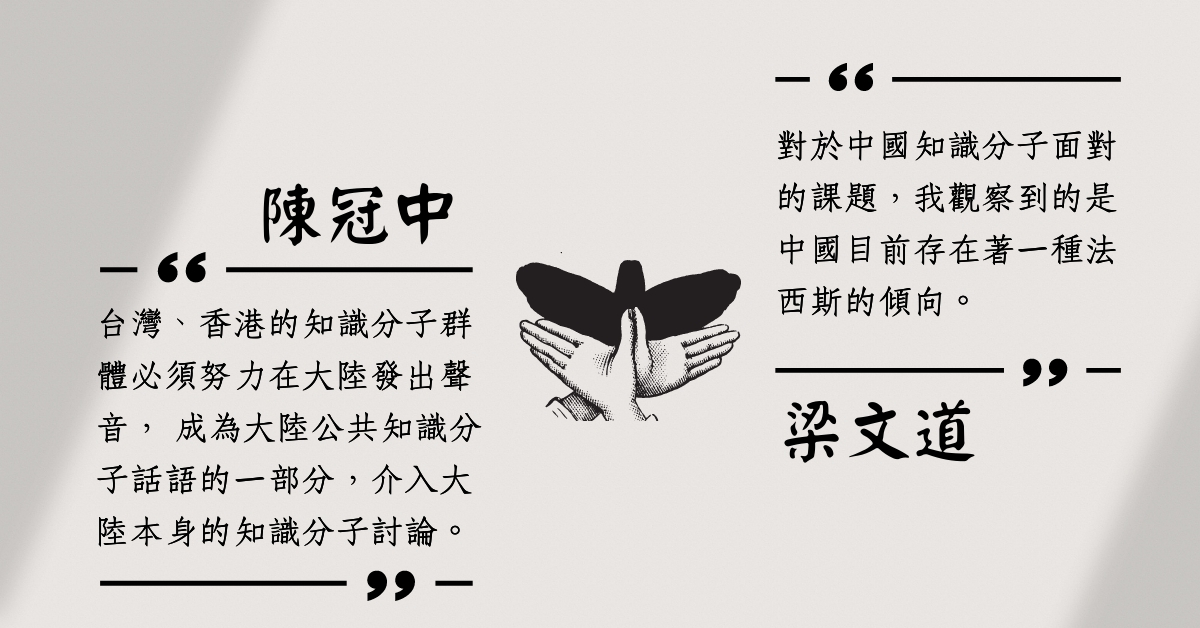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