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惡世間普通男子,這種感情甚至波及到了自身,以至於產生出了一種自我嫌惡、自我否定的乖張心理,導致寶玉的執拗異常之性別意識的原因,又究竟何在呢?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人一般不會對自己生下來就被賦予的性別予以質疑與否定。賈寶玉卻並非如此,儘管他所生活的是一個男尊女卑的時代,而且還是一位堂堂的貴族大公子,但他身上卻完全沒有作為一名男性的自傲,反而嫌棄自己的性別,逃避甚至否定自己作為一個男人的存在。作者一開始就將寶玉塑造為一個嚮往女性世界的「異端」,並將其希望再生成女子的強烈願望貫穿於整部《紅樓夢》。要之,如果我們不去解開賈寶玉為何會有這麼一個怪異的心理,我們就無法正確地去把握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的核心特徵,也就不用談去理解《紅樓夢》的主題以及作者的創作意圖了。
基於此,本章將集中分析《紅樓夢》中符合GID診斷標準「對自己的身體性別抱有持續的不快感」的描寫,進一步揭示出賈寶玉形象中的性別認同障礙者因素。
極端的男性蔑視、男性嫌惡.自我鄙視、自我否定
首先,寶玉具有一種極端的鄙視、甚至否定作為男性自我的強烈心理。此外,對於身邊的男性,諸如父親、叔伯、兄弟以及僕人都有一種強烈的厭惡感。這種厭惡感甚至還波及到了方外之人的僧侶與道士:雖然對甄士隱這種真正的看破紅塵之人以及渺渺真人、茫茫大士這種超凡脫塵之士無比尊敬,但對於混跡於寺觀之中靠化齋生活的僧人道士卻是無比的蔑視與嫌厭。在寶玉的眼中,世間的絕大多數男子都或是一群為了出人頭地而勾心鬥角的傢伙,或是沉迷於酒色,或是淪落於賭博,幾無一人可值得尊敬者。
然而,這裡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即使是世上男子確如寶玉所云之「臭男人」、「鬚眉濁物」,但一般也不至於嚴重到要去否定自己的身體性別。然而寶玉,卻毫不掩飾對將男性之自我的本能嫌棄,自嘲為「鬚眉濁物」、「怡紅院濁玉」,顯然對自己的性別抱有一種強烈的否定願望以及深度的厭惡心理。因此,庚辰本第七十八回「怡紅院濁玉」之脂評云其為:「自謙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評天下之男子,竟自謂。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矣。」
嫌惡世間普通男子,這種感情甚至波及到了自身,以至於產生出了一種自我嫌惡、自我否定的乖張心理,導致寶玉的執拗異常之性別意識的原因,又究竟何在呢? 我認為,寶玉的這種錯位心理,歸根結柢還是在於其對女性之異常追慕的心理,以及在現實中因無法變成女子而自我嫌惡所派生出來的深深的絕望感。
比如,類似以下之描寫在《紅樓夢》中可以說有不下十幾次。第二回借冷子興之口寫道:
說來又奇:(寶玉)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他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 將來色鬼無疑了!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這句話可以說是《紅樓夢》中最為家喻戶曉的一句臺詞了。又,第五回寫道:
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 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
這段話,寫寶玉被不知內情的太虛仙境仙女們錯罵為「濁物」,導致寶玉立即陷入了一種自我嫌惡的狀態之中。對於這段話,有正本脂評云:「貴公子豈容人如此厭棄,反不怒而反欲退,實實寫盡寶玉天分中一段情癡來。」
更有個呆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呆意? 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湘雲、黛玉、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
這些話,都指明了寶玉之徹底崇拜女性以及蔑視男性的心理。毫無疑問,這些出自寶玉之口的男卑女尊的見解,在當時可以說均是一些驚世駭俗的話語。由知,寶玉的心中已經徹底放棄了自己作為男性所應履行的尊嚴與義務了。
類似上述的這種描寫,還多次反復被穿插於第十九回、第三十六回、第四十三回、第五十八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六回、第八十一回、第一百零九回、第一百十一回等章節之中。通過這些描寫,寶玉的強烈的女性讚美以及蔑視男性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鞏固。其實,無論是無法抑制的蔑視男性及自我嫌惡思想,還是讚美女性及女性崇拜思想,都是基於同一種人格所產生出來的。而這種人格,無疑絕不可能一般男性所會具有的普通人格。
【性別認同障礙者(MtF)訪談餘錄】
筆者的提問:
寶玉的性格之中,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男性憎惡、男性蔑視、自己嫌惡、自我作踐等特徵。而與此鮮明對比的是,他又具有一種異常執著的女性崇拜、女性讚美之心理。這種性格的刻畫,也可以說是《紅樓夢》所要突出表現的男性觀與女性觀的一個重要特徵。只是為什麼《紅樓夢》的作者需要通過寶玉這個人物形象,來表現出這麼一種鮮明的男性蔑視與女性崇拜的思想呢? 過去往往將其推測為受時代風潮的影響,顯然這並不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我個人認為這是作者希望將寶玉塑造成為一個性別認同障礙者形象,所以才會出現如此鮮明的性格刻畫。在GID的精神療法之中,有一條是「改善因為自我嫌惡而導致對自己之過低評價」,也就是說,不難想像,性別認同障礙者往往由於抱有一種濃厚的自我鄙視的深層心理。您認為如何?
N.M 的回答:
我本人也抱有很濃厚的自我鄙視、自我嫌惡的心理。性別認知是自我評價之最為核心的一個部分。GID由於身體性別與心理性別不能形成一致,導致了在自我評價之時失去信心,無法得到一個完整的自我形象,因此很多人都會有一種強烈的自我嫌惡、自我鄙視心理。最終必然導致了憂鬱症的併發。這種現象,醫生和其他的友人也常常有所提及。
【研究報告書中所見到的實例分析】
《性別認同障礙的社會學》的作者佐倉智美寫道:「幼年時期父母總是會口無遮攔地強調『男孩就要有個男孩樣子』。父母的這種性別偏見(gender bias),導致了孩子總是處於一種心理極度緊張的狀態。另外,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往往都對於和自己同性的孩子抱有一種特別期待的心理傾向。⋯⋯這種期待往往會轉化成一種壓力,不能完成父母對自己的期待,導致孩子之自我評價之進一步的降低,很容易讓親子關係出現裂痕。」(頁三三)
作者所賦予寶玉的這種女性崇拜思想,還不是僅僅簡單地將女性當成一個普通的血肉之人來予以讚美與膜拜,而是將女性看作為了天界仙女的化身。
對女性極度膜拜的寶玉
從上引的例子不難看出,寶玉之「對於自己身體性別之強烈的憎惡感」,經常反應在其對於與之相反性別(女性)之異常的頂禮膜拜。然而,在現當代的GID(MtF)的診斷標準之中,諸如「女性崇拜」、「女性讚美」之類的要素並未包含在內。不過,這可以考慮為在提倡女士優先紳士風度的現代社會,有可能認為這種讚美乃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舉動,沒有認為其有多大的特殊意義。然而,在舊時代之男尊女卑之社會,這種舉動卻當視為具有極為重要之象徵意義。基於此,讓我們在此再來分析一些新的例子,來看看作者是如何通過對於寶玉之「女性崇拜」、「女性讚美」的描寫,來反襯其烙刻於心中之強烈的自我憎惡感。
比如,第四十九回描寫寶玉看見來投靠賈府的親戚家的女孩時,忍不住對襲人、晴雯等丫鬟歎道:
你們還不快看看去 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倒像是寶姐姐的同胞弟兄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更有大嫂嫂這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 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
一句「老天,老天! 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以看出寶玉對於嬌媚之女孩的讚美是如何的癡狂且不加任何掩飾,任由這種感情溢於言表。
又如,第五十八回之寶玉「天既生這樣人(芳官),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的感歎,第一百零九回描寫寶玉在黛玉死後,反反復復地叨念到:
「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 寶玉晚間回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
還要引起我們注意到是,作者所賦予寶玉的這種女性崇拜思想,還不是僅僅簡單地將女性當成一個普通的血肉之人來予以讚美與膜拜,而是將女性看作為了天界仙女的化身。這種描寫,其根柢還在於當時極為流行的仙女崇拜思潮。可以說,這一思潮才是寶玉之女性崇拜之本質,也是《紅樓夢》在建構整部小說框架時的一個核心的先決要素。於此,我在拙著《〈紅樓夢〉新論》第五章〈作為仙女崇拜小說的《紅樓夢》〉中已經有過比較詳細的考證,此處就不再贅言了 。
另外,第一百一十一回,寫賈母去世時丫鬟鴛鴦自殺殉死,寶玉聽到此事,驚得目瞪口呆,兩眼發直。在襲人的勸說之下,好長一段時間才哭出聲來:
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 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
這段描寫,更是具體地反映出了明末清初之「天地秀靈之氣,獨鍾於女子」之思想的濫觴 。可以說,這是《紅樓夢》之敘事展開的最為重要的基調之一。
上文也提到過,諸如「女性崇拜」、「女性讚美」之類的情感表現並沒列入現代GID之診斷標準之中。然而,如果我們可以超越時空去對明清時代之士人來作一個GID診斷的話,「對於與自己身體相反之性別的連續的認同感」這一診斷標準之中,「女性崇拜」、「女性讚美」無疑會是當時之士人之最為具體的行為反應之一。在從幼兒園就開始了男女共學的現代社會,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比以前的時代對於異性之了解要豐富得多。而由於現代社會科學思想的發達,也基本上不存在將女性視為仙女而予以崇拜的一社會風潮了。
凡此種種,導致了現代GID沒有將諸如「女性崇拜」、「女性讚美」的行為單列為一個診斷標準。可是在當時,如果作者要把寶玉塑造成為一位性別認同障礙者的話,那麼,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賦予其一種無視作為男性所應具有的自尊而去異常崇拜異性之女性的特質,並且還需不加掩飾地去用盡華美之辭藻去表達對於女性之追崇。而這又恰恰就是本節所指出的寶玉最為重要的人格特徵。
【性別認同障礙者(MtF)訪談餘錄】
筆者的提問:
在前面我們談到過的抱有一種自我嫌棄、自我鄙視的心理,很難融入儒教之男權社會的性別認同障礙者(MtF)之身上,而因此逆反出一種非常強烈的女性崇拜、女性讚美的思想,並且將這種崇拜具體表現在言談之中。這種現象在現實之中是否可能存在呢?
K.S的回答:
作為男性而被認知,就會被強加要求履行作為男性的社會義務。而作為MtF,與進入男權社會相比,他們往往更渴望融入一個女性社會,並且也為能得到女性社會之認同而做出巨大努力。這種努力,往往會直接通過一些女性崇拜的言談舉止表現出來。這種現象就我個人而言,可以說是極有可能的。不過,現代社會的MtF,由於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對女性行為以及心理特徵進行細緻了解,或許會認為賈寶玉的舉止言談過於顯露。不過,在古代社會之中,這種無法通過別的途徑予以表現的女性崇拜思想,被轉換成文學語言以求達到一種心理宣洩的效果,應該是非常有可能的。
【補記】寶玉之女性崇拜的本質
另外,在上文所引用的賈寶玉那些偏激而極端的女性崇拜及女性禮贊的發言,在封建社會無疑是一種背經離道的荒誕行徑,然而,到了近代社會,這些言行一方面被社會女權主義者予以了高度的評價;而另一方面,由於寶玉的女性讚美乃是一種極端的讚美,即往往限定在了處女,而不是無條件站在全部女性的角度,又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批判。如何來看待這一矛盾,於此再做一些補充說明。
譬如,第五十九回,有這麼一段描寫:
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倒也有些不差。(下略)」
這裡借春燕之口表述了寶玉之有關女人質變的思想:結婚之前的處女期、結婚(妻妾)之後的婦人期、年老色衰的老年期,時間越往後推,就變得越無趣味。寶玉特別憧憬的乃是那些還未結婚處於少女期的女孩們。如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是否還可以將寶玉看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女性崇拜者呢?
如春燕所言,通觀整部《紅樓夢》,我們可以看出,寶玉的處女崇拜思想是根深柢固的。不過,其思想卻絕不同於當時之男權社會中所蔓延的所謂的處女崇拜思想。有何不同,讓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段話,第七十七回有文如下:
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著他們,看走遠了,方指著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但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發狠道:「不錯,不錯!」
從寶玉的發言可以看出,他的女性崇拜思想,確實不是對於所有女性的崇拜。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在於女性年齡的多少、容貌的盛衰,其矛頭乃是針對那些被男權社會之風氣規範、禮法習俗所污染了的女性,正是這些沾滿了銅臭、滿肚子壞水的婚嫁女人,才被寶玉排除在「女性」這一範疇之外。上面引文中畫線部分尤其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寶玉之所以憎惡結了婚的女性,並不是僅僅在於女孩的出嫁成為阻礙他與她們繼續廝混的障礙,而更在於他擔心這些純潔的女孩們,一旦進入了男權社會,受到污染,會變得比男性更加勢利與市儈,而其本最吸引寶玉的清淨無垢的「純潔心靈」則會蕩然無存了。寶玉對於結婚女性之貶低,本質仍在於此也。
又,第六十六回借尤三姐之口寫寶玉道:
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咱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 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繞棺,咱們都在那裡站著,他只站在頭裡擋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髒,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倒。他趕忙說:『我吃髒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三姐所描述寶玉的這種被常人視為怪癖的行為,可以說《紅樓夢》中隨處可見。要之,寶玉所崇拜的乃是那些沒有被男性或男權社會所玷污的年輕女孩及其純潔的心靈,而極度厭惡那些被男性之臭氣所浸染了的已婚而變得愚鈍的婦女——「寶玉素習最厭勇男蠢婦的」(第三十五回)。如果我們僅從是否符合封建社會之傳統價值觀,或者是否符合近代女權主義思想的觀點去分析寶玉的女性崇拜思想的話,就無法與作品中之寶玉之真正的形態達到吻合。其思想的核心還是在於對於男性的極度厭惡,這也就是性別認同障礙者之最為本質的特徵。
(本文節錄自合山究 (Goyama Kiwamu):《紅樓夢新解: 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標題為編者所擬。)
參考資料:
- 汲古書院,一九七七,頁一七九——三〇〇。
- 參照拙著,《〈紅樓夢〉新論》之第二章〈明末清初之女性崇拜的進展與《紅樓夢》〉中的相關考證,頁五三——八六。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漢學家。自2006年《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出版以來,書中見解經東西方學者多次徵引,甚而啟發出眾多相關研究,誠為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的劃時代經典論著。從1997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論》,到2010年《紅樓夢》的研究總結《《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合山教授為明清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所挹注的豐沛活力與卓越貢獻,早已深受學界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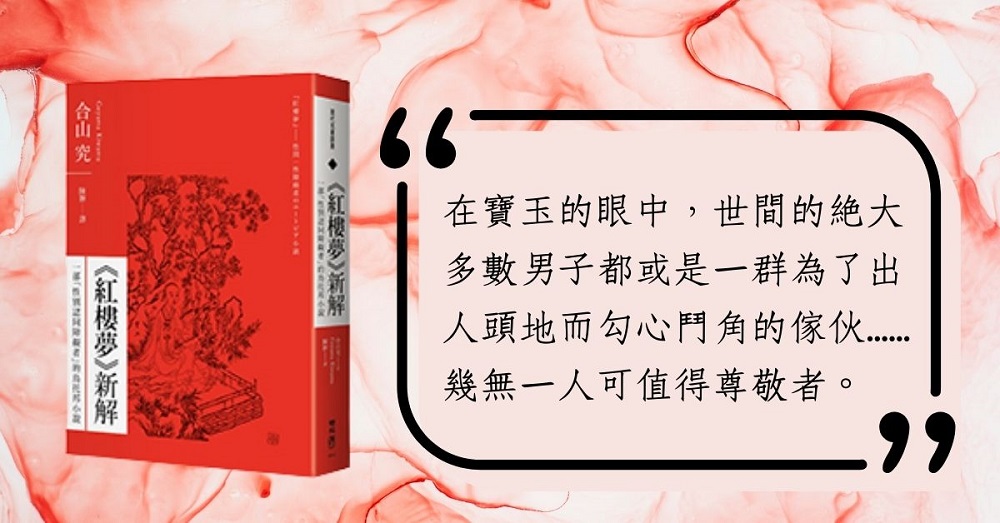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