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是一個人的工作,你一個人安排這些情節,這些人物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無中生有的。」
「下午三點的陽光都是似曾相識,說不出個過去,現在,和將來」,這是《長恨歌》裡的經典一幕。此書作者王安憶,於2017-18學年受邀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小說寫作課程。趁此機會,「虛詞」在中文系的辦公室拜訪了這位產量頗豐的作家,時間恰是下午三點;訪談亦隨著王安憶的思緒,穿梭於無法明述的時間流之中。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
文學精英的邊緣意識
王安憶與香港的淵源頗深。1983年,隨母親從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歸來,她便第一次來到香港。此後,王安憶發表了《長恨歌》、《天香》等作品,在華語文學界廣受關注,亦受邀參加不少香港的文學活動,也在多間院校擔任駐校作家、教授小說寫作。小說《香港的情與愛》裡,主角老魏心中曾想過:「積蓄香港經驗,就像在往臨時的空房子裡添置東西」,或許也暗示著她自身與香港的微妙關係。
問及對香港的第一印象,王安憶的感受卻並非常人所道的繁華、商業。彼時住在北角三聯書店招待所,她從民居生活中見到了香港更市井的一面:「來到香港後,我看到了繁華後面的世界,因此對這裡的華麗印象就有些褪色。」中國人喜「大」,推崇宏觀敘事、書寫正史,王安憶卻著眼於日常精微之處:坐在馬路牙子上的老人、站在弄堂後巷裡的女人,都是她暗中留意的對象。從她的視角看出去,常能收穫到焦點以外的風景,而這也體現著她的邊緣敘事美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們還能看到一些另類的東西,比如J.D.沙林傑(J. D. Salinger)的《麥田捕手》、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麗塔》,都在描寫社會規則之外的人。然而這一百年來,人類生活卻愈來愈體制化、格式化。」批量生產的生活模式叫人不安,也令她預見我們的寫作對象將隨之變得愈來愈單調。
王安憶說,理想的小說是要呈現不入流的人物、旁門左道的事件,讓秩序以外的事物成為小說的主體。這或許也與她的邊緣身份有關——幼年住在南京軍區大院,一歲時舉家移居上海,外界的語言聽不太懂,到了學齡被迫要學上海話,但直到現在也講得不算流利。王安憶笑說自己一生操作「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沒有正統的口音;而她心中秩序之外的故事,也在這混雜的語境中生成。
道德線外,以虛構創造美學價值
文學小說寫甚麼?對王安憶而言,「病態人格」、「畸形情感」都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元素,承擔著文學「破格」的要義。在課堂上,她推薦學生讀《洛麗塔》、《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試圖透過文本探討,找到當今學生關心的話題。結果不難預料:凡與同性戀、禁忌之愛有關的文本,都引起高質量的討論,這也引發了她的思考:「虛構與道德底線之間,有著複雜、微妙的差距。納博科夫的《洛麗塔》面世之後,挑戰也隨即出現:我們該如何對待倫理和美學?」謹慎的王安憶不願輕易將兩者剝離,而是嘗試提出疑問、釐清箇中關係:「創作是否要遵從社會現實?如不需要,我們又應遵從甚麼來進行虛構?」就此問題,她指出非虛構有著明顯的道德標準,而美學不然,它的標準應當獨於現實之外。
米蘭·昆德拉曾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寫道:「如果我們想在走出這個世紀的時刻不像進入它時這麼傻,那就應當放棄方便的道德主義審判,並思索這些醜聞,一直思考到底,哪怕它會使我們對於甚麼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質疑。」在突破禁忌與撲面而來的質疑中思考,或是為了華麗地「走出這個世紀」。王安憶憶述,八十年代的中國小說也常有對禁忌的挑戰,每一次的「突破」實際上都帶有對道德的挑戰。時至今日,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知當年的破格創作是否也為此埋下過種子?
「小說是想像、虛構的,又是要參照現實的。這也是現在小說寫不好的原因——生活太爛了。」王安憶真是一針見血。小說不僅僅是對生活的體現,還應表達我們對生活的期望,然而當生活卡住了想象的脖頸,小說應該如何繼續寫下去?對此難題,她卻自成一套方法:「虛構寫作建基於現實,但更需要想像力,材料的『價值』應完全由作者賦予。」寫作的同時,作者還須反復思考:為甚麼而寫?要寫成甚麼樣子?讓不堪的現實與虛構能量銜接、並行,從而應對美學與道德之間的難解命題。
某些故事能夠自行發酵
小說基於現實而寫,要賦予現實材料「價值」並不容易。王安憶寫小說,從不堆砌或強求粘合素材,而是任憑故事在腦中發酵,逐漸生長成作品。
最為讀者們熟悉的《長恨歌》,也是發酵得來的作品之一:「《長恨歌》的原型,其實是我很早以前看到的一個社會案例,過了十幾二十年我才坐下來寫,這時才發現記憶已經變形了。能夠變形,也是因為它本身擁有一種能量。」寫作高度自覺的王安憶,卻鮮有抄寫筆記的習慣,反而將不同事件一股腦兒放在心裡,不怕遺漏、淡忘:「好的東西總會自己留下來」。
然而不是每件事都有機會發展成一部好的作品。王安憶自認是「投資型」的作者,要看到事件生長的機會,才願投入去寫。可是有機物的生長不能全然預期,有時想寫中篇,後來發現能源不足,只好縮減篇幅;也有些作品如《匿名》,本打算寫成短篇,寫的時候卻猶如「走進一個很小的洞口,才發現裡面很大」,最後洋洋灑灑寫了三十幾萬字。「寫作發酵」過程看似隨機,其中卻蘊含著作者多年積攢的功力。
每位小說家都有不同的創作方式。席間我們提到香港作家黃碧雲,寫作前常作大量資料搜集,沉浸在素材的時代世界裡。王安憶捕捉到其書寫特性:「黃碧雲寫《烈佬傳》時,與書中的周未難(囚犯志榮)接觸了好多次,她是一個非常重視自己體驗的作者,能進入自己書寫的世界裡。」反觀她自己,寫作時則多帶有「操作」的成分:「我還是與寫作對象保持一些客觀的距離」,這是王安憶投入寫作的方式。兩位小說家都從現實事件中擷取元素、進行發酵,唯前者著重主觀感應,後者則較為冷靜、抽離;這讓我們看到小說家也有不同型態。
寫小說比上舞廳快樂
寫作中的王安憶是孤獨的,她不斷強調「一個人生活」的狀態:「寫小說是一個人的工作,你一個人安排這些情節,這些人物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無中生有的。」寫作不比拍電影、演話劇,沒有集體配合,有的只是一個人、一支筆,孤軍作戰,王安憶亦即自己創作世界中的文字統帥。
然而外部世界光鮮、好玩,不斷考驗著寫作者的耐力:「我年輕的時候也會去玩、去旅行,或晚上在歌舞廳玩到深夜,但回頭想想,還是沒有一件事讓我感到比寫作更有趣。若不讓我寫作,一切都沒甚麼意思。」王安憶不是清心寡慾的隱居者,但比起招搖的外部世界,她更願意沉入內心繼續書寫。為了讓這種寫作的熱情得以穩固延續,自二十年前開始,她便堅持每天早起寫作,恪守時間規律,每天寫作的「滿意度」也成了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之一。
「我可能是那種特別喜歡寫作的人」,作家略帶腼腆地說。寫作四十載,個人生活與外部局勢幾經變遷,簡簡單單的一句表白,也隱含著對文學、寫作的諸多疑問。生活繼續爛下去,小說何以繼續企盼未來?書寫建基於初心,思考緊追而來;寫作雖是一人勞作,那一個人,也在面對著整個世界的問題。
(感謝《虛詞》授權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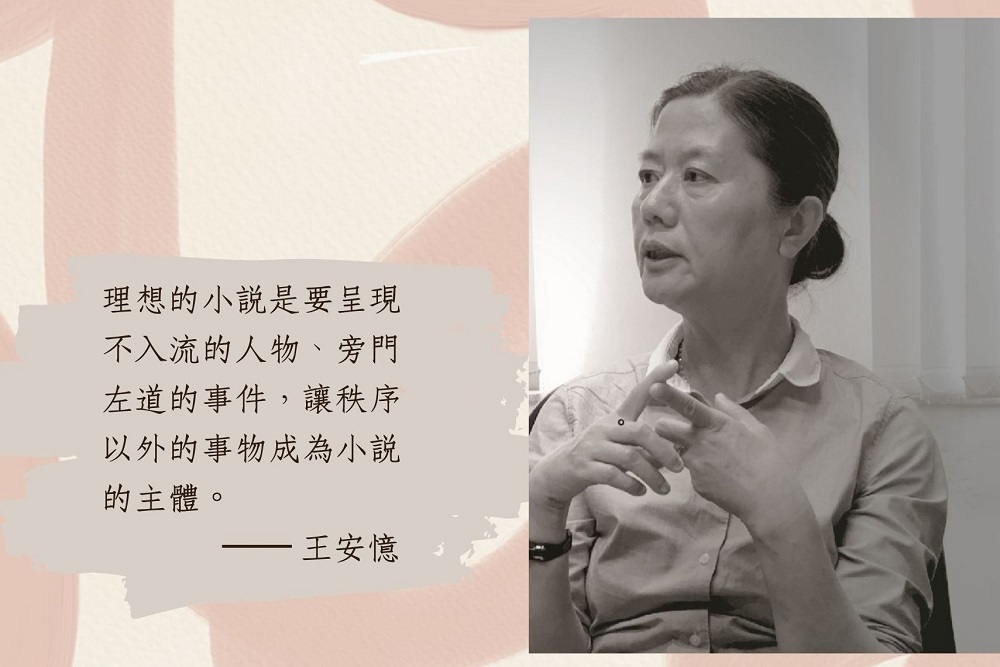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