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能成為「寫戰勝佛」。寫而不鬥,不鬥而勝,戰勝時代的偏見、時代的障礙、時代的病態、時代的潮流,然後成為善於筆下生花的小菩薩。
前兩年我在科大講過「文學常識」,共二十二講。這一次我講述另外一個題目:「文學慧悟十八點」。「慧悟」這個詞,錢鍾書先生很喜歡,他告訴我,這兩個字可以多用。慧悟,就是要用智慧去感悟萬物萬有,包括社會人生與文學藝術。我準備講述的是文學的起點、特點、難點、基點、優點、弱點、戒點、亮點、拐點、盲點、終點、關鍵點、制高點、焦慮點、死亡點、審視點、回歸點、交合點等,講述的方式也是慧悟,用這些文學的「要點」作題目,既可明心見性,又可區別流行的教科書。我的講述包含許多自己的經驗和體悟,算不上研究。正如我對《紅樓夢》的閱讀,不稱作「研究」,即不把《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只作為感悟對象,所以我寫的書叫作《紅樓夢悟》。
寫作沒有快捷方式,只能靠不斷修煉。每天讀,每天寫,自然就會進步。我的課程,只能是幫助大家理解文學,明白文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的人搞了一輩子文學,最後還是不知道何為文學。對文學有了一定的理解,寫起文章自然就不同。
在第一堂課裡,先講我們的課堂關係。我與大家的關係不一定叫作「師生關係」。我愛讀《金剛經》。《金剛經》裡面說不要有「壽者相」,那我也不要有「教師相」,只想少些教化腔,多些大實話。之前在《文學常識二十二講》的開頭,我借《紅樓夢》中的一個詞來界定我與同學們的關係,就是「神瑛侍者」,賈寶玉前世的名字。「神瑛」就是「神花」,「侍者」就是「服務員」,我是你們的服務員。其實,好的老師、好的校長、好的編輯,都是「神瑛侍者」;蔡元培先生就是偉大的「神瑛侍者」。這一次新的課程,我還想用新的詞來界定我們的關係。《西遊記》裡,唐僧、孫悟空一行到西天取經,最後師徒四人有兩人被「封佛」。孫悟空被封為「鬥戰勝佛」,可是他不在乎,只希望能摘掉頭上的緊箍兒,重獲自由。其實不必把「佛」看得太沉重,孔子講的「聖人」、莊子講的「至人」,也是佛。我此次借用「鬥戰勝佛」這個詞,並改動一個字,希望大家能成為「寫戰勝佛」。寫而不鬥,不鬥而勝,戰勝時代的偏見、時代的障礙、時代的病態、時代的潮流,然後成為善於筆下生花的小菩薩。寫作,要克服許多的困難,希望大家無論是學文科的還是學理工科的,最後都能成為「寫戰勝佛」——這是希望,也是祝福!
有人說我是「紅學家」、「自由主義者」,我非常生氣。我是為寫作而寫作,像高行健說的,「沒有主義」。
你們已經自我介紹,那我也自我介紹一下。關於我自己,想講三點。
第一點,我的「生命四季」,春夏秋冬。
我的「生命春季」始於小學時期,到高中畢業時基本上就結束了。這個時期,是年少單純的綠色,除了瘋狂讀書,什麼也不顧。我在福建國光中學讀高中時,那裡有全省最大的一座中學圖書館,我沉浸於其中。當時愛讀書愛到管理圖書館的老師都感動了,他把圖書館的鑰匙交給我,讓我隨時都可以借閱。讀莎士比亞的三十幾部劇本,讀得很快,最怕的是把它們讀完 這麼精彩的作品,讀完了怎麼辦?少年時記憶好,那時看的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到現在還是我生命的一個部分,其中的人物情節還時時在我的靈魂裡燃燒。高中一年級時我讀的是泰戈爾、冰心,很單純;二年級時讀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開始關注生命的衝突和矛盾;三年級時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就進入靈魂更深處。魯迅的小說、高爾基的「三部曲」,讀得更熟。我講這些,是希望大家珍惜所處的生命春季。我在美國跟李澤厚先生散步,他說要給「珍惜」加上一個定語,叫作「時間性珍惜」,意思是說時間很快就會過去,一旦消失就不會再出現。就像我們現在上課,過去了就永遠不會再有。我喜歡「瞬間」和「永恆」這對哲學概念,「永恆」就在「瞬間」當中。人生是很辛苦的,今天上課,很多同學要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很辛苦,更不用說人的一生了。卡繆說,最大的哲學問題是「人為什麼不自殺」,我們為什麼感到值得活下去,就因為眷戀一些「美好的瞬間」。比如我今天跟大家相逢,就是一個「美好的瞬間」。日本人很重視「永恆」和「瞬間」的哲學命題。櫻花哲學,便是「永恆」就在「燦爛的瞬間」當中。武士道精神,三島由紀夫寫的作品,都是在講「永恆」與「瞬間」。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生命的春季,每天都盡可能生長,每天都盡可能讀書、寫作,有所前進。
到了大學,就進入了「春夏之交」,我的心靈開始出現了分裂,那是文學與政治的分裂。開始是小分裂,後來是中分裂,到了「文化大革命」,則是大分裂。外面是兩個「司令部」,我心裡面也是兩個「司令部」。社會太政治化,兩條路線,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幸而有文學的積澱。文學救了我。有文學中的人性墊底,我就排除了許多「政治病毒」。文學讓我守住「不可傷害他人」的道德底線。因為有文學的積澱,我終於戰勝了政治的狂熱,沒有墮落。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就不只是心靈分裂,而且是心靈「破碎」了。又是文學,讓我的心靈重新恢復了完整。
出國以後,我進入「生命的秋季」。「秋季」最重要的事,是由「熱」轉「冷」,開始冷靜了。我跟高行健先生是最好的朋友,他是「冷文學」的一個代表。他對我說,到了海外,我們兩隻眼睛要分開使用,一隻眼睛要「看天下」,一隻眼睛要「觀自我」、「觀自在」。高行健的「觀自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寫劇本《逃亡》,發現人最難衝破的地獄是「自我的地獄」;他寫《對話與反詰》,寫「夜遊神」,都是對自我的冷觀。在世界文學史上,他創造了一個嶄新的「人與自我」的維度。我和林崗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罪與文學》,也是在觀自我。我們認為,過去所出現的錯誤時代,自己也參與創造了,自己也有一份責任。我寫《紅樓四書》、《雙典批判》,很冷靜。我在美國建造了一座「象牙之塔」。魯迅說要走出「象牙之塔」,要擁抱社會,參加戰鬥,改造中國,拯救民族的危亡,這在當時是對的;可是現在是商品社會、商品時代,商品覆蓋一切,所以我們又需要一座「象牙之塔」。在「象牙塔」中,可以贏得「沉浸」狀態、「面壁」狀態,這樣讀書才有心得。
我現在是「冷藏」在「象牙之塔」裡,進入了「人生的冬季」。如今,我跟松鼠、野兔的關係,已經大於人際關係了。馬克思所講的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對我來講已經不合適,我更多的是「自然關係的總和」和「個體存在的總和」。個體存在,有生理存在、心理存在、意識存在、潛意識存在、感官存在、精神存在等。《紅樓夢》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我的內心也很乾淨,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我說「冷藏」,並不是開玩笑,我的老鄉、明代思想家李卓吾,他寫的書不求發表,自稱「藏書」、「焚書」,這樣才有寫作自由。為了發表而寫作,會受制於報刊。無目的的寫作,就像賈寶玉為寫詩而寫詩,在詩社裡能寫詩他就很高興。他的嫂嫂李紈評詩時說寶玉壓尾,第一名是林黛玉,然後是薛寶釵、探春等人,賈寶玉就開心地鼓掌,連說評得好。可見寶玉不在乎評獎,他是無目的的寫作,這是比較高的境界。把真情實感寫出來,這是我生命冬季的一個特點。
春夏秋冬,生命四季,這是「我的心靈史」。無目的寫作,是我最後的覺悟。有人說我是「紅學家」、「自由主義者」,我非常生氣。我是為寫作而寫作,像高行健說的,「沒有主義」。王強(新東方英語學校前副校長)給我的一本書作序,說我的寫作很像《一千〇一夜》裡宰相的女兒(給國王講故事的人),意思是,講述只是為了生命的延續,只是為了自身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沒有外在的功利目的。
「文學狀態」一定是非功利、非功名、非集團、非主義、非市場的狀態。
第二點,我的人生為什麼感到幸福?因為,有文學陪伴著。
擁有權力、財富、功名等,未必幸福。我的幸福感不是來自這些外在之物,而是來自文學。文學是什麼?簡單講,能豐富人類心靈的那種審美存在形式就是文學;或者說,文學最大的功能就是豐富人類的心靈。「心靈」是個「情理結構」,「情」是情感,「理」是思想,是對世界、社會、人生的認知。文學能豐富人類的情理結構,能豐富人性。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如此表述過。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全國青聯會的時候,我作為文學界的委員,被我的朋友、中國音樂家協會的副主席施光南邀請去給歌唱家、演員講座,我講的題目就是「什麼是幸福」。幸福,就是對自由的瞬間體驗。現實生活中是沒有自由的,比如沒有情愛的自由,但是透過文學可以實現這份自由。幾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人很辛苦,神經之所以沒有斷裂,文學起了很大的作用,讓人在瞬間體驗到自由。比如曹雪芹寫《紅樓夢》,其實他在現實中沒有自由,但透過懷念幾個「閨閣女子」(都是夢中人),他體驗到了瞬間的自由。
我的人生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文學一直陪伴著我。我從中學時代開始,就有精神上的戀人,我深深地愛上了她們,中國的有林黛玉、晴雯等,西方的有《威尼斯商人》裡的鮑西亞(朱生豪先生的譯本譯為「鮑西霞」)、《奧賽羅》裡的女子黛絲德蒙娜、《羅密歐與茱麗葉》裡的茱麗葉、《哈姆雷特》裡的歐菲莉亞,還有托爾斯泰筆下的娜塔莎等⋯⋯好多女子都成了我的「心上人」,我從少年時代就愛她們,直到現在。文學進入我的心靈,成為我心中永遠的「戀人」,我總是和她們一起憂傷,一起歡樂,一起訴說,這是非常幸福的。夏志清先生批評我把小女兒送去讀計算機科學,認為是一大錯誤,我認為很有道理。從事文學的一大好處,是讓我們永遠生活在心愛的崗位上,而且總是感到心靈很充實,很踏實,很豐富 這是莊子所說的「至樂」。
第三點,對於一個從事文學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三十年前,我和李澤厚先生有一段對話,我們提出的一個觀點是:勸作家不要多讀理論。李澤厚先生提出了一個理由,說如果太重理念,可能會讓理論篩選掉最生動的感性內容,寫出來的作品會概念化;我的解釋是,我們的理論不是一般的理論,而是「反理論」,反教條,反固定化模式。講理論,只是為了幫助大家從教條中解放出來。我這次講的每一課,都是希望幫大家從理論的老套中解脫出來。我跟高行健先生聊天時說,我們要走出老框架、老題目、老寫法,不要講老話、套話,要講新話,講別人說不出來的話。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說天才只遵循「無法之法」。佛家關於「法」有近百種解釋,我們一般解釋成「規則」。寫文章沒有什麼固定的規則,可以寫千種萬種。我寫散文詩,從不遵循權威們規定的三五百字的法則,偏寫三五萬字的散文詩。我寫過兩千多段悟語,零零碎碎的,刻意打破體系,沒想到莒哈斯就提倡「碎片式」的寫作。
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說,他的課堂不是要教學生如何當作家,而是要教他們放開思維。我的意思也是如此。我認為,對於作家,最重要的不是文學理論,而是「文學狀態」。閻連科帶著中國人民大學寫作班的十三個學生來落磯山脈看我和李澤厚時,我講到了這一點。什麼是「文學狀態」?我在評述高行健時說,「文學狀態」一定是非功利、非功名、非集團、非主義、非市場的狀態。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金耀基先生說,我用「文學狀態」四個字來評論高行健先生,是「一字千鈞」。這雖是鼓勵我的溢美之詞,但說明他深知「文學狀態」格外重要。另外,「文學狀態」還是孤獨的狀態、孤絕的狀態、寂寞的狀態。要抵達陶淵明的那種寫作狀態是不容易的,一要耐得住清貧,二要耐得住寂寞。
「文學狀態」還可以從各種角度描述,我多次用「混沌」狀態表達。《莊子》裡的一個寓言: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莊子.應帝王》
這是說,人的「混沌」狀態,是對某些東西永遠不開竅,比如對金錢、權力、功名不開竅,不知道輸贏,不知道成敗,不知道功過,不知道得失,便是這種狀態。賈寶玉沒有世俗的生存技能,不懂得仇恨,不懂得嫉妒,不懂得算計,不懂得報復,也是「文學狀態」。把得失、功利全都放下,才能有「文學狀態」。禪宗講「本來無一物」,王陽明講心學,也屬於「文學狀態」。我們的課程,就是要引導同學們進入「文學狀態」。擁有這種心靈狀態,是文學的關鍵點。
(本文節錄於劉再復:《文學四十講:常識與慧悟》,原題為〈寫作的關鍵點〉,標題為編者所擬。)
1941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劉林鄉。196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新建設》編輯部。1978年轉入中國文學研究所,先後擔任該所的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所長。1989年移居美國,先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加拿大卑詩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科技大學、臺灣中央大學、東海大學等高等院校裡擔任客座教授、訪問學者和講座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客座教授。
著作甚豐,已出版的中文論著和散文集有《讀滄海》、《性格組合論》等六十多部,一百三十多種(包括不同版本)。著作、文章被譯為英、韓、日、法、德、瑞典、義大利等多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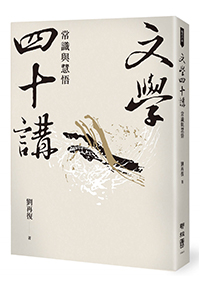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