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瑞明,曾任記者、教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年青生活哲思20則》、《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合著)、《上有天堂的地方》,編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吾考通識,通識唔考》,喜寫書評。
哲學軌跡 | 曾瑞明 and 專欄

文 / 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疫情帶來了社交距離和封城,的確推動一些公司加快自動化,而自動化的動力來自人工智能(AI)。人工智能不只是機器,它是迄今最重要的人類發明,會是人類歷史的拐點。曾是谷歌(google)首席運營官(Chief Business Officer)的作家莫・加多(Mo Gawdat)在《可怕的聰明》(Scary Smart: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ow You Can Save Our World)一書作出了警告︰人工智能已來到,我們不能阻止,他們還比我們聰明。我們要小心照料人工智能「孩子」,否則整個星球也會有災難。不過,他樂觀地說,未來仍在我們手中。但未來真是在我們手中?我們是誰?這就是這類流行書藉的盲點,好看、易看,但總是給人一點幼稚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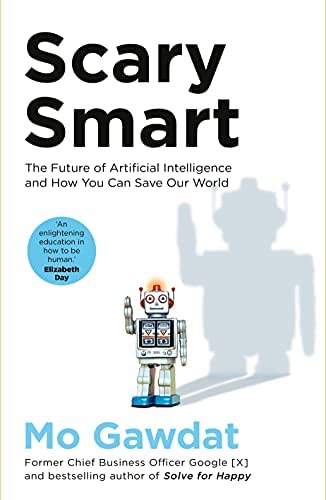
哲學在時代中
不過莫・加多提出要發動一場運動去讓大家關注人工智能,卻還是點出了人工智能的政治性。我們以為這是科技的事,或者可以嚴肅一點說這是科技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的事。但我們卻不能不看到人工智能牽涉擁有(property)、分配(distribution)的問題,這些當然是政治的問題了。更深一點說,人工智能還會改變我們對一些政治概念的理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說哲學是在其時代中的,在這個人工智能年代,我們又怎能以為哲學能獨善其身?
在維也納大學任教的哲學家馬克 ‧ 柯克爾伯格(Mark Coeckelbergh) 之前寫過人工智能的倫理學(AI ethics)一書。但他認為不應把人工智能帶來的問題侷限於倫理學。他於2022年出版了新作《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學》(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I),就指出人工智能充滿政治性,而非只是一種工具或者關於智能(intelligence)的東西。人工智能關乎自由、平等、正義和權力等重要政治哲學課題。
書中他談機械人會否變成我們的奴隸,若果不能的話,我們該怎樣看待他們?或者我們對人的理解也會不同?他也談人工智能造成的偏見和歧視,會否違反平等和正義的價值。在社交媒體盛行下,迴音壁效應(echo chambers)又會否導致由機器控制的極權(machine totalitarianism),還有大數據下帶來的監測(surveillance)。都是我們熟悉的議題,但卻是由政治觀念去考察。人工智能是技術的,也是政治的,不只是應用哲學。
在人工智能的脈絡
筆者認為本書最深刻的,還是指出政治觀念如何因人工智能的出現而受衝擊。德語小說作家弗蘭茲 · 卡夫卡(Franz Kafka)1925年發表了《審判》(The Trial)。小說主角約瑟夫‧K在一個早上,不明所以地被捕。這當然是一個政治寓言,是一個對自由被壓制的恐懼投射。在極權和壓制性的地方,人們的確可以不明所以地被消失或者被剝奪權利。1925年的世界,已有這種恐懼,當然是因為國家體制的建立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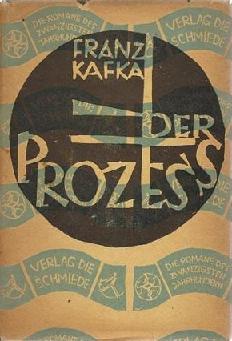
然而,在今天人工智能和機械人都急速發展時,我們的自由又是什麼意思?自由主義哲學家柏林(Berlin)那著名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喪失常是我們的標竿。消極自由是指我們不受國家或者其他人的干預、不受阻。消極自由的喪失,往往是我們最大的恐懼。我們看過電影《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都知道有所謂預示式維護治安(predictive policing),即用機器去預測誰會犯罪行為。我們要問的是,這種干預是否能夠合理?會否損害我們的消極自由?
我們往往以為社交媒體是我們的自由空間,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的是社交媒體公司可以垂直式監視我們一舉一動,就連我們的「朋友」,也能監測我們一言一語。不少人都因為忘記了這一點,在社交媒體被人「篤灰」、CAP圖,而成眾夭之的。但話說回來,誰在社交媒體提供內容?是我們自己啊。老大哥不用親自動手,我們自動獻身。就算不用社交媒體,我們用的活動追蹤器或者智慧型手錶也將我們的一舉一動和行蹤暴露。當我們理解消極自由是沒有一個人用槍指嚇我們或者用身體檔著我們,但在當今數字世界裡,我們的確沒有這種「干預」,但真的有消極自由嗎?當我們被要求做人臉識別時,我們又有沒有被侵犯「消極自由」?

我們有積極自由嗎?
用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在人工智能世界又是怎樣的一回事?積極自由是指我們能做到自我掌控,有自主性,也即是我們是自我選擇的,而非被別人操控。
我們上網購物時,就會明白我們有幾自主。當然,從沒有人在背後用槍指著我們要買人什麼東西,但是我們的潛意識卻很容易受商家擺佈,或者如經濟學者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說的輕推(nudging),就可以被改變選擇的結構(choice architecture)。按演選法給我推薦的書藉和電影,的確大大提高了閱讀和購買那些作品的機會。也許想聽音樂的時間,大腦都不會高度戒備,在「聲田」(Spotify)聽音樂,十之八九都是演選法推薦什麼我就聽什麼。我的自主性,我的積極自由又去了哪裡?
可見,我們在政治哲學耳熟能詳的概念,放在人工智能的脈絡時,會有不同的呈現。作者當然希望更多哲學家能關注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學,但同時他也指出這問題並不是哲學家的事情,而應該更多公眾討論和參與。莫・加多之類的普及讀物就變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忘記科技是全球性的,不受國家的限制。到底人工智能跟全球正義該如何結合?我們該如何考慮同時間存在的文化差異?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又會如何影響討論?這都是很值得思考的政治哲學問題。
政治哲學的前路,是資本主義,還有人工智能,以及它們的結合。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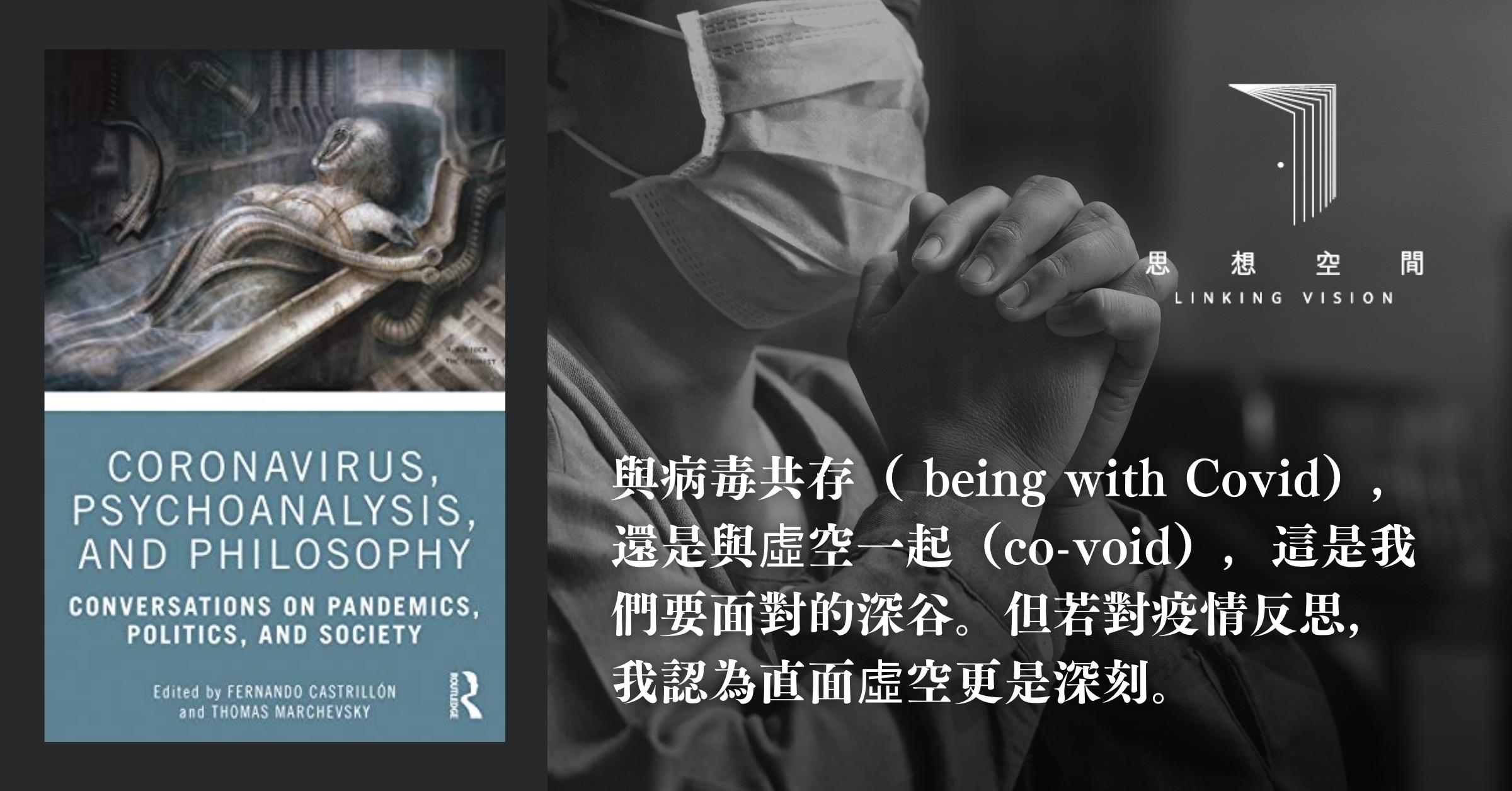


曾瑞明,曾任記者、教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個哲學問題》、《年青生活哲思20則》、《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合著)、《上有天堂的地方》,編有《守住這一代的思考》、《吾考通識,通識唔考》,喜寫書評。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