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永義
編按:2022年10月10日,著名戲曲學者曾永義老師於台北辭世,享壽81歲。曾永義是台灣第一位以戲曲研究成就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台大中文系教授,在教學、研究之餘,亦長年從事民族藝術之維護發揚與研究工作。此外,為人重視朋友情義、也喜歡品酒的曾老師,曾與朋友一起組成「酒党」,並被封為党魁。他說他的「党」底下的字不是「黑」而是「人」,關心的是人的情感,尚人不尚黑;今年11月出版的《酒党党魁經眼錄》,亦是他生前最後一部著作。本書不僅是曾永義老師與藝文人士、學者友人之間的交往回憶,也收錄了他對個人生命經驗、治學歷程的回顧。新書出版之際,讓我們透過字裡行間的記憶,來懷念老師的純粹與豪情。(* 本文摘錄字《酒党党魁經眼錄》丁編〈書寫党魁〉,標題為編者擬。)
臺大中文系之大學生活
大一註冊時,中文系主任臺靜農老師,一襲長袍,極為儒雅。問我考幾分,我應以四百零五,他對我點頭稱許,而中文系甚冷門,只要三百二十分就可上榜。我因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考第一名,報紙登出榜單,我於五千多名錄取名單中榮登「榜首」,弄得鄉下人喧騰一時,記者還將我大頭照見報;但知「行情的」,向我父母親說,你們家永義大學畢業,準是國中教員。


由於我是「系狀元」,被選為「班代表」,又任《臺大新聞》總編輯,頗為活躍。我規定班上郊遊,女生不可穿窄裙。「旗下」記者、編輯女生頗多,常要我辦大學生最時髦的「舞會」,我五音不全,又沒節奏感,只能旁觀冷落。好心的女同學邀我教我,可是三兩下就摔出場外,因為我手腳不靈,不知怎地扶抱對方,動不動就踩得使之「花容失色」。此後我就與「跳舞」絕緣,包括任教後與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先生在屏東卑南族的篝火晚會上的手拉手兜圈圈的「踏謠」土風舞,也被卑南姑娘從她身邊推開來,因為人家抬左腳我就舉右腿,人家向前踢我就向後揚。
大二那年,由於校長錢思亮鼓勵學生各就所願轉系,我們班上經聯考錄取的三十二人,只剩下九個人。我當然「屹立不搖」;如此加上港澳東南亞來臺就學的仍有六十幾人,可見僑生之多。那時文學院的歷史系、中文系合班上課的科目不少。歷史系的李姓同學絲髮披肩,眼睛發亮有神,笑起來抿著嘴唇,煞是好看。我和她上英文課,坐前後排,她北一女畢業,英文好,我們臺南一中,以英語最差,聯考我才得三十三分。課前從不查單字,只抄她的生字簿。老師問我問題,我三不知,她指書上答案,我近視看不清楚,乾脆整段念一遍搪塞,老師也不置可否;由於我是中文系班代,上下課都要喊「起立敬禮」,比較顯眼,慢慢地和她在近代史、地理學、社會學等課堂上都坐一起。禮拜天她都先排隊等上圖書館為我先占個位置,同桌共讀,也會在椰林大道漫步。有一位機械系的,見她與我並肩同行,攔下她質問:妳不是說沒空嗎?怎的有時間在此閒逛?她沒理會,拉著我就走。她認為我應多讀世界文學名著,把她讀過的悉數交給我,我讀一本她就和我討論一本。我獲得自然人文科學獎學金二千元,那是每班第一名才能申請得到的。二千元那時可不是小數目,因為宿舍伙食費才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八十元;父親被友人倒債,父子倆為領這筆錢,還在暑假裡,特地從林鳳營搭慢車十二小時到學校來領取。她趁機向我說,我該請客。於是我們眉開眼笑地對食,撒漫了一碗五塊錢的牛肉麵,接著看下午場和夜場電影,由西門町進入植物園的花前月下到子夜時分,雇三輪車送她回延平南路的家。一打開鐵門就是高樓之前的小花園,女傭出來迎接,說:「小姐回來了。」原來她父親是名醫。我不自禁地感覺寒儉,頓起「齊大非偶」的念頭,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自慚形穢」,卻在她身上發生了。也許是因為我才從鄉下來的窮孩子吧!我在返鄉之前,向她說:「後天就回臺南了,明天能否看場電影?」她說:「不行,北一女有同學會。」我這一返鄉,就起了變化,一方面是我心中「有鬼」,一方面耳聞追她的人不止一兩位,包括我的朋友在內;而我是個天性就不爭的人。
我為她作了一首詩,始終沒有給她。詩云:
鬢影清風綺夢長,焉然兩靨泛斜陽。風搖翠篠輕盈態,霞映澄塘淺淡妝。
寒夜離魂人索寞,孤燈照壁夜淒涼。笛聲隱隱知何處,咽斷春心冷落香。
這首詩倒借給農化系的游兆平「使用」。兆平與我同住第九宿舍一一〇室,他上鋪我下鋪,平常交情好。

原來兆平心儀一位心理系的女同學,和詩中所描寫的長髮、輕盈、以及略帶羞澀都很相近,兆平就把那首詩獻給她。於是這檔事在心理系喧騰起來,當時任助教、後來成為要人的某公說,游兆平怎會有詩才,準是那位中文系的代筆。結果這位長髮美人,每在陳紹馨教授的社會學課看見我,就瞪著大大的眼睛對我欲言又止的樣子。某公當了教授以後,主持我在座的媒體座談會,他介紹與談人,我三十五歲升教授不久,他看我簡歷,望我一眼,把我降為副教授,有人即刻糾正,是「教授」。他當上中研院副院長,演講時,有人問他「莊子」,他反問「莊子是誰」。
兆平留學美國,任芝加哥大學教授,我在他家叨擾幾次,他宿舍只因一街之隔,就和黑人區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率領的小西園布袋戲團一行十餘人,他還在家擺了大筵席。我和媛在密西根大學,他掛來電話,最後一句說:兄弟回頭見。沒想他和大嫂蘇麗娜隨即開車趕到安雅堡來,一起吃頓晚餐後就又趕返芝加哥。我們常有音問,都會互相訪探。


同寢室外文系的蕭敏雄很喜歡我們班上嫻靜寡言、容貌端莊的蔣姓女同學。我使蕭敏雄旁聽戴君仁老師的文字學課,坐在一起,我從旁作陪。敏雄多愁善感,很有詩人的氣質,敏雄要我替他轉達專為她作的詩。我課間請她到走廊窗前,對她說:「詩是心聲的流露,希望妳仔細讀。」她聽我的「柔情蜜語」,臉上泛起紅雲。對敏雄的情愫卻沒什麼反應,反倒對我親近些。我每年總成績一向第一,有次蔣同學第二,陪她一起到醫務室健康檢查、辦理申請獎學金手續,恰好上課鐘聲已響,來不及進教室就座,便撐著向敏雄借用的大雨傘和她走在椰林大道賞雨中的杜鵑花。中午回宿舍,卻見敏雄躺在床上呻吟,唉聲嘆氣,口中念念有詞地說:「像這樣的朋友,口中幫我,暗裡奪愛,撐我的傘在花前林下談情說愛。」「這事」可「大條」了,我百般「告解」,他總是不相信。我對蔣同學也逐漸疏遠,免我有傷「義氣」的嫌疑。而我忽然想到:搞不好敏雄的情詩,她誤以為是我作的。畢業後,她寫了幾封信給我,我沒熱絡地回應。事隔二十五年,我在桃園文化中心講演,聽眾席上倏地發現她坐在那裡,素妝雅服,一樣姿態明秀,還佩戴耳環,一時激動,即說:「今天下午何其高興,我二十幾年未見的同學也來了。」講演後,興奮地想要約她晚餐,她把身邊一位校長介紹給我,說是她的先生。這盆冷水直往我頭上潑來。彼此寒暄留下電話,假藉「酒党」今晚有會,沒有接受他們的接待。

中文系晚我一班的許進雄、章景明、黃啟方締結金蘭,號稱「三劍客」,才情都高,啟方作詞的一首歌傳唱不絕,人又長得俊美,很受女生的愛慕,進雄說他好不容易寫了一篇文章投給《大學新聞》,我給登出來,卻遺漏他的姓名。
我年少時即如此縱酒,壯年又「飛揚跋扈酒杯中」,躋身「酒党党魁」寶座,迄今年登耄耋,而尚腦清智明,並沒有被酒「澆毀」大腦、小腦,實是「天生異稟」。
而在家鄉,和我極親密玩在一起的是表兄黃惠隆和初中畢業後我鼓勵他考取臺南高工的毛明田。表兄惠隆和我一起長大,簡直同穿一條褲。他讀書不專心,考不上高中,我和他就大膽地到臺南照相館拍合成大頭照,以此報考臺南市立高中。六舅和我一起陪他赴考,第一堂數學,表兄說只會一題,我向舅父說,非我代考不可,抱著兩肋插刀,趙子龍一身是膽,直進考場。一般監考官,不疑有它;有一位在我左右正前方核對相片,對我起嫌疑。而當他每換一個角度審視我時,我即「大無畏」地抬起頭讓他看個夠,他見我的「表現」,終於離去。放榜時,表兄的名字,列在第十幾名。可是卻接到市中來函,說如果造假,就應知進退,否則事發不可收拾。原來我代考的其他五科成績都很高,與數學只得十分,相去太遠,而且一看,筆跡又不同,怎不露出馬腳。舅父也下令表兄不可冒險去註冊,而如果我們蠻幹到底,我一定被臺南一中退學。後來表兄自行考上麻豆高農。舅父母要表兄在寒暑假住我家,一起讀書。我們習慣在我家走廊輔以小黑板,我幾乎是表兄的小老師,有幾分「執教」的儼然。但表兄「志不在此」,把注意力移向我們家隔街花園中的樓房,住著六甲日據時代的庄長、鄉人敬重的士紳醫生毛昭川的女兒毛玉仙與毛玉娥。玉仙與我為國小同學。她們姊妹「居高臨下」,不知何時開始與表兄「擠眉弄眼」。表兄被我責備不專心,她們就向表兄在自己臉上做「羞羞臉」的動作。後來同學毛明田也來「共讀」,即使大街上迎神賽會的行列敲鑼打鼓地經過,我也「不許」走出看熱鬧。而我們「課餘」自然也常玩在一起。

有此因緣,大學肄業暑假,便常和明田一起釣魚一起「游獵」。明田家後院有池塘,我愛在那裡垂竿,也會到郊野溝圳水渠,戴著斗笠像「魚翁」,使得農家姑娘們指著我說:「那傻子又在那裡曬太陽。」明田家有支鉛彈氣槍,便常和他在晨曦初照時,沿著六甲經林鳳營、龜子港的行道樹下,邊打邊停地走了十二公里路,獵殺麻雀、伯勞、白頭翁、斑鳩,甚至鳥鶖、白鷺鷥。碰到斑鳩時,我們如見「至寶」,以軍中埋伏匐匍的姿勢襲擊,必須打中其頭部或翅膀,才能使之墜落。我最好的紀錄是十五發鉛彈打下十三隻麻雀,聽到鳥兒被擊中「剝」一聲就有快感,那是何等殘忍而卻不自覺。而明田的槍法比我更準。我們約近中午抵達我出自下營表兄的家,成績好的話,總有一百幾十隻麻雀,外加一、二隻斑鳩。於是舅母燒熱開水,我們一起為這些「戰利品」拔毛淨身,舅母就乾炒油煎,做出香噴噴的「爆鳥仔巴」,我們大快朵頤地飲米酒。有明月的夜晚還會在下營國小操場的「司令臺」,呼朋引伴地飲米酒或分量多而大眾化的烏梅酒,肆無忌憚地喧鬧,用以佐樽的正是「鳥仔巴」。我和表兄密切相聚,也常會花兩塊錢買一大碗公的鴨掌,邊啃邊飲酒,頗別有一番滋味。我年少時即如此縱酒,壯年又「飛揚跋扈酒杯中」,躋身「酒党党魁」寶座,迄今年登耄耋,而尚腦清智明,並沒有被酒「澆毀」大腦、小腦,實是「天生異稟」。
也因為表兄、明田和我常在一起,心中的「風花雪月」也逐漸青春萌發起來,「同謀共慮、互助合作」之下,使得各自都交上女朋友。新營家職、表兄鄰居的陳瑞玉,長得清俏明美、性情活潑爽朗,經表妹黃玉美與表兄慫恿,我與瑞玉彼此進入生命之中,開始有月下私約、山水同遊。然那時透過媒妁之言,陳家表妹、同學楊老師的女兒與我小學同班,成績不相上下,她們都文靜溫麗,還有一位官田的女孩,都表示可以嫁入曾門,而在雙方家長催促之下我選擇有感情的瑞玉結了婚,以完成母親「長子早抱長孫」的期望。新婚自然燕爾,我當預備軍官時,也不免隔離相思。可憐的瑞玉在她家長輩婆婆媽媽的調教影響之下,使她篤信神仙道佛外,還唆使她教她「嚴控丈夫」的技倆,而且日甚一日。我初任副教授薪水才三千幾百元,我在陪她往臺北木柵仙公廟的步道上,看她每碰上路旁小神祠的大「賽錢箱」,就紙鈔五十元一張一張地向下扔。而對待我,不只「沒收」全數薪水,還機靈地探知我開會、演講的車馬費和稿費,使我口袋分文如洗。同仁潘美月大姊,當我面說:「曾永義你好吝嗇,從不請客。」我不只「英雄勝概」盡失,而且「丈夫之氣」也幾近消磨。而可憐的瑞玉根本不知夫妻相處之道,只認為對我「嚴控」,使我「行不得也哥哥」效果彰著,「樂此不疲」,尤其在我從故宮館刊昌彼得副院長所付稿費一千數百元,送交父母親,表示一點難得的孝心時,她居然向父母親「提出異議」,把錢要回來,更不顧我難以忍耐和我大吵一架。因為同學曾金波向她說過:「曾永義是屬於妳的了。」而可憐無奈的瑞玉卻「信守不渝」,無視我「積漸而成」的感受,持續執行她的駕御術,長達十九年。我終於遇到了「至意唯卿能解,身命唯卿堪託」的陳媛。在瑞玉同意下,辦理離婚。她要求我給她贍養費二百五十萬元,潘美月的溫州街臺大宿舍變更私有,不過五十萬。而我分文全無,弟弟永發、友人李明輝、曾德仁告貸於我;而表兄卻臨時變卦,找出理由,說他「愛莫能助」,使我夜晚於送他返家的臺北火車站淚流滿面。

我與表兄並未因此感情疏遠。我認為他說得也有道理,因為就他立場而言,他怎能「助紂為虐」。那時他從國中職員改行自營小紡織廠。他去職時在黑板上寫下:
悠悠十二載,埋沒大人才。此才非比材,永遠不再來。
他果然生意興旺,但好景不常,被友人拖累,犯上官司,法官敲詐,使他負債累累,赴馬來西亞吉隆坡重啟爐灶,不久即為華界大戶,以「總裁」領公司。往返馬臺,兒女於臺北基隆路開電子公司,能發明新產品,旗下博士一大堆,而他們都只是高中畢業。
表兄每次自吉隆坡返臺,一定和我相聚;我奉教育部安排巡迴馬來西亞講演時到他家駐足過,為他的事業感到高興。可是天有不測風雲,2018年3月21日夜表妹黃雪玉來電,謂表兄黃惠隆攜表嫂姜素美與女兒黃瓊篁遊美西,至猶他州遇雪,心臟病突發去世。驚聞噩耗,不禁嚎啕大哭,徹夜不眠,如有椎心之痛。枕上賦七律以弔之:
噓寒問暖與時更,七十年來兄弟情。噩耗青天三霹靂,冏途白雪更淒清。
孤魂渺渺飄飄蕩,萬里茫茫步步驚。欲弔荒原何處所,酸風奪目淚盈盈。
我深為瑞玉擔憂,因為她不知「生財」艱難,怕她手頭有大筆錢,霎時「千金散盡」,商量她留一百萬在我這裡,每月我比照我薪水付她一萬五千元,直到永遠。但她性格剛硬,不答應。她正在為一位臺中的朋友助選縣議員,慷慨地予以捐獻。最後她把餘款送進寺廟,落髮為尼,晨昏禮佛,也過得安穩。我今生今世耿耿於懷,雖然在她手頭拮据時濟助過她,但未減半分「負心人」,愧對於她的自責。當她簽下離婚證書的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放聲大哭,為迄今所僅見。因為我畢竟認為她是個「弱者」,而我難以照顧她。她六十八歲時,因胃癌入住榮總,我偕媛和三個女兒去看她,我看她憔悴的形容,充滿佛心地對我無怨無尤,我執著她的手,止不住淚水地倍感歉疚之情,直到現在。我和她生了三個女兒,大女兒湘綾,景新女高畢業,是小有名氣的女作家,她小時沒能好好教養她,我每存「補償」之心。次女湘芸,臺大外文系畢業,我要她出國留學,她沒答應,因為她被愛情沖昏了頭,我一再提醒她,陳俊吉善於取悅人,無一技之長,難以託付,她還是執著地嫁給他。終於湘芸看穿了,在我不知情之下,付給俊吉一筆不算少的錢,才解脫婚姻的束縛。她現在是臺灣手機公司的處長,生活平順,未再婚。湘珍生性活潑,善於公關,東山高中畢業,每遇考試就胃痛,我沒要她非考大學不可,不像她大姊連續挫敗四次才作罷。湘珍和女婿包一飛算早婚,生子包煜弘今已高師大畢業,服完四個月蔡政府手下的「公子哥兒兵役」,在一家設計公司上班;生女包寧,長得清俏可人,目前已是世新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2021)。公婆待湘珍如子女,一家安詳和樂。湘珍與一飛創立「兩人公司」,分主內外,一飛「發明」保全設備的特殊功能,賺了一筆錢,但不知申請專利,已被大型公司襲取,所幸老顧客尚能維繫他們家的小康生活。我三個女兒只有湘珍生兒養女,給我也有機會享受「含飴弄孫」之樂。因為湘綾迷上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和她交往多年,找他到我家問他主意如何,他已和同是原住民作家的妻子離婚,很快就和湘綾結婚,湘綾和瓦歷斯在部落國小教書教作文,被說成是「平地公主」,隔了七、八年,瓦歷斯又與仰慕他的青春女孩「故態復萌」,棄家庭父母與湘綾不顧,與該少女僻居在外,湘綾乃於2014年搬回臺北,與我們同住臺大長興街宿舍,迄今已八年,沒有與瓦歷斯離婚,也沒有「這小子」的任何消息。我曾為「這小子」謀出路,希望在我影響所及的文化界使他更上層樓有所發揮,可是「這小子」不領情,只愛他自以為「風流」的歲月。
三個女兒都對我和媛很貼心孝順,每星期都來看我,噓寒問暖。

我以榜首考入臺大中研所碩士班,自馬祖除役返臺復學,拜望鄭師因百,說我剛從離島南竿「解甲歸來」。鄭老師說:「你不是將軍,怎能說『解甲』?」我也自覺好笑。
馬祖南竿少尉排長
1967年,我分發六八軍團,被派往馬祖南竿服預備軍官役,任營部連彈藥排少尉排長。與屬下居山腰碉堡,夜晚出任務,與排副蹭蹬在墳場與濱海各哨站之間巡視。一個夜晚,我們軍校畢業長得白皙乾淨的上尉連長,率他的營務官和我排副揹卡賓槍,巡視兵器排守護的澳口,忽然有沙沙的聲響自澳口往上傳來。排副喝問「口號」,沒反應,聲響越往上逼近,排副說一定是共軍水鬼摸上來,因為上次守軍十二人駐守對面孤島,一夜間全部被割了頭。於是連長下令襲擊,兩支卡賓槍和連長的手槍,聲徹臨近的哨站和夜空。等子彈都打光了,猶未見「水鬼動靜」。排副大膽地打亮手電筒,發現一頭黃牛回頭緩慢地往下走。這時澳口的兵器排已架好機關槍,蓄勢待發,看到燈亮,以為我們勝利了。次日我和排副巡視「戰場」,「黃牛依舊」,只有肚皮中彈一枚,左前足足踝被打穿,屈臥四腳,仍就地吃青草。我把這次戰役稱為「夜戰黃牛」。除夕春節夜晚我率部布置澳口,自己在岸上碉堡以備不時指揮,儼然有海防司令的派頭。
我從《史記.吳起列傳》學到待士兵如子弟和歷代名將如鄭成功「寓兵於農」的道理,也用在我這個大如芝麻排長的身上。我履任之初,即為每位士官,私下備置簡單酒菜請其友人作陪為每位士官慶生,在酒酣耳熱中交融感情,閒話他們的過往;也趁機將他們每月的餉銀留存部分所需外,悉數存入郵局,將來回到臺灣後就有錢娶妻生子。對於菸癮大的,就答應由我每月補給若干包香菸;沒有一位士官不同意我的建言。我也因而發現我屬下三班的士官,第一班班長是韓戰時被俘投入的;副班長和他的兄弟駕駛士是在連江出海口捕魚被馬祖守軍抓過來的;第二班班長是在家鄉被強行徵召的;第三班班長則在娶妻的筵席上被死拉活逮過來的;只有他們共同的老班長彈藥士是投入行伍的。我雖帶領這成分繁駁的「雜牌軍」,但由於我關照他們,譬如駕駛士家眷在臺灣回去探親,也懂得買些馬祖黃魚乾和「老酒」,給他作伴手禮。我也從父母親那裡寄來各種蔬菜種子,開闢山坡地廣為種植,又買兩頭豬仔飼養剩菜殘羹,而將節餘的錢多買魚肉,加上士官身上儲蓄無餘款,所以吃得最好。士官得空不賭博,軍紀良好。每早點名晨操,我的「訓話」不八股,但發現哨站衛兵郎當一定責罰,尤其在我輪值連指揮官的時候,不管平常交情不錯的情報班長,如何請求,照樣禁閉他班上一位士兵在值哨時,將槍上刺刀倒地,雙手抱胸與其友人聊天所犯的軍紀。率全連隊伍赴團部集訓,途中秩序一定要整齊,否則即刻拉出破壞秩序的「害群之馬」處置。有個深夜,排上哨兵帶來一位少校軍官見我,我馬上致敬,因為他是駐地相鄰的砲兵連長。他說:「我因忘記『口號』,你的部屬守紀甚嚴,幸而我們喝過酒,記得你的名字,否則就更尷尬了。」我也因此被同袍譏為「小軍官大架子」。
我做了十個月排長,指揮部對全體預官作期末考試,我毫無準備,居然以兩分之差居第二名。退伍前夕,排裡殺一頭豬,一半留下;一半販售買雞買鴨買魚,包括魟魚那本來腥膻屎臭難於入口的魚,由我教以大量加醋以後,頓成鮮美無比,讓我的傳令兵兼伙夫、管豬管菜園子的老士官長忙得不亦樂乎。我們離情依依而無不開懷暢飲。我和每位士官兵對乾大半鋁碗一瓶才七塊錢的「福祿酒」,使我酩酊大醉。卻在朦朦朧朧中,隱約地聽見駐地集合場上有爭吵的聲音,帶著九分酒意起床,正是斜陽西落碧海的時候。看到二班黃班長正和平日嘰嘰喳喳的三班班長爭吵,排副也加入舌戰,二班李副班長則垂手站立一旁。原來黃班長酒後將李副班長訓斥一頓後,罰他站立悔過,排副管事,詢問原委,黃班長不服,張班長主持公道,更使黃班長頰露青筋。我見狀喝令:「都給我站好。」即拉著李副班長到床上按他脖子,命他不准動,好好睡覺。也說好說歹,與黃班長並肩而臥,說:「我陪你一起休息。」黃班長說,他盛怒時衝動得要拿槍對幹,如果不是老班長制止,恐怕連我都回不了臺灣;而我再度醒來時,看不到身邊的黃班長,循聲探看,卻見黃班長、張班長心平氣和地再談及剛才一觸即發的「慘烈」,彼此責備行為失當。我也忘了孔夫子「唯酒無量,不及亂」的箴言,如果不是老班長,就惹出了一場不可收拾的災禍。而我也感受到我排裡的同袍,不以我這位「菜鳥」為嫌,對我相當照顧。譬如全排弟兄築馬路車道,要我題路標時才去,好讓我在碉堡裡看《紅樓夢》。有次司令官到排駐地視察環境,留在排裡的士兵保護我好好地躲在被窩裡,由他們應付,萬一被發現也好裝病。結果司令官看到壕溝裡一坨大便,告知團長,團長就命連長正午到團部報到,報到時卻說沒事,再步行回去。連長為此向我抱怨,在大熱天裡被罰走路兩小時。我曾令士兵上大號,蹲壕溝再用土掩埋,既衛生又俐落,有人匆促間忘記,就露了破綻。我身上尚存三分「老百姓」的習性,喜歡穿拖板到處走,到菜園看綠意盎然,使得好些人也跟我穿拖板,有「拖板排」之稱。
我以榜首考入臺大中研所碩士班,自馬祖除役返臺復學,拜望鄭師因百,說我剛從離島南竿「解甲歸來」。鄭老師說:「你不是將軍,怎能說『解甲』?」我也自覺好笑。

我投入戲曲研究的緣故,在於我嵌入骨髓的天生性格,「人棄我取」,因為這樣可以與人無爭地「為所欲為」。
臺大中研所歲月
進入研究所,我主要的學習是磨礪治學的態度與方法。在大學所學的基礎課程,如文學之詩詞曲、杜詩、蘇辛詞,經學之《尚書》、《詩經》、《禮記》,子學之《論語》、《莊子》,以及中文系的必修課,文字、聲韻、訓詁、文選、文法都成績優良。尤其詩選習作被葉嘉瑩老師在黑板上當範例修改,詞作也被戴君仁老師於課上稱許過。至今我還常以作詩填詞製曲,用以抒發生活感觸,也用來編劇以評騭古今人物,都是扎根於當時。而許世瑛老師的聲韻學,是中文系學生最感頭痛的課程,我卻能在學年四次考試裡獲得三次滿分一百,一次九十八,所以每臨考試,我便成為同學圍繞的「補習老師」。我對聲韻頗具解析分辨的能力,雖沒再進一步研究修習、歌唱五音不全,但憑一年功力,竟能寫成〈中國詩歌的語言旋律〉那樣的專論,和近年完成的一部三十幾萬言的專書《「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


我投入戲曲研究的緣故,在於我嵌入骨髓的天生性格,「人棄我取」,因為這樣可以與人無爭地「為所欲為」。所以我以中文系最冷門選為第一志願,以戲曲在大學課程不被列入,選為研究對象。在張師清徽(敬)不厭其煩為我逐字逐句講解戲曲劇本第一名著《長生殿》,並大量閱讀老師第九研究室所藏的元明清雜劇、傳奇作品,開啟我探討曲學的正確門徑;也從鄭師因百(騫)的論文專書中體會治學的態度與方法,了悟一門學問要先用笨功夫打下深厚的根基。我從戲曲外在結構的體製規律入手,用一個暑假的時間斠律《長生殿》,由版本異同的差異、字音、韻協、句法、章法,考究其音節、意義兩形式並存,彼此往往不相侔,而其所產生的聲情、詞情則必須「相得益彰」,乃從中有言人所未及言、發人所未嘗發的見解。由此又進一步發現如【混江龍】變化多端的北曲,在鄭師「增字、減字」音節單雙式的理論說解外,尚有不少影響因素,譬如累字成句、複詞結構、增句原理、意象情趣感染力等。而其關目情節與舞臺呈現之間,尚有其文學藝術結合的宮調曲牌套曲配搭、腳色運用、穿關砌末的妝點等關鍵因素,創發了戲曲排場處理而為其內在結構的新見解,後來結撰成篇為〈評騭中國古典戲劇的態度與方法〉,可說是古今講求戲曲批評論最具體而完備的論述,榮獲第三屆「金筆獎」。而更由王國維治《宋元戲曲史》看出靜安先生的功底是由其《曲錄》、《唐宋大曲考》、《古劇腳色考》、《太和正音譜校注》、《優語錄》等十書分別先行系統考述,再取其菁華成書,使得《宋元戲曲史》只有五萬餘言,而字字珠璣,不只開啟戲曲研究新領域,而且是顛撲不破的經典鉅著。我乃將《洪昇及其長生殿》碩士論文,效法靜安先生,分別以〈洪昉思年譜〉寫〈洪昇的家世與生平〉;以〈楊妃故事及其相關文學的發展〉而從「主題學觀點」,寫《長生殿》的胎息淵源;分析每個字音、韻腳以見《長生殿》格律謹嚴,統計觀察《長生殿》之腳色人物出場搬演情況,以說明其腳色運用之得體,更結合關目布置、宮調曲牌套曲結撰、腳色主從、唱做繁簡,及舞臺穿關設置,以及文學語言之成分、特色而總結為《長生殿》之文學藝術實集大成,詞律兼善、排場新穎之偉然鉅著。為此,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國際《牡丹亭》學術會議」上,我為大會所作的總評中,引來鼎力提倡《牡丹亭》視為古今首屈一指的白先勇老哥當場表示異議。我只能於此簡單回應:此事話長,論戲曲當兼顧文學藝術,《牡丹亭》有文學、沒藝術,不像《長生殿》兩擅其美,有機會咱哥倆細加討論。而我發現許多研究戲曲作家作品的學位論文,便都步我後塵,同是出諸清徽師門下的新加坡學弟王永炳所撰的博士論文可說是最明顯的例子。


中文系的老師很照顧學生。我研二時,同學胡嘉陽向系主任臺老師說,她看到我在臺北的生活非常簡陋,就教我做系上助教。取得碩士學位,考上博士班榜首,又與鄭、孔二位老師商量我的「前途」,結果要我捨講師好能專心讀書。又將我命為「儀禮復原實驗小組」,在臺老師主持、孔老師指導下為助理;孔老師更給予至聖先師奉祀官府秘書名義,林文月先生也以我為她主編的《國語日報》「古今文選」做編輯。我生活無憂無虞,努力學習。在「儀禮小組」的分別報告中,我先後以《儀禮》樂器和車馬為論題撰論文。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與管理員成為朋友,進出書庫和特藏室都方便,除了一天可以親查許多文獻資料外,還閱覽大陸不少考古學出版刊物,從而深知文獻與文物相為印證的重要。這樣的修為,後來我又加上田野調查、劇團訪問和劇場觀摩,建構我戲曲研究資訊的五元素。
我研究《儀禮》樂器、車馬。先探討文獻中的樂器和車馬平面記載,再觀照具體出土文物作驗證,從而發現唐蘭和容庚兩大金石古器物名家,以鐘為甬鐘,鑮為紐鐘是錯誤的。鑮應為「特」一聲之轉,言單獨「特縣」用為樂縣演奏之節奏與導引。而所謂「誦鐘、誦磬」與「笙鐘、笙磬」如鄭康成所云之指「工歌」與「笙奏」之伴奏而言,並從而結合靜安先生之「說樂次」與「樂縣」之組織與儀式中,「無樂不成禮之成規現象」。又從車馬文獻中,得其五路玉金象墨革之名義,單馬、雙馬、駟馬駕御之場合,乃至蒲輪安車、車左車右僕御之位置,平衡、轅門輻輳、憑式之名義緣由,從而得知革路為軍用,以其飾以革,如同玉金象之因飾而為名一般,墨則飾以吉色,為大夫所駕,亦為士昏禮僭用為迎親之專車;路為大車之義,玉路天子以祀天地山川,金路以朝諸侯,象路則為諸侯之車駕。而考古出土,從無三馬、六馬駕車之例,若有此現象必為先秦以後事,蓋時重在安穩馳騁,車有軌,列國不同,所謂兩服兩驂,皆為左右均衡。從而糾正金文學家釋毛公鼎以「馬」為「馬三匹」,應作「馬四匹」為是,因「四與匹」合文,同用其中之「一」。亦勇於指出胡培翬《儀禮鄭注句讀》分解章句之偶然錯失。孔老師拿我寫的心得報告,向臺老師稱讚。中研院高去尋院士讀後也頗有溢美之言,所長李濟之先生為之欲聘我為助理研究員。臺老師請我們親近的張亨先生轉示我,不要到史語所去,我很世故地說,如果我能留在中文系,哪裡都不去,張亨先生說:「那當然。」臺老師還要我去向李濟之先生致謝,他當時是最負盛名的考古泰斗,殷墟就是他主其事發掘的。
臺大中研所老師教導我影響我最大的是鄭因百(騫)、張清徽(敬)兩位指導我博士曲學論文的導師,教禮學、金文的孔達生(德成),教經學的屈翼鵬(萬里),教子學的王叔岷和教文學史的臺靜農老師,他們的學術人格都使我有「望夫子」之門的景仰。我矢志像蜜蜂在花園裡釀取花蜜的抱負,我知道我才質不足,但努力以赴。我不只在課堂上聆聽他們的教誨,也喜歡安排師生小聚,同景明、啟方親聞謦欬,在酒筵間侍候老師。每位老師對我的啟示教導、行事為人的典範,我在本書的「感恩師門篇」中,已有頗為詳細的縷述。這裡就不再重複。
延伸閱讀:

中國靠「吸血」壯大經濟,走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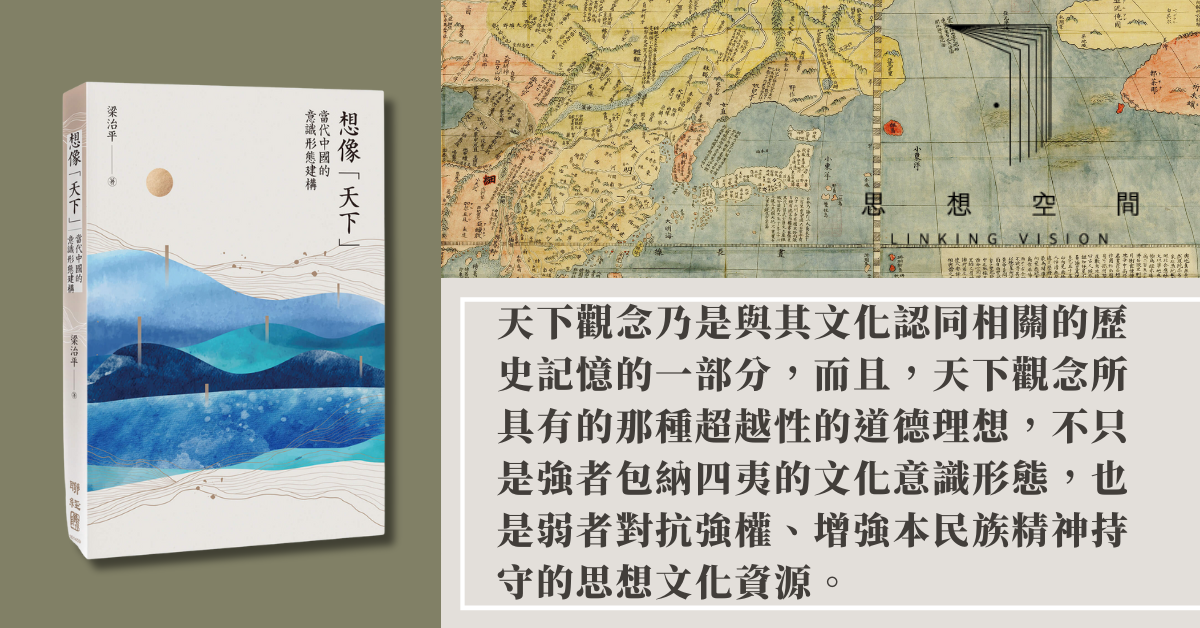
梁治平:天下因文明而立,其範圍伸縮無定,漫無際涯

理論思維的跨界形構和在地實踐——史書美《跨界理論》自序
| 閱讀推薦 |

國家文學博士,世新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大學特聘研究講座教授,2014年當選第30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和教學以戲曲為主體,俗文學、韻文學和民俗藝術為羽翼。海外訪學經歷豐富,曾以訪問學人或客座教授身分赴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密西根大學、史丹佛大學、萊頓大學、魯爾大學、香港大學等;並為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中國戲曲學院等大陸十數所學校之客座教授。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