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編按:如今對於知識分子、讀書人的研究數量頗豐,但你是否知道漢代知識分子有哪些類型?他們對於後世中國知識人的命運又有著怎樣的影響呢?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者許倬雲的經典著作《求古編》,搜集許倬雲多年來有關中國古代史的論述,從商周至秦漢,由文化遷徙、工商、兵制,以及物理天文、衣食住行、家庭大小、史學文獻等多元角度切入,宏觀探討中國上古史的各個面向,其中就包括對於秦漢知識分子型態的整理與觀照。(* 本文摘選自許倬雲《求古編》之〈秦漢知識分子〉,標題為編者擬)
漢代知識分子既是先秦的諸子百家繼承人,而漢代政治儒法表裡,是以儒法二家尤為重要。儒家與法家都以改革政治為其使命,因此漢代知識分子對政治有無法割捨的興趣。正是儒家的士(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政治的特徵。這是本文必須包括政治性角色的主要原因。
最早出現的政治性角色,是叔孫通一類人物,以其知識的實用價値為政治權威服務。此種人物可稱為政治權威的依附者,包括叔孫通之流,明禮儀知掌故的諸生,也包括明律法政令的文吏在內。事實上,這一類型是官僚制度的主要成員。符合韋伯所謂具有專門技能的專家。專家們並不具有任何個人的理想,可以為任何掌握統治機器的權威服務。規章條例繁雜苛細,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處理政府簿書,已非專才不可。[1] 因此漢代法律與經學一樣均多世家,父子相繼,家世傳授,西漢的于氏、東漢的郭氏,均是以律法傳家,甚至地方吏掾,也有世襲的情形。同理,禮學專家也多世襲,如普徐氏世為禮官大夫,也是由於禮儀複雜,非素習不能。[2] 這一類型的人物,以知識為換取祿位的工具,夏后勝每講授,常告訴諸生:「士病不明經術,經術句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知識只是商品而已。[3]
第二類是理想型,如前文曾論述的董仲舒一類知識分子,努力建立一套理論,希望用知識多少約束節制政治的權威,此中第一流人物,如賈誼、轅固生等人,頗能因為有道德勇氣而不輕易屈服者,是以賈誼曾說:「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屈服也。」[4] 其中特出的極端人物,則是眭孟、夏賀良、京房諸人,持守理想,以至用理想要求皇帝退位。其次也可以儒家理想,糾彈現實政治,蕭望之、鮑宣之類為數甚多。然而漢代的理論系統仍以維護君主政體為前提,因此儒家理想往往不免遷就專制政體。即使大儒如董仲舒,以及第一個拜相的儒生公孫弘都不免以儒術緣飾。[5] 西漢晚期的名相翟方進,以儒學起家,在朝方正,豪強畏服,然而仍不能自免於希旨以固位的毛病,所謂「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6] 是以班固在幾位儒家丞相合傳的傳末感嘆:「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7] 以上二類政治性知識分子,事實上均為官僚組織的一部分。漢代的知識分子中,這二類無疑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只是眭孟諸人不多見耳。

在知識分子獲得極重大的社會影響力之後,有若干知識分子開始以理想的世界來繩墨現實世界,這是第三類的角色,可稱之為批評性的角色。在西漢時,這種人物不算多,但《鹽鐵論》是儒生集體批評。在東漢則有好幾位代表人物,如王符、仲長統、崔實,都能以在野的身分,論刺批評當世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弊病。[8] 東漢由中期以後,社會危機,如土地集中,貧富懸殊,豪強顯貴橫行一時。王符、仲長統、崔實諸人的理論,確實是針對這些現象而發。[9] 然而若是知識分子沒有針砭當世的使命感,沒有一個衡量制度長短的尺度,沒有一個好惡分際的理想,他們不可能具有批評的能力與決心。同時,若沒有大批知識分子作為讀者聽眾,沒有別的知識分子為他們傳布和保存這些議論,他們名位不顯,批評了也不會傳留。因此,必須在知識分子群體已經成長到舉足輕重的地位時,有群眾,有影響,批評型的角色才會出現。

第四類的角色是反抗型的知識分子。東漢的黨錮事件,即是這一類的角色。由李固、陳蕃、李膺、張儉、范滂以下的知識分子,他們為了維持理想中儒家的君主政治,不畏強禦,與外戚宦官生死相搏。殉者視死如歸,生者前仆後繼,為中國歷史知識分子立一勇敢不屈的典型。他們之敢於如此,一則,京師又為人文薈萃,二則全國的知識分子經常接觸,形成了輿論,可以評論時政,月旦人物。范曄在〈黨錮傳〉序謂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於是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又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畏懼他們的貶議。到動,然加以援手者比比皆是,破家三族在所不顧。[10] 要言之,這批反抗型的知識分子有群眾,也追捕黨人時,天下騒有群體的認同,而更要緊的,他們具有知識分子善善惡惡的自覺。

第五類可稱之為隱逸型的知識分子。由漢初四皓不應高帝召命,漢代知識分子中已有了隱逸的典型。《史記》以伯夷、叔齊、魯仲連為第一等人物。多少象徵了司馬遷在專制壓力下無所逃死的精神避世所。先秦諸家中,道家原以隱逸為重,儒家用進退藏,或任或清原有入世出世兩條選擇。東漢重名節,不應召辟也是時論所尊重。漢代〈逸民傳〉中人物及終生不仕號為處士的學者,矯情沽譽的人不少,然而大多數知識分子若在目撃時艱明擺著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無法妥協時,逃世自匿,也是誠實的作法。[11]

第六類則是地方領袖型,這一類事實已兼跨上列各類中的若干人物,在其未仕前或退休後,大率都具有地方領袖的資格。第五倫是一個例證,他在王莽時組織宗族閭里以自衛。後為鄉嗇夫,得人歡心。中途退隱以販鹽自給,變姓名以自匿。及仕光武,職任修理,而糾彈貴戚,方正峭直為時所憚,一身具有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及第五類諸種身分。[12]〈逸民傳〉中的逢萌曾任亭長,後來赴長安學《春秋經》,王莽時隱居勞山,吏來捕捉,當地人民居然集眾捍禦,儼然是當地的領袖。[13] 又如〈獨行傳〉中的劉翊,家世豐給,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是第五型人物,及遇种拂守郡,為名公之子,則起為功曹。在任抗拒朝貴為民全利,行為同於第三型第四型人物。黃巾亂時,劉翊救濟鄉里孤寒乏絕,資食數百人。則是地方領袖。[14]

綜合這六個類型。後面四型都以東漢為盛,其原故為由於知識分子階層已成氣候。知識分子以理想世界來衡量現實世界,遂產生有淑世以救世及逃世以全節的矛盾。以個人言之,對於意念與理想,越忠實越認真,其以理想責備現實越甚,則其對社會疏離的程度也越深。反之,對於社會現實及正統觀念越深,則淑世之志越切,於是投身政治直接參與。但因此一念之間,有太過遷就而損害其原有理想者,也有因抗拒而以身殉者。至於為鄉里表率,為地方領袖,仍是知識分子的雋英地位所必致的角色。中國儒家治天下的任務原由鄉黨親族開始;因此在無法治平時,為一方的福祉盡力,也是好的。再以知識分子群體意識言之,群體力量越強大,群體的自覺與使命感也越迫切。因此,上述六型中第三、第四及第五三個類型,只能廣泛地出現於東漢而罕見於西漢。大致中國的知識分子,時時都在淑世與自好兩端之間動盪,聖之任者與聖之清者都不能兩全,而聖之時者是一個高懸而難以達到的鵠的。[15]
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受過教育的人士,因此知識分子必然有另一項社會功能,知識的追求及知識的傳授。本文將由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分析其類型。
第一類是文學家,如司馬相如一類人物,以辭藻之美為文學侍從,別無其他知性活動。不過在《後漢書》〈文苑傳〉中的文學家,則無復如西漢辭賦作者那樣的專業性了。[16]

第二類是經學家,其中當包括兩《漢書》〈儒林傳〉的全部人物,並兼及馬融、鄭玄、賈逵諸人。自從五經立博士以後,每經各有立於學官的幾家師說。經古文今文學派之爭,事實上涉及意識觀念少,涉及祿位利權者多。儒家典籍,因為相斥百家而取得了經典的地位(緯書是神聖傳統的衍生物,故不另論)。一旦成為經典,必有其相應而生的權威性與神聖性。於是經學家最重師承,以保持其神聖傳統。經學每多在一個家族中屢世繼承。西漢如此,東漢也如此。歐陽氏傳《尙書》,一家擔任博士八世之久。經學傳統也因此一方面具有保守的特徵;另一方面,支派曼衍,越分越細,重訓詁辭章,而失落了經學義理的本旨。《漢書》〈藝文志〉有一段評論:「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傳經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17]


煩瑣之極必有反正。漢世兩次由皇帝召集經學會議,一次在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制稱決焉。」又一次在章帝建初四年,也為了「《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大夫博士議郞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最後皇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18] 均是由皇帝以政治權威肯定經典的權威。
另一方面,又有若干不拘守家法的通儒如馬融、鄭玄諸人都兼通數經,擔起綜合的責任,貫通各家異文,甚至打破今古文的界限,使經文通讀恢復本來面目。[19] 除鄭、馬二人以外,鄭興、鄭眾、范升、賈逵,也當屬於這一類綜合工作者之中。[20] 在經典因為信仰而居於神聖地位時,學者持守傳統甚嚴,這種綜合的工作殆不可能。但一旦經典因煩瑣而必須乞靈政治權威肯定其地位時,這一番整理爬梳的工作反而有其必要了。
經學家的職業大抵為講學教授。立於學官任博士的經學家講學於太學。其支派弟子則為私家講學。一位大師,弟子少則數百,多則逾千成萬。尤以東漢為盛。據《漢書》〈儒林傳〉贊:「一經說至百萬餘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21]《後漢書》〈儒林傳〉論:「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牃不下萬人。」[22] 對比兩書,西漢大師中只有〈申生傳〉中有弟子千餘,眭孟有弟子百餘人,而在東漢〈儒林傳〉中,幾乎觸處均有成千累百的弟子。由此也可見東漢知識分子的眾多及活躍。
第三類為著作家,包括所有有創作的學者。其中當然又可大別為兩個分類。一是博學多聞,整理已有的知識。如劉歆之整齊舊書,班固、蔡邕之史學著作,甚至桓寬之《鹽鐵論》,桓譚之《新論》,都當歸入此類。另一類則是有創見的著作如:《淮南子》、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太史公之《史記》及揚雄之《太玄經》,甚至〈京房傳〉,延壽之卦氣理論,此類作者志在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立一家之言。兩類相比,第一分類撰述為主,其方法是歷史性的;第二分類則往往是形而上學的著作,方法是哲學的。即如《史記》,明明是史學作品,但太史公的抉擇出於自己歷史哲學的觀點,組織也戛戛獨造,前無古人。凡此著作家,道於創造性的學術活動。揚雄尤為其中最有創作能力者。《太玄經》雖說仿《易》,但以玄代道,以數字象徵代表現象,組織一個以數字為語言的形上學以解釋宇宙的本體與變化。[23]


第四類則是方術之士,漢代的方術包括星象曆算醫藥以至風角占卜,《漢書》〈藝文志〉列有方術三十六家。其實還可加上農家如《氾勝之書》等。這些著作大抵可以相當於今日所謂科技類的作品(風角占卜在今日為迷信,在古代則也是原始科學的一部分)。其作者則只有張衡稍有事跡可考,他的天文理論及技術也足以稱道。論方術之士的社會地位,除張衡本身別有功業外,大致都不甚高,或倡優畜之,或在市肆逐微末之利。

第五類則是批評家,如王充,而揚雄、桓譚也常有對學術的批評。《論衡》一書無論其論據未必服人,攻撃精神則十分勇猛。王充不依傍學派,疾忌虛妄,重視知識。雖然其地位在中國學術史上不必如胡適之先生所強調的重要,仍不失為著重知性的知識分子。[24]

今日知識分子在學術工作上的任務,以追求知識最為首要。知識的累積是由已知求未知,其中包括整理舊學探索新知兩個階段。但是在第一個階段的工作,整理舊學(已知)只是為了由已知更邁進一步。另外一面,在任何神聖傳統下,學問不是為了探索未知,而是在肯定神聖傳統已經是圓足的前提下,重新組合神聖的內容,無目的在為先聖立言,搜尋未發揮的意義,以及引申神聖傳統未解釋經典未載的事物或現象。這種知性活動,當可稱為求智慧。智慧與知識實在是不同的。[25] 智慧求圓足,知識則不以圓足為其持點。以此標準,漢代經學家一型的學術活動,當屬求智慧,只有創作家的分型,雖然往往是形而上學的思想家,其知性活動有求知識的趨向。不過董仲舒、揚雄的創作也在求取一個圓足的系統,其目的仍是為了智慧。王充對於神聖系統的知性活動取懷疑的態度。是有所破;但是他的《論衡》中並未有所立,這也是受其時代的限制了。至於文學及方術二類人物,前者追尋的是文字的表現藝術,後者以實用為目的,求知識只是手段而已。
漢代知識分子的主流,由其知性活動的性質說,與今日的知識分子並不同科,在政治活動的角度來看,漢代知識分子逐漸肯定了一個理想的秩序,因此可以自己懸道德為個人修養的鵠的,也因此可以用理想世界來督責現實世界。知識分子與官僚組織的結合,則一方面賦予知識分子擴大影響力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使知識分子的視野永遠被局限在政治活動的範疇內了。神聖傳統與政治視野相重疊的結果,漢代的知識分子雖有空前的影響力,雖有十分優越的教育機會受知識分子擴大與延績,然而知性的活動勢必表現為保守的與排他的,能「炒冷飯」而不能以大批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以開放與批判的精神,領導文化走向更高層次。漢代的知識分子因為濃重的政治趨向而獲得社會上無可否認的領袖地位,但是這番勝利也限制了此後的發展。這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兩難之局,由漢代直到近代,中國的讀書人始終受困於這個難題。
[1]《漢書補注》,卷四八,頁20。
[2] 同上,卷七一,頁5;卷七六,頁4;卷八八,頁20-21。《後漢書集解》,卷四六,頁2、9。
[3] 同上,卷七五,頁5。
[4] 同上,卷四八,頁29。
[5]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頁31-43。
[6] 《漢書補注》,卷八五,頁8。
[7] 同上,卷八一,頁21-24。
[8] 《後漢書集解》,卷四九,頁52,各人本傳;及王符的《潛夫論》、崔實的《政論》。
[9] 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 by H. M. Wright, New Haven: Yalc University Press, 1964),pp. 213ff.
[10] 《後漢書集解》,卷六七,頁1-3、19;又參卷六八。
[11] 同上,卷七三;又謙田重雄,《秦漢政治制度の研究》,頁511-516。
[12] 同上,卷四一,頁1-6。
[13] 同上,卷八三,頁3-4。
[14] 同上,卷八一,頁22。
[15] 這裡涉及若干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一些觀念。關於知識分子內在的壓力,迫使知識分子追尋世界的意義,以及意義現實之間的距離,參看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p. 124-125. 關於知識分子與外在現實世界的緊張及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之間的拉鋸戰。參看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Philip Rieff(ed.), On Intellectuals(Garden City: Doubleday Co., 1969), pp. 25-48.關於知識分子勢須保持疏離態度,參看Lewis A. Cos, Men of Idea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p. 360.而關於知識分子理想或正統理念之間的抉擇及知識分子與其整合的程度,參看Peter C. Ludz,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Intelligentsia,” in Aleksander Gella(ed.),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Beverley Hills, Colif., 1976), pp. 37-45.
[16] 《後漢書集解》,卷八〇上下。
[17] 《漢書補注》,卷三〇,頁27。按此節後半與桓譚《新論》差近。《新論》:「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之萬言。」四部備要本,頁11。《漢書》〈儒林傳〉中有秦恭,字延君,據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漢書補注》卷八八,頁13。
[18] 同上,卷八,頁23;《後漢書集解》,卷三,頁6。
[19] 《後漢書集解》,卷三五,頁10-15;卷六〇上,頁13-14。
[20] 同上,卷三六,頁1-6。
[21] 《漢書補注》,卷八八,頁25。
[22] 《後漢書集解》,卷七九下,頁16。
[23] 《太玄經》(四部備要本)〈說言〉,卷一,頁1-3;〈玄圖〉,卷一〇,頁1-4。
[24] 關於王充的評價,徐復觀先生近作則比較落實;參看,《兩漢思想史》卷二,頁428-441。
[25] 關於智慧與知識的分別,可參看Richard Hofstadt,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 Knopf, 1963), p. 25.
延伸閱讀:

楊儒賓:王陽明「大悟」,所悟的內容為何?

【2025TiBE國際書展現場】傾聽最真誠的叮嚀,對當下保持反思——《暴政》有聲書朗讀分享會側記

突破語言的藩籬:專訪《茶金歲月》客語有聲書製作團隊
| 閱讀推薦 |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曾執教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著有《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西周史(增訂新版)》、《求古編》、《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2020年榮獲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終身成就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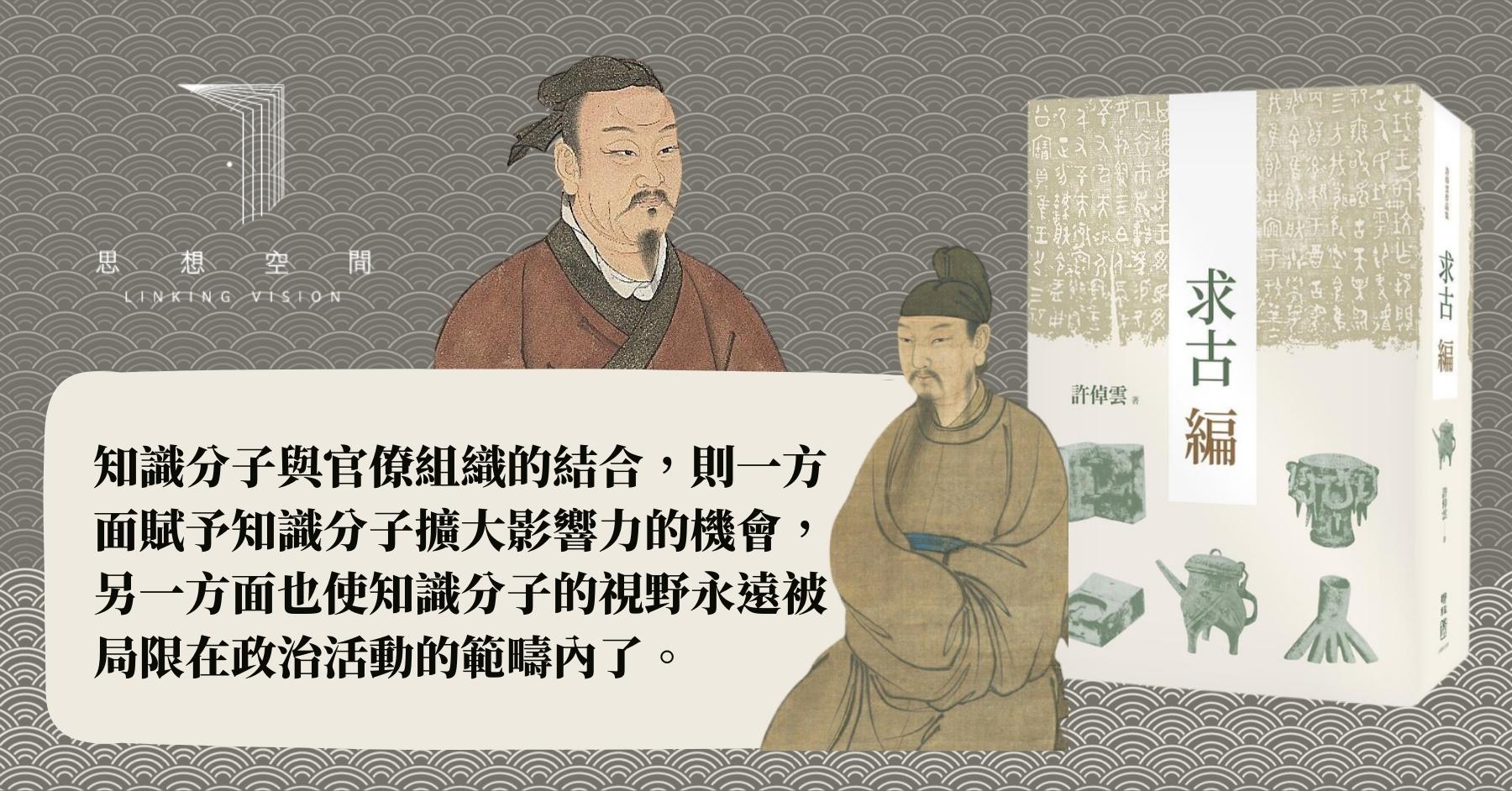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