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呂季儒
編按:2022年,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和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舉辦「原住民族專題系列」,共8場講座。9月15日,系列第7講「文化資產與文化再造:知本卑南族的文化復振」,邀請了逢甲大學文化與社會創新學程的助理教授、兼亞太博物館學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陳玉苹老師擔任嘉賓。作為人類學家,長期耕耘知本部落地方文化復振歷史的陳玉苹老師,從知本部落例子出發,探討台灣當代的原住民運動,在全球文化資產運動的風潮下,是否真的有助於台灣原住民社群重拾文化價值,從中得到力量?(*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標題為編者擬。)
|講者簡介|
陳玉苹,台灣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逢甲大學文化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兼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長期在台東知本部落和帛琉進行田調調查。研究專長為社會文化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殖民研究與台灣與大洋洲南島語族文化。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原住民?」這句話似乎精準的指出了當下台灣原住民的處境。在文化復振的問題上,碰到的困難除了政府法規之外,包括部落裡的族人們如何在現實生存處境的夾殺之下,持續有意識的保存自身文化,也成為一個艱難的議題。
人類學者陳玉苹現今花很多時間在台東知本,持續研究有關卑南族的文化復振相關議題。陳玉苹表示,自己與知本的有逾十年的淵源,早在碩士班期間就已在知本做研究。當時進入知本時,知本地方部落正剛開始進行文化復振(約民國87、88年),但那時文化復振的狀況已逐漸穩定。
陳玉苹指出,從文獻上能看到,從大概民國60年左右,人類學者在做卑南族的調查時,通常都會認為「南王部落」(卑南語:Sakuban, Puyuma,即普悠瑪部落)的傳統文化保存較好,而知本則因受到漢人和天主教文化的影響,文化流失的狀況較嚴重。但當陳玉苹去到知本時,部落的文化復振行動已經啟動,因而對此並沒有特別的感受。後來她離開知本,去帛琉做研究,花了快十年在帛琉完成博士論文,直到大概民國99年時才再度回到知本。當時知本和政府正發生嚴重衝突——為了發展觀光資源以及鐵路電氣化,政府發布公文,要求本卡地布部落與加路蘭部落兩地居民在期限內將公墓內的祖先全數遷走,引起了劇烈反彈。
回到部落,陳玉苹嘗試去理解衝突的原委和過程,由此產生困惑:從民國88年時看見知本在從事文化復振,過了十年之後,為什麼會有這麼劇烈的衝突跑出來?
或者像2018年的「知本濕地光電案」——新加坡的廠商想在知本蓋一個亞洲最大光電場,但在2016年的時候,台灣政府已經頒布了《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知本濕地因爲屬於部落傳統領域,若想進行開發,便需要通過部落的「諮商同意」。但在諮商的過程中,卻充滿各種程序上不尊重部落的爭議問題,也導致了部落內部的分裂。直到今年9月8日,法院才剛裁定卡大地布部落勝訴,施工需停止執行。
文化資產的登錄其實是現代化的一部分。它使用一種理性的系統,將不同的文化資產登錄,它屬於文化治理的一部分。
基於與部落的淵源以及長久以來的觀察,陳玉苹的研究切入點在於——這麼早就開始做文化復振的部落,有沒有從文化復振過程中凝聚出一股能量,去面對正在推動各類原住民相關政策的台灣?回顧走過的這段文化復振之路,當時為何開始?文化復振過程使用了哪些形式?當要面對一些當代產生的衝突,他們如何看待?事實上,不只是原住民,無論是閩南或客家文化,大家也都在從事各類文化復振活動。因此也需要思考:對於當代人而言,我們應該如何定義文化資產這一範疇?如何操作,才能使得文化復振重新豐富我們的當代生活?
陳玉苹指出,從1972年開始,UNESCO(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便開始推動文化資產的保存,但當時針對的主要是一些有形的文化資產,特別是針對在歐洲地區,如希臘、羅馬時代的古蹟保存。但到了2003年時,UNESCO便發現,若只保存有形文化資產,政府需要花很多錢去維護這些有形資產,但這些有形資產卻可能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完全脫節。因此他們開始加入推動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辦法,包括自然知識實踐、儀式、手工藝等等,皆可列入無形文化資產的範疇中。
雖然不是聯合國的一員,但台灣一直都很積極的回應這些國際趨勢。2016年前後,台灣也開始修訂文化資產類別。在觀察整個文化資產運作的過程時,陳玉苹發現:2006年《文資法》修法,開放一般民眾有提報文化資產的權力以後,屬於漢人的文化資產部分——諸如歷史建物、古蹟或是文物等——進行提報,變成了一種全民參與式的運動;但是反觀《原住民文化資產保存辦法》提出之後,相關提報比例卻非常低。
陳玉苹觀察發現,文化資產的一些相關規定,可能與原住民文化活動中的現實狀況有所衝突。例如事實上已使用了近百年的鄒族部落聚會所,可能因為仍會定期整理、翻修,因此不符合歷史建物的條件等(此條現今已有調整)。從上述台灣回應國際趨勢進行修法、以及後續修法調整、落實到原住民文化保存的過程中,陳玉苹理解到,文化資產的登錄其實是現代化的一部分。它使用一種理性的系統,將不同的文化資產登錄,屬於文化治理的一部分。那麼,理性化建立一個新的知識系統,這樣的方式對原住民部落有幫助嗎?或者論及全台灣(甚至世界),當我們需要進行文化保存時,怎樣才不會再度發生「只是將文化資產登錄,但卻與人們的當代生活無關」的狀況呢?
從英文heritage的概念來看,它事實上是一個「襲產」,承襲下來的文化資產或智慧。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話,那麼heritage應是一個意義製造的過程......
從2003年開始,一個國際的、大的政策,夾帶著大量的資源,開始讓不同的文化可以做登錄申請時,其實反映了一些理念——例如我們要開始承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它是一種承認的政治,是謀求公平的過程。但陳玉苹指出,若仔細看這個過程,當中同時有諸多不同的「力」在相互競逐。
過往人們可能會將文化遺產看作一個既成的事實,但從知本例子中能理解到,它其實是一個人為的、製造意義的過程,其價值會因為參與的人而有所交流、變動。陳玉苹主張,人們不應將遺產當成一個「死物」、過去留下的財產。從英文heritage的概念來看,它事實上是一個「襲產」,承襲下來的文化資產或智慧。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話,那麼heritage應是一個意義製造的過程,人們能夠重新認識過去留下來的智慧,這些智慧同時對當代社群產生影響。
如前文所述,陳玉苹認為界定遺產是一種現代性的表現。將文化切成許多類別,並將之登錄,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並且隨著人們嘗試去界定這些文化資產,我們也是在不停地分析它們的內涵。只是在此過程中,我們要如何不被現代化的過程控制或管理,並保存自己的主體性,來作為人們社群生活和生活實踐的動能?這是一個人們需要迫切思考的問題。
「我們的確學會了怎麼寫計畫和核銷,可是為什麼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化活不回去了?我們看到社區總體營造改善了生活環境,但我們的文化在哪裡?」
後文化復振時期:卡大地布部落的文化復振
透過阮俊達的碩士論文〈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1983-2014)〉,我們能夠發現: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中存在路線分歧。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便開始出現,包括「還我土地」運動、「原住民正名」運動等,有許多不同面向的原住民社會運動開展。這個年代也被阮俊達稱為「泛原住民運動」時期(1980-1990年代)。
到了1990年代後,原民運動逐漸分為兩種路線:一種是一些泛原運的原住民菁英份子開始進入體制內,因此出現了一些體制上的改革,包括原民會的成立等。她們嘗試在體制內創造空間,讓原住民菁英可以進入並思考這些體制,能夠如何與國家合作。另外一種則是一股草根的部落主義的實踐。隨著前面原運的能量進入各個部落,搭配台灣1993年開始實行的「社區總體營造」,以及到2019年出現的「地方創生」等政策持續發展直到現在。
雖然仍在持續摸索還發展當中,陳玉苹暫將「2010年之後」定義為原住民的「後文化復振時期」。因為在部落主義實踐的階段,其實有許多部落嘗試找回自己的文化實踐,如恢復祭典等。這個實踐過程可能結合了社區總體營造,可是卻難以斷言它究竟達成了什麼目標。當陳玉苹去訪談部落裡的人,談及「社區總體營造」帶來的影響時,受訪者表示:「我們的確學會了怎麼寫計畫和核銷,可是為什麼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化活不回去了?我們看到社區總體營造改善了生活環境,但我們的文化在哪裡?」這樣的反饋成為陳玉苹的疑問,在諸多文化政策的推行下,縱使有高尚理念,但落實時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政策是否真正活化人們的生活,皆成為疑問。
如同阮俊達在研究中所拋出的疑問和建議,「如果剛剛那兩條路線,泛原住民運動和部落主義兩條路徑往前走,她們可能要用用彼此都聽得懂的語言溝通,譬如說部落生活裡面這種很庶民的這種生活經驗,跟在政府部門裡工作的原住民經驗,我們要怎麼樣來讓彼此了解到底要什麼?然後可以透過體制裡面的改革,讓部落裡的人也可以往想要的路徑邁進」。也就是在「文化復振」和「民族權力集體保障」這兩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且又同時不與生活脫節,這與陳玉苹所在思考的問題不謀而合。因此對於陳玉苹來說,到了2010年以後的「後文化復振時期」,在原住民權力、文化認同跟生活之間,我們應該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目標?或是如何推進?透過知本的例子,陳玉苹嘗試回答上述種種關鍵問題。
在文化斷裂之後,將文化重新帶回來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經過意義的重組,並且它無法一次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長時間的討論和爭辯,進而逐步恢復。
從日殖到民國:知本的文化斷裂修復之路
1641年,荷蘭人進入台灣;1895年,日本人進入統治台灣,也改變了部落的經濟結構。當時設立的公學校,也就是以前男子會所的所在地,因而被日本人設立的公學校所取代,傳統習俗也被禁止。1901年時,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皇民化」政策,禁止使用母語、改日本名等。1949年,國民政府進入台灣,大致延續日本人的管理政策,包括對於原住民的分類等,而知本則轉生成為知本村,設立村長,正式納入國家體系之中。
1953年後,天主教正式進入部落,大幅影響了當地的信仰結構。1956年,知本天主堂司鐸費道宏神父,為了保存卑南族傳統文化,召集了許多當地耆老來做口述歷史。當時因此邀請一位人類學者——山道明神父——來協助做知本口傳歷史記錄。因這些口傳歷史資料而寫成的《祖靈的腳步》等書,成為後來文化復振時期的重要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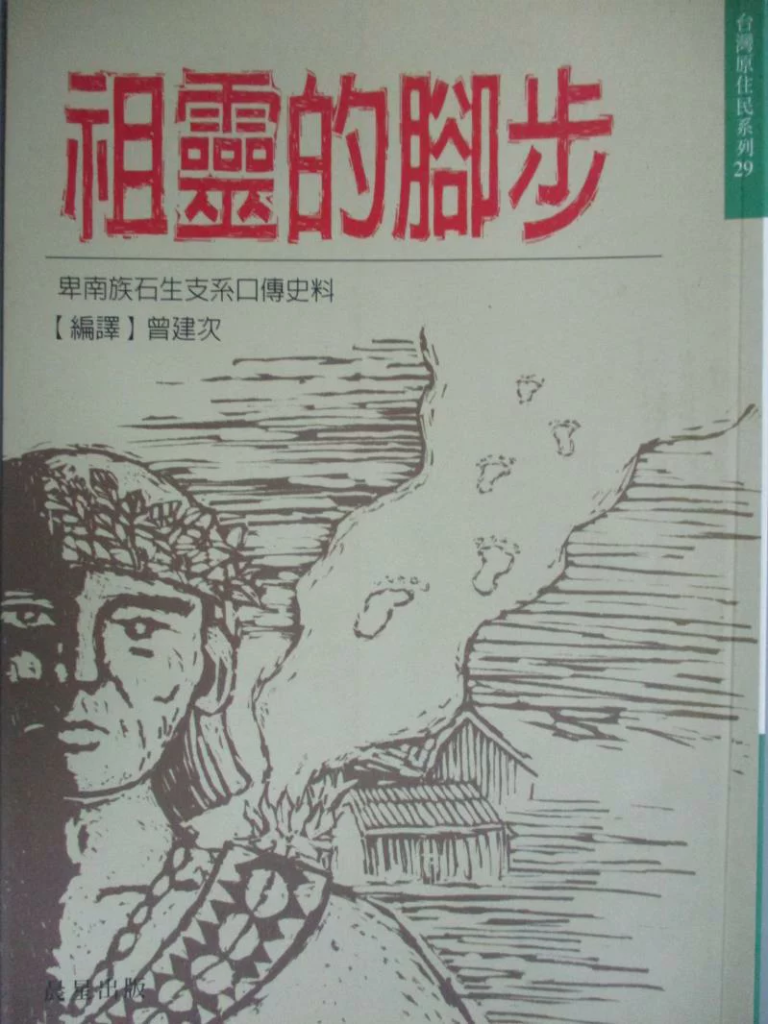
1980年代左右,當地部落開始恢復小米收穫祭的傳統。但是真正進入文化復振時期的契機,則是在1982年,許多原住民族參加了國家樂舞系列在國家劇院的表演。根據陳玉苹的訪問,1982年後開始陸續出現的歷史訪查和國家樂舞表演,使得族人有機會重新認識自身文化,她們也在參與過程中被深深感動,進而開啟了文化復振行動。然而在此契機背後能夠發現,知本地方部落的傳統文化事實上在經過日殖統治、國民政府管理和新興宗教傳入的影響,她的文化傳承體系早已斷裂,包括母語的使用,命名的方式,和傳統信仰的內涵等,甚至部落年輕人的離鄉,皆導致原來的傳統文化快速佚失。
因此從1982年後,因為對於自身文化的體認和感動,使得族人產生強大動力,擴大舉辦或陸續恢復傳統慶典,如1995年恢復少年猴祭、1997年恢復大獵祭、1998年恢復祈雨祭等。但斷裂的要重新接回,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例如為了恢復失傳的大獵祭,便必須透過訪問其他部落(如南王部落)、或參考過去口述資料,再逐漸調整成知本的版本。在此過程中也發生過許多衝突,例如要如何區別知本部落和其他部落的大獵祭儀式等。因此陳玉苹認為,在文化斷裂之後,將文化重新帶回來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經過意義的重組,並且它無法一次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長時間的討論和爭辯,進而逐步恢復。
而在部落族人自主發起文化復振行動的同時,國家從法令、制度和政策面等,也開始有所行動,如2006年原民會推動《部落會議實施要點》、並將卑南族大獵祭登錄為縣級文化資產民俗類別;2016年頒布《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等,但卻也同時發生如2007年大獵祭祭典成員因持槍遭到警察拘捕起訴、2010年的遷葬事件、以及2017年的光電案等矛盾衝突。陳玉苹認為,這意味著雖然台灣的上層社會嘗試推動改革,然而各部門和台灣社會對於法令的推動以及法令背後的精神其實並不了解。因此縱使有保護的政策出現,卻可能出現部落族人被告的矛盾景象。
重點可能在於我們如何在此過程中去組合與重組這些「現代」跟「傳統」的元素,進而創造出一個與我們當代生活較適切的意義。
結論:在二十一世紀要怎樣成為一個原住民?
從小就接受西方知識,在現代化過程中,文化內涵被系統性地剝除了,這可能使得我們與自身文化產生斷裂,然而這並不表示必定會被規訓。
陳玉苹提醒聽眾,若我們將文化遺產註冊起來,將它變成一種標榜文化特殊性的形式,使它脫離了日常生活的經驗,反而會遭受當地民眾的反對。若將它登錄成為國寶、古物,則可能會朝向商品化、標籤化的路線發展。但若我們將文化遺產當成是一種社會行動,以在地的主體為核心,政府政策為輔,在這過程中使之與在地的生活產生互動,才有可能使得「文化遺產」在文化治理的過程中,成為推進文化跟社會再生產的動力。
只是作為一個深陷相似處境的人,陳玉苹表示如何推動一個「更好」的文化復振行動沒有答案,但透過這個研究,她看見了許多具有「創新」意義的組合。陳玉苹認為,「怎麼樣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原住民?」其實亦是「怎麼樣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漢人?」重點可能在於我們如何在此過程中去組合與重組這些「現代」跟「傳統」的元素,進而創造出一個與我們當代生活較適切的意義。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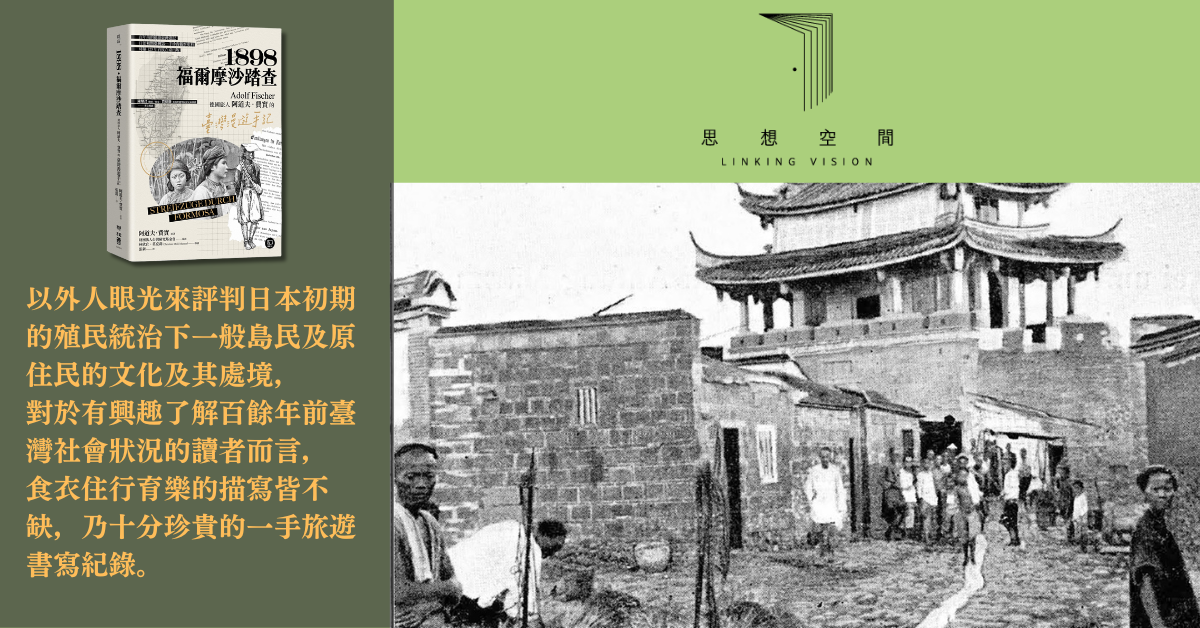
藝術與殖民之糾葛:阿道夫.費實的臺灣

林姵吟:以海為眼的夏曼.藍波安,如何開拓文學與歷史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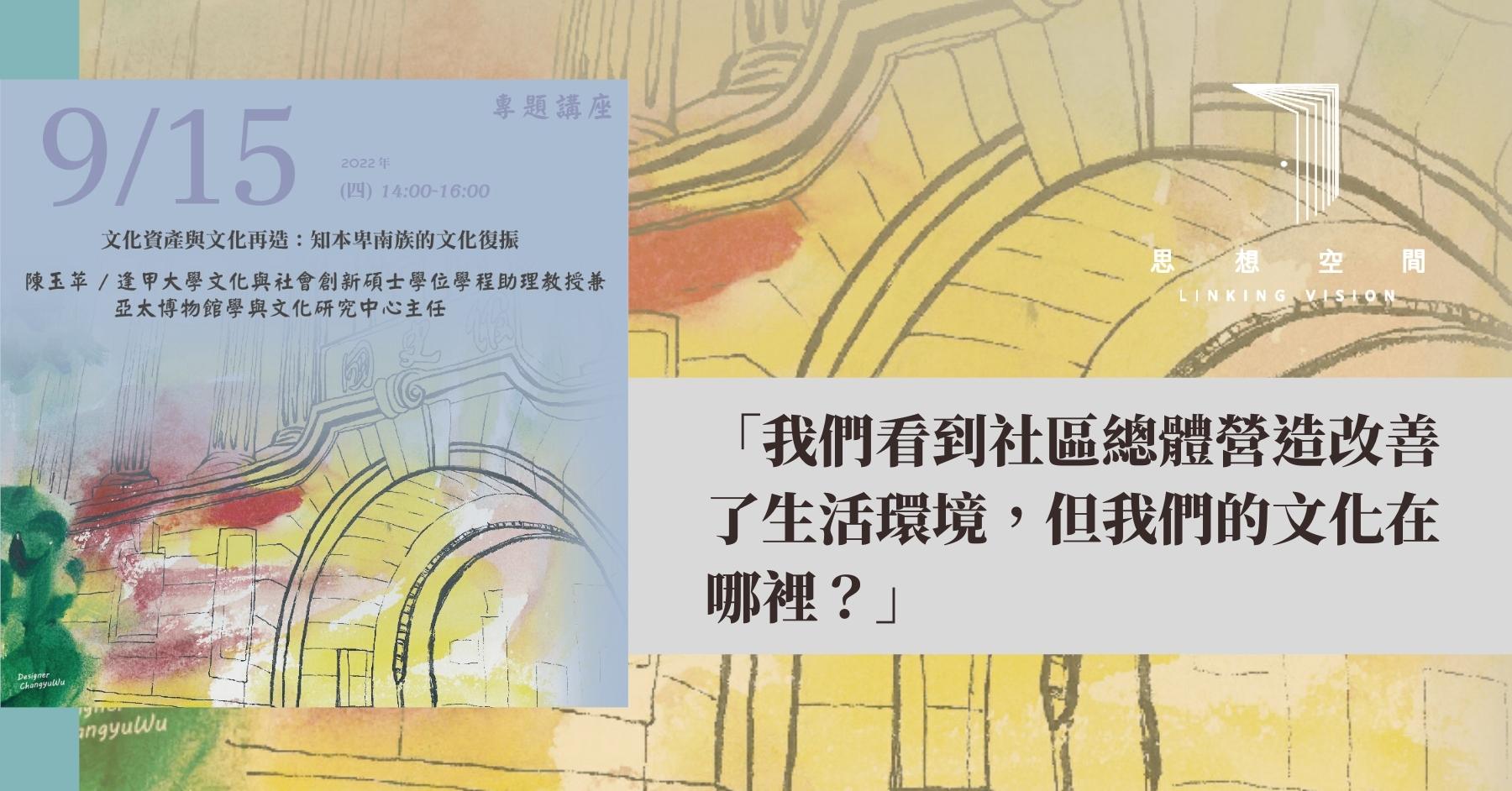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