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 / 葛兆光(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記錄 / 思想空間編輯部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時間過得太快了,余先生竟然往生一年了。在這一年裡,各種各樣紀念余先生的文章很多,余先生的詩、談話錄也出版了,現在聯經的文集也要出版了。一個真正的學者、了不起的學者,總是被人記住的。所以我相信余先生的文字,肯定是會永遠留在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
今天聯經給的題目是「回到余英時的客廳」,這讓我好像又回到了余先生的客廳。從2009年開始,我和太太在這個客廳裡,和余先生大概談了有三十多次,肯定超過一百小時。我記得我總是在那個客廳面向院子的大玻璃窗下面,回頭就可以看到養金魚的池塘,而右手邊是放著余先生跟林海峰下圍棋的照片。
我曾經說過,跟余先生聊天、談話,為了聊得盡興、不受約束,所以我們約定好絕不錄音、也不記錄,只是偶然的,我會在我的筆記裡面記下幾句。所以我只能根據我的記憶,挑出一些跟余先生聊天的話題給大家報告,就算是再次回到了余先生的客廳。

他當時笑了笑說:「我現在沒有精力,這事就交給葛兆光了」,我說我可寫不出來。我沒有余先生那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到現在也沒有能力寫出來,所以想起來也真是很慚愧。
未盡的「唐代佛教和文人」
讓我從一個非常具體的話題開始。我想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都知道余先生曾經有過寫「唐代佛教和文人」計劃。余先生就像王汎森兄說的一樣,「上到堯,下到毛」都有論著,偏偏沒有專門寫過唐代,所以大家都非常希望余先生能寫出來。可是直到余先生往生,這個計劃也沒有實現,大家都很遺憾,我也一樣。不過我在余先生的客廳裡,至少曾經有兩次關於唐代佛教和歷史的長談;現在我把它回憶出來,也許可以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余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
記得是2012年春天,我第三次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客座。那一年,我們不僅給余先生帶去了在他老家潛山拍的一些照片和視頻,而且我給他帶了一本自己的書,就是重新修訂過的《中國禪思想史》。大概半個月以後,在一次余先生客廳,他很認真地跟我聊起唐代禪宗的問題。聊得很多,大多數我現在都不記得了,但很清楚記得余先生接連問了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學術界對於唐宋的禪宗跟政治史的問題討論並不多?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禪宗對文學和士大夫生活影響這麼大,而對上層的政治影響很小?第三個問題則是禪宗在佛教的中國化,他問:「就像你說的『老莊化』,是不是導致了禪宗跟政治有所疏離?」這三個問題他至少問過好幾次,說實在話,這些問題我一直沒想清楚。

我跟余先生對宗教史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非常一致的地方是什麼呢?是我們都希望在歷史背景下去研究禪宗。余先生對胡適是非常熟的,胡適討論禪宗的文字,他都記在心裡、如數家珍,他也非常贊成我們應該像胡適那樣從歷史和文獻中去研究禪宗,而不是對禪宗的信仰有什麼興趣。
他曾經引用過一段評價陳寅恪的話,說:「俞大維曾經說過,陳寅恪對佛教有興趣,但是他絕對不是信仰佛教,而是對歷史有興趣。」我想我們也是一樣的,所以後來我在《中國禪思想史》再修訂版的時候,還特意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就是〈仍在胡適的延長線上〉。這是我們很一致的地方。當然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比如說剛才孝悌兄講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書,我曾經跟余先生說,我對他的一些說法有點懷疑——新禪宗是不是能夠刺激出韋伯說的資本主義的計算、理性和天職?但是剛才我們提到余先生講的幾個關於禪宗研究的問題,還真是至今沒有討論好的問題。在學術界,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對這個問題很好的討論。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非常多地去看日本禪宗的研究,覺得日本禪宗跟中國禪宗確實有非常大的差異——它(前者)介入政治非常深。可是我們要回過頭來想,為什麼中國禪宗跟政治之間的關係(薄弱),是不是我們沒有發掘出來?或者說它本來確實就沒有那麼深?而我們的禪宗史研究,確實比較少讓禪宗落下「雲端」,回到政治、介入社會。
過了一年,2013年的冬天,我再次到普林斯頓去客座。那次余先生讓我看《論天人之際》的校樣,第二年就在聯經出版了。看了之後,我跟他討論了很多,他就跟我笑著說這是他最後一本書了,可我當時就說「那不是最後一本,你還欠了一本唐代的佛教和禪宗以及歷史的研究」,他當時笑了笑說:「我現在沒有精力,這事就交給葛兆光了」,我說我可寫不出來。我沒有余先生那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到現在也沒有能力寫出來,所以想起來也真是很慚愧。
討論禪宗是兩次比較專業、學術的長談,但是我在余先生的客廳裡與他談得更多的,可能是學術界的各種見聞。余先生一生閱歷豐富、閱人無數,又有全世界論學、訪學的經歷,肚子裡有很多掌故,我真的是從余先生那聽的太多了。無論是歐美、日本、大陸、臺灣、香港,無論是他的前輩、同輩、還是他的後輩……他比我們的閱歷豐富得多,我也確實特別喜歡聽他講這些故事。聽他講故事不僅是一種享受,而且長見識,其實更多的是讓我們跟著他一起進入學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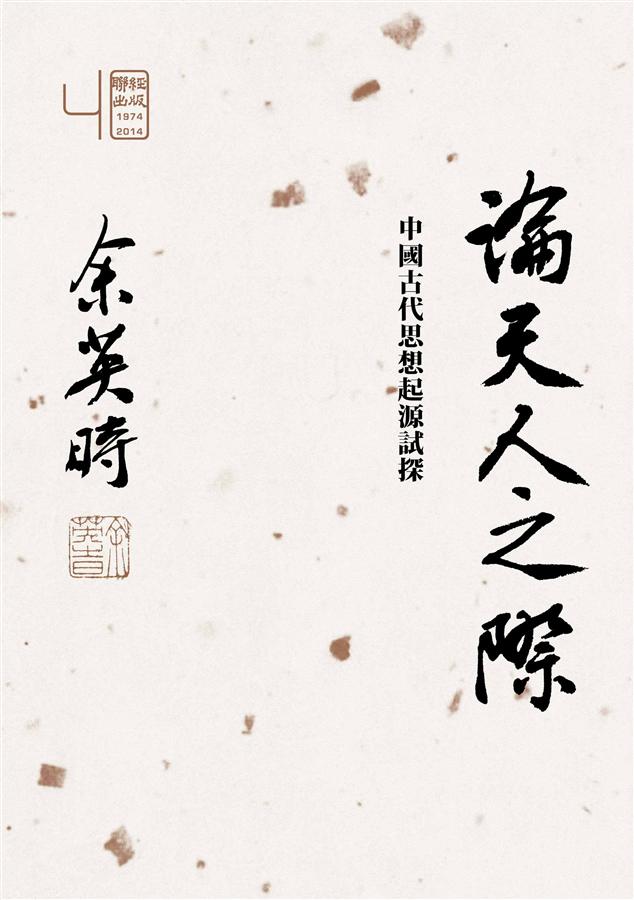
以前人所說的「掌故之學」,餖飣而且瑣碎。可是余先生不一樣,他心中有大的歷史判斷,總是能把這些東西放在思想和學術的大脈絡裡面,發現他自己所說的「暗碼」。
從日記、書信、詩詞洞見學術史
我記得余先生講過一句話,這句話我記的很清楚,他不僅是講過而且也寫下來過,他說:「哪個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後不說人?可是只要心存忠厚對人寬容……」 坦率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余先生對什麼人───無論是前輩或是後輩───講刻薄、過分的話,他總是非常寬容的。我聽他講了非常多,包括大陸的錢鍾書、王元化、李澤厚、李慎之、周一良、李學勤,美國的何炳棣、張光直、還包括劉子健,也包括我們這一輩學人,都很少聽到余先生講過刻薄的話,最多講一句:「不相干、不相干。」這是他的口頭禪。特別是對年輕的一代,就像我,以及比我更年輕的一代,他幾乎是(給出)最大的包容。就連我們看不慣的一些人,余先生都會非常正面、親切地去鼓勵,而絕不說不是的話。
談論學界的人,其實是學術史的一部分。最讓我感覺到驚詫和佩服的,就是余先生的博聞強記。大家知道《公羊》三世說裡面有「所見、所聞、所見聞」,在這一點上,我從來沒見過第二個像余先生這麼博聞強記的人。他非常喜歡看學人日記、書信和詩詞,以及各種年譜、傳記;為什麼我們特別談得來,就是因為都有看這些東西的愛好。余先生可以在這些細碎的文字裡面,觀察思想史的大問題、大背景、大趨勢。這也是我在余先生的客廳裡聊得最多的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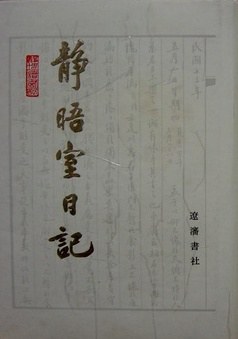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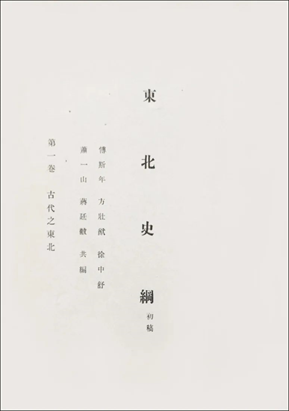
記得有一次,大概是2014年,我在哈佛訪問,去余先生家裡面去看他。我那時候在看金毓黻《靜晤室日記》,自己覺得很有感受,就跟余先生提起了一個特別有興趣的問題,就是金毓黻對於日本人稻葉君山的滿州史研究,其實有著非常多的緊張和評論。我總覺得這實際上是當時(「九一八」之後),中國和日本兩國學者在滿州史研究上的一種學術競爭。所以我也聯想到傅斯年的《東北史綱》,也提起繆鳳林對《東北史綱》激烈的批評。我覺得這是學術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涉及學術競爭、民族主義的大問題。跟余先生談起這個事情,真的沒想到,余先生提頭知尾,反倒來跟我講了很多「九一八」之後學術界的各種動向,顯然他比我看的多得多,知道的也多得多。
余先生看這些日記、書信、詩詞不是為了看八卦,而是為了從裡面看學術史和思想史,洞察過去人的心理和感情,他有很多論述都是從這來的。大家都知道,比如看《胡適日記》、《吳宓日記》、《顧頡剛日記》、《夏鼐日記》、《陳克文日記》,讀陳垣的書信、夏承燾的日記、讀陳寅恪的詩、汪精衛的詩……他常常跟我互相聊閱讀的內容。我當然也看過,但是我能從余先生那裡感覺到,同樣讀這些東西,是有兩種境界:有的人看得雞零狗碎,挑出一些八卦、找出一些軼聞,顯示自己能網羅掌故,這就是以前人所說的「掌故之學」,餖飣而且瑣碎。可是余先生不一樣,他心中有大的歷史判斷,總是能把這些東西放在思想和學術的大脈絡裡面,發現他自己所說的「暗碼」。
他對陳寅恪詩的解讀,能夠讓陳寅恪都說「作者知我」,這很不容易。他講到顧頡剛一生都暗慕一位女性叫做譚慕愚,如果你僅僅把它當作八卦那就錯了,余先生要說的是,其實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這幾年裡,顧頡剛思想的轉變其實跟譚慕愚是有很大關係的;而後來顧頡剛為什麼去辦《禹貢》、為什麼1939年寫下〈中華民族是一個〉,其實跟譚慕愚對他的影響有非常深的聯繫。所以余先生看日記、書信、詩詞,絕不是像有些人是為了瞭解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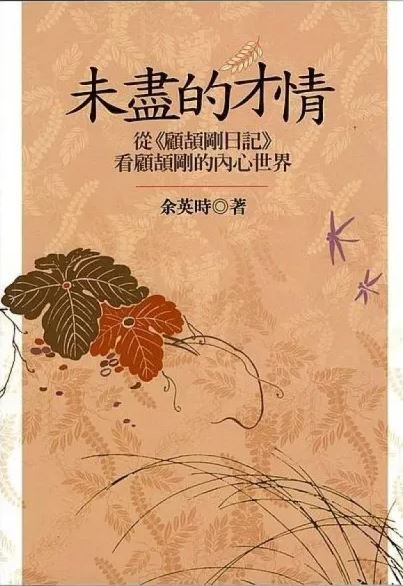
我記得余先生知道我非常仔細地看了《楊聯陞日記》,我也問過余先生對這個日記的一些事情。有一次,我對余先生提起1960年代(他)在劍橋住在什麼地方,而我是從楊聯陞日記裡看到的;余先生居然為這件事情,去找了他的一本書背後的題簽,上面就寫了當時的住址,他說楊聯陞記的是沒有錯的。但是我跟余先生聊《楊聯陞日記》的時候,他說他不能寫楊聯陞先生,因為楊聯陞是他的老師,捱得太近,不容易跳脫出來。這讓我想起陳寅恪先生一段話——他說他不能研究晚清,因為他和他的家族是當事人,容易動感情,不能夠推開來進行研究。這就是歷史學者的謹慎。並不是說余先生不關心楊聯陞,其實余先生是看過《楊聯陞日記》的,他也跟我聊過很多楊聯陞的事情,也看過我寫(關於)《楊聯陞日記》的兩篇文章,而且還跟我討論過。大家想想,余先生到了八十多歲還親自校訂楊聯陞的詩集,而且他還複印送了我一本,非常厚的一疊。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余先生讀鄧之誠的日記,而沒有寫出文章來。鄧之誠先生的日記影印好多次,字跡不是那麼容易辨認,余先生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去閱讀。余先生告訴我他讀完了,而且他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見過鄧之誠,跟鄧之誠先生的大兒子有很深的來往。他讀鄧之誠的日記,會聯想到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感受,而且也讀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內容,包括像鄧之誠先生講陳寅恪寫的一首詩是「反詩」。其實余先生看到了很多,可是很遺憾他沒寫出來,我們無緣得知余先生是怎麼看鄧之誠先生的日記了。

其實,「林下話滄桑」的地方,就是余先生的客廳,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我們重新回到余先生的客廳,我們真是感慨很多。
回望故地,幾回林下話滄桑
在余先生客廳裡談得最多的,當然還是中國。他曾經說他之所以跟我談得比較多、而且比較投緣,不僅僅是因為研究領域比較近,而且因為我是從大陸出來的學者,他其實始終關心著中國的事情。他常常向我問起大陸的情況,從學術到民生,也曾經幾次反覆地說:「你應該把你的經歷寫出來。」因為我經歷過1950、1960、1970、1980,經歷過文革也經歷過大陸改革開放的曲折過程。
余先生的心裡,對於政府和國家、對於「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和「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對於「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和「思想意義上的中國」,其實區分得非常清楚。很多人都知道余先生說過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其實他對他所生活過的那個中國的關心,真是深切得很。只是像他的一首詩裡面說的:「左言已亂西來意,上座爭參杜撰禪。」那裡已經不太像他記憶中的中國了。可是余先生為什麼會說:「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

我印象非常深刻,2012年我和我太太去了潛山,就是余先生的老家,給余先生拍攝很多照片和視頻,裡面有破敗不堪的余家老宅,也有他過去居住過的房間的破窗戶,還有余先生老宅門口已經乾掉的池塘,和大屋背後的竹林。我們在余先生的客廳裡,用電腦一一放給他看,余先生看得非常仔細,然後給我們一一地講他在潛山官莊的生活,講他半夜爬涉山路去桐城、去懷寧,講他在夜裡半山上怎麼遇見狼,也說到那時候他在竹林裡面跟朋友的一些活動……記得那天在客廳裡,看完錄像和照片以後,他有幾分鐘都沒說話,可能在想他過去的生活。這時候你真能感覺到,他對故鄉其實有很深的感情。
從2019年以後,我們就沒有再去普林斯頓余先生的客廳了。只是在朋友發來的照片上,我們看到余先生長眠的墓地和墓碑,那個地方靠近普林斯頓的公共圖書館,我們去過很多次。今年年初,我們請朋友代我們在余先生的墓碑前面獻了一束花,這束花上面別了一張紙條,寫了余先生當年送給我們的一首詩中的一句話:「幾回林下話滄桑」。其實,「林下話滄桑」的地方,就是余先生的客廳,今天有這個機會,讓我們重新回到余先生的客廳,我們真是感慨很多。謝謝各位。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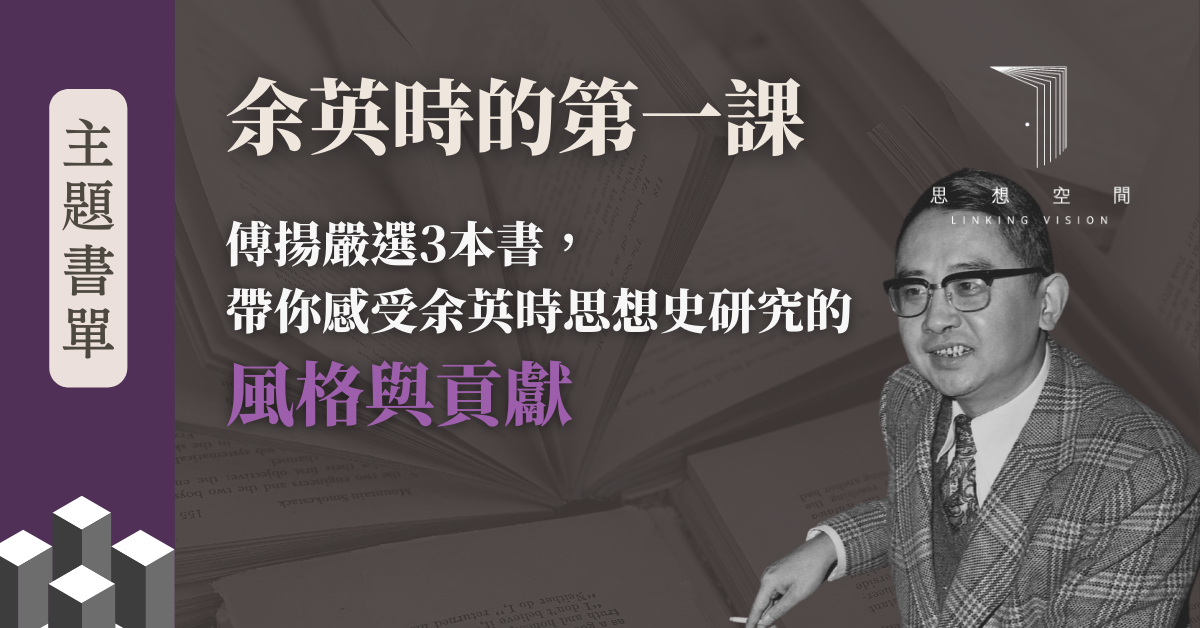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傅揚嚴選3本書,帶你感受余英時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與貢獻

容啟聰:第三勢力與冷戰:由余英時的《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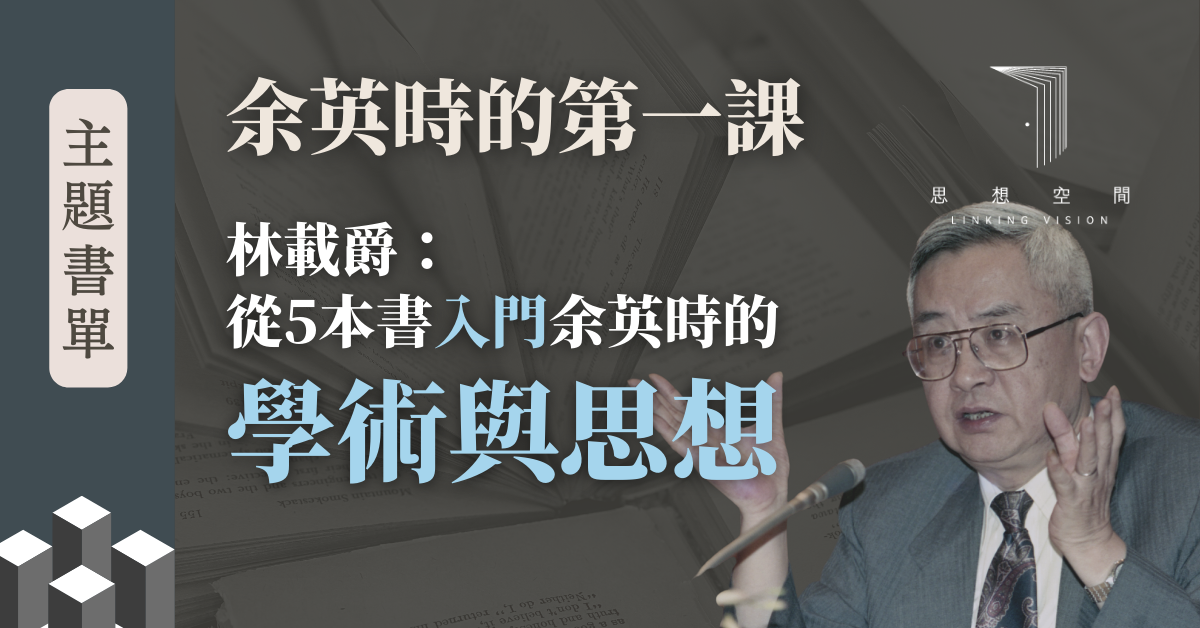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林載爵:從5本書閱讀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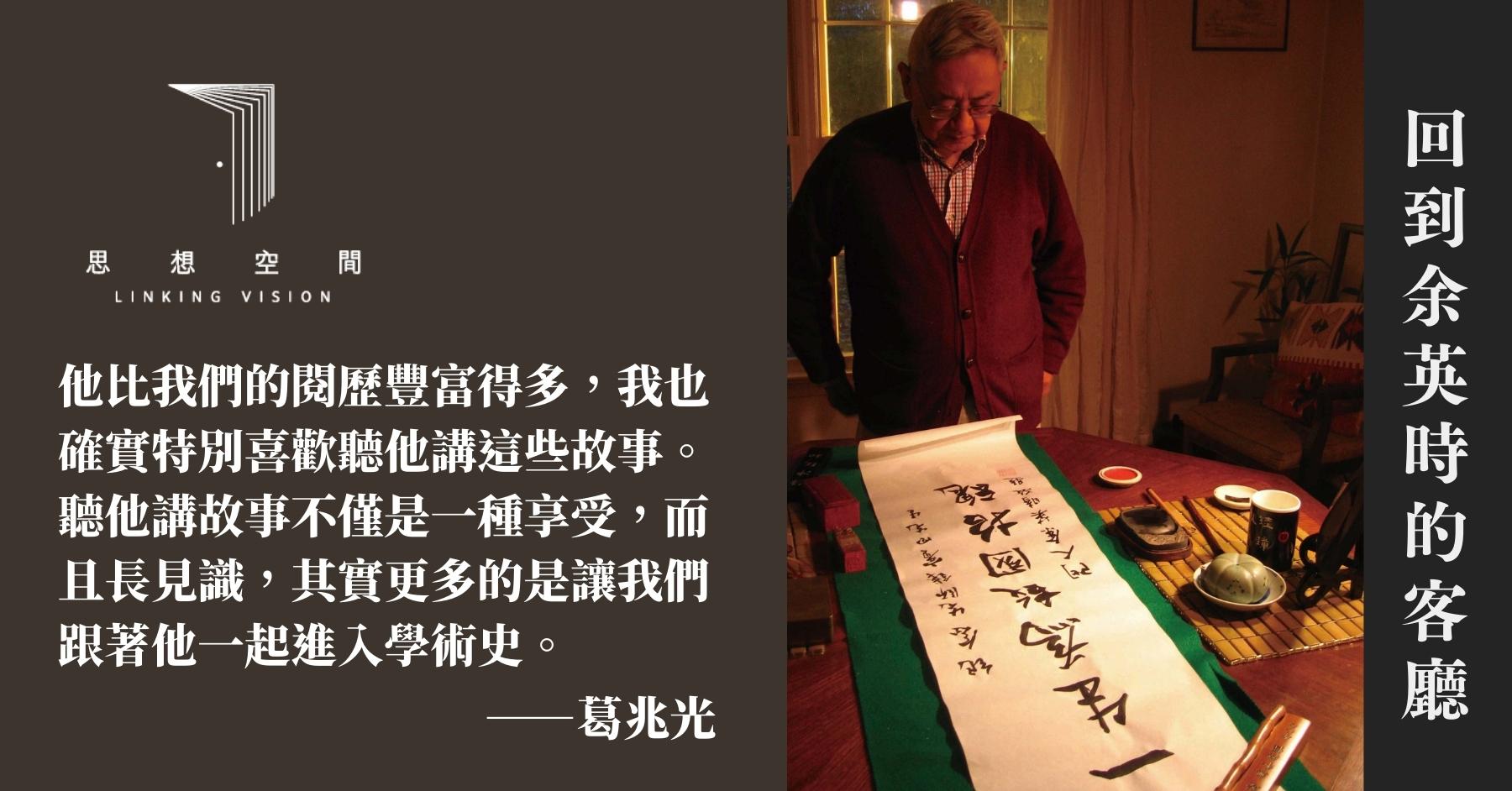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