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 /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
記錄 / 思想空間編輯部
編按: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寓所的客廳,是知交友人、後學晚輩、意見領袖、落難書生常常造訪的地方。余先生與夫人總是開門迎客,關懷各人學思經歷,處境遭遇,也不吝交流,盡力幫助。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談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本篇文章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李孝悌在活動中的發言輯錄。
有幾年我在香港工作,到最後,常常覺得案牘勞形。有一天,剛好收到葛兆光教授的《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就覺得非常興奮,有這樣的學術書可以讀。後來,我再收到剛剛丘慧芬教授講的《論天人之際》,覺得非常震驚。就像豐恩剛剛講的,余先生年紀已經這麼(大),仍然源源不絕,「為有源頭活水來」,寫了那麼一本震撼人心的著作。而對我來說,這特別是一個救贖,把我從案牘勞形裡面救贖出來。而且我覺得那本書有他一貫的風格——詳細的論證,陳述非常清晰。
在余先生這麼多著作裡面,從最後的《論天人之際》、到早期我們都要讀的《歷史與思想》,我覺得有一個特色——我們都知道余先生對西方理論非常熟悉,對西方的歷史著作也非常熟;他平常在書裡不太願意用西方理論,更對此有一些批評。當然《論戴震與章學誠》是比較特殊的一個例外,不過也只是簡單利用了柏林(Isauah Berlin)的「狐狸與刺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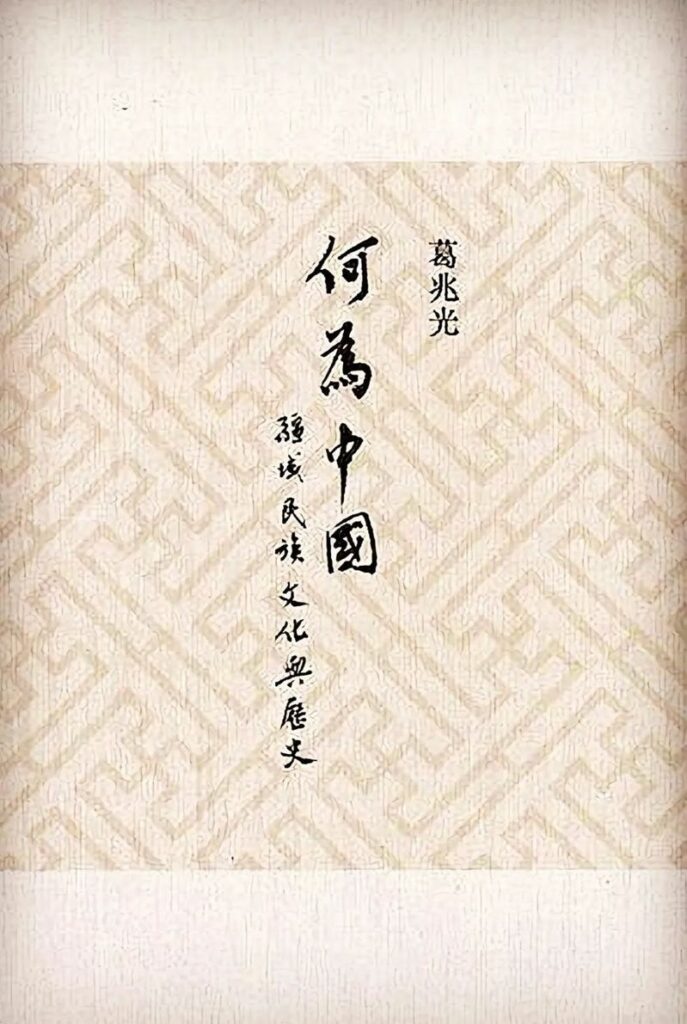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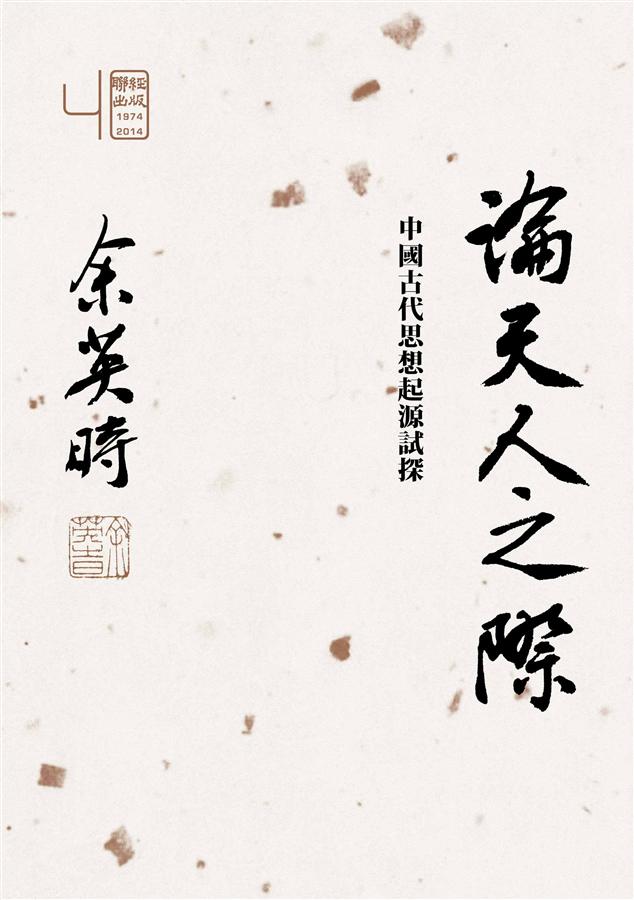
余先生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要跟韋伯「格鬥」(engage)。他很多地方完全不同意韋伯的觀點,他認為韋伯完全誤解了中國的宗教精神。
與韋伯「格鬥」的余英時
在這麼多著作裡面,余先生都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他有這麼多豐富的史料,要去寫書。我覺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書,整本書的出發點,幾乎就是要跟一位學術巨人───韋伯(Max Weber)進行「格鬥」。
這讓我想到了我的指導教授——已經逝世的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又名孔復禮)教授。孔復禮教授寫書有點嚴肅乏味(dry),可是他15年寫完一本書,就變成一個經典。他真正寫了一本暢銷書《叫魂》,又好又叫座。在《叫魂》裡面,無獨有偶地,孔復禮也借用了韋伯的理論,不過他跟余先生不太一樣。余先生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要跟韋伯「格鬥」(engage)。他很多地方完全不同意韋伯的觀點,他認為韋伯完全誤解了中國的宗教精神。
韋伯關於官僚的三個界定,其實界定得非常有用,因此孔復禮在寫《叫魂》的時候,是用韋伯「官僚說」來講這些故事的。當然還有一些,像是寫羅威廉(William Rowe)寫商業,也是要回答韋伯的問題。韋伯問了很多大哉問,例如: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沒有宗教、中國沒有城市……雖然他學問還不錯,是社會史界除了馬克思之外、影響最大的大家,可是他直接處理中國問題時,其中是有些錯誤的。而余先生這本書,幾乎通篇就跟韋伯在交戰。

從一開始,書名《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就是從韋伯那裡來的。我以前跟丘慧芬教授、林毓生先生一起讀書時,知道林先生對韋伯常重視,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社會學家,尤其覺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部經典;因此,我跟丘慧芬教授那個時候讀了好多遍。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要發展,是有很多條件的:要有制度、法律,要有城邦、要有自由……。可是到最後臨門一腳,還有一個神祕的、而且看起來是矛盾的(部分),就是新教倫理。
新教有很多教派,一般來說,我們覺得新教知識程度是比較高的,當然這個還是可以爭辯。天主教徒一般來說可以不用識字,每天去教會有神父幫忙解釋;而新教徒,因為可以自己讀聖經,所以識字率是比較高的。可是他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理論,就是一生活著的目的,是要確定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選民——而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帝選民的。因為上帝是一個全知全能(almighty)的神,人這麼渺小,是有罪惡、瑕疵的,(所以)不能了解上帝的意思。可是有一個線索,可以來證明你是不是上帝的選民,那就是如果你非常有錢,而且不花它,那就非常有可能是上帝的選民。所以這個資本主義的精神其實是非常神秘、不合理的,賺那麼多錢卻不花;當然在另一面向看來,你也可以說累積資本是合理的。所以這是韋伯最神秘之處,就是把新教倫理這麼玄妙的東西跟現代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
當然其中也有很多討論,很多人認為不要簡單地認定是新教倫理決定了資本主義。韋伯用了這樣一個大哉問,問完之後,又寫了《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韋伯說中國人太願意跟現世妥協了,他們缺少新教倫理的「入世苦行」——你想想新教徒、喀爾文教派多麼辛苦,每天拚命地賺錢,賺了錢又不能花,只是為了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就要累積財富,這是很不合理的。

儒家認為現實世界已經殘破得完全不能目睹了,所以它懸著一個高高的「理」,不管是道統的或其他。
「入世苦行」的實踐者們
韋伯把這個現象叫作「入世苦行」,而余先生整本書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三個宗教,從新禪宗、到新道教、到新儒教,都有「入世苦行」;而且它的很多精神,跟喀爾文教派是一樣的。余先生當然是有學問的人,他可以藉著韋伯這麼大的問題(來展開書寫)。因為韋伯對中國宗教影響很大,可是有一個極大的誤解,余先生大概覺得忍無可忍(當然他對韋伯是很尊敬的)。余先生也提及曾經讀過大量馬克思的作品,而他最後的結論是:這是一個錯的問題。可是這大量的、幾百萬字的資本主義萌芽,證明了16世紀中國商業已經高度發展,這些他都看過、也都知道了。最後,余先生得出結論三點:
第一,新禪宗。葛兆光先生是新禪宗的專家,他寫過一本非常暢銷的新禪宗(《禪宗與中國文化》),認為新禪宗是第一個代表了中國宗教的轉向。唐代所謂「百丈清規」,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雖然唐代有很多寺院經濟,大和尚看起來不需要供養,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從「百丈」之後,規定每一個和尚都要去勞動,不勞動就沒東西吃。他(余先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的新禪宗的入世轉向,所謂的「入世苦行」。這個(觀點)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
我們都了解新禪宗,也知道王陽明受到新禪宗的影響,以及新禪宗對儒家建立另外一個「理氣二元論」、建立形而上的世界,是有很大影響的。可這裡他(余英時)具體地引用了韓愈。韓愈真是文起八代之衰,他有兩篇文章,一篇是《原道》、一篇是《師說》。根據余先生所講,這兩篇文章受到新禪宗極大的影響,又對新儒學的入世取向,有著極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余先生覺得這是兩篇很關鍵的文字。

就《原道》而言,根據余先生的說法,唐代非道即教、非佛即道,又有儒學。唐代儒學可能繼承了魏晉,又不太像玄學,跟「人倫日用」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所以韓愈在《原道》之中,借用了新禪宗的說法,要把儒家重新從跟人生毫無干涉的東西(中釋放出來),來一個「入世轉向」,以進入「人倫日用」。在這篇文章裡面,他還建立了一個「道統說」——根據余先生的分析,這個「道統說」其實是陳寅恪講的,陳寅恪認為韓愈「道統說」其實是借用了新禪宗的「教外別傳」。道統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看似顛撲不破的儒家道統論,其實這個道統說是完全受新禪宗的影響。這是《原道》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地方:把儒家帶回現世,講求人倫日用,這是完全是一個入世取向的。
第二是《師說》。原來的中國是沒有老師了,老師都是談玄說理,到唐代不信佛就信道,要不然就讀章考據之學,沒有人去講大道了。後來受到新禪宗的影響,開始講「道」、「原道」。儒家是有「道」的,《師說》裡強調「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其實新禪宗的說法。傳統的漢代的解經家、儒家,他們沒有這個使命,沒有這個宏大的企圖,要「傳道、授業、解惑」,能夠把你一個小小的考據問題解決就不錯了。
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句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是非常平等的。在孔子的說法,這是一個非常有四民階級的(理念)。有人寫過一句話:「宗教來了把儒家席捲」。尤其對於北方的民族來說,儒家是有男女等差的,在男性中的等差是士、農、工、商,而女性則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北方民族為什麼不相信儒家,相信道教、佛教?因為佛教是一個愛無等差的社會,沒有任何的差等(discrimination)。所以北方民族很快就接受了佛教,佛教席捲半壁江山,中國人也受到這個影響。所以在這篇文章中,韓愈也受到了這種沒有階級之分(的影響)。
接著余先生跳到范仲淹。我們都知道范仲淹最有名的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余先生認為,這是儒家到了宋代,已經快要成熟,而這是一個典型的「入世苦行」。他用了史景遷的老師芮瑪麗(Mary Wright)(的觀點),認為這其實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的做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arguement。范仲淹,我們都覺得是很了不起的,更偉大的是他還「入世苦行」。我其實還學了范仲淹的精神,在哈佛也是入世苦行。
另外余先生也引用王安石——他為什麼要去做宰相?完全是受到新禪宗的影響。你甚至可以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所以宋代兩個最偉大的儒家,他們的「入世苦行」、去做這一番大事業,其實都是受到新禪宗的影響。「入世苦行」這幾個字在全書裡面是不斷出現的,余先生為了要反駁韋伯的觀點,就要證明中國的宗教當然有「入世苦行」。
韋伯解釋儒家,在余先生看起來簡直荒唐至極了;他(理解的)儒家太遷就現實、沒有一個理想面。儒家認為現實世界已經殘破得完全不能目睹了,所以它懸著一個高高的「理」,不管是道統的或其他。政治非常腐敗、人心非常沉淪,所以儒家才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理」;這其實就像宗教裡面不可超越的一個精神、一個高度的理想,要來針對現世的腐敗。所以余先生從這個地方也反駁了韋伯對於儒家的否定。


他(余先生)甚至認為有商人有「賈道」,是可以跟儒家抗衡的;他們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也有非常強的自尊心。
儒商不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的書中,第一部分講韋伯,第二部分講中國三個教的宗教倫理,下邊開始真正進入到「商人精神」。他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三個宗教,就跟喀爾文教派一樣,都有「入世苦行」的宗教倫理,而且這個跟16世紀明清商人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
從漢代開始,我們就認為「商」是「末道」,商人是被社會看不起的。余先生在這裡引了王陽明最後的一篇晚年定論,為商人方氏寫的墓誌銘。在墓誌銘中,王陽明已經肯定了「士、農、工、商」每一個人都可以捕捉到同一個「道」。這就有點像泰州學派的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掃地的人、小孩子,只要你努力、認真敬業,也可以變成聖人。所以對余先生來說,王陽明晚年幫方氏寫的這一篇墓誌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對「四民論」的重新翻案。
傳統儒家的階級社會,到這時候已經打破了,士、農、工、商不太分了。這個時候,商人有充分的自尊,很驕傲。他(余先生)甚至認為有商人有「賈道」,是可以跟儒家抗衡的;他們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也有非常強的自尊心。另外一方面,這些商人基本上都有相當多的儒家訓練。這個世界已經儒商不分,因為「四民」階級已經被打破了,商人已經完全建立了充分的自我認同跟尊嚴。這大概就是余英時本書的論旨。

我覺得余先生寫到這個地方,他寫完了,真正把儒家的宗教性寫出來了。所以我後來為這本書寫了一個標題,我覺得可以送給余先生,就是「入世苦行」。
儒教宗教化
這本書是在1987年出版的,我去年為了幫中研院寫一篇文章,看了之後覺得非常訝異,覺得這本書和我以前看的不一樣。1987之後,余先生又寫了一篇很長的〈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包括四、五個小標題,從1996年開始寫,完稿是在1997年。這一篇為什麼對我來說特別重要?余先生講的「三教」——禪宗、道教毫無疑問是宗教,但儒教是不是宗教?這是一個學術界辯來辯去、辯不完的問題。余先生在此講「新教倫理」,如果把儒教看成宗教,就是「儒教倫理」。到這個時候,他(余先生)把左派王學完全加進去了,在文中特別提到顏山農。顏山農在講學的時候,完全跟基督教的牧師一樣,有點像被附身;整個講學的氣氛,跟我們熟悉的儒家的講學活動是不一樣的。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是王陽明的左派,已經完全發展到宗教化了。
可是還有比這個更精采的,余先生談到林兆恩。我真正對林兆恩有深切的了解,是我這麼多年跟著鄭振滿教授,看了大大小小十幾次、包括台灣、兩岸辦的各個研習營。我們有一次到鄭振滿教授的家鄉莆田。莆田,有人稱它是中國的猶太人,什麼都做、非常有錢。莆田大概有1000種神,是非常富庶的地方,而且它其實是受儒家影響很大的,科舉中舉率也是非常高。所以莆田是一個有教養的地方,也是一個有錢的地方。在莆田,我去了一座「三一教」的教堂。「三一教」有它的經典、教義、說法,是跟道教徒一起念經的;他們共用一個空間,不管叫教堂或是教會⋯⋯所以林兆恩是「三教合一」,而且林兆恩是王陽明的弟子,他也是標準的儒家後裔。
不過林兆恩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最主要是晚明的倭寇。倭寇死傷都是非常慘烈的,在福建、浙江以南,動不動就是幾千萬。我們知道倭寇不一定是日本人,有的是中國人自己人殺自己人。死傷慘烈,林兆恩就負責救助跟收屍。因為整個社會的運動,林兆恩變成「三一教」大教主,而且對後來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我覺得余先生寫到這個地方,他寫完了,真正把儒家的宗教性寫出來了。所以我後來為這本書寫了一個標題,我覺得可以送給余先生,就是「入世苦行」。在歷史學這方面,他真是創業垂統。回到剛丘慧芬教授剛講的,這真是純儒百世,這是真正的經典。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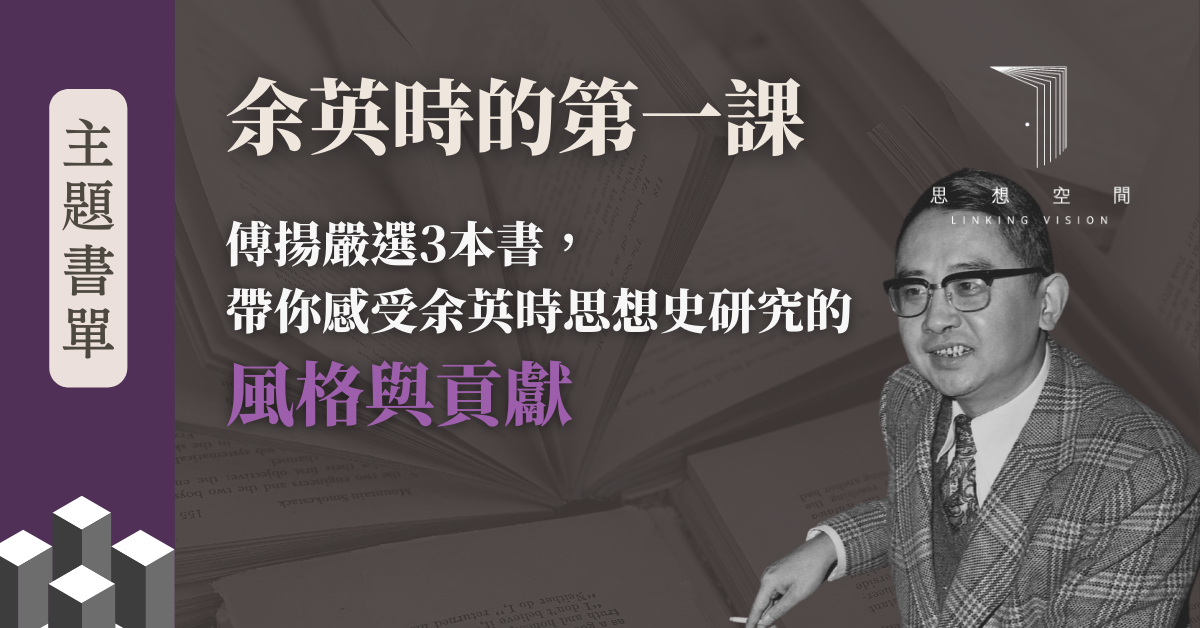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傅揚嚴選3本書,帶你感受余英時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與貢獻

容啟聰:第三勢力與冷戰:由余英時的《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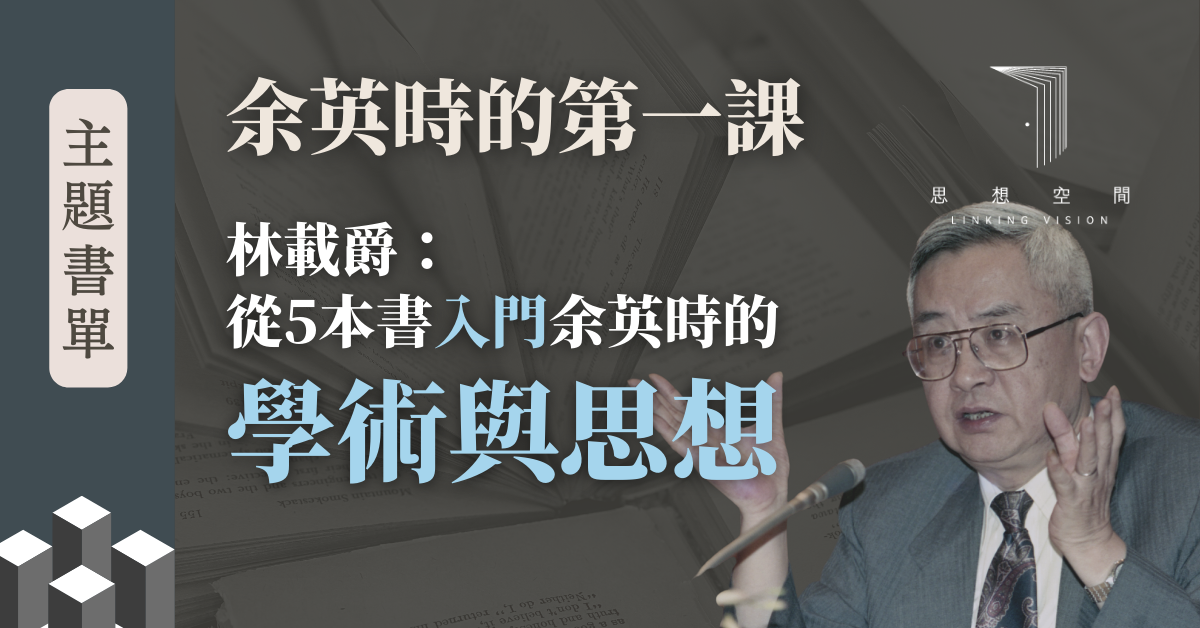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林載爵:從5本書閱讀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
| 閱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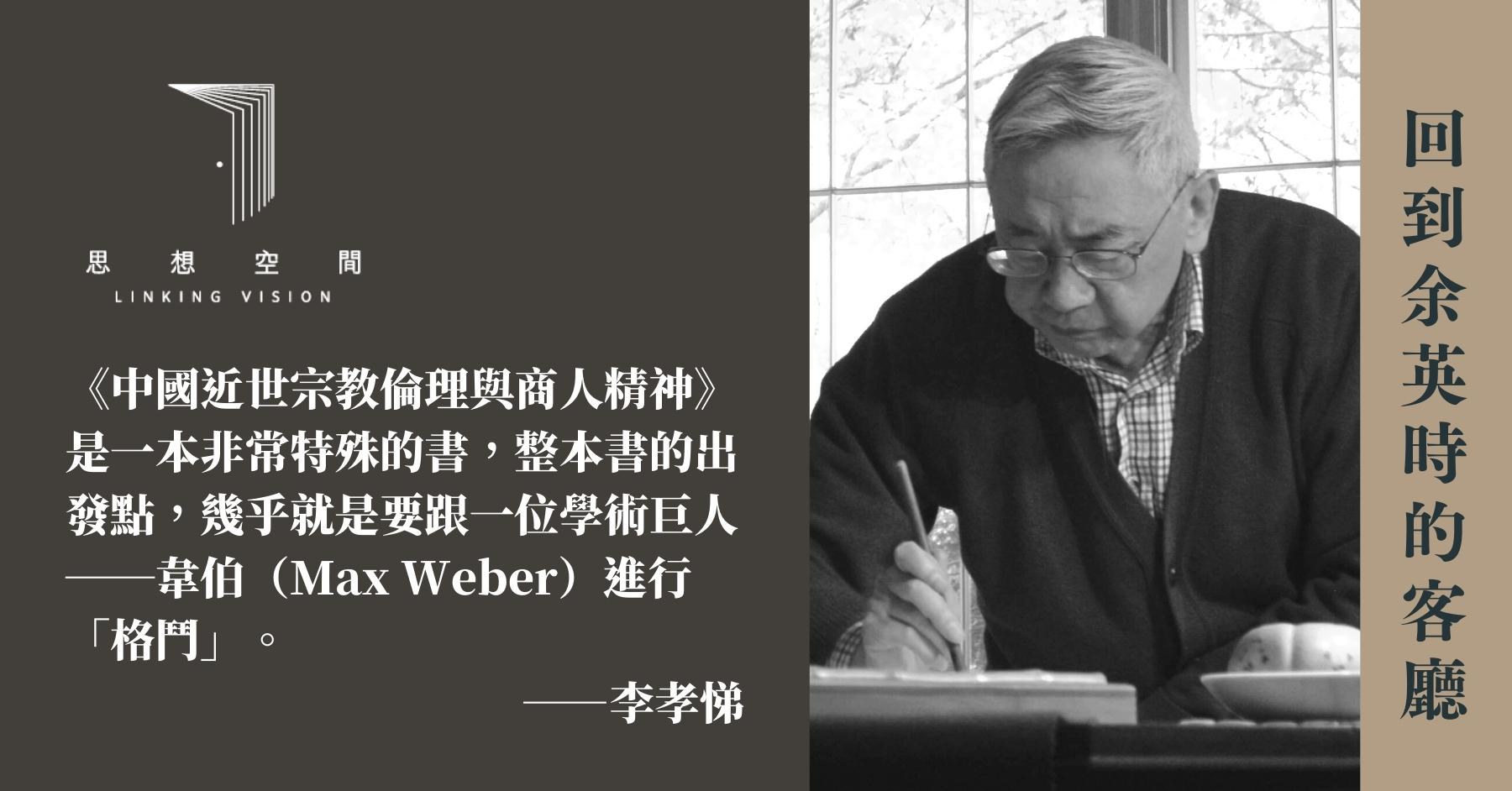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