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題為〈知識人的世界——讀《余英時談話錄》〉,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文/梁右典(大學教師)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學界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之一,去年(2021年)出版的《余英時談話錄》是關於余先生思想的最新著作。雖然余先生已經去世,但讀其「口述」內容,仍然感到十分親切。這是一本「知識人世界」的書籍,包括余先生對於一生經歷的省思,敘述如何在中國動亂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以及在香港的求學歲月,面對西方學界的種種經歷等等。如同黃進興教授在本書序中所說這是「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個人的學思及時代的見證,三方面有系統地整理出來」。
余先生最為人所知的首先是他的學術工作,《歷史與思想》、《朱熹的歷史世界》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在密西根大學任教期間,余先生就說「我喜歡關起門來自己做研究」(頁13);同時,有機會與文化界進行交流之際,余先生也很有提攜後進的熱忱。例如介紹黃仁宇給臺灣兩大報負責人,就是「希望他的學問得到發揮」、因為「他確實是有才有學,而且非常努力」(頁17)。
面對名家雲集的哈佛大學,余先生在任教期間也帶給他許多不同視野,但沒有完全接受,能有自己的判斷。例如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的影響力雖然大,但說他「有好多東西沒有好好消化,不大準的」(頁23)。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正義論》則是劃時代著作,「百年不見得出一本」(頁24)。如今學術已專業分工非常細緻,大師已經再難出現;然而就此來說「不一定是衰落,而是變化了,多元了,沒有人能籠罩一切。這是時代的關係」(頁24)。余先生識人方面的論斷,也在談話錄中可見,例如他說「史華慈是一個純讀書人;而費正清是一個事業型的人」(頁31)。
余先生的言論提醒我們,至少對於知識人而言,如何關心時代之餘,也能夠以讀書知識作為判斷基準,而不是隨政黨、情緒、好惡臧否人物。
「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
1973年回到香港是余先生感到用中文寫作很有必要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涉入大學改制風波,成為余先生生平的一件大事,也體會到「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要知道人的複雜性」(頁60)。所以余先生說「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頁62),以及對於文革歷史得到更鮮明的認識,即是「越是提拔的人越是要鬥他的,這就是人性」(頁133)。
余先生博覽群書的本事是他帶給人的鮮明印象,不僅廣泛閱讀吸收,對於有些書籍更是讀得非常熟;胡適、錢穆的書對余先生的影響自然不在話下,也包括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余先生自述:「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極大的震盪,這才開始進行陳寅恪的研究」(頁85)。在其他書籍方面,他則是推崇錢鍾書,認為他的《管錐篇》是很好的參考書,對於《談藝錄》也看得很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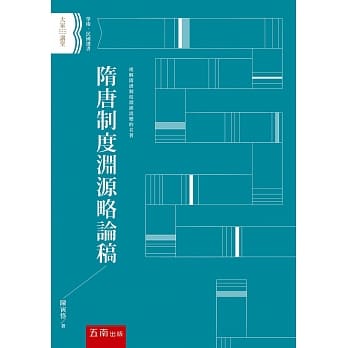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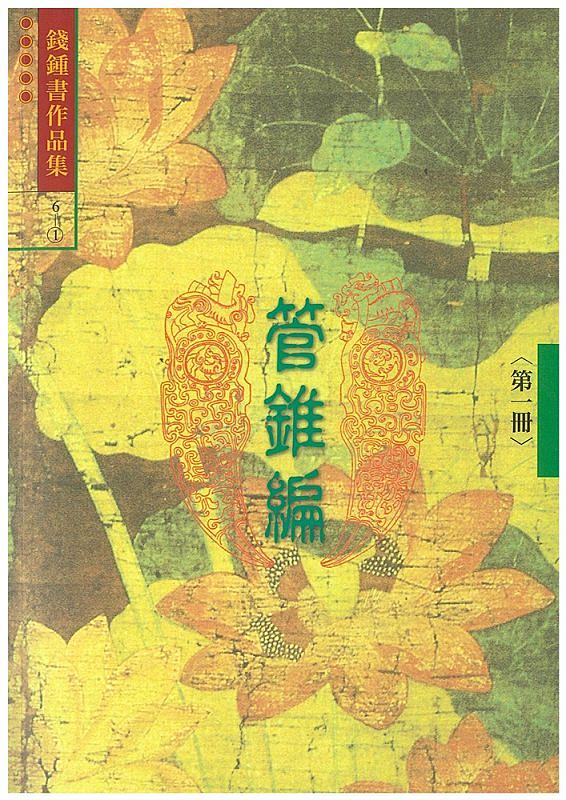
余先生作為專業史學家,對於中國史的研究,特別在思想史與文化史方面用力甚深;另一方面,余先生也很留意西方歷史與哲學的研究成果,對於文藝復興階段也花了很多精神。隨著時代發展,認為中東史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其中一環,這是因為「學科發展跟社會、政治發展的需要相配合」(頁124)。換句話說,歷史研究者要能貼近所處時代,真正進去這個生活的時代;即使研究的不是當代史或近代史,但是實際有助於研究者瞭解時空處境,何謂心同理同,當然也有包括背景因素的不同,避免造成以今非古的謬誤。另外也可以從歷史中學習,讓自己變得更聰明一點,而不是複製遵循某種歷史定律;余先生也說他受以撒.柏林的影響很大,例如對於歷史規律、歷史必然性之類的反駁(頁109)。
余先生關心政治,自己說「政治只是遙遠的興趣」、「只是做為人的尊嚴說幾句話」。他對於現實政治有批判、也能從史家的視野給予較為公正的評價;書中可見他對蔣經國、殷海光、雷震、胡適、汪精衛等等,對照現今有些評論一刀兩斷的說法,余先生的言論提醒我們,至少對於知識人而言,如何關心時代之餘,也能夠以讀書知識作為判斷基準,而不是隨政黨、情緒、好惡臧否人物。就事論事,「人只要能做一件好事,就要承認他做了一件好事」(頁177)。
相較於追求學問的篤實平穩中又能盡其曲折,也必定反覆檢視正反兩方論點,以及建立在第一手史料的細心解讀;此外,余先生對於「人」的關懷與好惡,顯得更為可親、可近與容易理解。他最喜歡的金庸武俠小說是──《射鵰英雄傳》,覺得裡頭有幾個人的個性都寫得很好(頁188)。《射鵰英雄傳》是金庸較早期著作,小說人物性格鮮明,很能激起年輕讀者的共鳴,余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而且,余先生也相信「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頁214)。
余先生並沒有形塑自己的學術派別或立場,成果既出,有沒有價值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而是後人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所以,他與錢先生一樣,都沒有門戶之見、派別之分。然而,余先生有提倡任何東西嗎?答案是「知識人」名稱的使用。西方是用「intellectual」,但不應翻譯成「知識份子」(因為份子有壞的成份在其中);余先生也說這可能是受語言學家陳原談「分子」文章影響。余先生當然明白語言本是「約定俗成」,但是語言是有可能變質的,並且那是影響人類很深遠的東西。於是,2002年他正式提出來,並在之後著作的用語已經調整,「盡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份子」(頁226)。余先生始終關心知識人的心理變化,面對時局的精神層面如何表現出來;對於《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吳宓日記》的閱讀,都是由此觀點所做的研究延伸,也可以透過日記看人生百態,並不僅是學術議題而已。
讀書法中也很有「守愚」、不賣弄學問的味道──就如同愚人一樣,埋頭苦工,一部一部書去讀、不追求新奇炫麗、平穩紮實方是正道。
「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客觀研究過程中,自然也會發現或優或劣的種種面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中獲取許多人生智慧。余先生的書房名為「小書齋」,這是鄭板橋的字(另一個有名的「難得糊塗」也是出自鄭板橋,那是最有名的)。眾所周知,余先生的天資高又夠努力,在《胡適日記》記載中就有一則文字描述余英時父親余協中先生與胡適的談話,稱哈佛上上下下都稱讚余英時的聰明才智(雖然余先生認為,那是父親喜歡為自己兒子獻寶,不能算),胡適則是抱持較為嚴謹的態度回應。如今看來,似乎也是某種程度上,希望余協中傳達給余英時──這位優秀的年輕學者雖有「兔子的天才」,也必定要有「烏龜的努力」精神方能有成(頁247)。
之所以引用以上所說,可以明白余先生確是十分努力做學問的學者,胡適的話也應驗在余先生身上。不過,他沒有見過胡適(余先生也說他不大有想見名人的習慣),雖然早年受胡適思想影響很深。余先生在七十餘歲還完成《朱熹的歷史世界》、八十餘歲則有其思想史收官之作《究天人之際》問世;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專注與耐力,這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此,記得思想史家林毓生院士也曾提及余先生好像一開始學問就很好、就是很有學問的人;從余先生一生的學思歷程來看,這必須歸功於他的天資和不斷辛勤的努力。然而,更有趣的一點是:余先生似乎比較欣賞「守愚」的一面,也就是說:做人與做學問方面他似乎看起來偏向保守、帶有「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性格,但就如他引用古人所謂「智可及,愚不可及」所說,進一步說明「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讚美的話。西方經典《愚人頌》中就說,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愚鈍的人不是言詞便給,但是對人生有些很深的體驗」(頁240)。記得他也很推崇朱子談讀書的文字(見其〈怎樣讀中國書〉),讀書法中也很有「守愚」、不賣弄學問的味道──就如同愚人一樣,埋頭苦工,一部一部書去讀、不追求新奇炫麗、平穩紮實方是正道。我相信這也是余先生希望知識人具有的人格特質,也是所謂的「讀書種子」,更提醒我們「你千萬不要迷信什麼學者大師之類」(頁240)。
當然,在當代也有許多可佩服的人,古人也有許多值得佩服的,因為從歷史角度來看,古代的「士」(即現今的知識人)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或是為後代早已提供某種人生智慧與文化秩序;另一方面,真正對知識有熱情追求的人,自然又不拘泥守古,而能在傳統中擷長補短、與時俱進。
余先生的這部談話錄,是其晚年與李懷宇先生的談話與訪問,大致費時共十四年之久。余先生晚年時期接受訪談,對於「死亡」與「得失」之間也有他的體會;「儒家講死亡,就是面對它而視為平常,這是真的儒家精神」(頁240),用孔子的話來說,相關觀念則是「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想要在生前抓住某些東西,可能是物質上的,也可能是名譽上的。余先生雖然名滿天下,但謗亦隨之;但是他總是以平常心面對,也不太在乎旁人的毀謗,純粹做自己的學問,說該說的話。也可以說這就是順其自然、順其本性、順其對時局的觀察,並以自己專業史學的角度,提供種種學術上、文化上的意見。余先生曾寫過圍棋界林海峰「平常心」的故事,我覺得「平常心」與「寧靜致遠」似乎可以視為是他的人生格言。基本上,就是盡己之責,做好該做的事,並有對別人有益處;另外,則是不要怕寂寞,他在書中提到黃宗羲所說「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不但這是人之將老、也特別是讀書人最難克服的問題之一吧。
余先生的特別之處,不論在研究上或實踐上,都將「道」進行某種程度的「現代化」而為世人所知,成為豐富的思想資源。
知識人的學術際遇與精神世界
閱讀《余英時談話錄》有一種感受:余先生好像在種種偶然中決定他的際遇;1950年從大陸到香港、1955年到哈佛求學、寫《朱熹的歷史世界》等等都是偶然。凡是事先計畫的,後來總是不那麼照著他的心意發展;特別的是精彩之處多是偶然,卻是讓人津津樂道。換句話說,余先生的人生發展往往出於他的計劃之外,這也是很有趣的生命際遇。但在偶然中並不虛無,余先生強調的平常心,好好的讀書研究,當有機會來臨時,就能把平常累積的力量展現出來。
他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偶然,但平常就很留意朱子文集、語類及一切相關研究,早已瞭然於胸。也說錢先生已寫《朱子新學案》,本來是不想再碰這塊領域,但在機緣之下(為出版朱子著作寫序),引起相關議題迫使必須深入探索,在曲折爬梳政治文化史料的過程,終於將朱熹的歷史世界呈現出來。余先生謙虛說這是在錢先生《朱子新學案》屬於學術史的領域之外的補充研究。本不想再研究朱子的,但後來重新檢查朱子全集,補充錢先生來不及進一步從政治文化史背景進行研究的部分。一方面可見他對錢先生的佩服與尊重,另一方面不難明白余先生所做的是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以此作為他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
關於研究這件事,在余先生身上好像不那麼「按表操課」,不那麼「機械」,偶然中、無意中反而更有蘊味。而且研究時間拉得很長,無法速成的。學者的生活雖然平淡,但精神世界卻是相當有意思。
另外,余先生接受電視或電話訪問,都曾提及他接下來要研究的是唐代,特別是唐代的高僧與詩人,因為這是唐代精神世界最主要的兩類人物。雖然,余先生並未來得及完成,但從他對歷代知識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不難明白他的思想史或文化史取向,往往建立在無數可供分析的原始資料,並參考一流的學術著作,透過抽絲剝繭、盡可能鉅細靡遺將分析成果呈現出來。所以,雖然不知道余先生研究唐代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論,但是從他對其他朝代的歷史研究,早已給我們一幅關於中國歷史的思想圖像,特別是從思想史或文化史視野分析來看。唐代的精神世界最值得留意的人物,據余先生閱讀資料提出的暫時看法認為不是儒家、也不是學者,而是高僧與詩人。可見余先生研究歷史,或是瞭解知識人的精神世界,以客觀發生的事實為主,並沒有要把某種學派,例如他研究心力最多的儒家思想放在首位。能夠突破某種既定思維,讓歷史材料擴展我們對於古人精神世界的認知,也是很值得學習的治學態度。
余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理性」與「人文」是其中的關鍵詞;他對於中國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客觀研究,另一方面也帶有很深的「文化情懷」。印象中他對於「宗教」議題,至少在閒聊和談話訪問之際是不太說的,因為容易流於主觀之見。但是,他對於「天人之際」的思考,除了數十年的歷史研究可見端倪,更在其專著中「從醞釀到完稿,先後經歷了十二、三年之久」(頁292),也說「沒有信仰,這個民族就不會有文化」(頁310)。
然而,這似乎在目前的人文學科研究中較不容易看到的,也可以稱此為一種領悟,用余先生的話來說就是「精神世界」,也就是先秦諸子所謂的「道」。我認為余先生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從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視野考察中國歷代的知識人精神世界,如何面對變局,「道」始終都在知識人心中發揮一定的作用。而余先生的特別之處,不論在研究上或實踐上,都將「道」進行某種程度的「現代化」而為世人所知,成為豐富的思想資源。正如他所說的「現代化」就是「把已經有的價值用現代的語言和方式跟其他文化中的東西聯合起來,講成同樣的東西,不覺得生硬和冒昧」(頁315)。讀完《余英時談話錄》之際,亦正有此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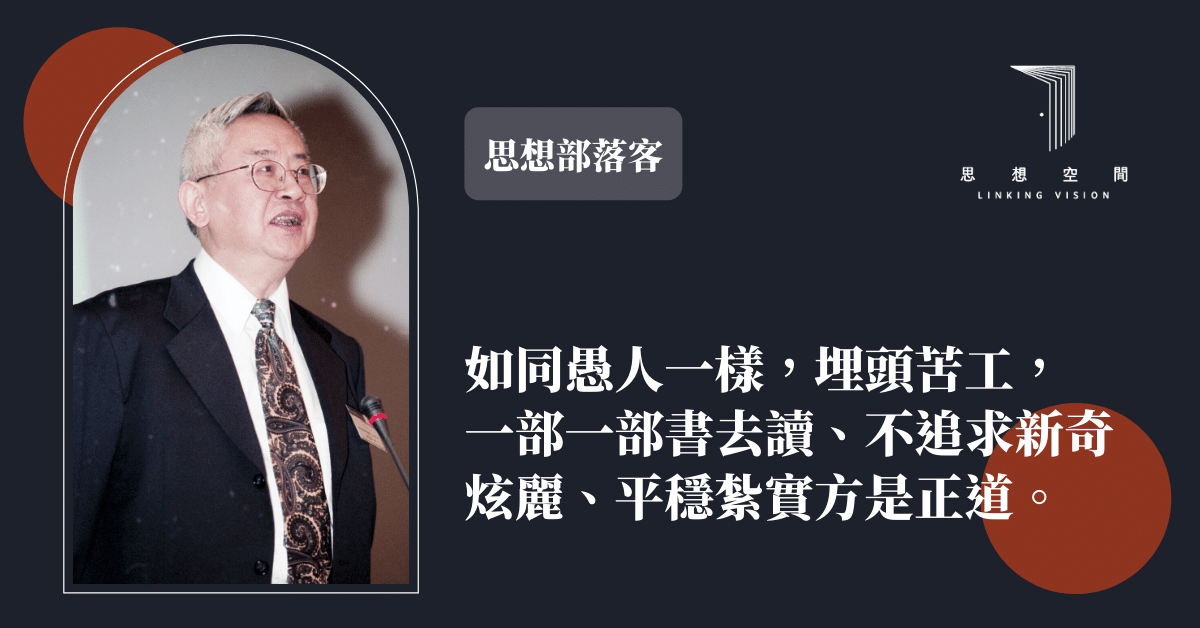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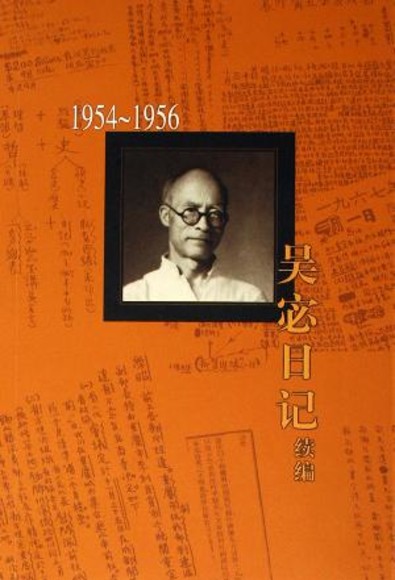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