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工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系博士候選人。論文研究範圍包括當代文學,批判理論與殘障研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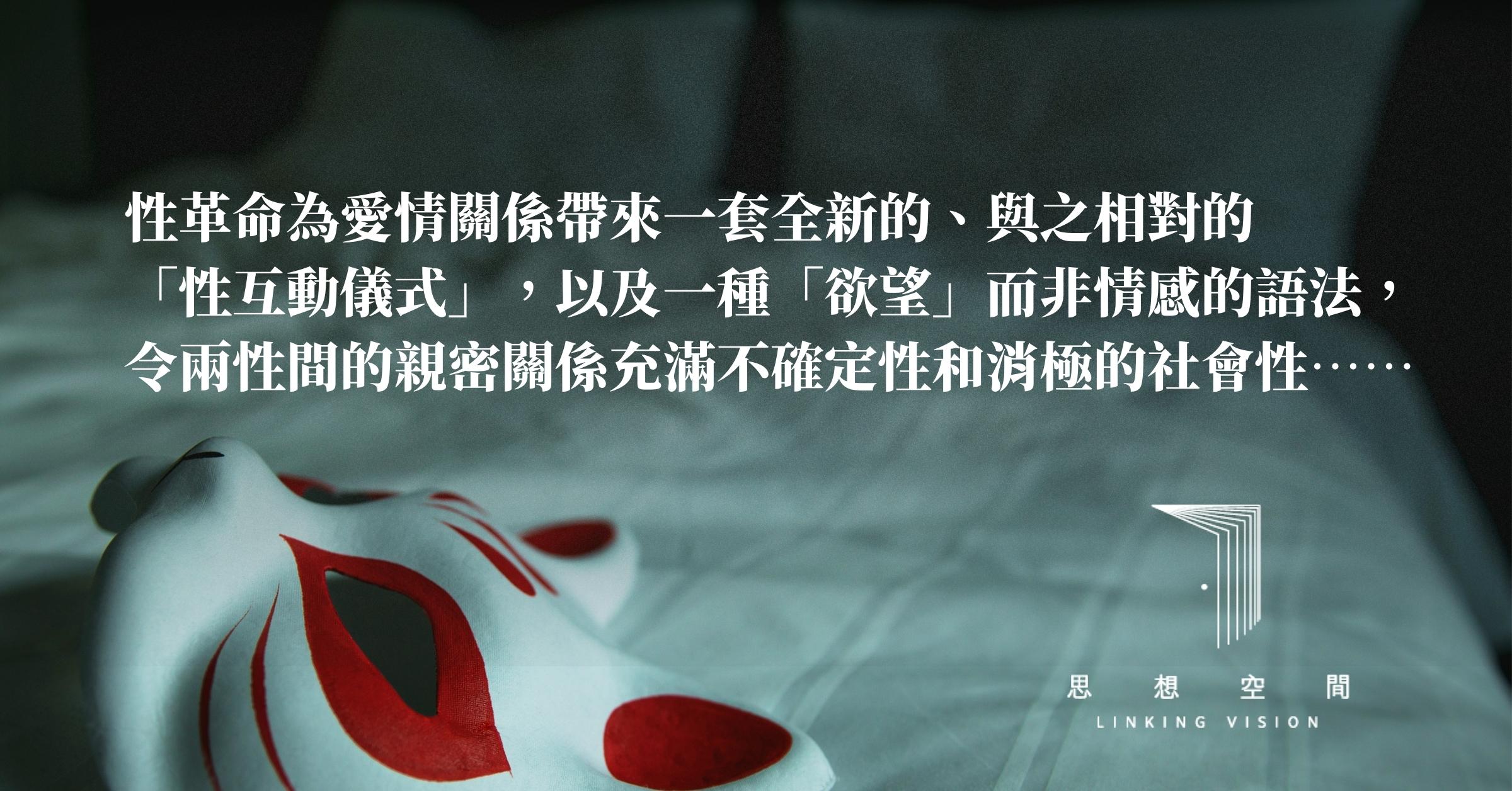
文/盧勁馳(文學工作者)
我想在這樣的前題下,閱讀依娃以樂斯(Eva Illouz,又譯:伊娃 ‧ 易洛斯)的《為什麼不愛了——更多自由卻更少承諾,社會學家的消極關係報告》時,就可能以為,書中所舉的例子,那些用以描述一種普遍的隨便性愛關係的繁多案例,以及那些似乎在不斷重複、強調關係不確定性的論點,不但毫不新穎,而且不必,也似乎不無勉強地,用上太多學術性的修辭,來描述一套關於為什麼不愛的陳腔濫調。尤其當讀者對於社會、女性主義、或酷兒政治全然不感興趣的話,要花時間看這本書,倒不如從圖書館裡翻回那些《男女大不同》一類的通俗讀物,還來得省時和有趣。
然而,我似乎不得不在這個艱鉅的論文寫作過程裡翻到這一本書,就是從一開始,我就對本書那個「為什麼愛與不愛」,或書中那些關於隨便性愛的現象描述,完全不感興趣。而反覆讀了這本書的中英文版數次,對照過不少理論與摘錄過幾篇筆記後,我才感恩於它用上這些似乎極為庸常的案例,以及如此清晰分明的策略,正如何寬容地,為我們提供一套極具前瞻性的、探索情感關係連結的社會學視野。
在華語世界,興起了幾近二十多年的性別研究裡,社交愉悅,從來都是理解身份、性向認同、以至社會存在不可忽略的一個核心關鍵詞。
「消極關係」:輕盈深處的理論框架
這本著作為何令我如此震撼?其所涉及的思想背景,在此我亦不想詳明。我只想簡單地指出,全書最令人刮目相看,似乎是唯一、亦最令人深奧難懂的一個概念,就是書名副題用上的,這個「消極關係」。
消極關係這概念,聽來有點輕盈,但當我留意到,書中在討論消極關係時,與之對話的、關於社交愉悅(Sociality)的理論辯論,才突顯出全書最大的看點。因為在華語世界,興起了幾近二十多年的性別研究裡,社交愉悅,從來都是理解身份、性向認同、以至社會存在不可忽略的一個核心關鍵詞。但在進入作者那個幾乎沒有任何外行人可以全然消化的社會學理論討論以前,我覺得還是必須介紹一下全書在探討「隨便性愛」背後,所設下的一個非常精細的理論框架。
相對於書中大量關於「隨便性愛」的討論,我認為在書的前半部份,似乎極為概略地總結的、用以理解傳統婚前求愛歷程,被稱為結構化儀式的傳統婚前求愛模式之中,內藏著一套社會「紐帶」的語法。她(依娃以樂斯)認為婚前求愛之所以是一套儀式化的情感互動模式,是由於它會依據戀人雙方通常熟知的、各種關於言語表達、互動與交換的規則,來建立一系列的社會連結點,並帶來了對於未來的確定性理解,令兩個人的關係不存在任何疑慮。為說明這種具備確定性的紐帶如何形成,她分別從道德規範、本體、評價、程序、情感等幾項人際互動的屬性,來解釋求愛過程中的種種行為,如何成為一套情感的互動模式,從而因應對規範的認知、社會訊息、身份地位、社交規則、落實情感表達的能力等要素,來剖析其中存在的確定性因素。
這種物化的媒體現象,同時能為女性主體提供愉悅、賦權並肯認其感受,因它能使更多女性的身體獲得賦權的感覺。只不過這種賦權的經驗,亦會使女性對自己的價值產生不確定感。
「隨便性愛」,欲望與情感的全新語法
只有全面地認識到這些確立互動關係確定性的關鍵因素,我們才可理解——為何性革命為愛情關係帶來一套全新的、與之相對的「性互動儀式」,以及一種「欲望」而非情感的語法,令兩性間的親密關係充滿不確定性和消極的社會性,讓戀人經常頻繁投入又退出關係。我固然無法複述一次,她如何認為交友程式所衍生的隨便性愛文化,可以完整地體現得到這種性互動儀式裡的種種細節。我反倒想借她在討論視覺資本主義時,援引到女權主義批判理論,有關女性如何被媒體性物化的討論,探討一下這種相對於傳統婚前求愛的消極社會關係,是如何把一種傳統的求愛社會紐帶語法、轉變成一套性欲的語法。並且我想指出,這種完全是承繼著那些後結構女性主義文化理論的分析思路,為何在一種社會學視野的鑑照之下,成為了一套更完備的身份政治分析框架。

以樂斯先指出,在視覺資本主義裡,女性的身體固然被各種廣告、流行媒體所物化,那當然是一種老掉牙的媒界批判觀點。然而她更指出,這個物化的過程,是同時建基於市場對物理身體的估值和評價。當女權主義者過去一直關注媒體的物化現象如何以性化手段,單純肯定性感的人,而剝奪不夠性感的人的機會,以樂斯透過對比求愛社會紐帶和性欲兩套語法,指出了另一個事實:這種物化的媒體現象,同時能為女性主體提供愉悅、賦權並肯認其感受,因它能使更多女性的身體獲得賦權的感覺。只不過這種賦權的經驗,亦會使女性對自己的價值產生不確定感。
為何同一個物化現象,能為女性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體驗呢?因為在以樂斯那不無繁複的分析裡,她發現到不管女性是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實際的經濟利益,那些社會的評價和對性的貶值,帶給女性最大的影響,並不如那些女權主義者所想像般,涉及女權的政治表達和實踐。只要我們把這個性貶值的問題放回愛情,或她所謂社會互動儀式的角度考慮,性物化這個問題不過是對人的自我及其價值,產生了一種本體論上深深的不確定性。其中,自我被兩組東西弄得四分五裂,一邊是身體及其器官與用於產生自我的消費物品,另一邊是產生性互動的消費活動與消費情境。兩者結合起來,對女性的最大損害,就是失去了過去婚前求愛儀式裡,一度擁有的從屬、卻又穩定的關係。
當作者自己似乎都意識到,她把傳統求愛儀式與性解放作為對比,不過是一套簡化的策略,其中沒有掌握那些今日社會裡與傳統慣習依舊相似的行為範圍,亦忽略了過去一直留存至今的東西。
探索身份政治的全新視野
這似乎是一種典型的文化研究學者,思考現代社會中那些穩固的社會關係時,點出它如何受科技、價值觀等衝擊所引發的解構式思路。但由於這裡強調著愛情語法的社會演化,而不是後結構主義者所推崇的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我倒在其中看出,這套綜合了社會學與情感話語分析的方法,並不單純用以描述從婚前求愛、到隨便性愛背後社會演化的過程中,兩性之間存在著的不平等關係;當作者自己似乎都意識到,她把傳統求愛儀式與性解放作為對比,不過是一套簡化的策略,其中沒有掌握那些今日社會裡與傳統慣習依舊相似的行為範圍,亦忽略了過去一直留存至今的東西。這留給我們更大的思考空間。
在這種傳統紐帶和消極關係相互重疊的地帶,還有不少涉及權力關係的——如種族、健殘、或社經地位的領域,將如何與這種兩性權力關係相互交織,我們自能就現代愛情,提出更多層次的社會學分析。譬如,若不單是指女性的物化,而是殘疾女性的話,面對著慈善產業,以一種勵志宣傳的方式,去爭取市場的估值與評價時,它所面對的不確定性,他的充權空間,又將對應著哪些視覺文化、醫療復康產業,才得以構築起一種類似的消極社會互動關係呢?這都是社會學的嚴密框架,給予我們繼續探索身份政治的全新視野。
(* 本文原題為〈當愛情成了一種社會關係——讀依娃以樂斯《為甚麼不愛了——更多自由卻更少承諾,社會學家的消極關係報告》〉,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延伸閱讀:
李明翰:歡迎進入消極關係
李尚文:苦澀的愛情社會學——我們是自由的,可為何還是「愛無能」?
專題:【再見愛情】
| 閱讀推薦 |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