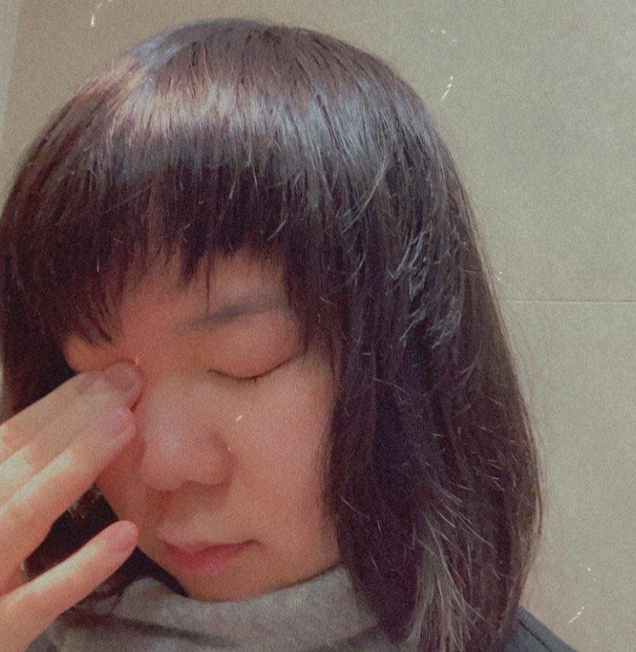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拙作散見於《聲韻詩刊》、《大頭菜文藝月刊》、《城市文藝》、《工人文藝》、《小說與詩》、「虛詞」、「好燙詩刊podcast」、「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等。校內乒乓球隊隊員,愛貓貓,愛看海。

記錄/劉子萱
編按:粵語流行曲是香港音樂工業多年來的主要動力,但有關其起源的問題卻眾說紛紜。2022年8月26日至27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研究課程」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從跨學科角度探索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演化,重新思考其意涵內藴,並嘗試就香港流行文化研究提出新視點。其中一場由廖志強、黃念欣、呂永佳,分別從80、90至10年後的香港流行曲談起,探討每個年代的流行音樂特性、時代影響與轉變過程。(* 本文獲主辦方授權撰寫,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 講者簡介 |
廖志強,文學碩士及傳理學哲學碩士;現任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報刊特約撰稿/編輯、演藝評論家協會董事、藝術發展局審批員。曾任電視/電影編劇及副導演、中學教師、研究助理、報刊編輯、藝術節目策劃等。著作包括《一個時代的光輝──中聯電影作品評論及資料集》、《光影中的香港》、《同窗光影──香港電影論文集》等。
黃念欣,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及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香港文學、文學理論、研究方法、女性文學、粵語正音等。她課餘曾擔任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及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並於報章撰寫專欄,積極推廣語文常識、閱讀與文化。
呂永佳,生於香港。香港詩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著有詩集《無風帶》、《而我們行走》、《我是象你是鯨魚》;散文集《午後公園》、《天橋上看風景》。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城市文學獎、李聖華詩獎等。曾任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城市文學獎評判。作品曾被翻譯為英文、韓文、日文等。
三位報告人不約而同以「世」定題,分別按時序梳理。先從廖志強80年代的「盛世」,再到黃念欣90年代的「末世」,最後是呂永佳10年代的「轉世」,共同勾勒出80年代至今,在數量龐大的廣東歌背後所呈現的紛繁面貌。
廖志強也舉出當時的創作人如顧嘉煇、黎小田、黃霑、林子祥、許冠傑,結合他們的學養背景,指出他們能結合中西樂創作流行曲。
廖志強:古今中外混雜(Hybridity)而成的80年代
廖志強提出粵語流行曲是傳統與現代,東西方匯集而成的混雜(Hybridity)。由於該時期的流行曲數量龐大,故選取「有代表」的作品和音樂人,從文本、風格及創作背景論證「混雜」的多元是匯成「盛世」的條件。又參考兩大頒獎禮: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與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強調頒獎禮的歌曲不一定最好,所謂「有代表」,只是資料選取上的方法。
他先歸納80年代粵語流行曲所具有的傳統要素。其一,深受粵曲與小調的影響;其二,受到3、40年代上海國語流行曲的影響。同時,西洋流行曲在香港的影響,體現出由傳統到現代,東西方之間的混雜。故當時的樂曲多以中樂輔以西樂。在歌詞方面,則呈現出「文言味重」的特點。廖志強也舉出當時的創作人如顧嘉煇、黎小田、黃霑、林子祥、許冠傑,結合他們的學養背景,指出他們能結合中西樂創作流行曲。也看出當時創作人接受所有新衝擊與新思考,不考慮任何限制。
再從編曲與翻唱上看出「混雜」。如顧嘉煇作曲編曲的〈倆忘煙水裡〉,「編曲中運用了風鈴、琵琶、單簧管、電吉他、低音電吉他、弦樂器及鋼琴等中心樂器」。如陳百強的〈今宵多珍重〉,改編南來音樂人的作品,填上粵語歌詞。最特別的是林子祥〈每一個晚上〉,由英語音樂劇〈Cats: Growltiger’s Last Stand〉和中國音樂家黃自為白居易雜言詩 / 詞譜曲的〈花非花〉結合而成。再者,在奠定粵語為本土文化前,粵語流行曲認受程度不高。廖志強以「互動接受認同」來歸納了香港人與粵語流行曲之間的關係。
粵語流行曲受歐美英文流行曲、跳舞音樂、台灣國語流行曲,及日韓流行曲等「混雜」的影響,才成就80年代粵語流行曲的「盛世」。包括改編英文歌曲融會成粵詞西曲風格;改編日本流行曲融會成粵詞日式的風格,也邀請日本音樂人參與作曲與編曲。他指出這種改編對香港本土創作造成了不健康的影響,但也為創作人帶來衝擊,在汲取外來音樂元素後創作出自己的風格。廖志強在總結中提出:混雜性的「無限制」,是帶來了養分上的提升。
黃耀明〈天國近了(你們應當遊戲)〉、達明一派《萬歲!萬歲!萬萬歲!》中的〈春光乍洩〉等,可以明顯體會到「意亂情迷極易流逝」的末世感情。
黃念欣:在末世認真嬉戲的90年代
在黃念欣看來,90年代是非常認真的時代。她先用19世紀的世紀末和20世紀的世紀末做比較,總結出「末世」的特征:cultural crisis和fragmentation。黃念欣所選取的歌曲來自1990-1999四大頒獎禮,同時關注唱片封套與歌者形象,而重點研究對象是歌詞。由此,她也指出了有趣的現象——朗讀90年代的歌詞時,很容易變成唱出來。黃念欣認為這是90年代流行曲獨有的,一來是耳熟能詳,二來這或許是歌詞發展趨向口語化的分水嶺。
回看90年代以前,黃念欣指出此時的香港流行音樂已進入突破與嘗試的階段,也是重新洗牌開始的時候。諸如〈傳說〉(1987)、〈下雨天〉(1989)、〈你知我知〉(1989)及〈風再起時〉(1989)等歌曲,都是這一階段的例證。
而進入90年代之後,則是男性偶像愛情主題的回歸。黃念欣在此以張學友〈真情流露〉、劉德華〈愛不完〉、郭富城〈對你愛不完〉、黎明〈夏日傾情〉為例,對這一現象進行表述。儘管該時期的頒獎禮上,常常呈現出「陽盛陰衰」的面貌,然而黃念欣卻認為同期女歌手的作品是「相當成熟,令人驚喜」。以林憶蓮《野花》中的〈花之色〉為例,黃念欣指出了這首歌中的城市觸感,女歌手音色上的空靈宛如末世之音,道出女性在愛情主題下的徘徊與反省。而在《’EX’ All Time Favourites》中的〈忘記他〉,則說明翻唱在致敬之外,也傳達出了末世的靡靡之音。
在90年代的香港本土性以外,黃念欣還指出了一些中國元素,包括王菲的〈南海姑娘〉、〈分裂〉、〈不安〉、〈野三坡〉,同時又有黎明的〈我來自北京〉(1992)等。到了90年代後期,就是「天國近了」——從黃耀明〈天國近了(你們應當遊戲)〉、達明一派《萬歲!萬歲!萬萬歲!》中的〈春光乍洩〉等,可以明顯體會到「意亂情迷極易流逝」的末世感情。因此,黃念欣也總結道:看著千禧年代,90年代是相當認真的年代。


呂永佳總結了這十年間香港流行音樂展現出新的「混雜」,關鍵不在於能不能寫,而是在於怎樣寫——怎樣在邊界內外書寫,以呈現獨特的風景。
呂永佳:在限制中書寫吶喊的10年代
呂永佳指出「轉世」是以新方式將內裡不敢講的東西重現;以魯迅「鐵屋」的隱喻為框架,他反思了10年代流行曲與香港社會的關係,發現這十年間出現了很多「二元對立」。
10年代以來,香港社會急速變動,此時歌曲頒獎禮已不完全具代表性,故呂永佳開始關注網路上的流行歌排行榜。他以〈年少無知〉為例,認為此曲是三場社運前的先聲,新舊價值的對立,反映出那一代年青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控訴。此外,呂永佳又以陳奕迅的〈陀飛輪〉為例,指出理想與物質的二元對立——10年代相較於80年代,社會流動性不強,在理想與名利的對抗上更強烈。〈六月飛霜〉更是超遠基層市民與有錢人的二元想像。這時期的流行歌,可以看出年青人珍視個性,抗拒上一代的成功格言。就像謝安琪〈獨家村〉對社會主流價值的抗衡,但這種抗衡是無力與感傷。
而在社會運動間,又出現不少與社會現況相照應的歌曲,Rubber Band〈發現號〉便是其一——這首歌中隱含了與社會歷史事件的對照。不過呂永佳直言,從文學角度看,這類流行曲是過於單一和口號式;但是能夠召喚群體,也是流行曲特有的功能。
10年代的一個重要的母題是「去與留」,又能與8、90年代的移民潮作對比。〈鐵塔凌雲〉、〈同舟共濟〉、〈千千闕歌〉等歌曲,均呈現出對「母地」的眷戀;〈今生不回家〉所呈現的是決斷,同時是對傳統倫理關係的挑戰。而在抒情方面,麥浚龍的〈我在切爾諾貝爾等你〉是較為深刻的,他以情歌的方式,抒發對現世社會的不滿,兼及「去與留」的母題,由是社會的符碼亦隨之依附於整首歌曲。
這就是10年代的「轉世」——依舊使用情歌的寫法,同時隱含社會的意義。在報告中,呂永佳提出「限制書寫」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課題;「限制書寫」除了是創作人的符咒,同時也是養份。以現代文學的研究為例,呂永佳指出「限制書寫」孕育出不同面貌的文學作品,包括如何面對傷痕、與傷痕前後的感悟。
在報告的最後,呂永佳總結了這十年間香港流行音樂展現出新的「混雜」,關鍵不在於能不能寫,而是在於怎樣寫——怎樣在邊界內外書寫,以呈現獨特的風景。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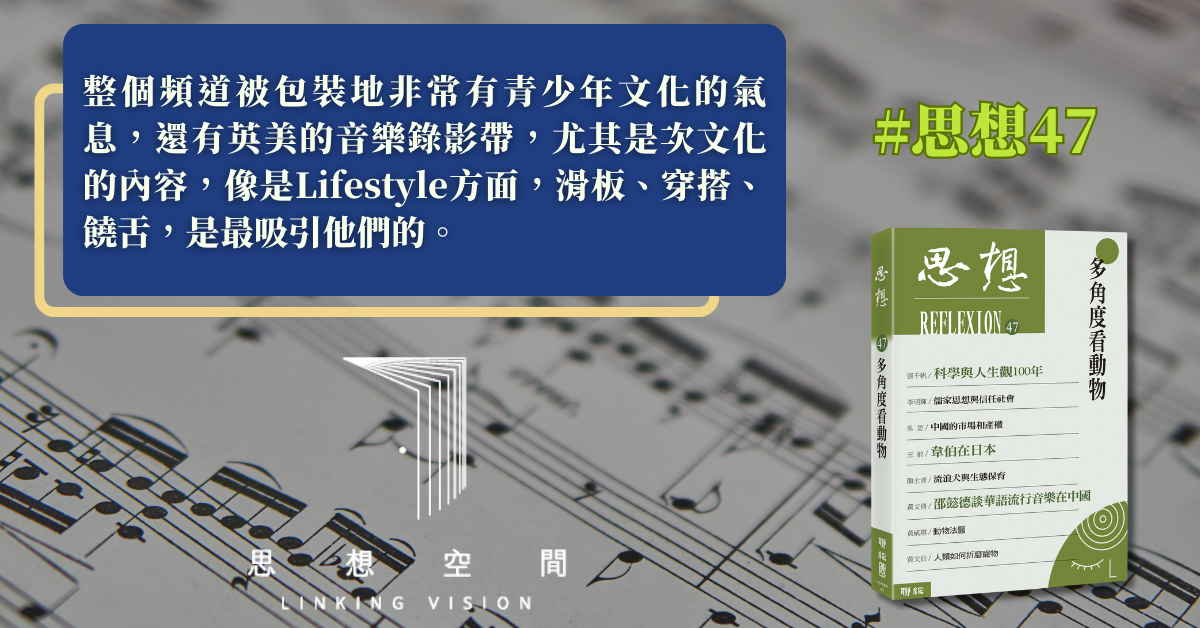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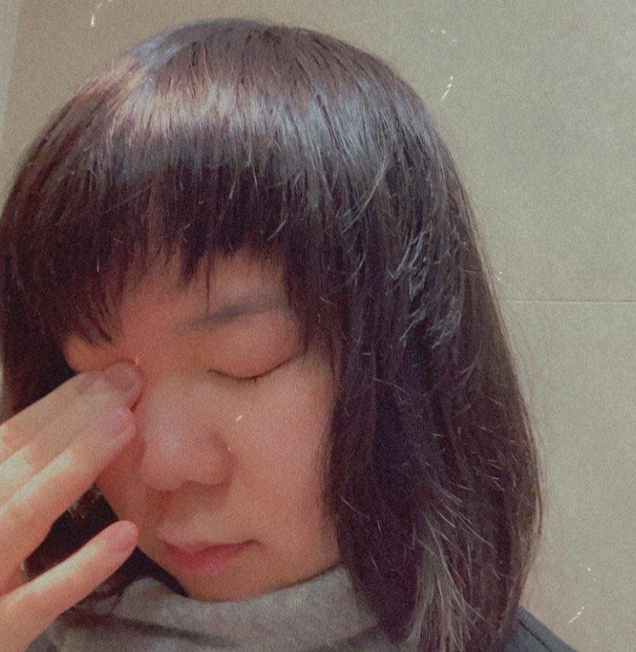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拙作散見於《聲韻詩刊》、《大頭菜文藝月刊》、《城市文藝》、《工人文藝》、《小說與詩》、「虛詞」、「好燙詩刊podcast」、「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等。校內乒乓球隊隊員,愛貓貓,愛看海。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