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永祥(學者、《思想》總編輯)
作者按:奧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竟然有中譯本在台灣出版了!回想起多年前我針對此書寫過書介。當年初生的嬰兒如今已是壯年,當年10歲的小學生現在可能已是成熟的學者。時光流逝,不知舊文還有多少可讀的價值。勉強貼出舊文,感謝此書譯者和出版者,祝賀這個中譯本問世。(補充:這篇舊文對新生世代有沒有意義,跟文章的好壞關係不大,而是完全繫於他們是否關心奧威爾這本書裡所論述的問題與觀點吧。)
(* 本文原刊於作者臉書專頁,思想空間經授權轉載)
你的名字和你的事跡
在你的骨骸乾枯前已被遺忘,
你被謊言屠殺
那謊言已埋在更大的謊言之下;
但我在你臉上所看見的
沒有力量可以自我心中奪走;
沒有炸彈的爆炸
能震碎你那水晶般的精神。
—— 喬治 · 奧威爾(1943)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佛朗哥將軍率領軍隊發動政變,企圖推翻合法的共和政府,恢復王室、教會及舊封建勢力的統治。共和政府措手不及,只有工會所組織的民兵團,對佛朗哥的法西斯武力展開激烈的抵抗,延續兩年半的西班牙內戰就此爆發。
就戰事本身的規模和影響而言,這場內戰自然不能和先後兩次世界大戰相提併論。不過,在意識型態的層次上,西班牙內戰是本世紀左右兩個陣營在歐洲最慘烈的一場鬥爭。介入這場內戰的力量,包括了已在德國及義大利取得政權的法西斯主義,正在世界經濟大蕭條中掙扎的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政黨,在斯大林支配下的共產國際,以及必須同時抵抗法西斯和斯大林的左派反對派。這些力量之間奇特的勾結和敵對關係,決定了西班牙內戰的發展途徑與結局。西班牙內戰雖然基本上屬於西班牙歷史,雖然內戰直接、間接殺死的六十萬人是西班牙人民,但是所反映的衝突與鬥爭,卻具有強烈的國際性格和意識型態的色彩。
在西班牙內戰中有大批外國知識分子介入,適足以表現內戰的這種背景和性格。許多文人、藝術家或者志願遠赴西班牙參戰,或者在本國以文字與作品表達自己對內戰雙方的立場,名單開列出來堪稱琳琅滿目。這個現象,構成了西班牙內戰一個突出的特色,竟致有人稱之為「詩人的戰爭」。當然,意識型態的政治,難免對介人的知識分子施加最嚴厲的考驗,西班牙內戰也不例外。它摧毀的固然是西班牙工人階級的肉體,敗壞的卻往往是歐洲知識分子的靈魂。只有少數人渡過這場考驗,冶煉出「水晶般的精神」(the crystal spirit)。這中間以喬治 · 奧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1903-1950)最突出;他的經驗,頗值得我們玩味。
要了解奧威爾的西班牙經驗,我們需要先略述當時歐洲左派知識份子的處境。
一夕之間,昨日毫無原則地吹捧蘇聯的粉紅色知識份子,今日又毫無原則地泣訴自己的幻滅。他們演出的這齣鬧劇,和奧威爾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犧牲和成長,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九三〇年代的知識份子,面臨的處境相當艱難。他們眼前的最大威脅。是日益壯大猖獗的納粹及法西斯勢力。但是他們能站在什麼立場上反抗法西斯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悸猶在;這場戰爭的帝國主義爭霸性格,讓人無法再度以護衛傳統西歐政治體制為名作戰。世界性的經濟恐慌,嚴重的失業率,顯示資本主義已瀕臨危難,因此傳統的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也同樣無法作為足以和法西斯抗衡的另一條路。保守派、自由派、社會民主派,若非附從法西斯的邪焰,就是對滔天的亂局一籌莫展。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知識份子轉而把希望寄托在蘇聯。畢竟,只有蘇共一貫地指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帝國主義戰爭,只有蘇聯正受到資本主義列強及法西斯勢力的圍堵和威脅,也只有蘇聯的新生制度,象徵著歐洲社會的一條出路。許多歐洲知識份子變成了蘇聯的「同路人」,三十年代也就變成了「粉紅色的年代」。
在事實上,當時的蘇聯,已經喪失了老布爾什維克的國際主義與革命要求。在蘇聯境內,斯大林獨攬權力,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行恐怖統治,積極剷除左翼和右翼的反對力量。在歐洲,隨著德國、匈牙利、義大利、英國工人階級運動一連串的挫敗,以及納粹的威脅,國際共產主義已從國際革命的先鋒,淪為維護蘇聯一國利益的工具。驚弓之鳥般的斯大林,非但不敢再在資本主義國家鼓動革命,反而以「一國社會主義」、「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為口實,積極和西方資產階級結盟,向英法等國求歡,目的只是要照顧蘇聯一國一黨的安全和利益。不過,這個政策並沒有贏得資本主義國家反法西斯的決心,也沒有遏制納粹勢力的擴張。它只是犧牲了歐洲工人階級的利益,癱瘓了他們的鬥志和組織力量。
在莫斯科的操縱之下,共產國際在一九三五年的第七次大會中,決議採取「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作為反抗法西斯的鬥爭策略。所謂「人民陣線」,就是放棄工人階級社會革命的激進路線,改為和資產階級及社會民主黨共同採取階級合作的戰略。緣於蘇聯的革命聲望以及反抗法西斯的客觀需要,開始時,人民陣線確實為民主派與激進派提供了團結的機會。但是很快地,人民陣線的內部矛盾開始爆發: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各方面,資產階級和工人群眾有著本質上不同的要求。西班牙的革命局面裡,這種矛盾愈演愈烈,終於發展成左派陣營內部的鬥爭。在斯大林的導引之下,鬥爭進一步變成了蘇聯國內政爭在國際上的延續,鬥爭手段也無所不用其極。任何人,只要對斯大林的恐怖統治表示批評,對蘇共或國際的領導表示懷疑,或是堅持無產階級的激進革命路線,都被指為「托洛茨基派」、「在客觀上協助法西斯」,成為暴力或文字打擊的對象。
三十年代向蘇聯靠攏的西方知識份子,很少有人看出斯大林主義的反動本質。在反法西斯的熱情鼓舞之下,他們盲目地歌頌斯大林的統治,粉飾蘇聯國內大整肅的暴行,義正詞嚴地誣蔑不接受斯大林路線的獨立左派。到了莫斯科大審的真相逐漸浮現,德蘇協定公佈,左派反對派被捕殺殆盡,許多人才逐漸憬悟。一夕之間,昨日毫無原則地吹捧蘇聯的粉紅色知識份子,今日又毫無原則地泣訴自己的幻滅。他們演出的這齣鬧劇,和奧威爾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犧牲和成長,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前線戍守四個月,他沒有真正作戰的機會,每天只是窮於應付寒冷、飢餓、睏倦、以及無事可幹的無聊。在這段期間,西班牙左派陣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他幾乎全無所知。
在西班牙內戰中,人民陣線的策略,第一次走上戰場和法西斯交鋒。這場實驗的結果是西班牙民主派及左派的失敗,法西斯的勝利,以及人民陣線口號的破產。奧威爾親身經歷這一過程,在他的名著《向卡塔隆尼亞致敬》 中,嚴厲控訴斯大林與其同路人背叛西班牙工人階級。透過他的西班牙經驗,他沒有走上變節或幻滅的末路,反而發展出堅定的「革命社會主義」(這是奧威爾所用的字眼)信念。
據奧威爾自已的敘述,他之所以赴西班牙參戰,並不是因為他有強烈的社會主義信仰,或志在追求任何意識型態的聖杯:
在我初抵西班牙及其後相當一段時期裡,對於西班牙的政治局勢,我不僅是沒有興趣,甚至根本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我知道有一場戰爭正在進行,但並不清楚是什麼樣的戰爭。當時你若是問我為什麼加入民兵團,我的答覆會是:「和法西斯戰鬥」。你若是再問我戰鬥是為了(追求)什麼,我會答說:「為了基本的作人道理(common decency)。」(HC,p.46)
把「common decency」譯作「基本的作人道理」,或許讀者會側目。但這個譯法至少有一個優點:它彰顯了奧威爾政治動機的樸素與實在。事實會證明,只有這種樸素與實在的動機,才是革命者可以憑藉的道德資源。
奧威爾的「政治教育」,開始得非常偶然。當時大部份前來參戰的英國人,都會經過英共的安排,加入屬於共產國際系統的國際旅(International Brigade)。可是英共拒絕對奧威爾提供協助,他只好透過英國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中友人的介紹,在巴塞隆納加入聯合馬克思主義工人黨(Partido Obrere de Unificacion Marxista,以下簡寫為POUM)。這是一個屬於激進左派的組織,在意識型態上攙雜有無政府主義及托派的成份。它的領袖寧(Andres Nin, -1937)一度曾經擔任過托洛茨基的秘書,後來在POUM被鎮壓時,死在俄國人手上。
據奧威爾說,巴塞隆納是他第一次見到的「由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城市」,而POUM則是「整個西歐」政治意識最強、最具革命性的工人團體。他生活在一個「革命的氣氛」中:
將軍和小兵、農人和民兵,都以平等相待;大家領同樣的薪餉、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互相都以「你」和「同志」相稱呼;沒有老闆階級、沒有下人階級、沒有乞丐、沒有娼妓、沒有律師、沒有教士、沒有奴顏諂媚、沒有畏葸求恩。我呼吸的是平等的空氣……。(HC,p.66)
奧威爾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抵達巴塞隆納的。在前線戍守四個月,他沒有真正作戰的機會,每天只是窮於應付寒冷、飢餓、睏倦、以及無事可幹的無聊。在這段期間,西班牙左派陣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他幾乎全無所知。
他懷疑斯大林有誠意維護西班牙工人階級的利益,他痛恨自由派及共產黨同路人用謊言誣蔑POUM,他更看出了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打擊異己時手段的殘忍和卑鄙。
一九三六年底到三七年初,在卡塔隆尼亞省的人民陣線已經發生嚴重的內部矛盾。三七年五月三日,共和政府、共產黨、社會黨的聯合武力,開始攻擊POUM以及屬於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工會CNT。左派在巴塞隆納的這場巷戰雖然很快就結束,但資產階級和共產黨已決心要消滅POUM。
五月事件發生之前,奧威爾已回到巴塞隆納。原先他有意離開POUM,參加國際旅,以便調到比較有戰況的地方去。經過五月事件,他完全放棄了這個念頭。他和POUM在一起的四個月生活,讓他有機會呼吸到以「平等」為基素的「革命氣氛」。在他的心目中,這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內容。但是現在他已知道,這種「社會主義」,和斯大林派的社會主義有截然的差異。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將一切社會生活納入一元的官僚機器支配的統治方式,而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著重點卻是個人的平等和自由。奧威爾似乎缺乏理論思考的興趣和能力,因此他沒有用概念來舖陳自己的觀點。他只是平實地透過內戰中一些深刻的經驗,尋找自己的路。POUM是他的正面範例,斯大林派在巴塞隆納的行徑,則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
在《向卡塔隆尼亞致敬》中,奧威爾對西班牙內戰的性質提出了他的看法:這不單純是一場內戰,同時還是一場革命的開始。這個陳述,其實正是當時左派辯論的核心問題。
共產黨及一般左傾知識份子支持內戰論:在內戰中,西班牙共和政府和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聯合抵抗法西斯,護衛西班牙的資產階級民主制。POUM則持革命論:工人階級在戰爭中抵抗法西斯的同時,還要建立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權和武力,改變原有的社會制度和階級關係。
奧威爾起初接受的是共產黨的說法,但逐漸地,他開始接近POUM的立場。他的轉變,不涉及理論層次的反省或社會學的分析,而是起於經驗和觀察。他不信共產黨的策略對反佛朗哥的戰事有利,他懷疑斯大林有誠意維護西班牙工人階級的利益,他痛恨自由派及共產黨同路人用謊言誣蔑POUM,他更看出了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打擊異己時手段的殘忍和卑鄙。
不過,對他產生最大衝擊的,可能是他在四月底從前線返回巴塞隆納時目睹的改變。當初在POUM及CNT控制下的巴塞隆納,是一個革命而平等的城市。到了他重返巴塞隆納時,「革命的氣氛已經消失了」,「社會中正常的貧富、上下階級區分,已經又出現」。「在漂亮的餐廳和旅館裡,擠滿了有錢人狼吞昂貴的大餐,對工人階級而言,工資雖然沒有增加,食物的價格卻巨幅飛漲」。政府及共產黨正在努力把巴塞隆納變成一個「正常」的城市,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的,自然是工人階級。
這個怵目的經驗,替奧威爾解決了應該選擇共產黨人民陣線策略抑是POUM革命路線的問題。他所關心的不是理論分析,不是意識型態,而是對工人階級的認同。當五月三日政府及共黨所支持的官方武力對POUM以及CNT發動攻擊時,
問題對我已經很清楚。一邊是工會,另一邊是警察。對於布爾喬亞的共產黨人心中所想的理想化的「工人」,我沒有什麼特別好感,不過一旦看到真實而有血有肉的工人和他的天敵──警察──發生衝突,我不需要再問自己要站在哪一邊。(HC,p.119)
奧威爾很自然地與POUM併肩作戰。
據他的一九四六年自述,從西班牙內戰之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取向」。這種取向,是如何從他道德領域中的信念衍生出來的呢?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POUM遭宣佈為非法組織,共產黨控制的秘密警察四出搜捕POUM份子。當時奧威爾不在巴塞隆納(因為五月二十日他在前線負傷,這時正申請退伍)。到了六月二十日他返回巴塞隆納時,警察正在找他。他躲藏了幾天,終於平安離開西班牙,六月底回到英國。
離開西班牙的前夕,奧威爾在寫給友人的信說:「我已見到了了不起的事情。我終於真正信仰社會主義了;在以前,我從不曾真正相信過」。在《向卡塔隆尼亞致敬》中,奧威爾再三申述民兵團中「平等」的經驗,如何鞏固了他的「社會主義」傾向。他有一段話,值得我們長篇引錄:
幾乎是靠偶然的機緣,我闖進了在西歐唯一的一個以政治意識和對資本主義的不相信為常態的小社會。在阿拉岡(Aragon)這裡,你處在成千上萬的人之間,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工人階級,大家在同樣的水平上生活,平等地來往。在理論上,一切都是完全平等,即使在實際中,離完全的平等也不算遠。就某個意義上說來,我們確實是初嚐社會主義的滋味——我的意思是說,瀰漫著的精神氣氛,是社會主義的氣氛。文明生活的許多正常動機——倨傲做作的身段、攫錢貪財、對老闆的畏懼等等——完全不復存在。社會上一般的階級劃分消失的程度,在充滿銅臭味的英格蘭,幾乎是無法想像的;這裡只有農人和我們民兵,誰也不是主人,可以擁有另外一個人。當然,這樣的一種狀況無法持久。它只是正在整個地球表面進行的一場大遊戲中的一個暫時的、局部的階段。但是這已經足以讓經驗過的人,受到它的影響。不論當時你怎樣詛咒,事後卻會發現,你接觸到的是某種奇異而可貴的東西。你處在一個小社會裡,其間希望比冷漠無情或者玩世不恭來得正常,其間「同志」的稱呼,代表同志之情,而不是像大多數國家中一樣,只是騙人的玩意兒。你呼吸到的,是平等的空氣。我知道,現在的時尚是否認社會主義和平等有關係。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裡,都有一大群黨裡的文棍和油滑伶俐的小教授,忙著「証明」社會主義不過是指計劃性的國家資本主義,貪婪動機則原樣不動。幸運的,是還有另一種與此大不相同的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吸引普通人,使他們願意為它犧牲,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魔力」,正是平等這個理念;對於絕大多數的人,社會主義指的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否則它實在毫無所指。正是因此,在民兵團中的幾個月,對我是可珍貴的。因為當時,西班牙的民兵團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無階級社會。在那個沒有人意在圖利,一切都短缺,但見不到特權,見不到奴顏諂媚的小社會中,或許正可以粗糙地窺見社會主義的開始階段可能是什麼一番模樣。到底,它非但沒有使我幻滅,反而對我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它的效果是讓我比以往更迫切地希望看到社會主義的建立……。(HC,pp.101-103)
這樣的文字,讀起來當然顯得太過天真、太過浪漫、太過理想主義、太缺乏理論的內容和現實的意義。但是寫這段文字時的奧威爾,距離他在西班牙戰地吃盡苦頭,身負法西斯的鎗傷,被共產黨的祕密警察追捕,不過才幾個月而已。在這麼真實的個人經驗的擠壓之下,他不太可能一反自己的習性,開始做理論的分析或是政治的宣告。在這段文字中,他其實是在整理、反省自己最真實的經驗和感受,找出那對自己生命有最強大支配力量的道德價值。
這樣來看,奧威爾的西班牙經驗,同時在政治方面以及道德方面,對他產生了「教育」效果。據他的一九四六年自述,從西班牙內戰之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取向」。這種取向,是如何從他道德領域中的信念衍生出來的呢?
對於政治,奧威爾的態度是冷靜而平實的。他再三強調,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是政治性的作家;但是他也頻頻提醒介入政治的人,政治是一種有限而骯髒的活動。一九四八年,在一篇題為〈作家與利維坦〉(Writers and Leviathan)的文章中,呼籲作家應該以非作家的身分主動或者被動地介入政治時,他這樣說:
……我們看出了參與政治的必要,同時卻也知道政治是何等骯髒、何等降低尊嚴的一回事。可是我們大部分人,卻仍然有一種留存不去的想法,認為一切選擇——尤其是一切政治上的選擇——都是善與惡之間的選擇,認為凡是必要的事,就當然是正確的事。我想我們必須去除這種托兒所階段的想法。在政治裡,人所能選擇的,永遠不過是決定兩惡相權何者為輕;在某些情況中,人只有像惡魔或瘋人一樣行動,才能闖出一條生路。
奧威爾這個說法,並不表示人不能用政治為手段追求理想,不過,所謂理想,也應該在塵世的層次上落實。一九四四年,奧威爾針對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的作品寫了一篇書評。柯斯特勒早年是共產黨員,參加西班牙內戰後,因為對蘇聯的幻滅,終於離開共產黨,寫出了曠世名著《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奧威爾說:
不論〔塵世的樂園〕是否應該存在,問題是或許它不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苦難,或許是無法從人生中完全消除掉的。人所面對的選擇,或許永遠是兩害之間的相權。或許就連社會主義的目標,也不在於使世界完美,而只是使它變得比較好。一切的革命都是失敗,但它們並不是同樣的失敗。柯斯特勒之所以會一時走入死巷子,原因就是他無法承認這一點……。
在這個意義上,奧威爾所認定的道德價值,便是很真實的東西了。在他看來,所謂社會主義,所謂平等,原本都是人生日常經驗的一部份,在人人身受的羞辱、迫害、剝削、壓榨中,在受難者的掙扎、反抗、詛咒與希望中,這些概念逐漸結晶,變成理想的存在。因此,由這些概念所引導的行動,也不須要去配合任何歷史的邏輯、社會的發展規律、或是超經驗的原則。在這些概念指引下所發的行動,無法構成任何正統(orthodoxy),因為它們無意提供全面的答案。這樣的行動,不需盲目的信仰,也不需要理知的犧牲。這種行動者所關心的,據奧威爾說,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選擇:一般凡人能有機會過一種像人的、合人性的生活呢?還是沒有這種機會?是再讓這種人被推回泥濘中掙扎呢?還是不容許這種事發生?
為了答覆這些問題,奧威爾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初抵巴塞隆納時,他遇到一位義大利來的參戰者。他們沒有交換姓名,也無緣再見面,但是這個義大利人的臉,給奧威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張「凌厲、悲哀而直率」(fierce,pathetic and innocent)的臉孔。本文開篇所引的詩句,便是奧威爾寫下紀念這位義大利人的一首詩的結尾。 奧威爾認定,以這個義大利人為象徵的一般凡人會在鬥爭中獲勝,他只是希望,這種勝利能夠早點來到而不是晚點來到,在一百年以內來到,而不是在一千年之內來到。他說:「這是西班牙內戰、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未來一切戰爭的真正問題。」
當年曾帶給奧威爾多少焦慮和痛苦的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已經暫時消散,不過他所憂心的一元整體主義,仍在以其他的形式威脅著人類。
從西班牙內戰之後到他去世,奧威爾始終堅持著他的「社會主義」立場。他繼續抨擊法西斯、抨擊斯大林主義、抨擊資本主義社會,但他的立足點,從未離開過這種以平等為基調的社會主義情操。在他眼中,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與階級支配、共產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官僚一元支配(totalitarianism),不論在其他方面有多少差異,但它們否定了人類的平等則一。他相信唯有在平等的條件之下,個人的自主和自由才能蓬勃發展。
今天的人所認識的奧威爾,往往只是《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與《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的作者。這兩本書出版時,冷戰的年代正好開始。在當時的氣氛下,奧威爾被賦予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形象。可是如果我們前溯他的西班牙經驗,尤其是讀《向卡塔隆尼亞致敬》,或許可以比較清楚地掌握住他在後期兩本書中所要傳達的訊息。臨死前,他公開強調《一九八四》用意不在攻擊社會主義或英國工黨,而是對瀰漫全世界的一元整體主義的趨勢提出警告。這個說法,應該放到奧威爾從西班牙內戰開始的心路歷程中來了解。
西班牙內戰結束已近五十年,西班牙以及整個世界的局勢,都有了基本的改變。當年曾帶給奧威爾多少焦慮和痛苦的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已經暫時消散,不過他所憂心的一元整體主義,仍在以其他的形式威脅著人類。他所謂的「社會主義」、「平等」、乃至於他時時強調的「基本的作人道理」,今天聽起來確實嫌空洞,但這並不表示他努力想用這些形式來落實的道德價值是虛幻的。我們能不能像奧威爾一樣平實而樸素地肯定這些價值,找到新的形式讓它們落實——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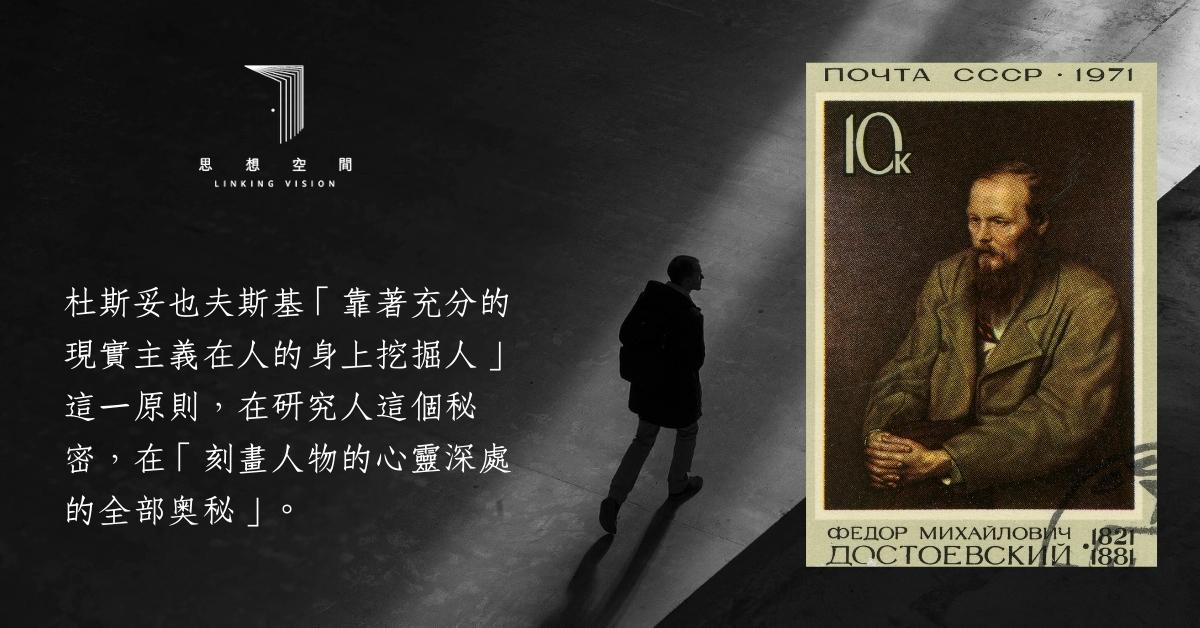
【深度導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在黑暗中看人性掙扎與虛幻光明(二之二)

【深度導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寫透過渡時期的畸形與荒誕(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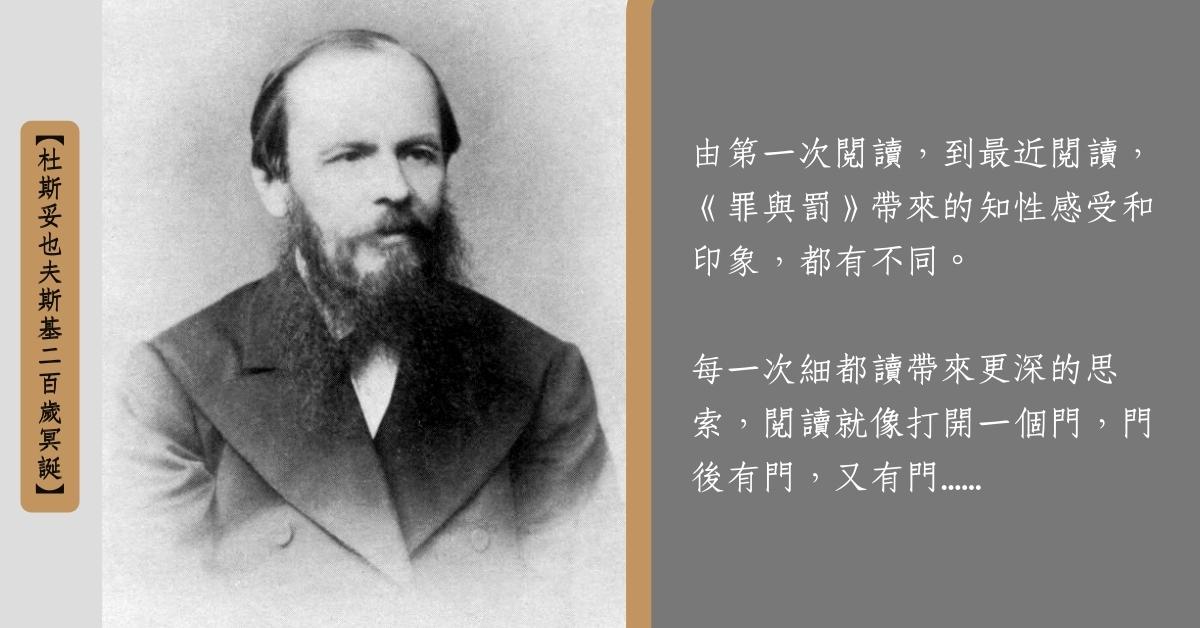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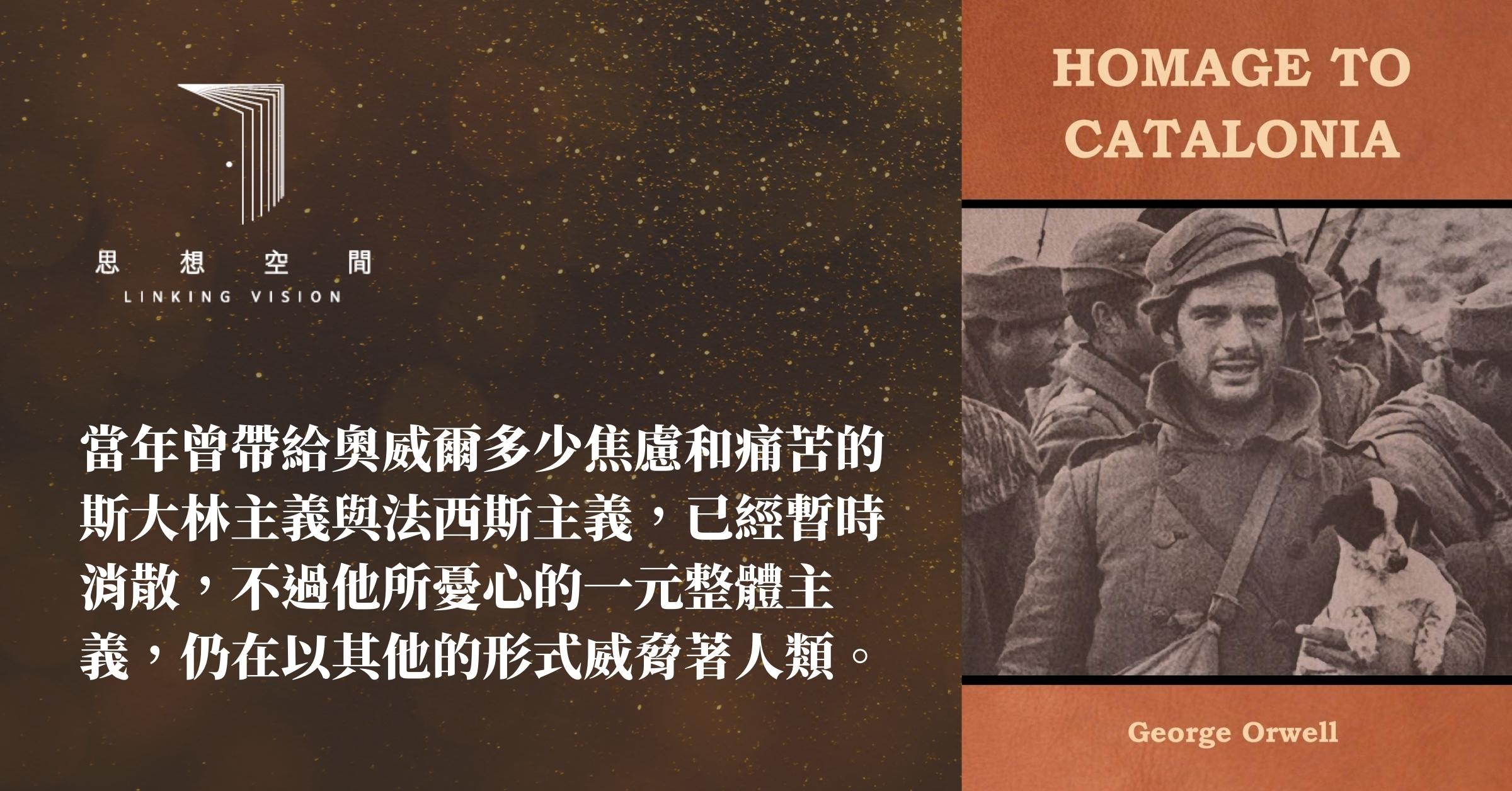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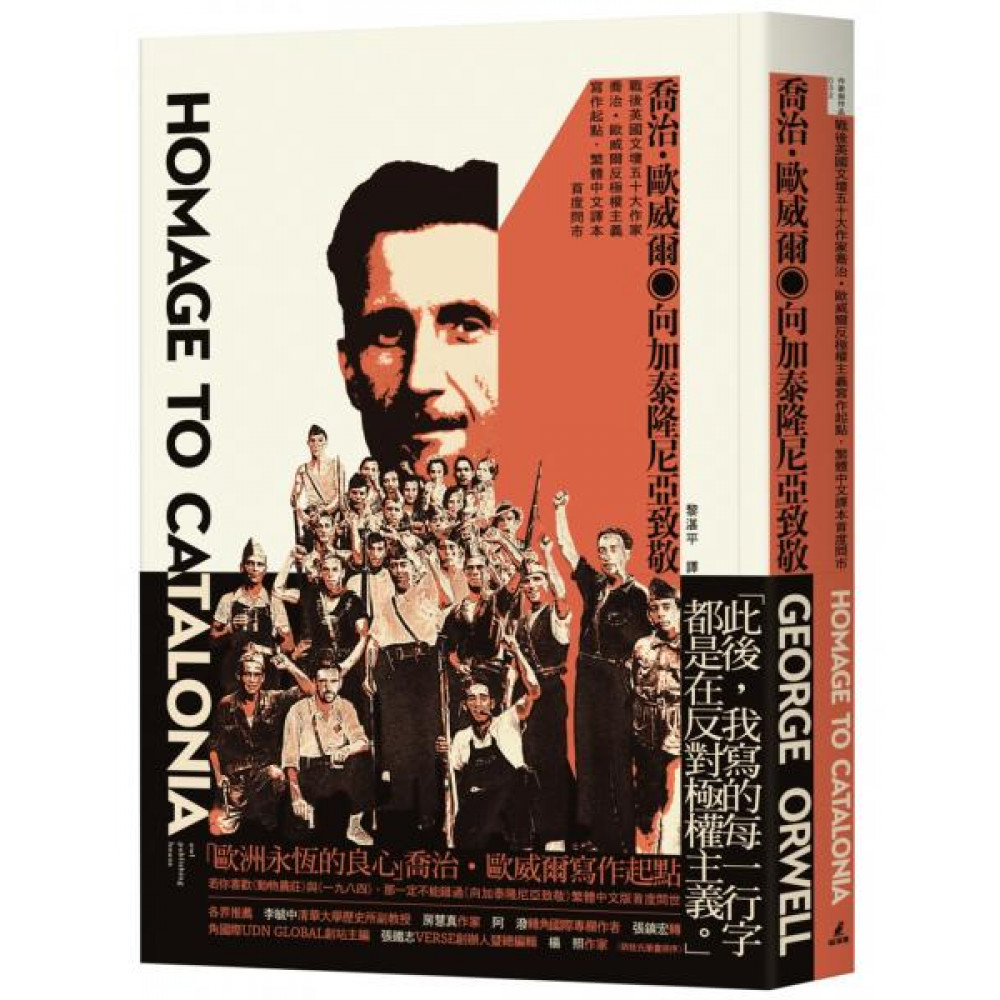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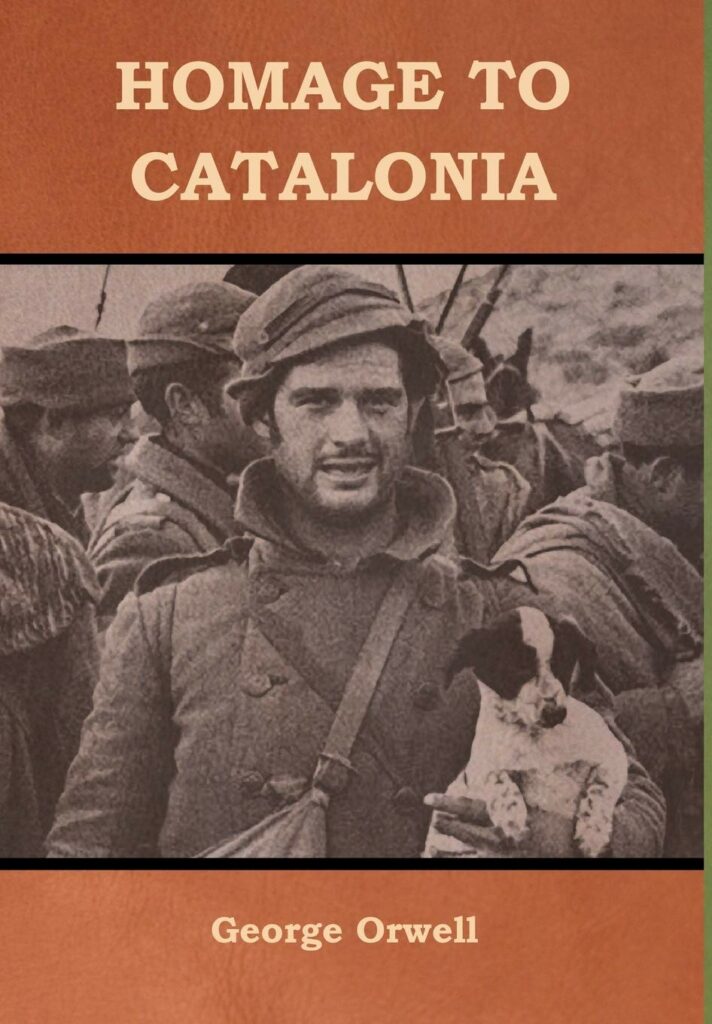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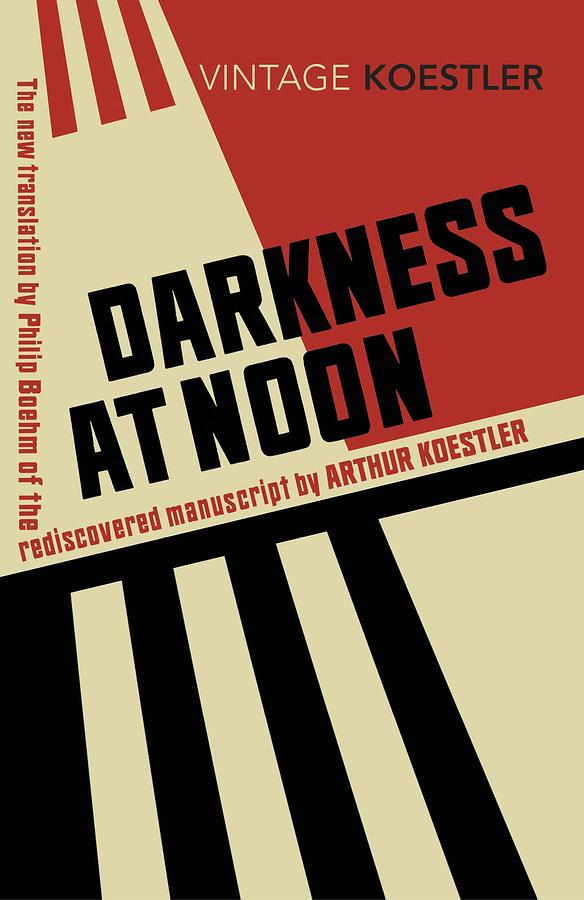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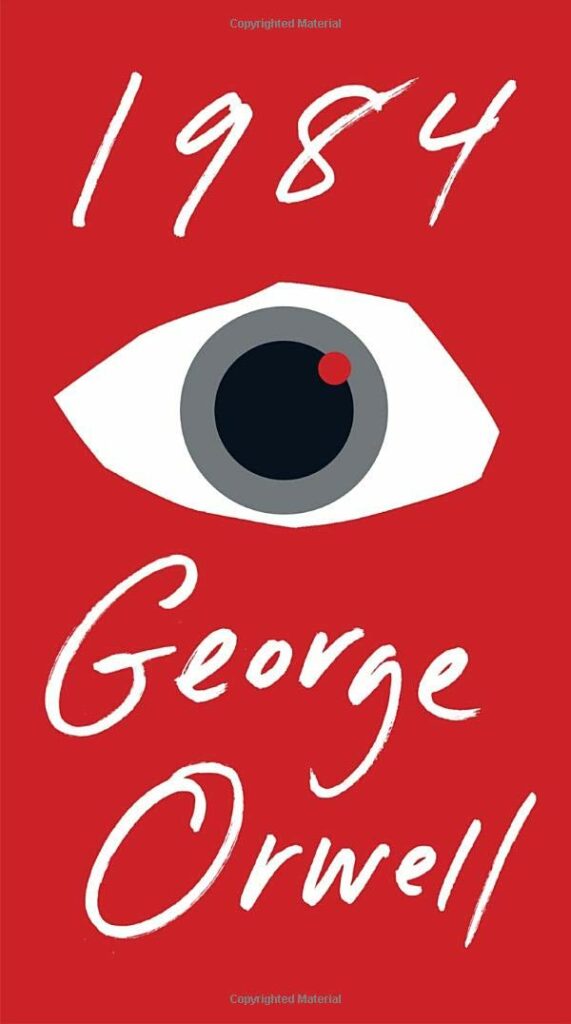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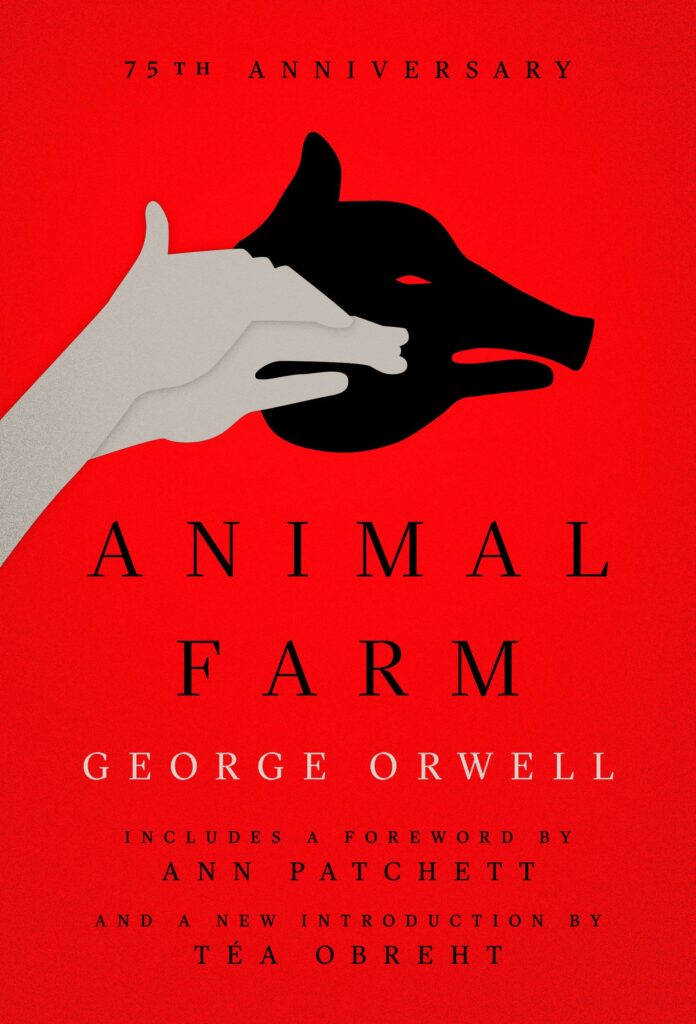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