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民劻(獨立音樂愛好者)
為逃離城市的高昂租金,躲進價廉實惠的工廠區,因而形成在工廠大廈的獨立音樂生態,使香港的indie scene 興旺蓬勃起來。
近年,男子偶像組合Mirror 在香港具現象級影響,有人說笑銅鑼灣因姜濤生辰成了「姜濤灣」。由東角道到崇光百貨一帶,滿佈萬千少女少婦,為23歲的愛與和平之子賀壽。
筆者作為獨立音樂愛好者,便感嘆何時香港的獨立音樂可以有如此的影響力,莫說曾經走出國際的livehouse也消失。這個疑問經常在腦中縈繞不散,台灣有孕育不少著名音樂人的女巫店;日本有下北沢SHELTER,傳奇樂團Toe 和 Ellegarden 也曾在那裏成長,那麼香港呢?
過去作為本地文化地標的Hidden Agenda (下稱HA) 曾是香港獨立音樂圈的萌芽之地,卻黯然離場。為逃離城市的高昂租金,躲進價廉實惠的工廠區,因而形成在工廠大廈的獨立音樂生態,使香港的indie scene 興旺蓬勃起來。小眾的音樂種類也可欣賞到,如metal 及post-rock等。
這個得天獨厚的獨立場景,因多次被政府指違法經營所造成的寒蟬效應而萎靡,不少在工廈的小型音樂空間停運。 搖身一變合法經營的TTN (This Town Needs) 延續HA的自由氣息亦以倒閉收場,因疫情關係影響收入,無法經營是近因, 問題的癥結是長期入不敷支, 缺乏政府的資助難以應付商業大廈的昂貴租金。香港的live house 的宿命,仿佛永遠面對「資本主義」和「政府」這兩大敵人。
筆者有幸訪問了一共五間小型音樂場地的livehouse 組織者,包括Hidden Agenda、Lost Stars Livehouse Bar & Eatery、留白、Backstage Live 和在某工業區的場地(因保密關係下稱XXXX),望藉結合訪問的實證研究與空間政治理論,回應香港livehouse 的沉寂期。
寒冬不過未來盛夏的開端,潛藏遁隱的心態或可為音樂空間另辟蹊徑。
把原為不合時宜的工業空間納入規劃和發展的藍圖,建立受商業歡迎的美麗花園。以綠化和可持續發展為名,不斷改造轉型的空間為都市,推動仕伸化的巨輪。
音樂烏托邦的冒起與受限
眾所周知,香港是資本主義掛帥的地方。樓價攀升不在話下,行業出路狹窄,若不是從事金融、炒賣、地產、銀行或金融等與資本急速流動累積的行業,或是專業人士,員工如何努力,收入永遠也不及資產擁有者。勞動階層無論如何勞勞碌碌,只能為僱主賺錢,僅足以糊口。
在這寸金尺土的地方,要求玩獨立音樂,看似遙不可及, 痴人說夢話。可是,HA曾是另類獨立的烏托邦,位於觀塘的工業區,擁有3000 呎空間,舉辦過千場音樂會,音樂種類多元,包括搖滾、爵士、金屬和嘻哈。這個小型live house 更設有band Tee小店,也有小食和酒水小賣部,應有盡有,形成工廠區內獨有的音樂村落。
第一代的HA 位於財利工業大廈,因為工廠區租金低廉,得以進駐較邊緣的工廠區。正值香港工業凋零,工廈對比商業區的市場價值較低,租金低廉且空間寬敞,讓收入微薄的藝術家和音樂人得以進行文藝創作, 逐漸形成一帶藝文空間,藝術工作區、樂隊練習室和表演場地的出現,證明創意工業的多元和百花齊放。HA 數次被逼遷的故事,相信不用再多詳述。
自政府於2009年推出「活化工廈計劃」政策,工廈的市場價值提高,第一代HA 因整幢大廈被業主收購已搬移。業主可以免補地價,免費將大廈改成不同用途,如辦公室、食肆、零售及甚至酒店等,省下原本需要的補地價費用。
第二代HA 遷移到高良工業大廈,便受各政府部門注意,引來違規經營和違反土地使用用途等事宜。地政處多次向業主施壓,如繼續容許HA經營警告釘契,HA 唯有屢次搬遷。如要合法經營,需要搬到容許作娛樂場所用途的大廈, 承受高昂不菲的租金,才合資格申請公眾場所娛樂牌。
在工廈,除非有龐大的資金改動整幢大廈的地契,或本身業主不害怕釘契(註:釘契,指當房產或房東面對法律訴訟而構成產權負擔時,相關文件會在土地註冊處登記,從而使得房產難以再出售)。同時,政府實行起動九龍東計劃,為加速九動東轉型發展為香港第二個商業金融中心,把原為不合時宜的工業空間納入規劃和發展的藍圖,建立受商業歡迎的美麗花園。以綠化和可持續發展為名,不斷改造轉型的空間為都市,推動仕伸化的巨輪。
其實,背後政府一切操作的邏輯都是關於資本累積所產生的仕紳化。Harvey的理論對都市改造有精闢分析。根據他的理論,資本的累積可分為三個循環,第一個階段是交易透過機器生產的商品所生產的資本;第二級迴路是投資能轉換資本的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將生產中多餘的資本轉移到固定資產上,比如房地產投資、耐用品投資和基金等。空間於房地產市場被商品化,淪為可交換的產物,市場只重視空間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實際價值一點也不重要(use value)。最後,第三級迴路是以科技為方法,加速資本循環,保證資本可再投資和積累,解決在第一和二迴路資本過度積累所產生的問題,如金融科技和NFT等。在建設有利投資的人造環境中,需要將資本轉化為固定資產,當中涉及轉換資本為貨幣的過程,使空間可作為商品在市場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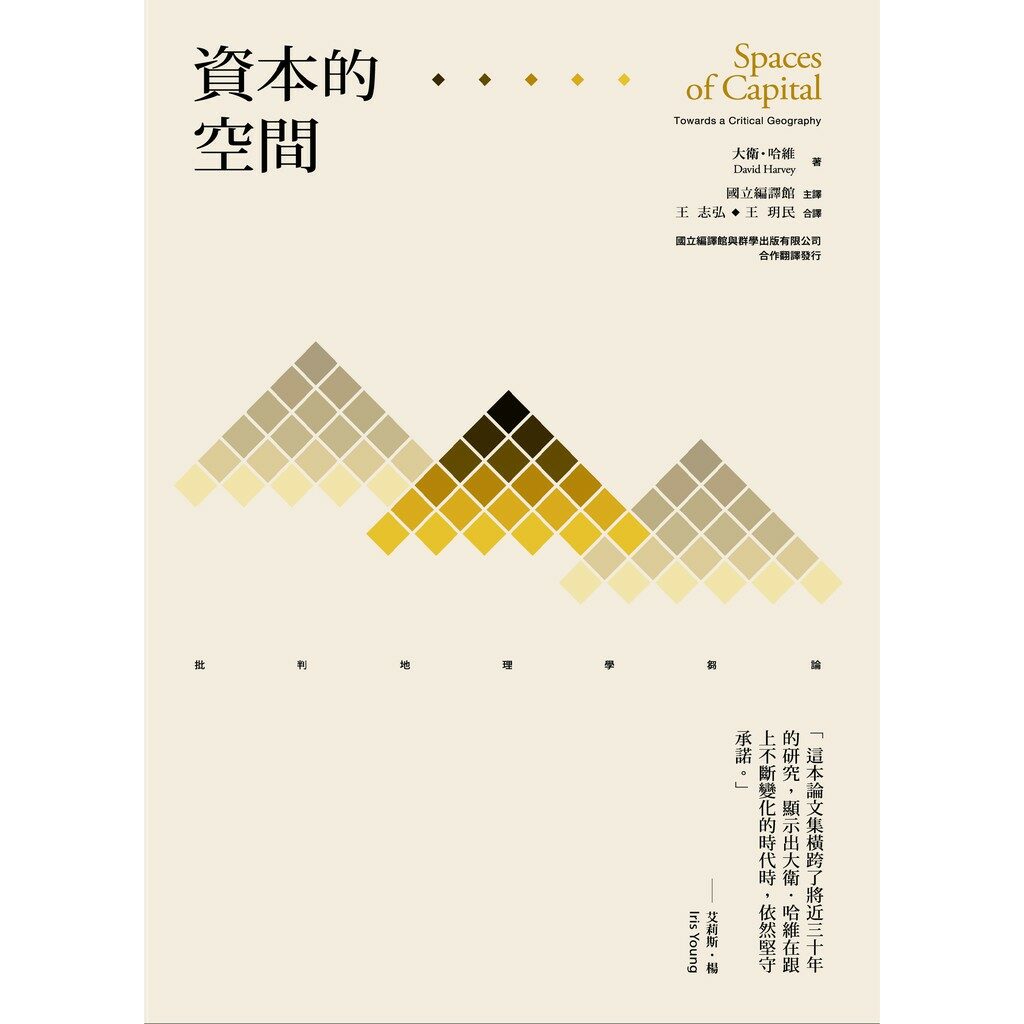

但轉換過程需跨越空間原有的障礙(barrier), 以九龍東為例,要發展觀塘為第二個核心商業區,需清除廢棄的工廈、改建高樓大廈、營造壯麗園區和建立有利商業活動的配套如交通,通過空間都市(urbanization)可解決這些問題,其中空間的市場價值(即交換價值) 增加資本流通。一旦轉化失敗,投資者便會撤資,減慢資本流動,地產的價格逐漸下降,實現可再投資機會的。想想觀塘十年前的凋零工廈,正值等待被重新投資的機會,當政府銳意發展在觀塘新核心商業區,就是第二迴路的來臨。這解釋仕紳化在觀塘發生的過程,讓擁抱新自由主義的金融中心繼續蓬勃發展。
基於上述論點,對藝術文化空間的破壞,可以理解為解決社會因無限需求,而過度生產的荒謬問題。地理空間反映資本循環系統的流動,通過生產人造環境,本為創意廣闊無限的空間會被急速發展殲滅和規範。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實現空間的配置、重組和地域擴張,將空間融入全球市場,這是仕紳化背後的緣由。
在空間中引發了一種宰制力量,當地藝術空間往往因高地價和發展商收購而消失,導致藝術家流離失所。
新自由主義下,城市空間仕紳化
新自由主義殘酷的去蕪存菁,亦見於政府在政策上,渴望營建自己品牌的文化空間。早於1998年,政府已有興建巨型文化表演場地的構思,宣佈打造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計劃,冀使香港成為具國際地位的文化藝術中心,提升香港文化的水平與世界接軌。經過多年的方案篩選,這計劃最後演變為現今綜合文化場地的西九文化區,主要設施包括博物館、演藝場館和劇場。其中自由空間為主要表演場地 ,當中有一間與政府合辦的livehouse 叫留白,以餐飲形式營運。問題便來了,為何在民間、在工廈,一直有默默耕耘的組織者和藝術家掙扎求存,政府一方面對他們卻不聞不問,一方面又大興土木旨在發展文化?
Richard Florida 所提出「創意城市」的概念正解釋政府的「矛盾」。官方行用政策干預,以創意以吸引投資和加速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體中的資本增長。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獲得了作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創意能力,揭示了後工業時代的發展轉向。當經濟增長出現放緩和飽滿,透過商品化藝術家或從事文化的創作﹐產品中的新意念能刺激消費,吸引投資。然而,引來的後果是仕紳化和以數十億計的重建計劃,以通過改造城市為新自由主義服務。因發展所需的競爭力將原來獨特風土面貌的社區再生為具有經濟效用的產物。因此,在空間中引發了一種宰制力量,當地藝術空間往往因高地價和發展商收購而消失,導致藝術家流離失所。仕紳化和城市更新計劃對政府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們能產生越來越多有利可圖的休閒場所,促進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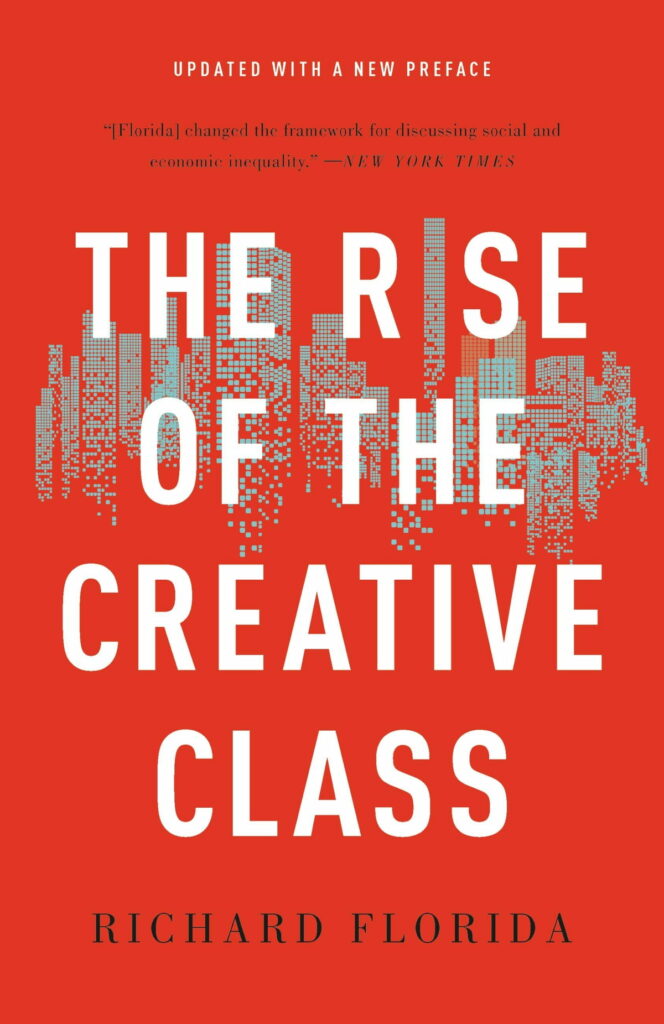
在此理論視野下,西九文化區的建設是一項大規模的重建文化項目,旨在打造文化產業中心,建立具有競爭力的全球城市形象,文化被約化(reduced)為資本玩兒的包裝紙。該項目由香港旅遊協會牽頭,建設過程投資28億美元。希望成為城市繁榮中的文化區;當地藝術家參與、發展和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及舉辦和創造引領世界的展覽、表演和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
此外,政府聰明地活化再利用文化原址,讓當地藝術家參與再生過程。例如漫畫家和動畫師的展覽空間Comix,以及兼具商業和娛樂實踐的混合工作室PMQ。本地藝術家的加入,理論上應該帶來可持續的文化發展,西九亦曾三次舉辦「自由野」音樂節邀請本地音樂人表演,錄得數萬人次入場。同時,政府在舊工廈區大肆發展,執法部門隨之而來,草根表演與練習場地一掃而空,西九所提供的平台不其然令人聯想,政府刻意令音樂表演空間只能於它認可的和受規管的空間發生。 西九的存在確是好事,讓繁忙的香港人在週末有休憩的空間,亦提供更多專業的表演場地。問題是音樂場所並不夠多元,香港能容下的小型音樂表演空間屈指可數。
位於利奧坊的Lost Stars 亦是兼顧飲食的表演空間,持牌經營,擁有公眾娛樂場所牌。主理人與我分享,成功申請牌照前需要支付一筆昂貴的牌照顧問費用。利奧坊亦是恒基地產的新地標式住宅項目,Lost Starts 得以生存,第一個條件是可以承受地鋪的租金,所需的費用價值不菲。第二,因為利奧坊是新發展項目,土地使用用途合乎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資格。這個案例告訴我們,若 livehouse 要在香港生存,直白一點,一是被政府收編,一是接受資本市場的洗滌。自發組織的音樂空間只能無奈被政府驅逐,或因資本赤裸淹沒而流逝。

在政府眼中,對大眾或他自身有利的是經美化包裝的創意城市, 民間組織的Livehouse 從來不值一提,更加不樂於見到在工廈的音樂空間……
官方「創意城市」想像的背後
最後,政府透過行政的管治術,規範個體的行為,為符合官方理性管治整體人口的思維。這是Foucault 所說的governmentality,對香港的政府來說,安全為最高標準, 消防條例和公眾娛樂場所牌的規格十分嚴格,在工廠大廈設置下是沒有可能成功申請,執法部門屢次巡查警告只為維持現有的秩序和知識體系。消防署曾派員檢查HA,結果都是合乎消防條例,曾在表演做演習火警和放置足夠的滅火器。死結在於營運Livehouse不符合約五十年前訂下的工廈土地用途,進行的音樂創意產業也不符合政府對工業的理解。
為何音樂與藝術文化不能被認可為創意產業,發展本土創意文化?政府不改動僵化的工廠大廈條例,推動活化工廈政策只為加速仕伸化,玩樂隊的和藝術家早已經將工業區活化,變為本土文化溫床。 簡單說,在工廠大廈無牌營運Livehouse就是危險, 罔顧人命,但持牌營運就是安全, 這反映極其荒謬奇怪的管治思維。若以私人名義舉辦聚會和派對,不涉及從公眾獲利的話,又可說是合法。在政府眼中,對大眾或他自身有利的是經美化包裝的創意城市, 民間組織的Livehouse 從來不值一提,更加不樂於見到在工廈的音樂空間,Livehouse 的掙扎求存只顯示政府的冷漠和老謀深算。曾有Livehouse組織者與藝發局開會商討,換來的,只是得悉各文化劇團的撥款資助分配, 對討論扶植Livehouse發展的配套政策漠不關心。
處於中環的 Backstage 與HA一樣,都缺少公眾娛樂場所牌, 但從沒遭受執法部門的阻撓。我認為關鍵在於兩者應對政府方法的不同。HA自活化工廈條例推出,已經積極組織社會運動,務求給予壓力政府改變。 唯事與願違, 多次曝光於大眾媒體與政府,協商修改工業用地用途, 結果是將自己從灰色地帶, 暴露在危險當中, 加速引來政府注視下的規劃改造。Backstage多年來安然無恙,也許是恰巧處於模糊之中, 政府概然不了解所進行的活動,Backstage就如一個自由孤島,獨享城市裡僅餘尚存的文化氣息。
即管異質的空間存在於剎那間,只有瞬間的片刻能彰顯個體的自主,這仍然能反映個體擁有反抗的無限可能。
如何為藝術找回公共空間?
最後,唯有藉獨立樂隊Bad Math 的Neon City 作結,The neon city, what a pity。在高舉資本主義的香港,以發展和經濟增長為金科玉律,不知將多少百花齊放的本土文化扼殺,埋葬在名為現代化的墳墓,死於五光十色的城市裏。Livehouse 在香港這個不毛之地,可說是奇珍異獸。
過去HA 的代表多次與政府交涉對話,換來的只是政府部門的執法阻嚇,搬遷到油塘的商業大廈,持牌經營卻敵不過高昂的租金。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清拆與重建,城內只剩下一式一樣的高樓大廈、毫無二致的辦公室,還有同質劃一的名店商鋪,人的創造力渺小如微塵。霓虹的都市,看似映照著繁華光輝,璀璨中卻帶著難以言喻的頹靡失落,盛載活力自由的文化空間煙消雲散。 聽到It descends into darkness, Devoid of hope,讓人感嘆無比。
或許,在香港短時間內也回不到數年前的日子,可以隨意到HA 狂歡一晚,與同好到大大小小的獨立音樂場地體會音樂與酒精帶來的繽紛美好。無論資本主義空間(capitalist space) 如何因有利資本累積被生產,人作為個體仍然擁有一定的能動性(agency)回應驅逐的宿命。空間之所以為空間,說到底是基於人類活動所構成。
Lefebvre 指出人在不經意的時刻,能創造一個異質空間,違反空間固有的規矩,甚至組織集體活動反抗有權者的規劃秩序。關鍵在於,我們要敢於想像空間其他一切的可能性,跳出固有框架思考,即管異質的空間存在於剎那間,只有瞬間的片刻能彰顯個體的自主,這仍然能反映個體擁有反抗的無限可能。
早在觀塘被「起動」、興建音樂噴泉之前,已有一群音樂發燒友在廢墟的橋底,即現在觀塘海濱舉辦樂隊表演, 最誇張的時候橋底下有三對樂隊在三個角落表演,可想像當時氣氛又多熾熱。又曾闖入廢棄巴士廠舉辦音樂會,搞天台音樂會和游擊表演等這些民間自發的活動證明空間是可以被顛覆的。 由此可見,人的創意可說是無窮無盡、千變萬化, 文化就是這樣生出來。
遺憾的是在極權時代下的都市,實行這些反抗行動變得天方夜譚,但Livehouse 仍可以地下化的形式存在。依筆者考察,在香港仍然倖存的小型展演場地 XXXX(排除以餐廳或酒吧形式營運的場地),都是以私人聚會的模式營運,只招待熟悉可信的朋友。以口耳相傳的方法宣傳表演,需表明身份、實名認證, 恍如回到社交媒體出現前的時刻。香港的Livehouse 讓我們重新反思什麼是公共空間,或許掛著私人之名,反可在寂寞空洞的城市中找回公共之實。
( *本文原題為〈從香港的空間政治視角下,Mirror 是否我們唯一的選擇?〉,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延伸閱讀:

【思想音樂】麥偉豪:馬來西亞「黃火」運動25週年 —— 燃燒抑或幻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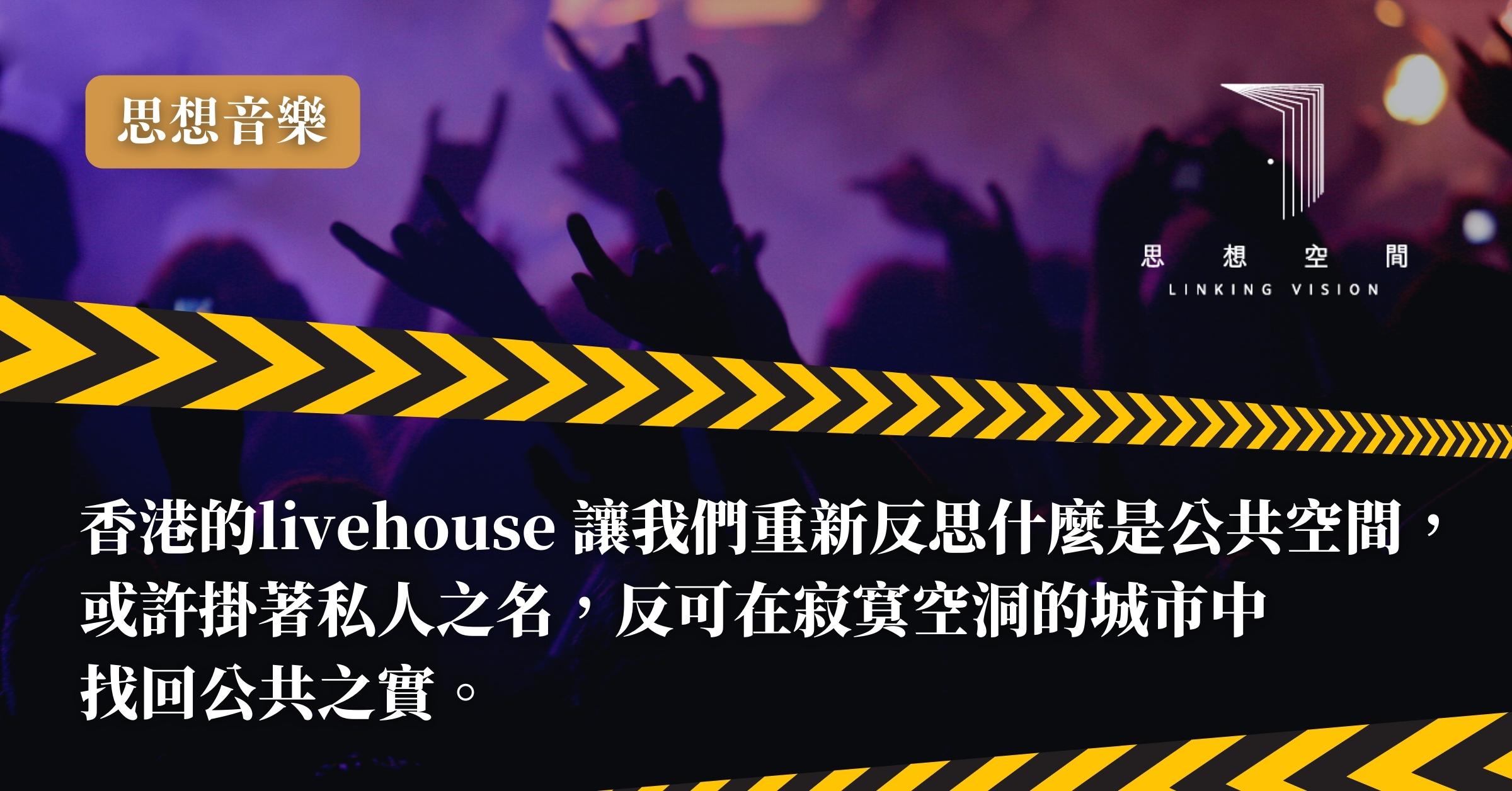
【思想音樂】黃民劻:盛載自由的音樂空間,如何面對被驅逐的宿命?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