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出世,屋村band仔,英國民族音樂學博士生,回港做點事。 前大學講師、電台DJ。著有《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音樂文化評論集《拆聲》;合著有《我們來自工廈》、《Fractured Scenes : Underground Music-Making in Hong Kong and East Asia》等等。參與樂隊包括remiso、fragile、Pusshitachi等等。曾參與電影配樂包括《岸上漁歌》、《移家》等等。

文/黃津珏(「思想音樂」專欄主編)
編按:思想空間最新開設「思想音樂」專欄,特邀香港獨立音樂人、前大學講師黃津珏擔任特約主編,串聯獨立音樂搞手、熟悉音樂、書寫音樂文化、具批評性的業界人士參與,展現獨立音樂的思想與批判,探討從音樂出發、如何構成跨地域的共同體。本期「思想音樂」則以近期戰事為背景,由黃津珏擔任主筆,從烏克蘭朋友Sasha的跨域經驗、談到討論獨立音樂的理念與展望。
因為搞獨立音樂,在香港認識到烏克蘭朋友Sasha。
Sasha習非洲鼓。2014帶著鼓,少量盤川,與朋友作全國巡演。走過十多站後,遇上戰爭,回家鄉Adveevka之路已變得不安全,於是輾轉抵達克里米亞半島(Crimea)。當地巧遇全職街頭賣藝的俄羅斯音樂人Vetya,他比Sasha多跨國界的遊牧經驗,曾靠街頭賣藝旅居亞洲,把經驗心得全盤分享。Sasha從中獲得啟發,毅然離開烏克蘭,數年間足跡踏過香港、澳門、泰國等地,至今從未回國。
跟Sasha對話,發覺他不像我們想像一般,離鄉背井必然伴隨愁緒,掛念自己的出生地,甚至高舉自己的國家、民族,並感到驕傲。他沒有說過一句「真係好X鍾意烏克蘭」、沒有說「烏克蘭真係好靚」,反而不諱言批評家鄉Adveevka,多數人整天都在喝酒,有點無聊。Sasha與我身邊絕大多數音樂人一樣,反戰反侵略基本已成共識;但一定程度上,這個反戰意識並非建構於自身國族身份之上,而是通過重想人與人之間的另一種集體身份認同,然後去反對戰爭本身。他說,世界就是一體,只要有人願意聽自己的音樂、有音樂人願意交流,身處的地方就變得不太重要。
然後我發覺身邊的朋友,特別是獨立音樂圈,或次文化領域的活躍份子,不少都有一種好奇怪的作風。怎樣奇怪?就是言談之間,日本朋友喜歡罵日本,法國朋友喜歡鬧法國,馬來西亞人喜歡數馬來西亞種種不是。我當然也會對香港種種主流文化陋習,與及失能政府,毫不保留的批評。然後我們的集體身份,一定程度上就是產生於這種對自己民族鬧過痛快的奇怪過程之中。當然明白,政治動蕩下,甚至因為政治動蕩而必須逃亡離散的受害者,好可能特別需要通過想像、甚至美化自己的民族根源來排解顛沛流離的苦況。但藉此短文,希望能夠讓讀者窺探「另類」集體認同的可能性。甚至乎,或者就是動蕩之中,這種往往被忽略的想像共同體,才更值得書寫。
Sasha的例子,正正跟最近越來越多學者都想帶出的,世界主義的另一種面向吻合:有種人,除了屬於文化經濟上的弱勢,同時抗拒國界種族的身份,卻因為次文化活動,而建立一種「無國界世界主義」。
Sasha的例子,大概就是D’Andrea筆下[1]的新遊牧主義(neo-nomadism)範例。新遊牧者雖然跟不少跨國人口流動,如現代外勞、遊客、離散(diaspora)等等,一定程度上都是人口超流動(hypermobility)的現象,但主體性卻有獨特差異。首先,新遊牧者通常不以跨國作為消費性活動,反而倒過來,將跨國的超流動性融合經濟手段。新遊牧者大多相對地,對目的地的主流文化未必感太興趣,也不太著眼於融入當地傳統之中,而是透過遊牧過程,於次文化領域中安身立命,重視尋找與連繫志同道合。近年結合次文化音樂與新遊牧生活的例子大幅增加,除了如Sasha的街頭藝人外,D’Andrea就用音樂人策劃與參與Techno、Trance等等的國際電音派對作例。其實新遊牧主義的意識型態,不一定是從這種跨國流動出現的;反而數碼化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先促成這種生活方式的想像,然後才透過實踐,鞏固這種獨特的主體性。
D’Andrea觀察到,這些裝扮跟音樂品味都很另類的次文化份子,不少除了對新的國族身份不感興趣外,更希望對自身的種族身份保持一定距離,甚至乾脆作出拒絕,以世界公民、地球人、地球生物自居。因此新遊牧者,有異於傳統離散人口研究,成為一種特殊的「負離散」(negative diaspora)群體。如果傳統離散,因為跨國界遷移,必須要在異域面對身份建構與主體性的挑戰;那麼,負離散就是剛剛相反,他們擁抱遷移的機會,並借助異域,否想過去被根植的民族身份,再通過跟其餘次文化圈內的負離散作出交流,去想像另一種可能性。
本來,這種「世界公民」的口吻,可以是一種危險。經常掛「世界公民」於嘴唇邊,有時是已發展國家菁英的特質。一定程度上,世界公民利用自身的經濟與文化優勢,幻想世界都是暢行無阻的遊樂場。當然這種批評是有力的,因為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本來是從西方啟蒙運動中繁衍出來,不能忽視當中的歷史權力關係。好像表面上擁抱普世性的世界主義,曾經被不少人批評為只是一種中產消費者凝視世界的方法;也可以是一種透過想像自己的文化共融性,來凸顯自身民族的優越感的手段。但Sasha的例子,正正跟最近越來越多學者都想帶出的,世界主義的另一種面向吻合:有種人,除了屬於文化經濟上的弱勢,同時抗拒國界種族的身份,卻因為次文化活動,而建立一種「無國界世界主義」(non-nationality cosmopolitanis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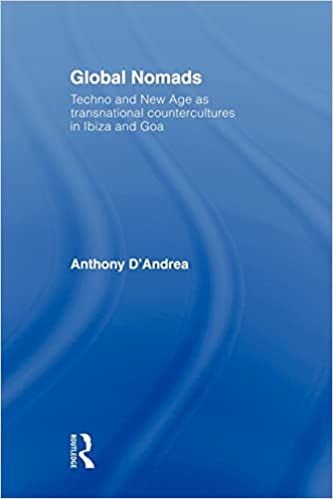
他們都明白搞獨立音樂的美好與困難,在自己的領域,拼命思考與經營本來就不存在、不受重視的另類聲音,在不同的挑戰中,耕作文化。
雖然完全無法類比,但說Sasha的故事,看到烏克蘭被侵略,百姓離國逃難,身邊不少音樂人朋友對侵略者咬牙切齒;難免會聯想到香港的移民潮,與及運動之際,多少海外音樂朋友高度關注,甚至身體力行在自己的家鄉搞抗議活動。我會感到奇怪,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他們為何會如此著緊痛心?我不斷言這些朋友都是無國界世界主義者,但有趣的是,獨立音樂圈,卻好像相對地容易聚集這種想法「不切實際」的人。這種人,或者就是如前英國保守黨首相Theresa May口中嘲諷的群體:「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世界的公民,那就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原來就是有些人,討厭國族想像,「好管閒事」,無論是出生地,或是從來未踏足過的地方,只要有不滿,就批評抗議。
或者,他們未必有豐富的跨國流動經驗,但原來獨立音樂,卻一定程度上腐蝕了部份的種族框架。可能聽音樂,玩音樂,能帶我們出走,離開瘋狂的現實,到達共同想像的理想地。如果新遊牧者視人口遷移,為否想問族身份的啟機,那麼我們也一定程度上曾經於音樂中遊牧,一起走得遠遠,然後輕視地上的種種平板無聊。可能就是這樣,身邊的香港獨立音樂朋友,在艱難時間,也不用靠消費販賣香港人身份的主流音樂,來刷集體身份認同;也傾向不忽然愛港,繼續一起對香港文化中的守舊封建,敢怒敢言。
如今在香港,失去跨國流動自由之時,更想念這個獨特的國際社群。承蒙厚愛,就是於思考這個跨國界的獨立音樂共同體的時候,收到《聯經思想空間》邀請任音樂文化版特約編輯。重任當前,雖然擔心力有未逮,但好希望利用這個版面,連結跨華文世界的獨立音樂人,於是放膽迎接挑戰。說共同體,說連結,我想最適合的方向,還是廣邀身邊搞獨立音樂、熟悉音樂、能書寫音樂文化、具批判性的業界人士參與。他們都明白搞獨立音樂的美好與困難,在自己的領域,拼命思考與經營本來就不存在、不受重視的另類聲音,在不同的挑戰中,耕作文化。希望將來,這些獨特的觀點,在這平台上能編織成線、成網,互相啟發,帶動討論,為這個珍貴卻被忽視的獨立音樂圈,這個本來就是跨地域的共同體,留一點線索。
[1]D’Andrea, A. (2007). Global nomads: Techno and new age as transnational countercultures in Ibiza and Goa. Routledge.
[2] Skovgaard-Smith, I., & Poulfelt, F. (2018). Imagining ‘non-nationality’: Cosmopolitanism as a sourc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Human Relations, 71(2), 129-154.

香港出世,屋村band仔,英國民族音樂學博士生,回港做點事。 前大學講師、電台DJ。著有《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音樂文化評論集《拆聲》;合著有《我們來自工廈》、《Fractured Scenes : Underground Music-Making in Hong Kong and East Asia》等等。參與樂隊包括remiso、fragile、Pusshitachi等等。曾參與電影配樂包括《岸上漁歌》、《移家》等等。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