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選自《思想的求索(思想1)》,原題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文革四十週年反思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乃至社會底層的賤民們,利用了紅色始皇帝毛澤東「對走資派造反有理」的聖旨,報復了自1949年10月以來一直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紅色官僚特權階層。
「五湖四海戰鬥隊」
在皖南宣城、郎溪、廣德的丘陵和山區一帶,有多個勞改和勞教農場,那些多半是1950年代末尾建起來的,主要是收容和關押從沿海地區及本省各地押送來的犯過小罪、判了輕刑的所謂「壞分子」。犯過大罪、判了重刑的,就不會關在我們那兒,而是送到青海、甘肅、新疆去了。
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開始衝擊到了「公(安)、檢(察院)、法(院)系統」,勞改和勞教農場都是它們管轄的,也隨之亂了套。管教幹部多半成了被批鬥對象,被管教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就趁機逃離囚羈之地,跑到自由社會上來。他們中的一部分膽大之徒甚至成立了造反組織,通常起名叫「五湖四海戰鬥隊」——這隊名乃是對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的產物,毛的小冊子《為人民服務》裡有段名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逃離囚籠的勞改和勞教分子自稱為「五湖四海」,是雙重意義上的誠實: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是從各地被抓被押運來的;他們從今以後流竄五湖四海,哪兒能混日子,就到哪兒去。他們把毛澤東的遊擊戰術學得也挺地道: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讓你逮他不著。想來這也自然,千百年來的綠林強人,包括水滸梁山好漢和毛澤東當年率領的遊擊隊,都是靠這方法謀生存的。
五湖四海戰鬥隊中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因為小偷小摸、拐騙欺詐、調戲婦女、破壞公共財物而被抓被關的;在關押期間,少不了承受管教幹警的打罵,於是把歷年所有積壓的憤恨,都及時地在五湖四海戰鬥隊的大旗下發洩出來,報復正常的人們。他們當然不敢去攻擊有武裝有組織的軍隊和造反派團體,也不敢到城市來搗亂,就專撿偏遠的鄉村去騷擾農民,搶劫財物、屠殺牛豬、調戲民女、乃至縱火焚燒老百姓的房子,都幹得出來。被多次騷擾的偏僻鄉村,有些就沿用中國歷史上兵荒馬亂年頭的辦法,自組民團保衛家園。每個村莊都設立了暸望哨,一發現有五湖四海戰鬥隊流竄而來,就吹號鳴鑼,周邊鄰近村莊的民團便趕來接應。雙方的武器,多半也就是長矛大刀、鳥槍土炮。偶爾有被民團活捉的五湖四海戰鬥隊隊員,他們就捆綁來送到城裡的駐軍部隊。在三縣兩省互不管的地帶,民團活捉到五湖四海戰鬥隊的,往往就動用私刑來報復他們。我們聽到的最駭人的一件,是宣城和鄰縣交界處的山區裡,民團把在當地屠殺耕牛、洗劫孤立小村子的五湖四海隊員抓獲,就將他們「栽」進麥地裡,只露出肩膀以上在地面,然後把耕牛套上犁,鞭抽牛耕耘而過,幾個來回,露出地面上的幾顆腦袋就被犁得乾乾淨淨。用這個辦法報復五湖四海戰鬥隊,是為日後萬一上面有官追究責任,好脫干係,村民中無人可被明確認定為「動手殺了人」。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們正在本派武鬥大本營區域的一個小院落裡休息——白天休息,是為著準備夜間打仗——突然院門外哨兵通報有貧下中農代表來求見。進來的五、六個農民訴苦,說他們那一帶久經五湖四海戰鬥隊的侵擾,好不容易把民兵組織起來跟他們打了一仗,俘虜了一個人,綁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部隊卻拒收。拒收的理由也說得過去:部隊沒有監獄,把俘虜關在哪裡?部隊一接到命令就得開發,帶著個五湖四海分子,又怎麼辦?貧下中農代表說:這年頭他們最相信的人就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的解放軍,和毛主席的紅小將。既然解放軍不接收,只好請紅衛兵小將們處理俘虜了,你們最懂毛主席的路線政策!
貧下中農代表把捆成一團的俘虜往地下一丟,就告辭走了。當時在院子裡負責那一支武衛小隊的,是白大舌頭。他出身農家,忠厚耿直,嫉惡如仇,聽說俘虜是一個為害鄉下農民的小土匪,就喝令立刻升堂審訊。審訊犯人得要有法律上的依據,紅衛兵小將們雖然狂妄透頂,也多少曉得這個道理。白大舌頭的武衛小隊商量了一下,拿不出個主意,也讓我們文攻小隊的成員過去參與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最高指示」就是法,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裡哪幾條能對得上號,馬上就運用起來。紅司令沒讓他的紅小將們失望:《毛主席語錄》小紅書裡能在這場合用上的,有好多條,比如,「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這是紅小將對他們臨時組成的審判機構的命名——由白大舌頭擔任審判長,他挑選了他信得過的幾個人作助手,基本上全是武衛隊的隊員。俘虜像一個大濕泥團,歪歪斜斜的半躺在地上。審判開始的時候,我不得不趕到本派總部所在地縣麵粉廠大樓去,負責明天清早就要印出來的《戰報》上「血淋淋的戰鬥檄文」——那是我的本職,每天夜裡都要紅著眼睛幹到兩、三點鐘的革命事業。第二天中午吃過飯回到那間小院子去睡大覺的時候,一進門就發現與平時不大一樣,氣氛壓抑,遇到的人都不怎麼說話。一問,嚇我一跳:出人命了!
昨天傍晚的審訊進行了兩個來小時,俘虜供認了很多:他原來是勞改農場刑期未滿的「壞分子」;在五湖四海戰鬥隊裡擔任小囉嘍;曾經參與過多起搶劫農民財物牲口的行動;那一次放火燒村民房屋是不得已,因為人少打不過貧下中農自組的防衛大隊,情急之下爬到一家茅草屋頂上,掏出火柴吆喝威脅:「你們再不退到遠遠的我看不見的地方,我就點火燒屋了!一盒火柴二分錢,燒你幾十間!」農民自衛隊沒後撤——他們哪個敢撤?所有的動產不動產全都在村子裡哪!
俘虜說,他見不動點真的嚇不走農民,就劃著了一根火柴,朝茅草屋頂湊去,邊湊邊吆喝:「我真要燒啦!」誰知夏末秋初的天氣,茅草屋頂讓烈日烤得脆乾,那根火柴還沒有碰上屋頂,就「騰」地燃燒起來。俘虜說,他嚇得一滾身摔下屋頂,躺倒在地爬不起來,被生擒活捉;十幾間茅草屋立時就燒塌了。俘虜的供詞劃了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法庭」再一次請示了「最高指示」,毛主席《對鎮反工作的批示(1950年12月19日至1951年1月17日)》早就教導說:「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掉的反動分子」。縱火燒掉那麼多貧下中農房屋的監獄逃犯,當然屬於「一切應殺掉的反動分子」之列。於是自封的「法庭」審判長審判員們一致投票,判處被俘的五湖四海隊員死刑。
死刑宣判了,可是執行卻成了問題:紅衛兵小將們敢於判決——那是抽象的殺人,卻不太敢去執行——那是具體的殺人。日後上面追查起來誰出頭露面去負這個責任呢?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紅衛兵武衛隊的總頭目「大肚子」回來了,問清了前後緣由,把白大舌頭一夥人痛罵了一頓:「你們這幫蠢貨,為什麼攬這種事?解放軍都不接收,你們充什麼大頭?你們以為農二哥(那年頭叫工人老大哥,農民老二哥)自衛隊都是老土?他們就是不願把這種殺人的麻煩事做到底,才把這個爛西瓜捧到你們手裡的!」 白大舌頭他們被罵開了竅,發現這個爛西瓜真正是不好收拾了:你不能把他給放了,放出去他再搶劫縱火甚至加倍報復村民怎麼辦?你也不能把他給斃了,你畢竟不是國家正式的法庭和行刑隊,槍斃犯人跟武鬥中互相開槍亂打是不一樣的。你把他往哪兒送呢?「公檢法」機關已經被打倒了,那裡早就沒人上班了。想不出個好辦法,他們只好把俘虜捆綁在院子中間的那棵大樹上,怕他半夜裡跑掉,手腳都給粗繩子打了死結。
開始的時候,俘虜還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紅小將們喂了他幾口水,又灌了他一點稀飯,就把他擱在那兒了。第二天早上七、八點鐘紅小將們醒來,發現那俘虜不吭不唧的、軟軟的靠在樹上,很慶幸他半夜裡沒有逃掉。過了一陣子見他還是沒動靜,也不要水要飯,就納悶的過去察看。湊近一看,人已經沒氣了。
「死人啦!他死啦!」所有的人都被這叫喊驚動到院子裡,望著那具死屍,束手無策。請示過本派大本營之後,紅小將們還是去把當地駐軍的代表纏過來,把前前後後的緣由說了一遍,做了筆錄,然後把那具死屍埋葬了。部隊來的一位軍醫(他臨時充當了法醫)說,那五湖四海隊員早就讓農民自衛隊給打得半死了才送過來的,而且好像是包在厚麻袋或者破棉被裡狠打的,所以不怎麼露外傷。農二哥們很精明,把這個麻煩輕易地拋給了革命小將。
一年多一點以後,武鬥息止了的宣城,置於全面的軍事管制之下,白大舌頭被軍事管制委員會下令逮捕,罪名是非法設立法庭、打死一名遊民。白大舌頭被關押了將近一年,其間他的可憐的父母家人為他四處奔波,找證人寫證詞,證明那名遊民其實是非法逃離勞改農場的犯人,證明他逃出來後還累累為害鄉民,證明那逃犯其實不是白大舌頭動手打死的,證明當時解放軍的兩名幹部還到場察看了五湖四海隊員事件的處理。近一年之後,大約是在1970年的年尾,白大舌頭被釋放。是無罪釋放?不是。是帶罪釋放?也不是。在既非「有罪」也非「無罪」的含含糊糊的背景下,白大舌頭日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賣力氣的活,養家糊口。
在白大舌頭被捕、坐牢的關頭,足智多謀、同時也是主要見證人之一的大肚子也幫不上忙,因為大肚子自己也落了難。他三次被莫名其妙地抓捕,三次被莫名其妙地釋放(邪門的是,他每次被捕,我都在場)。在看守所裡,他經受了各式各樣無產階級專政的折磨,包括大熱天正午烈日下,頭頂一盤水跪在水泥地上「反省」,水盤翻倒了就再加一個鐘點;把他的一隻手同另一個犯人的手鎖在一起,讓他們吃、睡、拉、撒都難伺候自己;24小時對他的「號子」(即小間牢房)播放高音喇叭,或者24小時在他的號子裡亮著五百瓦的大燈泡,讓他發發神經病。
大肚子反反覆覆被抓被放,也是宣城的專政部門趁心跟他玩「貓捉老鼠」的把戲:明明搜集不到他該坐大牢的證據——他雖然是我們紅衛兵的武衛隊大頭目,不過並沒有親手打死、打殘過人,也就是沒有血債、沒有債主——但卻恨透了他,要讓他嘗嘗「沒有終結的恐怖比恐怖的終結更恐怖」的滋味。此乃是因為「公檢法」系統在1966年夏至1967年冬期間,是屬於對方保皇派陣營的,經常被我們這一派衝擊,幾個主要的幹部也被我們戴高帽、掛牌子、遊街和批鬥過。用他們日後私下裡的話說,「我們專政系統的人,從來沒有給人當猴子玩過,你玩我,能讓你白玩?等到老子收拾你的那天,就要你大開眼界了。」
說白了,還是報復:被毛澤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號召鼓動了的造反派造過反的「專政機器」,同樣憑著毛澤東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的號召,報復那些造了他們的反的造反派頭頭。1969年下半年宣城處於軍事管制之下,老「公檢法」系統的幹部就專司臨時看守所——一處位於宣城北門長街中段的大院落,四周高高的、憂鬱的灰磚牆,那裡成了我們眾多紅衛兵頭頭和骨幹分子的「學習班高級階段」。「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是毛式政治智慧的精妙體現——不循任何法律程序把人抓起來、關起來,進行期限不確定的心理的、肉體的多維度懲罰,而又不冠以「監獄」的惡名。
「學習班初級階段」的所在地,便是我們宣城中學第二教學大樓的樓下大教室,可以容納二三十張上下鋪雙人床,我們這一派紅衛兵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四十多人,都住、吃、「學習」 在裡面。「學習」的內容就是每日每時沒完沒了的檢查交待:在過去的兩年武鬥期間,有沒有打砸搶抄抓、衝擊軍事禁地、搶奪槍枝彈藥、劫取國家機密、組織大規模武鬥、殺人放火放毒?其實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這些都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們——特別是林彪和江青——前兩年號召我們幹的,現在又反過來對我們秋後算帳。
每天清早我們就得起床、點名、排隊、上操,然後就是一整上午、一整下午外加夜晚幾個小時的「學習」。每隔兩三天,通常是上午十點來鐘或者下午三點來鐘、正值我們學習班成員精力充沛之際,就會有軍事管制小組和看守所的軍警人員來到我們學習班門口,學習班的班長——實為監管我們的人——一聲緊急集合口令,學習班成員們必須放下手頭的所有東西,跑步出教室來到樓前的小操場上排列成隊。這時刻從看守所來的原「公檢法」幹部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大聲地、緩慢地念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的最高指示,經過縣無產階級專政部門的查證,報縣軍事管制領導小組的批准,特此宣布對壞頭頭(或打砸搶抄抓骨幹分子)某某某實行隔離審查。」此時立刻就會有如狼似虎的三、四個「公檢法」人員搶進我們的行列,抓住被點名的那個人的頭髮,反扣他的雙手在背後,推搡出行列。扭轉他的身子,面朝向我們,來的警員拎起手中的紅白相間的一公尺多長的大棒,一個橫掃將他擊跪在地,帶上手銬。與此同時學習班班長帶頭呼喊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震天的口號聲中,人被跌跌撞撞的帶走。
所有這套程序,對我們紅衛兵小將實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黑色幽默的極致高度。在過去的兩年多裡,我們每天每日就是用這樣的程序對走資派們(包括那些「公檢法」系統的頭頭腦腦)作革命專政的——當時稱之為「颳十二級紅色颱風」,或「紅色恐怖」;現在對我們這幫紅色恐怖的先鋒部隊實施同樣顏色的恐怖,一點不改,一絲不苟,真是妙極了!我們學習班開辦之初,有四十餘人;就這麼每隔兩、三天被提走一人,誰也不知道人被提走的詳細緣由,誰也不知道提走以後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誰將是下一個被提走的——沒有終結的恐怖,遠勝過恐怖的終結,法國大革命陰影下的雨果之言,不虛矣!
一個半月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到末尾,我們「學員」裡面少了十幾個人,剩下的每個人少了十幾斤肉。我們那一幫人對中國政治、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對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之悟察洞悉,在「學習班」期間有了突飛猛進。
1989年5月底至6月初,鄧小平報復了膽敢再一次要掃除官僚階層的制度性特權的大學生——在他們的口號和行動上,鄧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了的那幫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幽靈再現。
還是江青說的到位
真正把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深層動機和這場革命自身內在的動力學一語點破了的,還是江青。她在「文革」一開始,就著手系統地迫害那些1930年代在上海演藝界比她有名、有錢、有地位、讓她吃過肉體或精神虧的男士女士們。演藝界裡她最想幹掉的人之一,是孫維世;孫是周恩來的乾女兒,中共那一代裡有名的美女和才女。她非但瞭解江青1930年代的底細,瞧不起江,而且據說1946年孫剛從蘇聯留學回國後,便被毛澤東看中且染指,是江青的多重意義上的敵人。1967年秋天武鬥高峰上,江青對林彪的夫人葉群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孫維世於是被葉群動用空軍部隊秘密抓捕關押,一年後不明不白的慘死獄中[1]。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的一場大會上評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林彪對此進一步展開:「壞人鬥壞人,這是『以毒攻毒』」[2]。
這兩位對「文革」中各色人等相互打鬥報復的精彩評說,大概都是摸透了毛澤東的心路思路。1966年北京和全國的「紅八月恐怖」的廣泛打人狀況傳到毛那兒後,毛的議論便是:「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3]。當時官方檔案稱江青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稱林彪為「毛主席最好的學生」,真不是拍馬屁;他們兩位對毛發動「文革」的心機和動機,確實理解得格外準確。
革命就是報復
我終於達到「革命就是報復」的普適性的理智認識,要歸功於一條後來查無實據的新聞報導。1989年六四慘案之後的頭一、兩個星期裡,各種各樣的謠傳飛滿天下。某一日我從美國的一家英文媒體上讀到,四川、重慶赴北京遊行示威的大學生們被從天安門廣場清場趕出京城後,悲憤於他們的同學和平請願卻挨殺被捕,立志要報仇雪恨,於是星夜趕回四川,欲去鄧小平的故鄉廣安挖掘鄧家的祖墳,這麼幹的理由是:「你老鄧下令殺大學生,讓別人家斷子絕孫,我們也要刨你的祖墳,讓鄧家斷子絕孫。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這條報導寫得有聲有色,令人讀來始而血脈賁張,繼之毛骨悚然——到了20世紀的末尾,中國統治集團中最具世界視野和大歷史感的改革總管鄧某人,與中國社會裡思想最激進、最渴望政治自由的大學生,在血仇報復這一點上,卻是那麼的心心相印!
以後的幾個星期裡,我一直密切關注著英文中文媒體對這條消息的追蹤報導;奇怪的是,猶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了音訊。我揣摩,那篇英文報導,當是洋人記者基於在中國的現場採訪參加學潮的大學生而寫成,因為那種刨祖墳報仇雪恨的觀念是典型的、地道的中華傳統的,非洋人所有。發了那種豪言壯語的大學生,可能說時有意,到了行動的時候或許就沒了膽;或者有膽量也沒機會——鄧家祖墳乃是龍脈所在,豈是不設防任你外人可進可出可動土可移石的?
把所有這些可能性考慮進去,仍然改變不了那篇報導所透露出的歷史深層訊息——革命就是報復。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乃至社會底層的賤民們,利用了紅色始皇帝毛澤東「對走資派造反有理」的聖旨,報復了自1949年10月以來一直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紅色官僚特權階層(此前,任何這類犯上的言論和行動,都會遭到及時的鎮壓)。鄧小平作為這個階層的最高首領之一,不但自己丟職喪權、受了諸般淩辱,他的基本上無辜的大兒子也被折磨成終身殘疾。1989年5月底至6月初,鄧小平報復了膽敢再一次要掃除官僚階層的制度性特權的大學生——在他們的口號和行動上,鄧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了的那幫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幽靈再現[4]。
旁觀者清
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那個冬天,我在哈佛文理研究生院宿舍的原來同樓層的好友Blanford Parker——他是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公認的過去十幾年裡最優秀的研究生[5]——忽生奇想,要與我合作一本英文書,敘述我自幼年起一直到進入美國為止的經歷。我們在飯後飲餘(他滴酒不沾,但每日飲胡椒味可口可樂的消耗量是我飲啤酒量的三到四倍),談論我的經歷跟他這樣同年齡美國人的經歷之差異時,他每每感歎:在他們聽來,我1980年代以前在中國的生活境況,是屬於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那些時代才可能有的事情。所以他覺得眾多的美國讀者一定會對這本傳記感興趣的。我們把書名都初擬好了,叫做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我告訴過他,我的祖父祖母是偏僻之極的鄉村裡貧賤之極的農民,活了一輩子只有姓,沒有名。
每星期有兩個下午,我倆在火爐旁坐下來,準備那本傳記。我口述,答錄機轉動,他隨時提問,發掘細節,理順故事的脈絡,一共錄音了將近40盤磁帶(每盤60分鐘)。他主張:我們的書就從1989年六四事件後四川籍大學生誓言要去鄧小平老家挖掘祖墳的報導起頭,因為——他解釋說——這個情節最具有古典希臘史詩和悲劇的意涵及韻味:它用「復仇」這一人類最本能、也最強烈的動機,把文化大革命同「文革」以前中國的政治社會不公,與「文革」以後的中國政治陰謀和搏鬥,天衣無縫地貫通一體。
還是旁觀者清。他對中國當代政治鬥爭在「革命」的大纛之下演繹出的一幕又一幕,比許多的中國問題評論員——黃皮膚的或者白皮膚的——看得都要明白。
[1] 參閱《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上冊(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再版),頁285-301。張朗朗:《孫維世的故事》(浴火鳳凰:http://chinatown, 無出版年月)。
[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頁74,268。
[3] 據紅衛兵1967年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未正式發表的毛澤東言論集),第二卷,頁204。
[4] 這當然不是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對「文革」造反派的首次報復之舉。1984年我出國前夕,在北京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說,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的原辦公室主任、哲學系名教授郭羅基剛剛被驅逐出京,發配至南京大學,就是有人恨郭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頗有影響,故在鄧小平面前告狀說:「文革」中鄧的大兒子就是被郭的那一個造反派組織折磨至殘的(告狀者並沒有出示任何證據,很可能毫無根據)。原本對郭羅基個人並沒有什麼印象的老鄧,勃然大怒,下令立即把郭「趕出北京」。
[5] 他的成名之作是研究18世紀宗教與詩歌關係的著作,學界對之評論極佳:Blanford Parker, The Triumph of Augustan Poetics: English Literary Culture from Butler to John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他堪稱慧眼識聖:早在1985年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任教皇的初期,他就對這位宗教領袖敬仰不已,稱之為當今世界上兩、三位最偉大的人物之一。20年之後,2005年4月8日星期五,全人類都見證了這一點。
| 新書快訊 |
| 閲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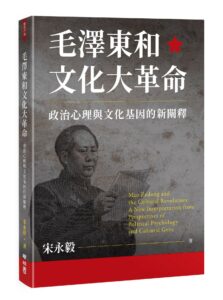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