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選自《思想的求索(思想1)》,原題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文革四十週年反思之一〉。
親身經歷過「文革」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於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論這「一般化」是由哪一個政治立場(中共官方的也罷,中共官方對立面的也罷)做出的。
一位美國老太太的提問
這大約是在1987年的暑假,哈佛大學的幾位資深教授(其中包括在西方名學府首開「中國文化大革命」一課的Roderick MacFarquhar [馬若德先生]),應邀赴美國西海岸三藩市地區的哈佛校友會作系列學術演講。此乃哈佛的傳統,在校友集中的北美洲的中心城市,每隔一、兩年舉行圍繞一個大專題提出系列報告,以便於哈佛歷年畢業的校友們有機會更新知識,瞭解他們所關心的那些學科裡正在從事什麼樣的開創性研究。這種知識的聯繫,會引導校友們對母校的捐贈和支持。
那一年哈佛校友會三藩市分會的新任會長是位李姓華裔人士,三藩市地區又是美國華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哈佛大學的教授演講團選取的大主題,因此都是與東亞區域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相關的。我當時剛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鬆了一大口氣,也被邀請進演講團。馬若德教授要求我以親身經驗為背景,講一講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那場激進得無與倫比的革命,卻導致了共產主義世界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資本主義化革命——鄧小平的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
每個講者只有一小時的時間,一半演講,一半回答聽眾的問題。我以我的初級階段的英語,概略的講了一下我當初為什麼成為紅衛兵中最狂熱激進的一翼的骨幹分子,把本校、本縣、本地區的走資派統統打倒了還不過癮,又殺奔外地,先是到省城去參與打倒省委書記、省長的造反行動,後又不辭辛苦,跑到鄰省的南京去聲援江蘇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他們省裡的頭號、二號、三號走資派的壯舉。我還講了我們怎麼編印紅衛兵戰報——我當年最有成就感的革命傑作之一,便是用19世紀的老式鋼板、鐵筆、蠟紙,手刻出小報的「原版」,以手推滾筒的技術,每張蠟紙「原版」油印出一千幾百份的紅衛兵小報,與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交流。我還不忘記強調,「文革」是我輩一生的首次、也是一生中最豐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訓練。懷存由「文革」學來的經驗教訓,你不但可以在中國政治風暴裡潛下浮上、死裡求生,而且可以在異鄉他國的政治濁流中辯風識潮、進退自保。
我的話音剛落,坐在聽眾席前部第三、四排右邊的一位六十出頭的清瘦高挑的白人老太太站立起來,用緩慢有力、一字一頓的語氣向我發問:「根據我從書籍、報刊上讀到的,從電視、電影上看到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數千萬的人受迫害、數百萬的家庭喪失了親人、無數的學校和文化遺產被毀壞,人類文明史上很少有幾次政治運動,破壞規模能夠比得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又讀到聽到,所有那些破壞人的尊嚴和生活、搗毀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動,都是由毛澤東的紅衛兵組織當先鋒隊的。令我不理解和驚訝的是,你作為一個紅衛兵參與了那些激進活動,如今已經來到美國,進了我們國家最好的大學讀博士學位,竟然至今你不為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感到懺悔。你在談論你們當年從事的造反運動的時候,甚至有自豪的語氣。我真為此感到非常困惑!」
老太太問完,並未立即坐下,立在那兒好幾分鐘,大概是胸中怒氣難消,凝視著我,示意她是在等候我的答覆,頓時全場氣氛凝重。我雖然被她重炮轟擊質問,但她一臉正氣,儼然是為不在場的千千萬萬「文革」的受害者們仗義執言,我也不好把她的嚴詞質問當做是對我的人身攻擊。於是清清嗓子,禮貌地作了應答,大意是「文革」整體雖然是件大壞事,但「文革」中被批鬥衝擊、皮肉受苦的人並不全然是無辜的好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無法無天地騎在老百姓頭上稱王稱霸、作威作福,造反派在「文革」中對他們的批鬥體罰,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的藉機復仇洩憤,雖然也不合法,但是有正義性,云云。
我所應答的,確實是我想說明的一個大道理,可是當時就覺得沒能把這個道理說透;沒說透,是因為沒想透。自那以後,每逢與人討論起關於「文革」的評價,我總是想起那位正義凜然的美國老太太,而我也老是不能忘記,當時她顯然並沒有信服了我的解釋。這麼多年來,我時不時地在腦子裡點擊那個問題。我也特別注意到曾經參與「文革」的海外人士中,有兩個同我的觀點很接近——楊小凱與劉國凱;這兩位關於「文革」的主要評論,都列入我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激進學生運動的比較」課程的學生參考讀物中。他們兩位都堅持對「文革」中的一些造反行動的原則性肯定(這一點使人易於誤認為他們是「極左派」立場),他倆同時又堅持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徹底批判(這一點又使他們與所謂的中國「新左派」、「極左派」涇渭分明)。
事過多年,我倘若再面對那位美國老太太的問題,會這樣向她解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各種人報復各種人的亂糟糟的大革命——說它亂糟糟,是因為一個本來就沒什麼法制的巨型社會,又讓一個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皇帝把他平時管治民眾的官僚體系跺得稀巴爛——其中有壞人報復好人,有好人報復壞人,有壞人報復壞人,也有好人報復好人(這四類經典分法的出處下文有交代)。當然這四種類型的報復所占的比例不一樣:似乎壞人報復好人的,最終要遠超過好人報復壞人的,而其他兩類報復的比例更小。所以親身經歷過「文革」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於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論這「一般化」是由哪一個政治立場(中共官方的也罷,中共官方對立面的也罷)做出的。
母親問我出不出面講句好話?我莊嚴的告訴母親:這不是張家跟我們家之間的私事,這是革命造反派和走資派之間的鬥爭大事。
「永世不得翻身」
我已經記不清是1967年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的哪一段時間的哪一天,我的母親——她從來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但從來為我擔憂不止——悄悄的問我:敬亭山(就是李太白所詠的那座「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的皖南山巒)國營農場的張書記的老婆想來看看我,不曉得我給不給她一個面子,接見她?
母親老老實實轉述的這句話,令我觸電般一震之餘,感到天下真是變了!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讓我們人下人翻身一躍成了人上人。我這個十幾歲的未畢業的初中生,憑藉一枝筆(文章和大字報)、一張嘴(演講和大辯論),成了本地紅衛兵的文攻主將,整個一大派造反組織的風雲人物。這「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革命小將凜凜威風,竟也令張書記的老婆低聲下氣的求見!「文革」以前,張書記在縣城十多里開外的敬亭山麓下,可是令男女老少聞之喪膽的名字。他領導的那個大農場,是這片頗為貧瘠的黃土地上數千農場工人及其家小(其中包括母親和我)謀生的亦農亦工的國營單位。聽說張書記當過解放軍裡的副營級幹部,見過外頭的大世面,也識得一些字,對他手下那些多半為文盲半文盲的農場工人和家屬,根本就把他們當做農奴加以管教。張書記走夜路時清清喉嚨隨便咳嗽一聲,周圍原本汪汪叫的狗們也會嚇得四處逃散。
在全農場裡唯一不怎麼怕張書記的,是位高副場長。高副場長也當過兵,是連級幹部,但他在「抗美援朝」的惡戰中被美國兵一槍打壞了一隻睾丸(即在臺灣頗為有名的“LP”)。他算得上是一位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一旦為什麼事極不順心,就會拎著瓶燒酒,爬上辦公室或者自己家的屋頂上(都是比較高的一層茅草大屋),坐在那兒邊喝酒邊罵人:罵缺德的美國兵哪兒不打,專朝他的命根子打,害得他成了半條漢子;罵某某同事(多半是農場領導班子成員)不尊重他這個老革命,欺負他大字不識一個,給他鳥氣受;然後就是向黨組織提訴求,要「賠老子一隻卵蛋」。那年頭的共產黨並沒有掌握先進的生物工程技術,哪來活生生的「卵蛋」賠他?張書記對他也只好讓三分。農場裡的任何其他人,都缺乏高副場長那樣的革命履歷,對張書記和對他家養的那條大狼狗一樣,畏懼之極。
大約是在1962年的夏初,農場由上級部門分配來一架模仿蘇聯型式的小麥收割機。巨大的木鐵結構的收割機停放在露天的曬糧食的場地上,對我們這些從未見過現代化大型農機的鄉下孩子來說,不亞於是侏羅紀的恐龍再現。孩子們圍著收割機又是看又是摸,膽子大的甚至爬上駕駛座,裝模作樣地扶著方向盤。夕陽西下的初夏的熱烘烘的曬場上,孩子們興奮過了頭,竟然沒有注意到下班路過的張書記。張書記一見到他視為無價之寶的嶄新的收割機旁竟然圍滿著小孩,小傢伙們竟敢對收割機又是撫摸又是攀爬,怒不可遏,大喝一聲,撲將過來。他有條腿不太好,平時走路,手裡常撐著一根木拐杖,時不時地也可以用來揍職工兩下。這當兒那根棍子被充分地利用,孩子們揍得哇哇鼠竄。
這群孩子裡數我個子最瘦小,而且我也不喜歡玩動手動腳的物事,全因為我手腳明顯的笨拙(往後長大了才知道那是小腦不甚發達的緣故)。別的孩子圍著收割機動手動腳,我只是站在一邊看熱鬧;張書記用棍子揮擊孩子的時候,我趕緊躲到遠遠的大草堆旁,還是看熱鬧。張書記沒去追逐孩子,轉身回來察看收割機,大叫一聲短缺了什麼東西。抬頭看見我站在草堆旁,喝令我走過去,問我是誰擰下了那只大鑼絲帽子?我搖頭說不曉得。張書記不由分說,揪住我的一隻耳朵就往他的辦公室拖。一邊拖,一邊斥罵:「你們這幫小雜種,敢碰我的收割機。一只大鑼絲帽幾十塊錢,你們拿小命來抵也抵不了。」他的辦公室離那塊曬場有一、兩華里之遙,中間還隔著一個小山坡。我的左耳被他緊緊擰著,跌跌撞撞地跟在後面小跑。開始的時候左耳根的劇痛還令我哼哼嘰嘰地哭叫幾聲;漸漸地,耳根麻木了;又漸漸地,左半邊臉也都麻木了。被他拖拽到辦公室後,他讓我靠牆站著,命令勤務員傳話到養兔隊去叫我的母親來訓話。
兔子養殖隊是國營農場下屬的一個小分隊,距離農場總部辦公室也有幾里地,張書記不耐煩再等下去,他拖絏著我跑了那麼遠,也累了。於是叫勤務員看管著我,自己先回家去歇氣乘涼。等到我母親從養兔隊跑來,我已經在張書記辦公室裡背靠牆根坐在地上半睡著了。母親看著我腫了半邊的臉,紫紅的成了一條線的眼睛,渾身的灰土和草葉,拖破了的膝蓋結著血痕,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天大的事。張書記的勤務員交待了幾句,就讓母親把我先領回去,說扣工資賠鑼絲帽的事明天再處理。母親問我事情的原由,我說我沒碰過收割機。母親把我渾身上下一搜,果然沒有什麼鑼絲帽。看著我腫得像爛南瓜一樣的臉面,母親眼淚一把、鼻涕一把地牽著我回家了。
那個初夏的夜晚原是很靜美的,敬亭山農場坐落的丘陵地帶有成片成片的桃樹,馬上就能收割的麥子散發著暖烘烘的、有點叫人頭暈的野香。天空清藍,月亮跟星星離我們都很近,收工回來的鄰邊的農場工人家裡冒著炊煙,把茅草的薰味播送到近近遠遠的四處。母親沒有生火做飯,她給我泡了一碗鍋巴,自己到屋後的草地上去哭訴。我對此已經習慣了——恐懼地習慣了。自從父親三年多前病逝以來,每逢遭遇到自己沒辦法對付的難事,母親唯一的去處,便是到亡父的墳頭上(如果路近的話)或者一片四周無人的荒地上,去跟父親的亡靈哭訴。母親相信父親在地下能聽得見她講述的一切,所以哭訴得實實在在、仔仔細細。末了她一定會埋怨父親為什麼把這樣重的一副擔子推給了她,讓她這麼一個一字不識的沒用的人活在世上,照看他的唯一的骨肉(指我)?為什麼不讓她去頂替了又識得幾個字又有一份正式工作的父親去死?老天為什麼瞎判人的生死?
第二天母親開始收拾東西,稍微有點用能帶走的,打起包;不能帶走的,送給了四鄰。幾天以後,母親領著我離開了國營農場,又開始了幾近討飯的生涯。兩年多以前,我們母子倆就是從幾近討飯的境地來到這家農場的。在母親送四鄰東西的時候,鄰居勸她不要捨了農場出走,這裡好歹有一口雜糧糊飽肚子。母親說她曉得,三年大饑荒剛剛熬過,誰還敢看輕了有口雜糧吃的日子!可是母親有她的擔心,對鄰居說了,大家也無言以對:「我孤兒寡母,張書記要你的命,你也只好給他。小歪頭(我在鄉下時的別名)大大——金寶圩的土話,即『爸爸』——只有他這個親骨肉,臨死的時候託付了我,做牛做馬也要把他帶大。呆在農場裡張書記把這孩子打成殘廢,我也沒的地方去告狀。」
誰也想不到的是——這不是套話,真是任誰也想不到——不過五、六年的光景,張書記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見她!母親一輩子受人欺負,對所有的落難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趕快答應下來。接見是在宣城北門的一間賣豆腐的小店鋪裡進行的,是在一個陰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馬大的張書記老婆不但自己來了,還帶來了她的大女兒和小兒子,讓我看在她孩子們的份上,幫她家說句話。「你曉得,」她說,「老張他死了。」她挽起破爛的外衣下擺擦擦眼睛,雙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裡令農場大人小孩不敢仰視的又冷又辣的光彩。
張書記的死訊我也是得悉不久,據說——我在這翻天覆地的「文革」高潮風頭上,忙得根本顧不上去敬亭山農場——他是被農場造反派連連批鬥而病死的。造反派們對這位走資派施加了比對其他的走資派酷烈得多的懲罰:給他戴的高帽子特別高,頂著這麼高的帽子遊街示眾,一不小心掉下來,就會挨耳刮子。有時候給他掛的牌子是用特別厚重的木板做的,鑽兩個孔,細鐵絲穿過去,掛在脖子上,批鬥會開兩、三個鐘頭下來,頸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滲出血滴。天不冷的季節,還會罰他穿一條單褲跪在尖細石子地上,向所有受過他種種欺壓——辱罵、捆綁、關押、毒打——過的農場工人和家屬們請罪。張書記剛開始的時候還嘴硬氣傲,不主動向他往日視同農奴的下屬們下跪請罪,造反派就強按著他的腦殼,一腳橫踢他的內膝,便撲通一聲倒地。幾次下來,他就學乖了,要他怎麼跪就怎麼跪,要他怎麼罵自己就怎麼罵。據說他的血壓與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腫。那個寒冷的冬天他沒能挨過,「翹辮子」了。
「老張他以前迫害革命群眾太多,民憤極大,死有餘辜,我們全家堅決跟他劃清界限。」張書記老婆像背書一樣熟練地說著那個年頭無數的黑幫、走資派的家屬都不得不說的話。「不過,」她的眼淚又淌下來,「他死後的喪事,我們家請求造反派按照毛主席的政策辦。」原來,農場造反派得知張書記死了,不讓他的家屬立刻入土安葬。據說造反派頭頭們為此專門開了會,做出革命決定:把張書記家那條咬過許多農場職工和家屬的大狼狗給打死,與張書記合埋一個土坑,潑上豬血人糞,這叫做「惡狗伴惡人」。
在那一片鄉村,按照代代相傳的信念,一個人死了若是與豬、狗之類的畜牲同葬,又潑上血糞汙物,死者就永遠不得轉世為人,而會一輪一輪作豬狗,死者的子女後代也永不得好運,像豬崽狗崽一樣卑賤,任人宰割。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都呼喊的一句口號:「把某某某(走資派的名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敬亭山農場的造反派們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要用這個葬法來具體落實「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造反判決。張書記老婆就是為這事來的,她求我去跟農場造反派頭頭們說說情,不要讓張家的子女後代因為張書記生前的作孽而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張書記老婆說著說著,就要讓她的女兒和兒子對我下跪哀求,我母親立時擋住了,說我一個孩子受人跪拜,會折陽壽的。張書記老婆馬上補加一句:小丁(她不敢再以我的鄉下別名稱呼我)也受過老張的迫害,不過小丁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革命小將,心大志大肚量大,不會計較過去的事。所以來請丁小將出面打個招呼,讓農場造反派手下留情。
我鐵著臉,沒表態。張書記老婆說到這裡,給我母親低頭深深彎腰一鞠躬,帶著兩個孩子退了出去。母親問我出不出面講句好話?我莊嚴的告訴母親:這不是張家跟我們家之間的私事,這是革命造反派和走資派之間的鬥爭大事。最終,我也沒有去和農場的造反派替張家講情;我不迷信,並不相信張家的子女後代會因為張書記與狗同葬而淪入萬世不劫的厄運,不過我認定惡狗伴惡人下土坑的葬法,乃是革命的正義的行動。
延伸閱讀:
丁學良:革命就是報復,文革的幽靈正不斷重現(二之二)
羅四鴒:專訪宋永毅——唯有甄別史料真偽,才能認識文革性質
陳永發:從解讀權力到探索人心——宋永毅的文革見證
| 新書快訊 |
| 閲讀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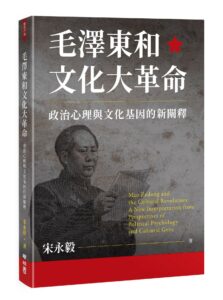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