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1年11月3日,哲學家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逝世,享年91歲。李澤厚是中國八十年代思想啟蒙和「美學熱」的關鍵人物,在哲學、美學、文學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1996年,學者黃克武撰文評述李澤厚的思想動向,刊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我們藉文回顧李澤厚先生的思想動線,了解其在當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 感謝黃克武先生授權轉載,論文原題為《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 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標題為編者擬。
李澤厚的思想內涵與變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因為硏究他的思想不但可以認識他一個人的想法,也可以了解受他影響的「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趨向……
摘要
本文的主旨在探討當代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李澤厚的思想變遷。在前言中作者描寫李氏的主要作品與基本理念,及其在海內外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無可否認地,他的思想是當代中國思想光譜中不可忽略的一環。 近年來有不少人對李澤厚的思想感到興趣,引起熱烈的討論,主要有以下六類:1.中共官方與正統的馬列主義學者的看法;2.海外學者的看法;3.台灣 學者的看法;4.大陸較年輕的學者,尤其是反傳統主義者,對李澤厚思想的評估;5.目前身居海外,在思想方面已經擺脫了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又較傾向自由主義之大陸學者的意見;6.墨子刻教授(Thomas A. Metzger)的看法。作者認為以往的研究主要都依靠1989年3月以前的作品,來顯示李氏思想中結構性的特點,而忽略了思想的變遷。本文則以李澤厚與劉再復最近所出版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1995)為史料,注意到李澤厚思想發展的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亦即是文中所提出的從「轉化」轉向「調適」的過程,作者很詳細地描寫此一變遷過程,並進一步分析其在當代思想史上的意義。
一、前言
1930年出生於漢口的李澤厚是當代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初中畢業之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開始廣泛閱讀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書,據事後的回憶•在當時所接觸的各種學說之中,讓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馬克斯主義」。共產革命成功後的第二年,李澤厚以第一志願進入北大哲學系,師事後來治中國哲學史享有盛名的任繼愈先生。1958年他將進入大學以來所發表有關改良派思想的五篇文章集成《康有爲譚嗣同思想硏究》一書,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文革期間他在河南明港幹校接受勞動改造,並偷偷地閱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1972至1976年依靠以前的筆記撰成《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提倡將康德、黑格爾與馬克斯結合成的「主體性的實踐哲學」[1]。
李澤厚在哲學、美學、文學史、思想史方面的硏究成果,在數量上十分龐大,1978年之後是他的著述的高峰期,主要的作品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美的歷程》(1981)、《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1985)、《中國古代思想史論》(1986)、《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美學四講》(1988)等書。李氏原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硏究所的硏究員,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因同情民運,不容於當道,1991年底在多方支援之下獲准出國,目前在美國科羅拉多學院哲學系任教。[2]
李澤厚雖然廣泛地涉獵文學、史學、美學、哲學等科目,但其理論基礎無疑地是哲學,根據他的自白,在這方面主要的著作有1964年的〈人類起源提綱〉、1979年出版、1984年修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以及其後由此衍生出三個主體性論綱(即〈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關於主體性的補充說明〉、〈關於主體性的第三個提綱〉),最近的一篇則是1989年出版的〈哲學答問錄〉。[3] 他自己將他在文革之後所逐步建立的哲學思想槪稱為「中國的後馬克斯主義」、 「人類學本體論」或「主體性的實踐哲學」。簡單地說,他嘗試一方面保持馬克斯主義最基本的歷史唯物論,以「製造和使用工具」作為認識社會與個體的根本,又反對重視階級鬥爭並壓抑個性的馬克斯式的革命理論;另一方面則主張保留中國傳統的精華(其中包含儒、釋、道及其它成分),並加入西方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的一些想法,而在上述思想綜合的過程之中,美學觀念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和一些德國學者一樣,給予美學以最高的地位,以為通過審美精神的培養,可以使個人獲得自由,使社會得以改造,而天人合一的審美表現更可以「替代宗教」。李澤厚對傳統的肯定有許多地方是與他所謂的「現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 等人)等人很類似的,但很可惜,他並不肯定他們在「花果飄零」情況下的開創之功,反而說這些人雖有「一定的創造性」,但其作用比起馬列來,「渺不足道」。[4]
李澤厚的著作影響十分深遠,正如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兩位靑年學人陳燕谷與靳大成所說的:
當「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很多人還處於思惟混亂的情感宣泄狀態時, 大部分人還在撫摸昨日的「傷痕」時,李澤厚即以其獨到的洞察力和思想深度爲創造成熟的歷史條件進行了寶貴的思想啓蒙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實際上成為中國人文科學領域中一個思想綱領的制定 者,他的哲學、美學、思想史著作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他的)思想像一股暗流潛伏在每一個熱血的思考人生的人心中。[5]
難怪有人認爲從1978至1988的十年中,大陸學界四次有關意識形態的重要辯論都與李澤厚的作品有密切的關係。[6] 另一位大陸著名的學者劉再復也坦言,他的「文學主體論」觀念的哲學基礎即爲李氏的主體性的實踐哲學。[7] 而教委在全國的調查竟發現,「幾乎所有文科硏究生宿舍裏都有李澤厚著作」。[9] 因為李澤厚影響力的廣大,1987年9月香港《明報月刊》提名他爲當代四大思想領袖之一,與方勵之、金觀濤、溫元凱齊名。1990年法國國際哲學院選他爲院士,這是繼三十年代馮友蘭之後第二位當選的中國人。1994年合肥的安徽文藝出版社還爲他出了一套作品集,在大陸各地廣泛流通。
他的聲名不但在中國大陸、香港與海外,在台灣也是炙手可熱,除了《美的歷程》一書享有盛名之外,他的三本思想史論也幾乎是所有關心中國思想史之學子的必讀書籍,在台灣各地書店也多半可以找到他的作品。
1995年李澤厚與同樣流亡在外的劉再復出版了一本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以主體性實踐哲學理論批判二十世紀強調革命、 壓抑改良的歷史文化現象,並主張由此重新評估中國近、現代史,這些看法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雖然有些人對於他高度肯定鄧小平經濟改革的看法表示質疑,認為他有「非學術的用心」,但也有不少人肯定他支持改良的立場。[9]
毫無疑問地,李澤厚的思想內涵與變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因為硏究他的思想不但可以認識他一個人的想法,也可以了解受他影響的「整整一代人」的思想趨向;[10] 換言之,在當代中國思想的光譜(intellectual spectrum) 之中,李澤厚的思想是不容忽略的一環。 那麼他的思想有何特質?許多讀者或許也很想知道他是否脫離了馬克斯主義?又是否轉向英美的自由主義?在這篇文章中我無法對李澤厚的思想作一全盤性的硏究,這需要分析他所有的作品,並評估對他思想的重要討論, 可能要一本書的篇幅才能徹底處理。我目前只想扼要地回顧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尤其是他的思想中意識形態之傾向的一些主要的評論,而將之置於當代思想發展的前後關係之中;其次則是針對這些眾說紛紜的說法,提出我的觀點。我認為以往的硏究都看到了李氏思想中結構性的某些面向,而忽略了思想的變遷,尤其是沒有掌握李澤厚思想發展的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亦即是我在下文將詳細討論的從「轉化」轉向「調適」的過程,因而對李氏思想的認識有所不足。上述李澤厚與劉再復所出版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可以支持我的假設,因此我將描寫這本書的思想內涵,藉此顯示李澤厚思想的變遷,並分析此一變遷在當代思想史上的意義,冀望對「李澤厚硏究」乃至當代大陸思潮的了解有所助益。[11]
李澤厚的主要觀念是什麼?有何變遷?他的思想是否受到一些不自覺的預設之影響,而呈現出混雜、紛亂的面貌?……
二、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
李澤厚作品的涵括面非常廣,創作的時間又跨越了50到90年代的四十多年,其中自然表現出歧異性與矛盾性。在這樣的性格之下,他受到多方的抨擊,甚至遭到立場截然相反的人兩面夾攻,似乎不是一件讓人意外的事。綜而觀之,近年來對李氏思想的討論約略觸及了描述、因果分析與評估等三個層次。 在描述方面學者們希望澄淸的問題有:李澤厚的主要觀念是什麼?有何變遷?他的思想是否受到一些不自覺的預設之影響,而呈現出混雜、紛亂的面貌?描述工作也包含比較,這樣一來他的思想與馬克斯主義、黑格爾思想、以彌爾(John S. Mill)爲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以及中國傳統主流的價値取向有何異同?在因果分析方面,學者們所問的問題包括:他的思想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還受到那些因素影響?例如是否受到他所處的政治環境影響(有人以為政治的高壓使他表面上肯定馬克斯思想,但暗中加以唾棄;有人則以爲政治環境的鬆動,使他可以批評或調整正統馬克斯思想)?他的思想與文革後鄧小平所主導的經濟改革有無關係,是否為此一改革時代的反映?他的思想與心理上的苦悶有無關連?再者,是否因爲他無法挖掘出某些來自傳統的思想預設而影響其思想取向?在評估方面,他的想法是對還是錯?或更精細地說,那一部分對而那一部分錯?而評估的標準又是什麼?以下將分別敘 述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評論,以及李澤厚對其中幾種評估的回應。
- 中共官方與正統的馬列主義學者的看法。1988年之前李澤厚與官方仍維持較好的關係,因為他在學術方面的卓越表現,1988年李澤厚曾當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官方對他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六四之後至1991年底他獲准出國之前的一段期間。他們將李澤厚的思想描寫爲反對馬克斯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對他們來說,馬克斯主義是正確的。所以李氏受到負面的評估,其思想被視為解構正統意識形態的毒素。在前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部長王忍之與副部長賀敬之操控下,[12] 有關方面曾召開了兩次討論會,[13] 共有數十篇文章圍批李澤厚,所指控的罪名是「貶低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和歷史功績,懷疑或否定馬克斯主義的指導地位,蔑視和否定中國人民對 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香港雜誌的撰稿人認爲這些批判的語調、口吻與文革時的大字報是一樣的。[14] 李澤厚自己則說這些人是以煽情的方式拿「資產階級」、「反馬克斯主義」的大帽子來唬人,缺乏論證,不講道理,但是對「早已戴慣了大帽子的我,只覺得好笑,甚至一點也不生氣」。[15]
- 海外學者的看法,多半與上述中共官方之觀點截然相反。他們將李澤厚視為反對(錯誤的)馬克斯主義的異議分子,因而予以肯定,此外也有一些描寫與因果的分析。例如有些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以為李澤厚是代表知識分子的良心,他的作品中的馬克斯主義是在外在環境壓力之下,爲自我保護所披的一件外衣,李氏的內心其實已經抛棄了馬列主義。[16] 傅偉勳的意見與上述看法類似但略有不同,他認為李澤厚力圖打破馬克斯主義教條,但因爲種種原因,無法掙脫枷鎖,從而陷入一種心靈的苦悶,所以李澤厚的思想一方面還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表現出馬克斯主義教條在他身上的延續性,另一方面他對主體性的強調與美學上的努力則「有衝破馬列羅網之勢」。[17]
1992年在英國出版的The China Quarterly之上,有一篇Lin Min (林敏) 所寫的〈現代性的追求:1978至88年間中國知識分子之論述與社會一李澤 厚的例子〉(”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78-88 —— the Case of Li Zehou”),作者反對上述「拋棄」或「苦悶」的說法,而特別注意到現實環境與其思想的因果關係。作者以為78至88年之間,因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與相對來說較寬鬆的政治取向,使中國知識分子 有一較自由的活動空間,對馬克斯主義進行反思,他認為李澤厚正是這種社會與思想狀況下的代表人物。李氏的理論與中國改革過程中兩個特色:一是鄧小平重視經濟發展的現代化方案,一是基於國家與歷史文化傳統認同之民族主義,有一種「結構上的親近性」。他說「李澤厚並不想完全拒絕現存的意識形態,而是想修正與改革它,使之不那麼教條化,而變成一種更為開放與具有動力的思想」。他以李澤厚對主體性的討論來作說明,認為李氏主體性的觀念仍在傳統馬克斯主義以經濟基礎與客觀情況爲最優先的前後關係之中,只不過他強調人類實踐之客觀內容與主觀創造性是分不開的。總之,李澤厚思想是在馬克斯主義陣營之內的調整,他企圖使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更廣闊與更開放的哲學。[18]
- 台灣學者的看法。主要是評估性的,其立場與中共官方之觀點也是針鋒相對。他們以為馬克斯主義是錯誤或是有局限性的,李澤厚的問題在於他沒有離開馬克斯主義。如朱浤源在評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時指出,李澤厚對共產社會雖有批評,但基本上他肯定官方學說與國家領導人的正統性,「他完全是深深護著馬列毛。為了讓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得以更加發揚光 大,李澤厚勇敢地站起來,在共產的陣營裏,努力地在根處自我檢討」。他最後的評論是:因爲「馬克斯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這塊土地」,「馬克斯主義進入中國的局限,也正是李澤厚這位思想史家的局限」。[19]
- 大陸較年輕的學者,尤其是反傳統主義者,給予李澤厚思想負面的評估。如劉曉波激烈地抨擊李澤厚較「保守」而肯定傳統之「精華」的立場。 在《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1989)一書中,劉曉波談到他和李澤厚的主要區別「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他一分爲二,精華糟粕分得淸楚,我全盤否定,看不到精華,只見糟粕」,所以劉大力批判李澤厚所肯定的最深層的「中國的智慧」。[20] 例如對李澤厚來說,儒家「天人合一」的理想超越了倫理,達到了與宗教經驗類似的最高的審美境界,他認為此一境界不只是感性的愉悅,也是心靈的滿足或拯救,是人向天的精神回歸;[21] 但是對劉曉波來說,天人合一卻是中國人形成依賴人格之淵藪,這種依賴人格使中國人無自主性、無能動性,走向極致的奴化人格。劉、李兩人對傳統的不同評價,使他們對於未來應採行的方法有不同的構想。李澤厚倡導「西體中用」, 主張用新的現代化科技與本體意識來對傳統積澱或文化心理結構進行滲透, 從而造成遺傳基因的改換,亦即對傳統文化作出「轉換性的創造」;劉曉波則主張「全盤西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主要在於五四以來反傳統與西 化做得不夠徹底,他驚世駭人般地說:中國要實現一個眞正的歷史轉變需要 「三百年的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23]
李、劉兩人的爭論也涉及雙方對理性與感性的不同看法,誠如顧昕所指出的,劉曉波受盧梭、尼采與沙特的影響,有非理性與道德相對論的人生觀,肯定浪漫的偶像破壞情懷;李澤厚則強調「理性」的重要性,認為劉曉波是「紅衛兵心態」,他的文章「只有情緖意義」,是極壞的學風與文風。 [24]
- 目前身居海外,在思想方面已經擺脫了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又較傾向自由主義(尤其是英國學者伯林與卡爾波普之思想)的大陸學者的意見,他們的看法有描寫性也有評估性。這些學者認為李澤厚思想的根基是黑格爾,而不是他所宣稱的康德,有人並指出李澤厚的黑格爾思想是和儒家傳統的思想預設交織在一起;因為黑格爾思想及其相關的預設從自由主義的角度 來看是錯誤,李氏不自覺地陷入黑格爾主義,因此也是錯誤的。
較早提出此一觀點的可能是甘陽,[25] 他在1989年所出版的《我們正在創造傳統》一書中就說「儘管李澤厚1980大叫一聲要康德不要黑格爾,其實李 公之『康德』正是黑格爾式的『康德』, 其《批判哲學的批判》全然是從黑格爾來看康德的,道理很簡單:李澤厚若把康德與馬克斯相連,不通過黑格 爾爲媒介,根本辦不到。根本差異就在於:康德所謂的以『審美』來調和,乃 是『虛』調和,而非『實』調和,亦即只是在『藝術』中的調和,決非『社會』實際上的調和。在『社會』實際中,『工具理性』與『價値理性』不可能調和」。[26]上述的論點在顧昕1994年出版的《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中國知識分子:李澤厚硏究》一書中有更充分發揮,他提出對李澤厚思想的一個類似的詮釋:黑格爾主義是李澤厚思想中的一個幽靈。顧昕首先批評了上述傅偉勳(我認爲也包含部分台灣學者)的意見,他認爲為了了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不能從外部政治壓力來解釋,而應注意到這些人思想之中「未加反省的思想預設」,這樣才能認識到爲什麼這些異議人士一方面批判「官方正統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的教條」,另一方面交是「堅定的馬克斯主義者」。 顧昕指出李澤厚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斯主義其實是混雜了從中國傳統而來的「不自覺的」預設。他指出的預設例如:一元論與本質主義的思想情懷, 由此導致一種壯觀的「形上學建構」,以期爲終極的爲什麼問題提供一勞永逸的解答;一種與目的論歷史觀結合在一起的「進步」觀念;以及墨子刻所說的「樂觀主義的認識論」、「精英主義」等(下詳)。顧昕認為李澤厚「主體性實踐哲學」就是以上述的預設為基礎,他的結論是李澤厚將康德的主體性和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納入了一個黑格爾主義的龐大框架之中,他是一個深受傳統思惟模式影響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斯主義者。[27]
他進一步表示李氏的思想中歷史決定論、目的論與極權主義的深切聯繫。因為根據自由主義大師伯林(Isaiah Berlin)的說法,在目的論的體系之下的「不可避免」的觀念將使人們喪失選擇的自由,僅能聽從精英分子的領導,跟著他們所提供的唯一解答前進。所以:
儘管李澤厚在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統治依然堅固的中國是一位勇敢的不合作者,但是他在精神上卻和這種意識形態有著牢不可破的合作……這不是由於言論自由的缺乏而導致的一時的歷史現象,也不是深受極權主義政治迫害之苦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採取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文化危機之深的一個集中表現。
總之,顧昕認為雖然李澤厚是一個自由的愛好者,也對極權主義有強烈的批判意識,但是他在批判時所持的理由、思惟模式或思想預設同極權主義 「如出一轍」,這種吊詭的現象就是他所謂當代「中國文化的危機」。[28]
齊墨在1995年論李澤厚的一篇文章中對李澤厚的生平有翔實的敘述,至於思想方面的討論,他基本上同意顧昕上述的論斷。他說「顧昕在一項研究中通過詳盡的分析,令人心服地指明了李澤厚思想體系與黑格爾主義的聯繫」;他也跟著顧昕強調李澤厚思想的預設:李澤厚美學思想要將人類引向「人間天堂」,而他的主體性哲學表達了他對真善美統一,與創造理想社會 的信念。再者李在論證「美是自由的型式」時又說「真正的自由必須是具有客觀有效性的偉大行動力量。這種力量之所以自由,正在於它符合或掌握了客觀規律」,齊墨認為其中透露出目的論與決定論的歷史觀。接著他再次跟著顧昕從西方像伯林那樣的自由主義者的角度將李澤厚思想的預設與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連在一起:
現代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已經反覆證明,歷史決定論和一元論將導向極權主義。所以,儘管李澤厚在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大統治下,依然 保持了一個異議知識分子的身分,但在思想上卻有與這種極權主義意 識形態相通之處。[29]
上述甘陽、顧昕與齊墨等人的看法成為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最有力的批判,對於這樣的批評,李澤厚認為他們和上述中共御用文人對他的指控是類 似的,「大陸是『資產階級』、『反馬克斯主義』等帽子,海外的是『馬克斯主義』、『本質主義』等帽子,帽子不同,模式一樣」。[30] 很可惜李澤厚只是一語帶過,並沒有仔細地反駁這樣的指控。
然而這些指控是很成問題的。比方說,顧昕等人認為因為李澤厚將美學領域之精神自由與政治自由混為一談,形成以審美精神為歸趨的目的論的歷史觀,因而不自覺地成了極權主義的幫凶,此一說法有值得商榷之處。此一 分析的前半段是正確的,李氏的確有以審美為歸趨的目的論,但問題是這種目的論與極權主義有無關係。顧昕用伯林的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的區別,[31] 認為李澤厚所有的積極的自由觀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歷史必然性的觀念,使李氏一方面是自由的愛好者,另一方面與暴君和迫害者「形同伯仲」。這裡可能有對伯林的誤解,伯林在〈兩種自由概念〉演講中的論證是十分細膩的,他認為積極的自由可能但不必然支持集體主義或極權主義,有時它和消極的自由一樣會融入自由的個人主義傳統。[32] 顧昕與齊墨卻說李澤厚所主張的「自由」,因為帶有歷史目的論的思想預設,因而不自覺地「配合」甚至「增強」了極權統治。這顯然忽略了伯林所說兩種自由之間複雜的因果關係,也給李澤厚戴了一頂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帽子。
- 墨子刻先生(Thomas A. Metzger)的看法,多半是描述性的。他以為李澤厚仍然跟著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主流的一些思想預設。在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錢穆講座,墨氏以中國學者杜維明、楊國樞、金耀基與李澤厚和英國學者 John Dunn的思想為例,建構二十世紀中、西兩種十分不同的政治討論的論域。中國的主流思想他稱為論域一(discourse# 1),西方像Dunn那樣的想法則是論域二(discourse2)。他所說的兩個論域實際上包括了墨子刻先生以及我的一些作品中所多次提到的認識論方面「悲觀主義的認識論」與「樂觀主義的認識論」的對立,以及歷史觀方面韋伯與黑格爾、馬克斯對歷史本質與因果關係的互異看法。此外他還討論到兩者在群體之目標(goal)與實踐目標之方法 (agency)兩方面。
首先要對樂觀主義認識論與悲觀主義認識論兩詞略作說明,此一對立的概念由墨子刻先生所首先使用,代表了他在分析中國思想史時所提出的一個新的角度,最近顧昕的書中也多次引用。過去對「認識論」(epistemology)的 探討多數是哲學家研究「人們應該如何區別合理與不合理(sense and nonsense) 的觀念」。墨氏的用法則不談應該的問題,他強調的研究取向是儘可能中立地描寫歷史人物對於這個區別的看法。他所謂的樂觀與悲觀即是為了描述人們對於獲得正確知識所有的態度。根據他的區別,強調樂觀主義認識論的人傾向於表達人類在獲得知識上的信心;而強調悲觀主義認識論的人則注意到彌爾所謂的「個人在本質上的易犯錯性」(fallibility)的觀念,認為人類在本質上有很強的犯錯的傾向,所以知識的獲得是比較困難的。當然此一區別不是一種二分法,因為幾乎在所有人的思想中,樂觀與悲觀的傾向都是交織在一 起,只是有些人較悲觀,有些人較樂觀,問題是結合的方式與兩者的比重。 墨氏認為中國儒家傳統與二十世紀中國主要思潮(包括三民主義、馬克斯主義、自由主義與人文主義,當然李澤厚也在其中)都表現出對掌握真理的較強的信心,所以是傾向樂觀主義認識論的,即以為無論是在實然方面(此處所謂的實然包括情感性與形而下的現象,以及宇宙的本體,也包括文化的本質與歷史的法則),還是在應然方面,客觀的真理是存在的,人心能完全了解這些真理,並能將所有的真理會通起來,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而西方懷疑主義、相對主義以及彌爾的自由民主理念則較傾向於悲觀主義認識論。從悲觀主義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對於上述樂觀主義認識論所提出的命題,如人心可以了解應然的真理、了解宇宙的本體、能建立完整的體系等,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然而,不容諱言的是,西方也有傾向樂觀主義認識論的思想, 如黑格爾主義,更何況基督教思想。從墨氏的觀點來看,要評估那一個認識論最合理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李澤厚的樂觀主義認識論是否合理也是很有辯論餘地的課題。[33]
墨氏認為以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論域一與以Dunn為例的近 代西方政治論域二,不但在認識論方面是格格不入,也在關於群體的目標、現實世界(例如宇宙與歷史),與達成目標的方法等方面很不相同;換言之, 兩者對於界定目標、知識、歷史、方法等四項之「理性」有其自身的看法。
上文已討論過認識論方面的問題。就目標來說,論域一較具烏托邦色彩, 傾向將道德、知識、政治權力、個人自由融合在一起,以追求無私的政治, 並冀望能解除束縛與終止異化。論域二則較避免烏托邦理念,認為無法將知識、道德、政治權力與個人自由結合在一起,在上述四者之中特別強調個人自由的選擇,這樣一來人際的衝突、妥協是不容易避免的,而政治生活只能減低而無法消除自私、偏見、束縛與異化等現象。
在歷史方面,論域一傾向主張歷史的發展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很大規模的方向或有很清楚的系統,例如用「封建」或中國文化的「超穩定結構」 等概念來描寫歷史;並對每一個系統加以評估,以為它是一個壞的「幽靈」、 「魔咒」,或是一個好的「精神價值」等等。再者世界歷史被認為是朝向目標發展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當代中國,和西方比起來,因為由其系統所導致的諸多病症,無法正常地發展。論域二則不那麼強調大規模的模式(或系統)、清楚的歷史法則與進步的觀念,但吊詭的是,論域二的許多思想家也同意歐美是文明發展的模範,而中國則因各種因素逸出常軌。
在實現目標之方法方面,論域一有精英主義的色彩,認為人群之中可以清楚地界定某些具有道德與知識的群體,引導大家追求目標,像所謂的「先知先覺」者;論域二則以為正確的領導不那麼容易找到,即使有也可能是暫時性或試驗性的。[34]
墨氏主要依賴上述的分析架構以及李澤厚的三本思想史論來探討李氏思想的特點,他認為李澤厚和二十世紀很多其他中國知識分子有相同的思想預設,李氏屬於馬克斯主義版本的論域一的思路(Marxist version of discourse #1)。其思想有以下六個特點:1. 主張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此一唯物主義成功地將主體與客體結合在一起,而無論二元性的康德或一元性的黑格爾思想卻沒有達到此一主客統一的目的。(這一點他同意顧昕對李澤厚思想的研究) 2. 唯物主義包含了決定性的歷史則律,亦即辯證式的歷史發展。3. 人們應以積極而革命的方法來遵循此一歷史的則律。4. 此種革命的過程包括個體為群體的犧牲。5. 歷史的法律也指明人類歷史發展是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的過程,這是一種階段性的、目的論的歷史觀。 6.毛澤東成功地以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封建」,但是卻錯誤地,在物質基礎未有充分進步之前,冒然推行社會主義,因而釀成悲劇。[35]
他的看法與顧昕追求李澤厚「思想預設」的努力有不少是相互配合的, 顧昕在他討論李澤厚的書中即多次引用墨氏所說的「樂觀主義的認識論」(其中包括將實然與應然結合在一起的看法,頁83、138、281 )、「目的論歷史觀」(頁194),和「精英主義」(頁142)等,顧氏並對這些看法深表讚賞。
墨氏也以為顧昕的書有其長處,但他覺得顧氏在該書中所顯示與李澤厚的對話,不如李澤厚在他的書中與康德之間的對話來得平衡與深入。而且顧氏雖然區別了西方自由主義與中國人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了解,但是他卻沒有 區別黑格爾與「中國思想中的黑格爾」,更何況如果這方面沒有徹底的討論, 就很難決定思想的「幽靈」是什麼。比較重要的是,顧氏以為李澤厚主客合一的目標是從黑格爾來的,可是李澤厚自己卻明白表示這個目標與宋明理學 「天人合一」的理想相同,而宋明理學與黑格爾的看法卻不一定一致。關於 「一」這一個哲學範疇,在西方與中國哲學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此一概念在這兩個哲學傳統中的意義很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說李澤厚思想中有一個幽靈,這個幽靈的來源不一定是黑格爾,而很可能只是一些當代中國思想主流所共有的預設,即墨氏所謂的論域一。他更指出當代台灣自由主義思想到某種程度也帶有這些預設,難道這也是黑格爾的影響嗎? 顧昕針對這個批評,表示或許是因為中國天人合一的理想與黑格爾的觀念很接近, 所以許多當代中國思想家對黑格爾情有獨鍾。[37]
* 作者感謝美國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硏究所高級硏究員墨子刻教授(Thomas A. Metzger) 在本文初稿完成之後,多次提出修改意見;荷蘭Leiden大學的顧昕先生與本院多位同仁,尤其是翟志成先生,給我許多批評,因此而避免了不少錯誤,謹致最高的謝意;當然文中不當之處仍由我個人負責。此外友人區志堅先生與同事羅久蓉小姐惠示相關資料,亦表謝忱。
[1] 早年的經歷見〈走我自己的路〉一文,收入《走我自己的路》(北京:三聯書店,1986 ),以及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硏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的自序。雖然李澤厚常說他並無師承,但在後書的自序中他表示「特別感謝任繼愈老師在北大幾年對我多方面的教導和關懷」,頁8。
[2] 李氏對八九民運的看法見〈和平進化,復興中華:談「要改良,不要革命」〉(下),《中國時報週刊》,美洲版(1992.5.10-16),頁44。他認為這次流血鎭壓政府與最後拍板定案的人難辭其咎,但故意激化形勢製造對抗局面的廣場學生也要負責。
[3] 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錄在一起成為李澤厚,《我的哲學提綱》(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4] 李澤厚,〈略論現代新儒家〉,《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 頁 337。
[5] 轉引自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頁6-7。這樣的說法在大陸上是相當普遍的,例如後來被許多人視為共產黨御用文人的何新也說「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一代學人,都曾或多或少地沾漑過李澤厚的啓蒙」;何新,〈李澤厚與當代中國思潮〉,收入《李澤厚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頁5。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李澤厚對自己並沒有那麼高的評價,1987年在新加坡他曾與翟志成先生談到他認為他所寫的東西很快就會消失,而他在80年代中國大陸暴得大名,是一個「不正常時代的不正常現象」。
[6] Lin Min,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78-88 — —the Case of Li Zehou,” The China Quarterly 132 (1992), p. 976.這四次辯論是有關眞理標準、人道主義與異化觀念、中國文化傳統,以及美學等。
[7] 《告別革命》,頁6。
[8] 《告別革命〉,頁5。
[9] 香港《明報月刊》有兩篇書評,基本上都對此書持肯定的看法,一是千家駒,〈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問題:讀《告別革命》〉(1995年7月號),一是李以建,〈站在第二框架之中的回望:讀《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 1995年8月號)。此外正在硏究文革後中國大陸之文化與社會的瑞典籍教授Torbjorn Loden告訴我,部分海外民運人士對此書肯定鄧氏改革的看法感到不滿。該書在大陸雖不易看到,但《東方》雜誌曾介紹其觀點,有不少人支持他的看法,也有一些人大加駁斥;據我所知有些大陸學者懷疑此書別有用心,認為其否定革命說法不但反歷史,也是試探性地爲將來鋪路。再者,居於荷蘭的顧昕在《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12月)上的書評以為此書是翻案性質的「歷史學話語」,其目的是爲「鄧小平改革的合法性與歷史的合理性,提供理論上的論證」;在評估上,他以為此書「學術水平極低」。這是此書出版後各方面大致上的反應。
[10] 誠如顧昕所說的「如果不了解李澤厚,那麼也就沒有辦法了解中國更年輕一代的思想走 向」。顧昕,《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中國知識分子:李澤厚硏究》(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4),頁7。
[11] 《告別革命》是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共同創作,許多地方是兩人思想碰撞所迸發出的火花, 故應合倂討論-但本文的焦點是李澤厚思想的發展,對劉氏著墨不多,將來希望能以另 一硏究補足劉再復先生的角色。
[12] 王忍之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與副院長,最近在九六年工作會議中還表示「社會 科學硏究者需從各方面加強硏究,以堅持和發展馬克斯主義」,見《聯合報》1996.1.15,第5版。賀敬之是一位文人。李澤厚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中曾描寫他在「雷鋒之歌」等作品中對「解放」後中共政權的歌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312-316。
[13] 第一次是1990年5月5-8日在長沙舉行的「若干哲學、思想史問題討論會」,重點是批判李氏「救亡壓倒啓蒙」的觀點。第二次是1991年夏天由中國社科院、北大、人大等 在北京召開的一個會議,目的是防止國內外勢力對大陸進行的「和平演變」的顚覆活動, 會中李澤厚再度遭到批判。
[14] 璧華,〈文壇左派圍攻李澤厚〉,《九十年代》1990年9月,頁60-61。陳蘭,〈李澤厚出國與大陸學術重鎭西遷〉,《九十年代》1992年2月,頁86-87 。
[15]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頁83。此外在頁200-211,名爲「回應迷信政治打擊的大陸批判者們」的一章內,有更詳細的回應。
[16] 馬漢茂,〈但開風氣不爲師:中國八十、九十年代的異議知識分子〉,《大陸當代文化 名人評傳:公民社會的開創者》(台北:正中書局,1995 ),頁7。此書和顧昕先生的幾個著作都屬於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基金會所支持的「轉型的中國文化與經濟」硏究系列,他們對大陸當代知識分子的硏究已有很好的成績。
[17] 傅偉勳,〈李澤厚的荆棘之路——大陸學界的「苦悶的象徵」〉,《文星》,第101期 (1986);後收入《「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頁197-222 。 傅氏對李澤厚的美學也很感興趣,他認為李澤厚所帶頭打開的中國美學與美學史硏究的新路「最有突破馬列教條希望」,見傅著〈審美意識的再生——評介李澤厚與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頁173。
[18] Lin Min,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78-88 — —the Case of Li Zehou,” pp. 967-998.
[19] 朱浤源,〈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辑》第12輯(台北:國史館,1994)。孫廣德先生在評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時有類似的看法,見《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7輯(台北:國史館,1991)。
[20] 劉曉波,《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9), 頁15-21。
[21] 李澤厚,〈關於「實用理性」〉,《二十一世紀》,第21期(1994),頁101。
[22] 此處所謂西體按照李澤厚的說法是「從科技」生產力、經營管理制度到本體意識(包括 馬克斯主義和各種其它重要思想、理論、學說、觀念)」,而中用則是將西體運用於中國,以及以中學作為實踐西體的途徑和方式,見〈漫說「西體中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426-427。
[23] 齊墨,〈劉曉波評傳〉,收入顧昕,《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劉曉波與偶像破壞的烏 托邦〉(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3 ),頁195-286,引文見頁233。
[24] 關於劉曉波思想的硏究,請見顧昕,《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劉曉波與偶像破壞的烏托邦》。用劉曉波自己的話來說他和李澤厚的不同是「在哲學上、美學上,李澤厚皆以社會、理性、本質爲本位,我皆以個人、感性、現象爲本位;他強調和突出整體主體性,我強調和突出個體主體性;他的目光由『積澱』轉向『過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來」,見《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頁15。李澤厚對劉曉波的批評見 《告別革命》,頁62、81-82,在此書中劉再復也談到他對劉曉波的評估,這與李澤厚的看法是相呼應的,他說「在文化大革命(的激進與瘋狂)之後,劉曉波還大批理性。 在文學領域中,過去確實用國家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馬克斯主義理性』來扼殺生命感覺,扼殺偶然和個體,反對這一點,強調一下生命哲學,這本來是好的,你(指李澤厚) 一直這樣強調,所以我開始也支持劉曉波的議論。但後來才看出他在一切領域中反理性,表現一種仇恨一切、敵視一切、橫掃一切的反社會人格,這是危害極大的破壞性人格,這是紅衛兵性格消極的那一面在八十年代的延續和發展」
[25] 其實劉曉波在1989年的書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李澤厚雖然專門硏究過康德,但康徳對人類自負的批判,在李澤厚那裡似乎沒有留下一絲印痕,他仍然想成為黑格爾式的哲學家」,《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頁18。
[26]甘陽,《我們正在創造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頁20。墨子刻先生對甘陽的想法持懷疑的態度,他認為此一觀點是粗糙且易於引起爭端的,墨氏以為在 《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 一書中,李澤厚並沒有說他要跟著康德,而不跟著黑格爾,他所說的是康德與黑格爾都各有長短,而黑格爾的歷史辯證的觀點是很有價値的,因為他解決了康德所未能解決的問題。換言之,在此書中,他描寫了一個西方思想漸變的過程,其主線是從康德到黑格爾,最後到馬克斯與恩格斯而集大成。這樣一來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他要康德,不要黑格爾。如果我們說:李氏透過黑格爾來整合康德與馬克斯,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可是這一思想取向是他自覺地採取的,而不是一個不知不覺的錯誤。再者,批評李澤厚是從黑格爾的角度來理解與描寫康德思想,也是一個不恰當的說法,因為李氏很嚴格地將描「述」康德與「評」估康德分別開來。見1996.4.25他給筆者的信。
[27] 李澤厚所理解的康德是否如顧昕所說黑格爾式的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據專門研究康德的李明輝先生告訴我,我們不能從歷史目的論的角度來認定康德與黑格爾的差異,因為兩人都有歷史的目的論,只是這兩種目的論有所不同,見李明輝,〈歷史與目的:評陳 忠信先生的〈新儒家「民主開出論」的檢討〉一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卷 第I期(1991),頁204。另一個相關的研究是李明輝,〈康德的「歷史」概念〉,《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7期(1995),頁157-182,此文中作者也嘗試澄清康 德的歷史目的論與黑格爾歷史目的論的根本差異。
[28] 顧昕,《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中國知識分子:李澤厚研究》,頁144-147。
[29] 齊墨,〈李澤厚:轉型期的哲學家、美學家和思想史家〉,《大陸當代文化名人評傳: 公民社會的開創者》,頁57-58。有關「美是自由的型式」之論證完全引自顧昕《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中國知識分子:李澤厚研究》,頁159。
[30]〈告別革命〉,頁83。
[31] 積極自由指可以做什麼的自由,即個人成為自己主人的期望;消極自由則是免於某種形式的約束或壓迫的自由。
[32] 伯林,〈兩種自由概念〉,《自由四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頁251。
[33] 墨子刻先生有關西方悲觀與樂觀主義認識論的說法,主要是基於Richard FL Popkin與 Alasdair Maclntyre兩人的著作,見Richard H. Popkin, “The Skeptic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Problem of Knowledge,” in Norman S. Care and Robert H. Grim, eds., Perception and Personal Identity (Cleveland: The 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69), pp. 3一24; Alasdair Macl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悲觀主義認識論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方的懷疑主義,這一看法可以追溯到不僅是笛卡兒的時代, 也包括希臘時代所說的「知識」與「意見」之區分。雖然對希臘人來說,超越意見而臻於知識是可能的,但「意見」的想法中指涉有一些觀念其真理價值是尚未確定的,有了 這一範疇,人們可以防止將錯誤的觀念視為真理,而劃入意見範疇之想法也正代表了對一些觀念的真理性質的懷疑,這樣一來,怎麼區別合理與不合理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說希臘人思想中有悲觀主義認識論之傾向。顧昕在論李澤厚思想的書中將此一西方的看法叫作「對理性的幽暗意識」,《黑格爾主義的幽靈與 中國知識分子:李澤厚研究》,頁137-139。
[34] 墨子刻的題目是「政治理性與當代中國的政治議程」(Contemporary China’s Political Agenda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此一演講內容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墨氏對discourse #1一些基本預設的描寫請見他的“Some Ancient Roots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This-Worldliness, Epistemological Optimism, Doctrin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Reflexivity in the Eastern Chou,” Ancient China, no 11一12(1985一1987), pp. 61·117; “T’ang Chun-i and the Conditions of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3:l(1985), pp. 1一47; “Continuities between Modern and Premodern China: Some Neglected Methodological and Substantive Issues,”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pp. 263-292;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Thought of Chin Yao-chi (Ambrose Y. C. K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4 (November 1993), pp. 937-948;與他關於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之書評,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2 (December 1994), pp. 615-638.
[35] 這六項特點見Thomas A. Metzger, “The U.S. Quest for 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ssue of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in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eds., Greater China and U.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pp. 84-103.
[36] 有關墨先生對顧昕一書的意見,引自他於1995.8.18、1996.1.5與1996.4.24給筆者的3 封信。李氏感覺到他的主體性的實踐哲學所追尋的「合一」是配合宋明理學的理想,也 配合馬克斯的觀點·李澤厚說「只有在美學的人化自然之中:社會與自由、理性與感性、 歷史與現實、人類與個體,才得到真正內在的、具體的、全面的交溶合一。·,一這種統 一是最高的統一·也是中國古代哲學講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見《批判哲學的 批判:康德述評》,頁559,類似的觀點亦見頁579,上文也已談到李澤厚對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與劉曉波對李氏觀點的批評。
[37] 顧昕在1995.10.17給我的信中曾回應墨氏的批評。

1957年生於臺北,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專長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主要著作:《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1994)、《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1998)、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2008)、《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2010)、《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2013)等;並編有《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嚴復卷》等十餘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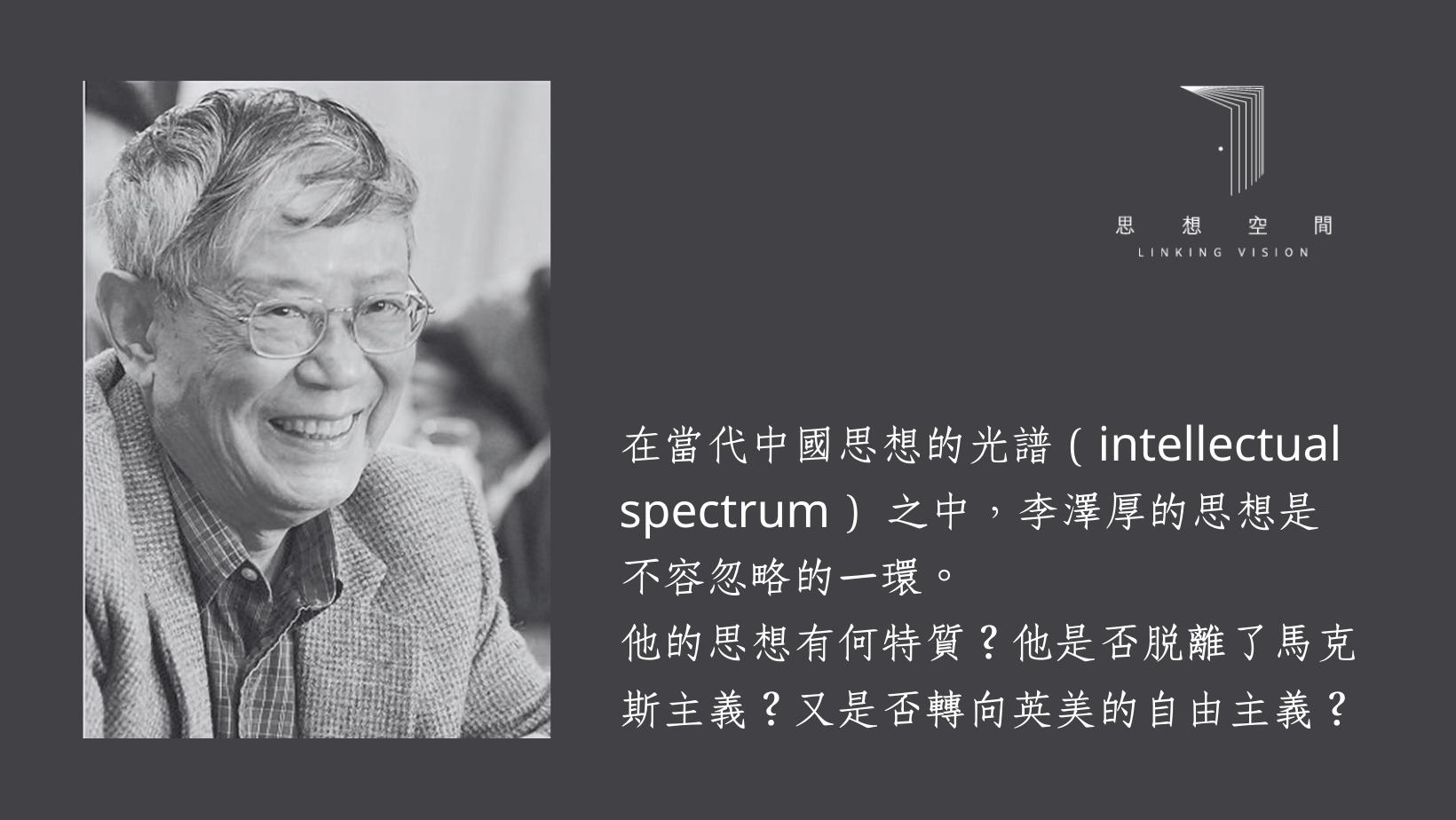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