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加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曾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專作有Racis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Ethical Theory and Social Issues、The Racial State、The Threat of Race 等等。研究領域包含:種族與種族主義,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社會法治研究,法律與社會、南非。研究計畫的贊助單位包含: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研究所(IMLS)、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 Hearst Foundation)、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洛杉磯猶太社區基金會(Los Angeles Jewish Community Foundation)、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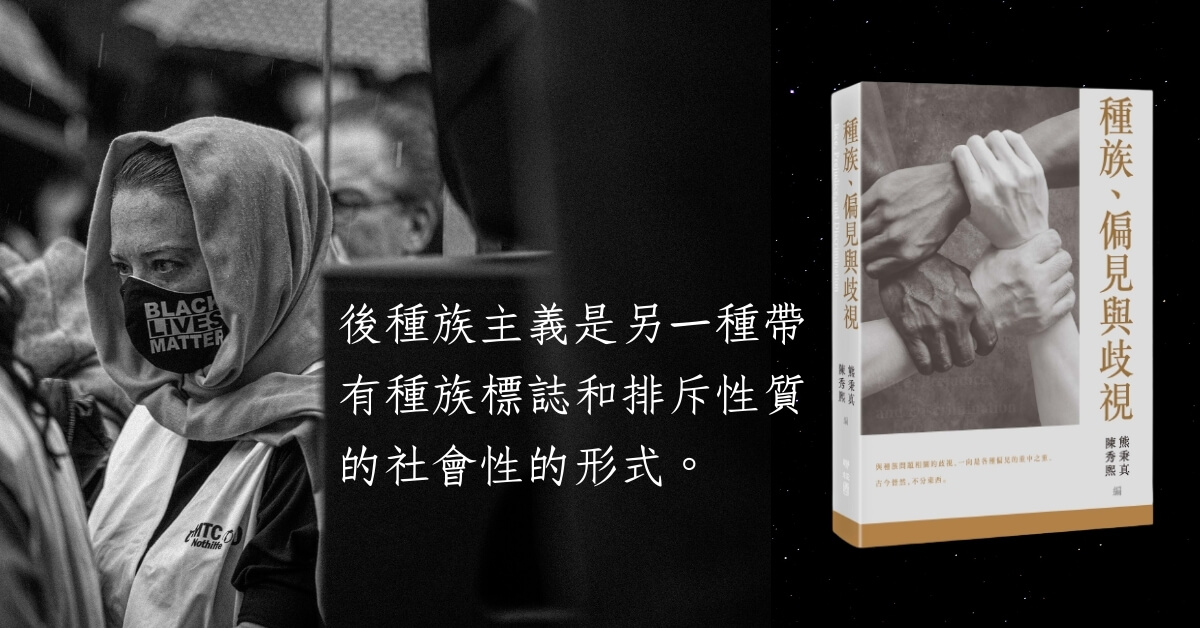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