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現代社會,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歧視的弊端,但顯性與隱性的歧視仍不時圍繞在我們身邊;在倡導多元文化的社會氣氛之下,性別歧視、種族主義仍然存在嗎?周家瑜的《平等》分析平等的歷史脈絡、社會議題,和其中相互矛盾的特性,也以羅列日常生活、新聞媒體等常見的例證,來討論這個時代中的隱性歧視與追求平等路上的難處。
* 本文摘選自周家瑜:《平等》(聯經,2019),第九章〈多元文化與差異:區別的平等〉,標題為編輯所擬。
一個民主社會如何在形塑共識與共同體情感的同時, 又面對多元分歧的社會團體呢?
什麼是多元文化?
我們常常認為自己身在一個「多元的社會」當中,但有時候我們珍視多元性(plurality)作為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的同時,也須面對「分歧」(diversity)導致社會對立的事實。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社會並不是高度同質性的團體,「社會」這個名詞底下,個別成員通常具有不同的團體身分,除了前面幾章所處理的種族與性別身分外,文化社群通常也是構成每一個人了解自我、形成自我認同時的重要指標。在本章中,除了探討一些深層的文化不正義,另一個主要的重點在於:一個民主社會如何在形塑共識與共同體情感的同時, 又面對多元分歧的社會團體呢?
首先自然的疑問在於, 什麼是「團體」? 又有哪些「多元文化團體」?一般而言,我們會將「團體」與偶然形成的「組織」和「集聚」區分開來。「組織」指的是自願參與某個團體的成員,「集聚」指的是偶然相似或具有同樣特徵的人的集合,這兩者與具有本身文化訴求,以某種身分或文化認同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團體」不同,而在這一章節中,我們要談的是後者。
學理上將多元文化團體簡略分為六類 [2] : 首先是所謂的少數民族(minority nations),在此指的是一些原本已經形成相當完整的社會與文化,但在歷史的進程中被合併進更大的政治國家當中的團體。學者金里卡(Will Kymlicka, 1962-) [3]將此類又劃分為兩種次團體,一種是在與主流民族競爭政治權力時落敗的「次國家民族」,例如英國的蘇格蘭人,或近年來積極追求獨立自治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人;另一種則是原本生於斯長於斯的傳統原住民,例如美洲印第安人與毛利人等。這兩類少數民族在與主流社會碰撞融合的過程中,態度雖各有不同,但某種程度上都是抵制整個政治共同體的國族建構過程,以爭取自己文化的保存。
除此之外, 金里卡也探討在西方民主國家中主要的幾種文化團體——諸如移民、奉行分離主義的宗教團體, 與不具公民身分的定居者社會中的主流文化團體——對待這些團體的態度儘管有細微不同,共通的問題與疑慮均在於: 這些文化團體與主流文化的整合程度界線在哪裡?
金里卡指出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事實:在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主流的政治團體多半採行壓迫與整合並行的政策策略,例如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法國就曾禁止在學校裡使用某些地方民族性語言,或甚至在出版品審查當中加以限制;近代較為明顯的例子,如加拿大的英國殖民者剝奪法語區魁北克人的自治權與體制,甚至試圖重新劃分法語區的疆域,以使魁北克人在任何行政區域中都無法取得參政的多數,藉以壓制魁北克人的政治訴求。[4]
加拿大當然並非唯一的例子,此處的另一疑問在於:在區域自治的分離主義壓力之下,主流團體是否有同化政策以外的選項?這是個可能需要另闢篇幅處理的複雜問題。
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刻意歧視任何團體,是立意良善且無心為惡的,然而在文化的不正義裡,不公不義經常便發生在這樣的無心日常之中。
分配的政治與身分的政治
對於類似的議題,前面幾章探討資源分配的分配正義政治觀顯然有所不足。社會資源的分配當然能解決一定的生活困難與自尊心問題,然而除了資源的分配,社會中多元文化團體被邊緣化的現象,似乎還存在其他的問題。首先,最明顯的可能是「身分等級」上的不平等,除了依照資源分配的多少而形成的經濟等級以外,「身分」也可能依照社會聲望的高低而形成等級。
雖然這個世界上如印度般存在著根深柢固種姓制度的社會並不多,但臺灣社會中是否存在著身分等級的不平等呢?在這個身分層級秩序之下,遭受身分不正義或不認同的程度又是如何呢?
有人認為:身分等級的層級秩序不平等只不過是一種假象,附屬於經濟分配的不平等上;換句話說,所謂的身分的不平等,其實不過是來自於經濟實力的差距,經濟的地位化約為其他層面的不正義。依照這樣的邏輯,解決資源分配的不正義,才是解決身分與文化待遇不正義的根源。然而在某些社會層面上,我們確實可見社會經濟資源充裕卻遭受身分與文化歧視的族群,例如享有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同性戀者,或是企業中出任經理職位的非裔美國人,抑或是在美國社會中的亞洲人與猶太人等等。
在臺灣, 最明顯的族群問題首先是原住民的訴求。直到筆者落筆的此刻(二〇一七年), 原民藝術家與導演馬躍. 比吼(Mayaw Biho, 1969-)為了蔡政府在今年初將原民傳統領域由一百八十萬公頃縮減為八十萬公頃的議題,已經分別在凱道與二二八公園露宿抗議超過三個月,試圖傳達保留原民生活空間之訴求;除此之外,馬躍.比吼也認為臺北市雖然沒有傳統領域的問題, 但應該也要留出原住民自治區域, 讓原住民能夠在城市當中結合空間與自己的文化。[5] 除了維持原有領地的議題外,原住民族群同時也面臨與主流族群之間文化整合與維持其文化獨特性的問題。在許多原住民村落的學校牆壁上,仍書寫著「我們是一家人」,但對於原住民而言,無論是學校教育、社會價值觀、文化政策各方面,原住民文化的獨特性似乎都沒有獲得特別的重視。雖然原住民新聞臺與原民文化似乎受到政府的資源補助,然而以社會價值觀而言,被同化的隱憂仍然存在,主流族群對於原民生活的印象也停留在淺薄的節慶活動,如豐年祭、小米酒等等。這些都說明了原住民的文化獨特性,與主流漢人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
除此之外,臺灣本土社會面臨的更明顯議題,應該是即將達到人口三分之一的臺灣新住民與第二代的文化衝擊。數日前的一封投書揭示了這個議題的沉重:一個母親為廣東裔柬埔寨人的年輕人,投書指出她在日常生活當中所要面對的,針對文化與身分認同的不友善。這篇震撼人心的投書,以一個假設的問句開啟:「如果臺灣是一個擁抱多元文化的社會,我可以用稀鬆平常的語氣,告訴大家我媽是廣東裔的柬埔寨人。我會在出生之後就打上耳洞,戴上媽媽精心為我挑選的耳環。在家裡跟外面,我會和媽媽用流利的廣東話和柬埔寨語交談,而大家的反應就會像聽見街邊的阿伯阿嬤說臺語一樣自然。」[6] 這篇投書凸顯了主流族群與弱勢族群的問題之一即在於, 弱勢族群在社會互動模式當中遭受壓迫,連使用自己的母語都遭受主流族群的異樣眼光,換句話說,弱勢族群的文化空間受到擠壓。我們經常說「臺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但在臺灣各文化族群間,美麗的風景似乎還欠缺了什麼。這裡所關注的並不是資源的分配不公或至少不僅僅是資源的問題,而毋寧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或身分不正義的對待方式。
具體而言,文化不正義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忽略、不往來、文化的支配與汙名化,我們可以在同志族群與社會主流團體的互動中找到一些例子。在國民教育教材當中,性別多元相關的部分頻頻受到某些社會團體的抨擊,認為與同志相關的性別認同教育不應該出現在學童的義務教育當中,這個訴求某種程度上認為多元性別認同與同志教育會影響孩童的身心,而主張不應當成為學童認識性別教育中的一環。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同志族群性別認同的一種貶低與「不承認」,認為弱勢族群的性別認同並不是義務教育中值得學習並接觸的教材。文化支配則表現在異性戀價值觀的主流地位, 當異性戀的價值觀作為一個評判何者適合孩童教育的標準時, 同志或跨性別族群的性別認同自然就顯得是「非主流」、甚至是「不正常」, 不應當出現在主流義務教育當中。這些被「避而不談」的族群因此在教育體制與課程設計當中被「隱形」了,隱形與避而不談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們經常在社會中「看不見」這些族群的身影;既然看不見,就更談不上矯正與重視這些文化族群所遭受的文化不正義的對待了。
除了文化認同的弱勢族群, 社會中經常被邊緣化與遭受忽略的團體,還包含以年紀與性別區分的族群。近年來臺灣社會出現了一個由兩個女生組成的團體名為「肉彈甜心」, 正是要以自身遭遇提醒社會大眾:在自以為平等的臺灣社會中,主流團體多麼容易忽略某些少數族群的需求。
該團體成員之一的Amy受訪時談起成立這個團體的契機,是她看到電視上的一則新聞, 講述某社區監視攝影機拍到一個「身材壯碩的女子」在某戶人家外面行蹤可疑,地方員警便上前盤問,該女子回答是該戶人家主人的小三, 警察心生疑惑, 覺得「該女子身材矮胖不太像小三」,因此進一步確認其身分,發現其為竊賊而將之逮捕。[7] 「為什麼某種人就必須是某種樣子?」這是Amy的疑問。社會主流價值觀是高瘦纖細的體型,因此認定身材與此標準不同的女性「必然」不受歡迎,甚至嘲諷地認定與體型肥胖的女性交往「必然是真愛」。在日常往來互動中,這個族群遭受貶低與不尊重,甚至在環境制度中也受到忽略,Amy便指出,從小到大教室的課桌椅或甚至火車或飛機上的座椅,都是設計給某種體型的人使用 [8],這樣的社會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刻意歧視任何團體,是立意良善且無心為惡的,然而在文化的不正義裡,不公不義經常便發生在這樣的無心日常之中。
文化正義:溫柔的復仇
這一章的最後,我想以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的故事作結。奧比.薩克思於二〇一五年來臺領取唐獎所頒發給他的法治獎,這個獎來自於他多年來在南非種族隔離的白人政府下英勇對抗暴政的事蹟。
一九五三年生於南非的奧比.薩克思是猶太移民後裔,對於當時白人政府所推動極度不正義的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非常不滿,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曾以故意選坐「限黑人」的座位的方式挑戰不公正的制度;後來在南非政府的汽車炸彈攻擊中,甚至失去了右手與一隻眼睛。
在遭受如此災難後,薩克思經歷了痛苦的復元歷程,在其出版的自敘中詳細描述了他所經受的痛苦。然而驚人的是,在南非不義的白人政府被推翻後,成為第一任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的奧比.薩克思,在種族不正義的補償與尋求正義的態度上卻充滿包容。一次同志遊行的演說上,奧比.薩克思感性地發表了一段演說,或許可以作為此處探討文化平等的小結:
親愛的朋友⋯⋯今天遊行的終點是這個公園,對我來說這裡具有特殊的意義,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常在這裡玩,這裡很美,有草地,有樹木,還可以看到桌山。之後這裡豎起了「僅限白人」的牌子——現在沒有了,但這實在是非常可恥,我們告訴人們:因為你是你, 所以你不能夠在這裡遛狗,不能推嬰兒車來這裡,在這裡玩網球,或是坐在長椅上讀書,不過其實還有其他記號——看不到的記號,但一樣是用暴力強加的。如果吸引你的人,或你愛的人剛好和你同性別,你也會被禁止進來這裡,這個美麗的地方不歡迎你,除非你假裝成另外一個人⋯⋯而我們想要的國家,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平等生活的國家——不論語言、歷史、喜好、信仰和出身。我們有權和別人不一樣,包括生活方式和個人的選擇,我們也有權利可以一樣, 不論是尊嚴或是公民權。
(《溫柔的復仇》,頁二七四)
[1] Albert “Albie” Louis Sachs (1935- ), 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
[2]學理將多元文化團體分成:少數民族,移民團體,持孤立主義的種族、宗教團體(如哈德萊特人、安米緒人),非公民居留者(包含非常規的遷徙者,或臨時遷徙者),非洲裔美國人與身分/認同受歧視的社會團體(如某些社會中的LGBT族群)。
[3] 威爾.金里卡,加拿大皇后大學哲學教授,也是中歐大學民族主義研究計畫客座教授。其經典作《當代政治哲學導論》(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已有八種語言的譯本。
[4] 威爾.金里卡著,劉莘譯,《當代政治哲學導論》,第八章。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三。
[5] 相關新聞與訪問,可參考〈北市原民居住大不易 馬躍比吼:設置原民自治區〉
[6] 相關投書可參考〈作為一個在臺灣的新二代,我感到很害怕〉
[7] 原新聞出處〈離譜!女賊闖空門行竊 瞎掰是小三找情夫〉
[8] 原訪問出處可見〈在肉彈的世界裡,人人都是甜心〉
延伸閱讀:
劉維人:為什麼我們即使沒有歧視,依然會剝奪弱勢族群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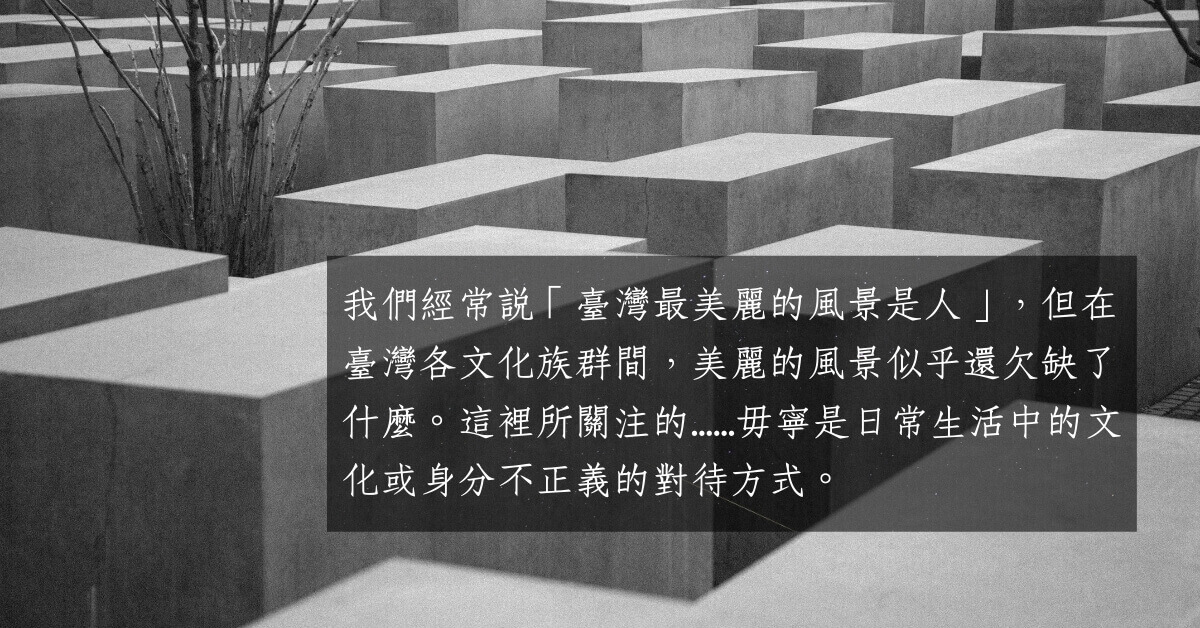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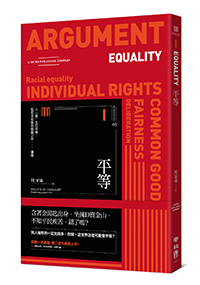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