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關注女性權益發聲的我們,時常將西方社會看作是性別平權的烏托邦。好像西方總是現代的、平權的,而亞洲是傳統的、父權的。本書為我們點出,即使是在如此「現代」的今日西方社會,傳統的、歷史之中的厭女陰魂仍然時時現身。
前些日子讀了小學社會科教材裡頭關於性別角色的單元。其中的一頁這樣寫:「傳統社會的女生會被要求處理家務」、「現在無論男生或女生,都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喜歡的職業」。
「現代社會已經擺脫傳統的性別規範了」這個說法似乎非常流行。我不禁想,女人被限制在私領域的家庭,女人不被鼓勵去公共領域掌有權力,這真的只存於過去的社會嗎?過去和現在,真的是完全斷裂開來的嗎?傳統和現代,又真的是完全對立的嗎?
本書正是要將過去和現在串接起來,把傳統與現代連結起來。它要讓讀者看見,現代社會公共領域中對於女性發聲和女性掌權的偏見,如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傳統中,也讓讀者看見,西元前的性別文化如何仍然非常鮮活的在今天的公共領域中出現。
畢爾德舉出許多當代西方社會壓抑女性公共言說的證據。在今日西方,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的女人,經常被描繪為著眼於瑣碎小事的嘮叨鬼,或被認為咄咄逼人,違反理想女人的樣子。而對公共事務大聲發言的男人,則相對較常被認為是充滿抱負與威嚴的理想男性形象。社會認為男人的低沉音調比女人的尖銳音調更具權威,迫使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接受壓低嗓音的訓練,因為她的形象顧問認為女性若用高尖的語調說話,不能使人信服。除了高能見度的政治人物,日常女性的公共言說也備受干擾。畢爾德討論推特上女性的公開發言,當有人反對這些女人的意見時,暴力威脅和性威脅的留言會蜂擁而來(我要把妳的頭砍下來強姦、無頭母豬、拔掉妳的舌頭、賤人閉嘴)。相較之下,男性在推特上公開發言當然也常受到批評,但批評類型卻甚少以暴力噤聲或性侵威脅的形式出現。
當代西方社會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對待女性言說?畢爾德將這種種西方社會中非常「今日」、非常「現在」的公共言說文化,追溯回古希臘羅馬的言說傳統。近三千年前,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潘妮洛普便被初從男孩長成男人的兒子斥道:「母親,請回您的房間,從事您自己的工作,操作織布機和捲線桿吧⋯⋯言說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人,尤其是我。」噢,當然。學會主導公共言說,並且開始壓制女人在言說裡面的角色,這在三千年前便是男孩長成男人的成年儀式。西元前四世紀,亞里斯多芬的喜劇虛構了一個關於女性管理國家的故事。毫不令人意外的,這齣喜劇的笑點恰恰在於女人無法恰當的進行公共言說,她們只能談論性事等瑣碎的話題,無法像男性一樣進行「嚴肅」、「高等」的政治對話。古典作家更是經常堅稱,女性說話的尖銳嗓音會威脅政體的穩定性。
除了女性的公共言說,本書也討論女性掌權。在今日西方,女性想要攀上權力階梯,仍然時常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阻礙。畢爾德穿梭古今,將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女性掌權的場景,和今日西方政治中女性掌權所遭遇的阻力關聯起來。比如希臘神話中的梅杜莎。這位強大、具有威脅性的女性的一頭秀髮,是成千上萬條蠕動的蛇。若說蛇髮再明顯不過的象徵了梅杜莎奪取陽具權力,她這位最終遭到斬首的神話女性,便是說明了女性若是敢僭越,意圖威脅到男性掌權的地位,她會遭受怎樣的下場。她的故事提醒女人應該回到自己真正所屬的地方——回到無涉權力的私領域。直至今日,梅杜莎的意象仍被當代媒體反覆挪用來嘲弄西方女性政治人物。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頭像時常被疊在梅杜莎的頭像上。關於英國首相梅伊的漫畫中,她也常被添上梅杜莎的蛇樣長髮。美國二 · 一六的總統大選中,川普的臉被鑲嵌在砍下梅杜莎頭的英雄柏修司圖像上,並一手高舉著被斬首的梅杜莎/希拉蕊合成頭像;這個圖像被製成 恤、馬克杯、電腦保護套,大量流傳。
在臺灣關注女性權益發聲的我們,時常將西方社會看作是性別平權的烏托邦。好像西方總是現代的、平權的,而亞洲是傳統的、父權的。本書為我們點出,即使是在如此「現代」的今日西方社會,傳統的、歷史之中的厭女陰魂仍然時時現身。如同畢爾德不斷強調的,本書並不是要主張數千年來公共領域中的厭女傳統從未改變。從西元前的社會至今,西方社會的女性地位當然已經大大改變,女性主義當然也已經打過無數場勝仗。然而,畢爾德提醒我們,儘管如此,性別偏見有它的歷史韌度。它穿越長長的時間隧道來到這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本文摘錄自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推薦序,原題為〈性別偏見的時光機〉,標題為作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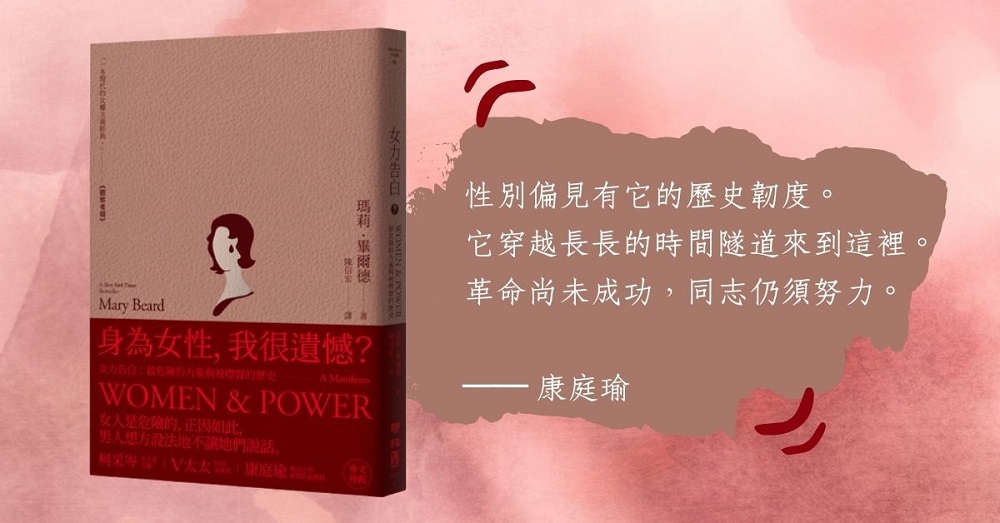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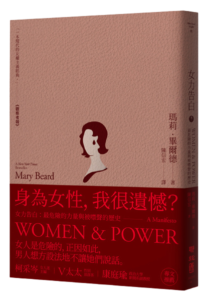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