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炎培早於一九五五年已和崑南、葉維廉、王無邪、盧因等創辦《詩朵》,那時他們雖然只是高中生,但那年代的學生早熟,在創辦《詩朵》之前,他們已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人人文學》和《中國學生周報朵》和稍後在《香港時報詩之頁》發表過不少詩作,他們在詩學上的認真和勤奮,亦見諸在《香港時報•詩詩圃》所創出的「蜻蜓體」新格律詩。當馬朗於一九五六年創辦《文藝新潮》,他們積極供稿,蔡炎培以「杜紅」為筆名發表詩作,崑南以「葉冬」為筆名發表散文和譯作,另以「崑南」發表小說和〈布爾喬亞之歌〉、〈賣夢的人〉等長詩,王無邪以「伍希雅」、「無邪」發表小說、詩歌和譯作,葉維廉分別發表多篇作品,盧因更獲「《文說獎」第二名(獲第一名的是臺灣作家高陽)。
六〇年代,他們各有不同發展,蔡炎培先後赴臺灣升學,崑南投身社會,稍後創辦《香港青年週報》,王無邪選擇藝術之路,繼而赴美進修,回港後一直專注藝術創作和教學;然而翻閱當時的刊物,可見整個六〇年代差不多十年間,即使他們選擇走上不同的路,依然可在《香港時報•淺水灣》、《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和崑南、王無邪、李英豪等先後創的《新思潮》和《好望角》,以至一些臺灣出版的刊物如《創世紀》和詩選集選如《六〇年代詩選》,持續讀到他們的詩作。
他們的詩作當然各有不同特色,但都共同關注身份認同和語言的問題,崑南〈大哉驊騮也〉、〈葉維廉〈賦格〉、王無邪〈筵:燃燒〉、蔡炎培〈七星燈〉都氣格龐大,從個人引申到時代與語言的思考,他們在詩學上的成長年也代和六〇年代港臺現代詩的交流密切相關,在談論六〇年代香港新詩的發展時,他們幾位的努力相信絕不可忽略。崑南、葉維廉、王無邪分別都有不少學者評論過,唯蔡炎培較少見評論,其詩亦實在不易評說。蔡炎培的詩歌語言特殊,語言性格突出,亦最能討論香港詩的語言問題。以下嘗試從六〇年代的詩語言和歷史承傳談起,最後歸結於詩語言的分析和省察。
一、蔡炎培、徐速與「密碼詩」論戰
一九六七年,蔡炎培曾以「林筑」為筆名在《當代文藝》發表〈曉鏡一寄商隱〉一詩,引起著名的「密碼詩」論戰,參與者主要包括徐速、宋逸民、萬人傑等人,首先是宋逸民一九六九年在《萬人雜誌》發表〈「密碼派」詩文今昔觀〉,將現代派挖苦地稱為「密碼派」,並嘲諷寄〈曉鏡一寄商隱〉一詩為「標準密碼派的新詩」,理由是:「這首詩雖然是用中國字寫的每個字我們都認識,但組成句子之後卻每一句都看不懂。」徐速則在《當代文藝》發表〈為「密碼」辯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也不認同現代詩的語言,但放下了嘲定的態度,雖然他也不認同現代詩的語言,但放下了嘲諷和全面否定的態度,較認真地檢視現代派詩歌的語言問題,只可惜該論戰無可避免地以意氣之爭的罵戰告終。
一九六九年的「密碼詩」論戰,在意氣和刊物立場(涉及《當代文藝》與《萬人雜誌》之爭)的維護以外,更核心的問題是徐速與萬人傑一輩對臺港現代詩和青年語言的態度。談起這論戰,蔡炎培他們一輩亦可說和徐速有一點緣,早在《詩朵》時期,年輕的崑南就曾以「狄斯艾」為筆名,發表針對性的〈免徐速的詩籍〉一文,批評徐速在詩觀上的保守;在六〇年代的「密碼詩」論戰中,徐速卻為蔡炎培的詩被指難懂辯護,雖然徐速的出發點主要是維護《當代文藝》的聲譽,也比起單單以難懂而全面否定、嘲諷現代詩語言的宋逸民、萬人傑等人,來得比較開明。六〇年代,「現代詩」在港臺兩地青年間迅速傳播,引發不少討論,就其語言的晦澀,有批評也有辯解,在「密碼詩」論戰之前,崑南也在一篇文章,為現代詩被指為「難懂」辯解:
「難懂」的形成,我個人認為是由於詩人的創新,使部份讀者在不習慣中產生出來的。所謂「不習慣」,因為當代詩人已不滿足昔日「詩化」的語言來表達個人的情感思想,遂決心創新的語言──非傳統的、非理性的、非邏輯的語言。這是很自然的。他們的新語言的實質不外乎反映這個時代的面目。
我在論楊際光的文中亦引用過上述崑南的文章,指出六〇年代現代詩中的「難懂」並非語文問題,不是在語意上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而是一種語言上的需要。現代主義文學在五、六〇年代的香港和臺灣同時掀起浪潮,都不純粹視之為一種藝術技巧的引進,而是為針對或回應現實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問題。對五、六〇年代的作者來說,口號式批判或浪漫的感傷筆調都再無法回應複雜又充滿矛盾的局面,而現代主義文學正提供另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有助於新語言的建立。
在肯定或否定之餘,六〇年代末另一趨勢卻是對語言的反省、調整和轉化。例如一九六八年《盤古》雜誌「近年港臺現代詩的回顧」座談會的反省、古蒼梧對臺灣出版的《七十年代詩選》的批評、戴天和古蒼梧在創建學會詩作坊提出對三、四〇年代詩的研讀、張曼儀等編選《現代中國詩選》、七〇年代初溫健騮提出「批判的寫實主義」等,及七四年也斯在《中國學生周報》後期譯介美國民歌和在「詩之頁」編「香港專題」,又是另一種調整。
蔡炎培未強調主張,較少理論闡發,但七〇年代以另一筆名「蔡雨眠」在《星島日報》專欄「碎影集」,明確地提出自己對三〇年代新詩的承傳,從何其芳開始,至吳興華(梁文星),特別在於後者,他多次在文中提及,並尊稱為「文星師」,可見出他的選擇,也沒有完全接受六〇年代以來的現代詩語言,反而在三〇年代新詩的承傳當中,對現代詩語言有所調整。
二、〈焦點問題〉的言說方式
蔡炎培一九六五年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的〈焦點問題〉是一首關於詩語言的詩,作者以此表達他的詩觀,這相信是本詩的基本意思。由這理解出發,或者可引申出其他思考,即使這未必是作者寫作時的本意。現在讀之,把這詩放在六〇年代的青年文化當中,有助我們思考六〇年代香港詩人的處境和現代詩的語言問題。
六〇年代的香港文藝青年,從投稿到五〇年代南來文人主導的《人人文學》、《海瀾》、《文藝伴侶》、《文壇》等刊物開始,也紛紛組織不同的文社,自辦刊物,六年代文藝風氣的形成,有其文學傳承上的內在因素,亦與西方思潮衝擊、流行文化的再造、政治上的醒覺等外圍發展相關,六〇年代的現代詩不單純是文藝的問題,而是整體青年文化的一部份,正如也斯所論:
六〇年代是一個複雜的年代,香港本身經歷了由難民心態為主導的五年代,來到這個階段,戰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逐漸成長。在六〇年代的民生中,傳統的價值觀念仍佔主導的地位,但西方的影響也逐漸加強,帶來了顯著的衝擊。外緣的政治變化對香港帶來了影響,中國在六〇年代中展開了文化大革命,六〇年代的歐美爆發了學生運動和人權運動,非洲國家經歷了獨立和解放運動,連香港本身亦因種種民生問題與累積的不滿情緒而在六七年爆發了動亂。處在六〇年代的香港,既放眼世界的新變化,亦關懷國家民族的命運,種種態度彼此既相輔又矛盾。而在原來偏向保守與嚴肅的文化體制內也開始更分明地感到了青年文化的形成、商品文化的衝擊。這種種政經、社會和文化現象形成了六〇年代的文化生態,也當然影響及改變了文學的創作、流傳、接收與評價。
六〇年代的香港青年夾處新舊文化、內地和香港的現實之間,迫使他們同時思考兩者。從五〇年代末至六〇年代初,王無邪〈一九五七年春香港〉、〈筵:燃燒〉、葉維廉〈賦格〉等詩已嘗試回應問題、思索出路;蔡炎培一九六五年的〈焦點問題〉也面向類近的問題和思考,不同的是,〈焦點問題〉沒有處理現實環境的問題,而是集中談論詩或觀念的問題,以內在世界的探詢,作建立語言的基調,向六〇年代香港青年以及作者們喊話。
正如它所要回應的語言問題,〈焦點問題〉一詩首先要讀者面對它那獨特的言說方式。全詩四節,先看首三節:
心象決定了形式。如果說
中國還是一個衣冠的民族
同樣從喃喃到語言的階段
凡寫下的必成為書
但有關西長甲感知粗與細
神祇守護皆因貼錯了門神
這裡明明並沒有甚麼蠱惑
神荼鬱壘無非是你破落的門楣
一首能讀的詩每每是心靈的探險
長空萬里實則寓困獸於自由
也許這裡可容納一個微妙的界說
言之未必有物。有物未必言之
詩的意義,也是其障礙,正來自它獨特的言說方式,這詩顯然不滿足於一般正尋求一種「微妙的界說」,一種觀察和解釋世界的新角度,藉以面對外在世界的一、二節,探討語言的本質、形式及其假象:「這裡明明並沒有甚麼蠱惑」,華背後,可能只是「破落的門楣」,但這詩不是要否定語言,而是思考詩怎樣為破重新塑造新的可能性。在第三節,這詩提出自由的真意,未必在於環境的自由:每是心靈的探險/長空萬里實則寓困獸於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觀念上的自由,問題,這「微妙的界說」在第三節提出,但在第三節的結句「言之未必有物。有是一個幌子,真正處理這問題的是全詩的末段:
一個獨腳少年留下三個足印
向海都是死水,向山都是囚牆
唯有囚牆近山脈。唯有死水遠波瀾然
而這僅是那人的把戲
一個憂鬱藝術神祇的偶然
偶然把你投入一面鏡子。鏡已裂
鏡中依然有你。你要破鏡重圓
「一個獨腳少年留下三個足印/向海都是死水,向山都是囚牆」,詩中那受限制或可視為六〇年代青年的處境,個體受制在諸多客觀環境的規限中,現實是死水和囚有囚牆近山脈。唯有死水遠波瀾」,在限制中未嘗不可另找可能。正視原有的限視之,限制也指向另一種可能,關鍵是破除常規和框架,「鏡已裂」代表認清既重新尋找、創造自己的言說方式,透過「破鏡重圓」式的詩的言說,重建對語言的信念。
結語
吳興華和何其芳,相信是蔡炎培詩藝的源頭,但蔡炎培還是創造出更多自己的語言。細讀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小詩三卷》,在蔡炎培自言的三、四〇年代新詩傳統以外,還可見另一文化的結合,如香港的市民文學、文言白話混合粵語的「三及第」語言的吸收和一點戲謔生出的反叛,如〈老K〉、〈風鈴〉等詩作,當中的反殖非出以左翼的政治語言,而是採用三及第式的民間語言,以不正規語言達到反建制效果,因此其詩中的廣東語言非為娛樂,而具政治性指向,當然蔡炎培的詩作,特別是六、七〇年代詩中的政治並非指向革命和批判,而是指向虛無。
六、七〇年代的蔡炎培詩作,在戲謔、反叛和玄思當中,更明顯可見的是憤怒和批評,他對香港和中國同時關注,自足的語言使他能來回於時代而不為所限。〈老K〉、〈風鈴〉、〈我們的節日〉等詩既保留了某種時代氣氛,亦以特出的個人語言和角度,作外在世界的回應,實可與崑南〈大哉驊騮也〉、葉維廉〈賦格〉、王無邪〈筵:燃燒〉等詩作等量齊觀,以見六〇年代的青年文化,一種有別於左翼取向但同具反叛和反抗的反殖、獨立的精神,當中包括對三、四〇年代詩歌傳統的繼承,調節六〇年代的現代詩語言,創造出他們一代人的文學語言,在今日仍值得我們借鑑、反思。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助理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站計劃」副研究員等職,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香港文學、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亦從事文學創作,2012年獲選為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之香港作家,2009年起參與陳國球教授主持之「香港文學大系編纂計劃」,擔任副總主編,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藝術家獎(藝術評論)」。著作有《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這時代的文學》、《愔齋讀書錄》、《抗世詩話》、《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另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文學史料卷》、《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一》、《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葉靈鳳卷》、《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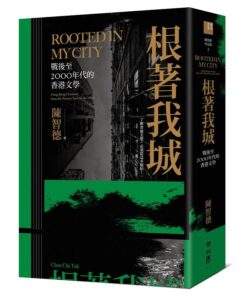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