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演化心理學家
編按:朋友遠比我們想像的更重要。羅賓‧鄧巴30年前就提出了「鄧巴數字」:一個人最多能保持關係的朋友是150人,其中關係最密切的不超過5人。《朋友原來是天生的》是鄧巴全面研究友誼、人際關係的科普大作。為何人類需要朋友、人類如何獲得朋友?為何你總是覺得與自己的摯友「心有靈犀」?在友情與人際關係中,還有哪些我們不曾認真想過的謎團⋯⋯(* 本文摘自《朋友原來是天生的:鄧巴數字與友誼成功的七大支柱》第九章〈友誼的語言〉,標題為編者擬。)
無論友誼有多少是關於人際關係的「原始感覺」或情感體驗,我們依然花費大量社交時間在對話上。在這方面,語言顯然扮演核心的角色,而就語言這個詞的真義而言,它是人類所獨有。學者對於由蜜蜂到黑猩猩等動物的語言能力已經有了很多研究,但現實是,無論海豚和猿猴的「語言」多麼巧妙,但牠們的語言形式與我們人類所能做的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牠們的表現充其量只和三歲的人類幼兒差不多——這正是你對位於擁有心智能力邊緣的物種所期望的。然而,動物的交流和人類的對話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由蜜蜂的「右邊第三片花叢有花蜜」,到猴子的「小心——一隻老鷹即將向我們俯衝過來」,動物只限於對事實發表意見。我們的對話則主要是關於我們所生存的社會世界,這是沒有物質形式的精神世界,因為它只存在於人們的腦海裡。不論動物之間的交流多麼密切,牠們從來沒有像我們這樣,經常進行關於這個世界的活潑群體對話。
話說回來,我們的對話受到語言如此強烈的支配,因此我們經常忘記在語言雷達之下實際進行了多少的溝通。我們怎麼說某件事通常與我們所說的內容一樣重要。如此說來,語言究竟添加了什麼?為什麼我們會擁有這種非凡的能力?為什麼不像猴子摸索和嘗試那樣,依賴觸摸進行所有的溝通?本章和接下來的三章把重點由我們社交世界與生俱來的那一面,轉移到我們如何利用我們非凡的溝通能力來建立和運用我們的關係。
成功的對話是會「流動」的——你來我往自然而然地交互發言彼此相接,一步接一步地建構故事。心智能力使我們能夠識別何時可以發言,以及哪些內容可以順利融入話題的發展。
語言的奇蹟
像人類語言這樣的現代語言的關鍵在於我們心智化的能力。談話不是喊叫比賽,好吧,有時也許是,但即使是和爭執無關的喊叫,對它們所建立的關係而言,往往也是教人相當不滿意的交流,因為喊叫(無論是多麼和氣的喊叫)通常不容許雙方互相嚙合。正常對話牽涉了大量的複雜交流,說話者試圖讓聽者明白他或她想說什麼,而聽者也必須非常努力地嘗試理解說話者的想法。此外,維持對話的脈絡在認知上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繁重得多,因為你必須知道在談話中什麼可能會吸引其他人,並了解你的發言如何促進談話,而不會因為一句不當的評論而使談話中斷。儘管當你停下來思考時這可能很明顯,但我們對此知之甚少:沒有人研究過對話行為的這一層面。
成功的對話需要我們運用非常高程度的心智技巧,因為在實際上,我們需要嘗試深入彼此的心智。如果我沒有做到這一點,並開始偏離切線的全新話題時,就會打斷談話的流動,使其他人——尤其是試圖解釋複雜事物的人覺得沮喪,或者更糟的是,感到惱怒。如果你這樣做太多次,就可能會發現人們避開你:與你交談太困難,而且無法令人滿足。成功的對話是會「流動」的——你來我往自然而然地交互發言彼此相接,一步接一步地建構故事。心智能力使我們能夠識別何時可以發言,以及哪些內容可以順利融入話題的發展。此外還得再加上一個事實,即社交對話通常會牽涉到對其他人的行為、意圖或心態的討論,你很快就得要提高心智化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這些程度非常高的認知技巧,我們就不會有如今的語言。只要我們有更多適度的心智能力,我們當然可以擁有某種語言,但它會缺乏我們用五級或偶爾五級意向性陳述的複雜和微妙的表達。根據大腦大小來看,我們估計現在已經滅絕的歐洲尼安德塔人和在現代人類出現之前主導了我們 50萬年演化歷史的其他古代人類恐怕只有四級意向性。一級意向性的差異就會對他們講述故事的複雜程度,以及他們對話時可以容納的人數產生巨大影響。
在這裡我不多談這點,僅強調我們在對話中使用語言方式的豐富程度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心智能力,而這些在認知上代價高昂,需要演化出執行功能比尼安德塔人和類似人類的大腦功能都大得多的大腦。對話是艱鉅的認知工作,並非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做的,然而你會很驚訝地發現考古學家或演化人類學家甚或心理學家並沒有注意到這相當基本的一點。這可能是因為身為成年人的我們在做這件事時不假思索——這是因為我們在由蹣跚學步的孩童到擁有各種能力成人的發展過程中,發展出如此熟練的技巧。要達到真正成人語言熟練程度需要漫長的時間,證明它牽涉大量的技巧學習,尤其男孩更是如此。它耗費了人生最初20年的大半時間。
奈特.歐許(Nate Oesch) 和我由實驗中得知,分解包含許多子句的複雜句子這種能力和個人的心智能力密切相關。心智能力有限(低於成年人正常範圍)的人不能完全了解有許多從屬子句的句子。這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透過說故事來說明。如果沒有同時處理多種心智狀態的能力,就不可能說故事。我們小組的研究員詹姆斯.卡尼在一項研究中就強調了這一點。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對一個故事的欣賞程度是由寫故事的心理層次決定的。詹姆斯寫了一些分別位於兩個不同心理層次上的短篇故事——一個不高於第三級意向(包括讀者的心態),另一個則達到第五級。然後根據受測者對這些故事的欣賞和參與度進行評估,我們也用了標準情境任務確定受測者的心智化能力(見第六章)。他發現,自然表現在第三級心理狀態的人較喜歡第三級心理狀態的故事,而自然表現在第五級或以上的人,則較喜歡第五級版本的故事。
提高溝通的複雜性對於能夠處理較大的群體至關重要。在所有的靈長類中,聲音和手勢的複雜性兩者都會隨著作為該物種特徵的社會群體規模而增加。陶德.佛瑞伯格 (Todd Freeberg) 對野生卡羅萊納山雀(Carolina chickadees,一種與歐洲山雀有關的北美小鳥)一系列精彩的研究首先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在同一物種中,生活在較大群體者的發聲也會變得更加複雜——你「說話」的個體對象數量越多,你的語言就必須更豐富,以確保溝是明確針對它要針對的個體,並由對方接收。安娜和山姆.羅勃茲(Anna and Sam Roberts)對烏干達野生黑猩猩手勢溝通複雜性所做的田野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正如塔瑪斯.大衛─貝瑞特(Tamás Dávid-Barrett )用電腦模型中所顯示的,溝通和團體規模很可能會經歷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兩者相補,雙方都容許對方小幅增加,直到它們通過臨界點,之後一切都會飛速增加。
由於有大得多的群體要聯結,因此正式語言在人類世系中可能因為下面兩種原因中之一而演化。一種可能性是容許有關網路狀態的訊息傳遞,也就是說,要追蹤的人這麼多,我們可能很難知道每一個人的資訊——尤其如果他們分布在不經常見面的不同小群體中。在我們碰巧見面時,你可以告訴我吉姆和佩妮最近在做什麼,這樣我就可以透過代理人更新關於他們關係的訊息,在我見到他們時,就不會犯下大錯,比如在他們鬧離婚之際問他們是否生活美滿。這就是語言演化的八卦理論基礎,在拙作《哈啦與抓虱的語言》(1996出版) 中有概述。第二種同樣重要的可能性是:人類用語言來講故事。故事和傳說把我們聯繫在一起,成為一個社群。它們告訴我們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為什麼對彼此有義務。傳說和其他故事構成了聯結更廣泛社群的重要基礎:我們之所以互相歸屬,是因為我們都聽過相同的傳說,覺得相同的事有趣,擁有相同的道德價值觀,在我們部族的起源故事中有相同的歷史。正如我們會在第十章中看到的,這些都有助於把我們繫縛在單一一個促進合作的社群中。
正如我們在許多研究中所發現的,無論哪一個原因先出現,我們的對話顯然都由社交世界主宰。在我們最早的一項研究中,尼爾.鄧肯(Neil Duncan)、安娜.馬利歐特(Anna Marriott)和我由咖啡廳和其他場所的自然對話取樣,每隔15秒就把這些對話的一般話題歸入十大類(人際關係、個人經歷、文化/藝術/音樂、宗教/道德/倫理、政治、工作等)。我們發現,不論男女,社會話題都占三分之二左右的談話時間。兩性之間實際上只有兩個明顯的差異:在全男性群體中,男性談論個人經歷比在在兩性混合的群體中要少得多,有女性在場時,他們談論其他人和技術話題較多。相較之下,女性在全女性和混合性別群體中,所談話題的差異小得多,她們比較會保持一致的話題模式。多年後,我和伊朗語言學家馬迪.達瑪丹( Mahdi Dahmardeh)合作,對伊朗的波斯語母語人士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因為我們記錄了這些對話,所以可以衡量出談論每個話題的確切字數。社交話題再次占據主導地位,在女性的對話中,約 83% 的談話時間是用在社交話題,男性則為70%。與英國的樣本一樣,在全女性和混合性別的群體之間,女性的話題比男性在同樣的情況一致得多。


亞利桑納大學的馬提亞斯.梅爾(Matthias Mehl)、西敏.瓦齊瑞(Simine Vazire)等人以我們的實驗為基礎,做了技術更複雜的實驗版本,他們說服了79名學生穿戴自動錄音設備,每小時記錄他們談話的八次,每次半分鐘。這些學生們戴了四天錄音設備,讓研究人員能夠確定穿戴者是否在對話,以及對話是隨意的(閒聊),還是更專注認真。他們發現,較少獨處,而對話時間較多花在有意義談話(而非「閒聊」)的人,有更高的幸福感。馬提亞斯後來也證明,這些結果在及成年人身上也一樣。他和助手還對上醫院就診的病患、一家成人身心健康診所的義工和一群離婚的人做了抽樣調查。儘管他們花在閒聊上的時間長短與他們對人生的滿足程度無關,但花在有意義談話上的時間確實可以預測他們對人生的滿意度。
我們用了幾個實驗研究來追蹤這些觀察研究,這些實驗研究用對故事內容的記憶深入了解語言才能的設計,其想法是,如果設計語言的目的是傳遞事實知識,那麼我們應該最容易記住事實細節;相反地,如果它的設計是以社交功能為考量,那麼我們應該更容易記住故事的社會內容,尤其是心理層面的內容。共有兩個系列的實驗探索這個想法,一個是由亞歷克斯.梅索迪(Alex Mesoudi,現為埃克塞特大學教授)負責,另一個由吉娜.瑞德海(Gina Redhead) 負責。兩項研究都顯示,與純粹的事實敘述相比,我們更容易記住故事的社會內容,尤其是與演員心理狀態相關的內容。換句話說,我更可能記住你為什麼打算做某事,而非光是簡單地記住你做到了。如果我知道你為什麼做它,我就可以重建你做了什麼,但我當然無法僅由知道你做了什麼來重建你的動機。
再一次地,這純粹是在於了解說話者的心理狀態,以及是什麼激發了他的行為。事實上,這個過程似乎是記憶過程的基礎。心理學家的研究顯示,當刑事審判中的證人在回憶當時發生的事時,他們並非重新播放發生情況的影片;相反地,他們記得一般原則,例如可能的動機,並且重建事件,以符合他們對潛在動機的了解——這說明了為什麼目擊者即使看到相同的事件,也經常會有分歧的說法。
在對自然對話內容的觀察研究中,我們發現批評性的評論(負面的閒話)相對較少(不超過對話時間的5%)。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在餐廳等相當公共的場所對談話進行採樣之故,人們可能比較願意把對他人的批評留在較私密的場合,以免被別人聽到。然而,負面八卦顯然具有社會效益:它降低了我們社會群體成員剝削我們的風險,即使對他人的抱怨不常有,卻依舊有助於減少不良行為的發生頻率。紐約州北部賓漢頓(Binghamton)大學的凱文.尼芬(Kevin Kniffin) 和 大衛.史隆.威爾森(David Sloan Wilson) 聽了划船隊員的對話,發現隊員對出力不如其他隊員者的抱怨經常可以產生讓預期效果,讓偷懶的人出力。
同樣地,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畢安卡.畢爾斯瑪( Bianca Beersma)和戈本.范克里夫(Gerban van Kleef)在實驗研究中發現,如果事先告訴一個團體中的成員,大家會傳播誰對團隊有貢獻,誰又沒有貢獻的消息,在團隊合作時,成員出力的可能性就會高得多。小道消息似乎確實能控制團隊成員,社會神經科學的先驅麗莎.費德曼.巴瑞特 (Lisa Feldman Barrett)把中性面孔的照片配上對此人負面、中性或正面的流言。當同樣的照片後來與中性刺激一同出現時,受測者較可能注意的是與負面八卦(「朝同學扔椅子」)配對的面孔,而非與中性傳言(「在路上走時越過一個男人」)或正面陳述 (「幫助老太太提東西」)相關的面孔。比起忽視一個好人來,受欺騙或受攻擊是昂貴得多的錯誤,所以如果有人名聲不佳,我們就較有可能會注意。我們會記住他們是誰,做為將來的參考。
不論多常批評別人,我們大部分的談話似乎都是關於我們自己的社會訊息交換(我們的好惡),關於我們的人際關係和第三方人際關係的討論,對未來社會事件的安排,以及對過去事件的回憶。在小規模的傳統社會中也是如此,儘管他們經常用社會八卦來監督人們的行為。畢生都在非洲南部波札那研究 !Kung 布希曼人的猶他大學人類學者波莉.魏斯納 (Polly Wiessner)對 !Kung 在夜晚圍著營火的對話,和他們白天的談話做了採樣,發現兩者有鮮明的對比。他們白天的對話通常與事實和經濟有關,並且經常牽涉對其他人行為的抱怨,而在晚上當他們圍著營火時的談話則主要是講故事和傳說。在白天,34% 的對話和抱怨有關,只有6%是故事;而在晚上,85%是講故事和神話,而只有7%是抱怨。
我們確實由聽某人說某事,以及人們在對話中如何互動,而獲得了很多關於他們關係本質的訊息。簡而言之,嘟囔抱怨的效果幾乎和言語一樣好。
重要的不是說什麼,而是說的方式
然而總體而言,我們使用的字詞只是等式的一小部分,尤其是在關於社交世界的訊息傳播方面。當我們說話時,會由環繞在我們話語周圍的非語言線索中獲得數量驚人的訊息。其中有些是臉部的線索(做鬼臉、微笑),有些是聲音(音調的起伏、語氣的高低),有些是姿勢(聳肩、手勢)。你說話的方式可以完全改變你所說的意思,這就是「那真是太好了!」(意思是:一百萬個感謝)和「那真是太好了!」(意思是:你為什麼對我如此惡劣?)之間的語氣差別)。
1970年代,伊朗出生的美國社會語言學家艾伯特.麥拉賓(Albert Mehrabian)以一些簡單精準的實驗為基礎,宣稱我們所說的訊息中,實際上約有93%是由非語言的線索所傳達(38%來自語調,55%來自來自臉部的線索),僅有7%是來自文字實際的含義。這個說法引起了相當大的注意。後來有許多心理學者質疑他的說法,隨後也有實驗反駁他的觀點,然而這些實驗也有它們自己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研究人員用演員來模擬不同情緒的話語內容,而且他們幾乎總是只使用一個單字或短語。這些刺激與真實對話的關係,就像米老鼠卡通片與現實人生的關係一樣。我們對話時,通常是兩個或更多人冗長的對談,這提供了更複雜的語境和語言的資訊。此外,這些實驗通常牽涉到的刺激是,語言內容表達一種情緒(「我很傷心」),但非語言線索卻表達相反的意思(「我很高興」)。對於這些「演員」實際上可以把這種相當複雜的表演水準做到什麼程度,我持懷疑的態度。這樣混雜的訊息對受測者造成的混亂,使我也質疑這類實驗的設計。
不過,最近的兩個實驗提供了一些理由,讓我們認為麥拉賓可能是對的。格雷戈里.布萊恩特(Gregory Bryant)負責安排了一項大規模研究,讓全球各地24種不同文化的人,有些是部落,有些則是已西化的文化,聆聽兩個美國白人一起笑的錄音片段,然後只要決定這兩人是朋友還是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整體而言,受測者的表現(55-65%正確)比隨機選擇(50─50)稍好一些。有趣的是,如果笑的兩個人都是女性,受測者識別出她們是朋友的成績(正確率為75-85%)就好得多。在另一個實驗中,艾倫.柯文(Alan Cowen)及同僚詢問美國人和印度人的樣本,要他們決定演員以許多不同的語言說出情感的字詞或短語是表達什麼樣的情感。他們發現兩種文化同樣擅長識別一組14種的基本情緒。再一次地,雖然他們的成績比純猜測要好,卻離完美還很遠。
儘管這兩個實驗都很高明,但還有很多需要改進之處,無論是在它們的設計方面,還是它們仍然未涉及對話的事實上。為了要在較現實的環境中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我在一項研究中與劍橋藝術家艾瑪.史密斯(Emma Smith)及音樂學者伊恩.克羅斯(Ian Cross)合作,我們讓聽眾聆聽一組八段由YouTube剪輯的真實生活自然對話。這八段對話中,每一段都是選來代表一種不同的關係(四種負面和四種正面關係)。一半的受測者聆聽的是英文的對話,另一半聆聽的是西班牙文對話。受測者除了聽原本的對話外,也聽了經過過濾的同一段對話,過濾的方式不是掩蓋了實際的單字(但保留了語氣和音調),或者更極端的,把聲音信號轉變為純音調(僅限音調)。它們是由智利學生胡安─帕布羅.羅布利多.德爾.坎多(Juan-Pablo Robledo del Canto)所設計的高明軟體所製作。在每一種情況下,我們都要求受測者用我們發給他們表單,辨識其上列的八種關係。為了提升複雜度,我們做了兩次實驗,一次是針對在英國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另一次則是針對在西班牙,以西班牙文為母語的人(西班牙版本由才華洋溢的馬德里主力研究人員伊格納西奧.塔馬利特Ignacio Tamarit負責)。
和麥拉賓的原始實驗(僅要求受測者辨識關係是正面或負面)一樣,我們的受測者表現幾乎和他的受測者一樣好:對於言語內容遭掩蓋的錄音片段,他們的正確度達到完整錄音片段的75-90%。即使要求他們辨識是他們所聽八段關係中的哪一段,他們對掩蓋內容片段的正確度依舊是完整片段的45-55%,比隨機猜測的正確度(大約12%)高四倍。更重要的是,不論是英文或西班牙文為母語的人,對辨識說對方語言者的關係,也和說他們自己語言者一樣準確,儘管大多數人都表示他們並不懂對方的語言。我們確實由聽某人說某事,以及人們在對話中如何互動,而獲得了很多關於他們關係本質的訊息。簡而言之,嘟囔抱怨的效果幾乎和言語一樣好。
觀察人們這些年來,我注意到不僅女性比男性更常微笑,而且她們微笑起來似乎比男性更自然。男性的微笑看似比女性勉強,我懷疑這與兩性頦骨結構的差異有關⋯⋯
當你微笑時,世界就與你一起微笑
如果對話和人際關係缺乏某個行為,將會無比沉悶,那麼這個行為必然是微笑。俗話說,微笑是世界通用的語言。微笑表示出興趣,允許對話繼續下去,表示鼓勵讓你知道你們的互動受到歡迎,表達歉意和同情,以及其他十幾種情感。大多數人認為微笑和大笑是同一回事,微笑只是尚未完全表達出來的笑聲。但其實大笑和微笑有個很重要的區別。如我們先前所提的,歡笑來自於猿猴在玩耍時的臉(嘴巴張開,但不露出牙齒),而微笑來自於猴子順從的臉。猴子「露出牙齒的臉」(齜牙裂嘴)代表屈從妥協,和歡笑時的圓張嘴(ROM)臉孔相比,微笑就像齜牙裂嘴一樣,把牙齒緊緊地咬合在一起,嘴唇分開,顯示牙齒。儘管這兩者都和友誼有關,但其中一種是建立關係,另一種則是表示順從。這就是當我們緊張或尷尬,或者當我們被介紹給不認識或地位比我們高的人時,會一直微笑的原因。換言之,雖然歡笑和微笑在人類身上有點混為一談,但它們的起源非常不同,也象徵實際上南轅北轍的動機。就像大笑一樣,微笑有兩種:不由自主的「杜鄉式的微笑」,表示安撫勸慰(延伸為包括同意之意)和自主的非杜鄉微笑,表示禮貌的默認。杜鄉式的微笑鼓勵進一步的互動,而非杜鄉式的微笑則表示不確定和緊張。
馬克.梅胡(Mark Mehu,當時是我的研究生,現在是奧地利韋伯斯特維也納大學的助理教授)做了一系列觀察和實驗研究,他發現,在兩人互動時,杜鄉式的微笑更常與慷慨分享相關。確實,微笑較可能被評為代表慷慨和外向,尤其是在男性的臉上。然而,這些效果的確表現出強烈的兩性異形(sexual dimorphism,同一物種雌雄兩性的差別)現象:微笑的臉孔是女性,而觀者是男性時,最可能會把微笑的臉孔視作慷慨的表現。他還發現,在如夜店等自由形成的社會環境中,處在年齡混合人群中的年輕男性比較年長的男性更常表現出非杜鄉式(勉強)的微笑,而較年長的女性則比年輕女性更常做出勉強的微笑。
羅伯特.普羅文對自然情況下的笑做了廣泛的觀察研究,得出類似的結果。他注意到女性對男性所說的話比對女性所說的更容易發笑;而男性對任何性別所說的話,都不如女性那樣容易微笑。他把女性的行為解釋為一種安撫,對男性尤其是如此,但對其他女性也一樣。微笑是臣服的行為,可能會鼓勵我們對別人不那麼挑剔或多疑。勞倫斯.瑞德(Lawrence Reed)發現,如果照片中的人綻開杜鄉式的微笑,人們較會相信對照片中人行為的陳述,但如果照片中的人露出非杜鄉式的微笑或勉強的微笑(就像你為了阻止自己露出杜鄉式微笑而裝出來的微笑),那麼人們最不相信對照片中人的陳述。
讓我順便提一下題外話。觀察人們這些年來,我注意到不僅女性比男性更常微笑,而且她們微笑起來似乎比男性更自然。男性的微笑看似比女性勉強,我懷疑這與兩性頦骨結構的差異有關,尤其是頦隆突(mental protuberance,下頦左右兩半結合在一起之處)的大小。男性的頦隆突較大,而且他們的下頦通常較方,角度更銳利,使他們的下頦突出更多。男性下頦的形狀似乎使微笑肌肉更難拉開嘴唇。下回你看到人們交談時不妨觀察一下,看看你是否同意這種說法。
延伸閱讀:

范耀宸:「無障礙空間」情感下的消極關係——讀《為什麼不愛了》

陳力深:不只是「約砲神器」——交友軟體的政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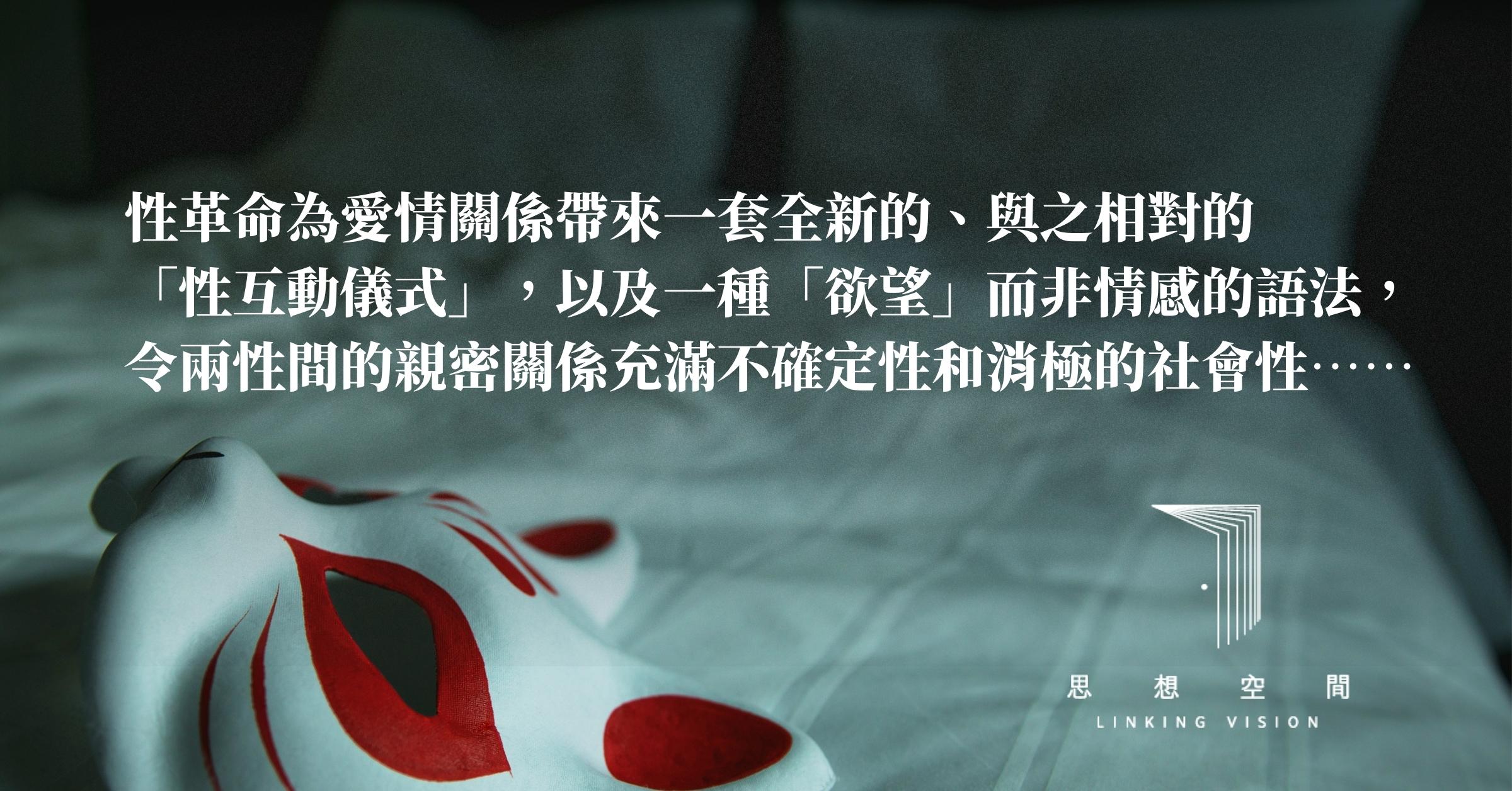
盧勁馳:當愛情成了一種社會關係,我們如何從中探索身份政治
| 閱讀推薦 |

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演化心理學家,也是牛津大學實驗心理系認知與演化人類學前任所長。他知名的作品包括《150法則:從演化角度解密人類的社會行為》(How Many Friends Does One Person Need ?)以及與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合著,被譽為「大眾科學傑作」的《哈拉與抓虱的語言》(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