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英時
編按:2022年8月11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發佈訃告,著名圖書館家、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先生(Eugene Wu)在美國加州離世,享壽100歲。1922年,吳文津出生於四川成都,青年從軍,二戰後就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及圖書館學院,復在史丹佛大學博士班攻讀中國近代史。吳先生曾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東亞圖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任職館長,收集了海量的歷史文獻,為現當代中國研究提供了非常堅實的史料基礎。2016年,吳文津的中文著作《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由聯經出版,該書敘述了美國東亞圖書館演變和發展、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之史實及其收藏,余英時先生亦曾為本書作序,詳述了吳文津的圖書館生涯之餘漢學研究史的重要意義。(本文摘選自《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序,標題為編者擬。)
吳文津先生和我相知已近半個世紀。現在為他的文集寫這篇序文,我實在感到無比的高興,因為這恰好給我提供了一個最適當的機會和方式,藉以表達對老友的敬意。讓我從我們友誼的始點──哈佛燕京圖書館──說起。
我初次接觸哈佛燕京圖書館,便得到一次很大的驚異,至今記憶猶新。1955年10月我以「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的資格從香港到哈佛大學進修。那時我正在進行有關東漢士族大姓的專題研究,因此行裝安頓之後立即展開工作。我雖然早已聞哈燕社漢和圖書館之名,但是它藏書之完備還是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之外。我在香港多年遍求不獲的書刊,在此一索即得。這是我受惠於哈佛燕京圖書館之始。第二年我進入研究院,它更成為我求知的一個最重要泉源了。
時間稍久,我終於認識到裘開明先生(1898-1977)作為第一任館長對於哈燕圖書館作出的重大貢獻。哈佛的中、日文藏書之所以在美國大學圖書館系統中長期居於領先的地位,裘先生的功勞最大。[1] 所以在哈佛從事中國或東亞研究的人,無論是本校人員或外來訪客,也無論是教授或研究生,多少都對裘先生抱有一種感激的意識。1964年費正清、賴世和與克雷格三位哈佛教授將他們合著的《東亞:現代的轉變》獻給裘先生,便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意識。[2] 我還記得,1960年代初期,我們都非常關注一件大事:裘先生不久將退休了,誰來接替這一重要職位呢?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重心也從傳統時期擴展到中國和東亞的現代了。這便是文津先生受聘為第二任館長的時代背景。但為什麼入選的是文津先生,而不是任何別人呢?
1966年我重回哈佛任教,裘先生已於上一年退休,繼任人則是吳文津先生,於1965年就職。吳文津先生前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館長,以收藏現代中、日資料獨步北美。由一位現代圖書館專家接替一位古籍權威為第二任館長,這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發展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我這樣說絕沒有絲毫故甚其辭的意思。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現在可以斷定:這件大事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因為它象徵著美國的中國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下面讓我試對這一論斷的根據略作說明,以求證於文津先生及一般讀者。
首先必須鄭重指出,1928年登記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自始便以推動國際漢學(Sinology)為它的主要宗旨之一。因此哈燕社最早的一位諮詢人是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Paul Pelliot);他同時也是創社社長的內定人選。但是他最後不肯接受社長的聘約,轉而推薦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作他的替身。葉氏出自帝俄世家。專治日本古典文學,畢業於東京大學。1917年革命後,他移居巴黎,在伯希和門下從事研究,並成為後者的學術信徒。在他的領導下,哈燕社的國際漢學取向便確定了下來。[3] 不用說,漢和圖書館為了配合這一取向,書刊的收藏自然也以19世紀以前的傳統中國與日本為重心所在,而且特別注重精本與善本。在這一取向下,裘開明先生的許多特長,如精確的版本知識以及他與當時北平書肆和藏書家的深厚關係等,恰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哈佛燕京圖書館終於成為西方漢學研究首屈一指的圖書館中心,絕不是倖致的。[4]
但是從20世紀中葉起,中國研究這一領域在美國開始了一個劃時代的轉向。這一轉向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就研究的內涵說,專家們越來越重視中國的現狀及其形成的時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漢學家們所最感興趣的傳統中國就受到比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徑論,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門的專業紀律獲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漢學傳統中的文獻考釋則退居次要的地位。
為什麼會有這一轉向呢?這當然是因為二戰後中國的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美國在東亞的處境受到嚴重威脅,以致當時美國朝野都在爭辯「美國為什麼失掉了中國?」的問題。事實上,1949年8月美國政府頒布的關於中國的《白皮書》是國務院內外的中國專家集體編寫的,主要根據現代史及檔案來解答「為什麼失去中國」的問題。美國許多第一流大學在1950年代群起向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進軍,而且成績輝煌,顯然是因為受到了上述政治氛圍的激勵。
我恰好見證了這一轉向在哈佛大學的展開過程。1955年費正清在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下,創建了「東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我清楚地記得,當年這中心網羅了一批校內外的專家,從事長期或短期研究。他們的專題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現代中國的範圍之內;其研究成果則往往以專著(Monograph)的形式出版,構成了著名的《哈佛東亞叢書》(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5]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和大學提供了較多的獎學金名額,哈佛研究院(Graduate School)中以現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博士生與碩士生也人數激增。他們遍布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門之中,因而將中國研究和現代專業紀律有系統地結合了起來。
相應於這一研究轉向,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收藏重心也從傳統時期擴展到中國和東亞的現代了。這便是文津先生受聘為第二任館長的時代背景。但為什麼入選的是文津先生,而不是任何別人呢?這是我要接著說明的問題。

自1959年繼任中文圖書館館長,獨當一面以來,文津先生搜求資料的精神才逐步透顯出來。這個精神我無以名之,只有借用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事實上,文津先生當時確是最理想的人選,因為在現代中國研究的領域中,胡佛研究所的資料收藏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而文津先生的卓越領導則有口皆碑。
胡佛研究所最初以收藏歐洲當代與戰爭、革命與和平相關的資料著名。二戰以後範圍擴大到東亞,分別成立了中文部與日文部。收藏的範圍以20世紀為限。1948年芮瑪麗(Mary C. Wright, 1917-1970)受聘為首任中文部主任,直到1959年移講耶魯大學歷史系為止。她是費正清的大弟子,後來以深研同治中興和辛亥革命為史學界所一致推重。在她任內,現代中國的收藏已極為可觀。其中包括1946-47年她親自從延安搜集到的中共報刊、伊羅生(Harold R. Issacs)在二、三○年代收羅的中共地下刊物、斯諾(Edgar Snow)夫婦所藏有關文獻等。[6]
但胡佛研究所的一切收藏最終匯為一個完備現代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圖書中心,則顯然出於文津先生集大成之功。限於篇幅,他的輝煌業績在此無法充分展示。但邵東方先生在2010年總結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對文津先生的貢獻有一段很扼要的概括,其文略曰:
作為美國華人圖書館長的先驅,吳文津對胡佛研究所的中文收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51年首任中文藏書館長芮瑪麗聘請他入館工作。1956年他已成為副館長。1959年芮加入耶魯大學歷史系後,吳則繼任館長之職(按:「中文藏書館長」也就是「中文部主任」。)1961年胡佛研究所決定將中、日文部合成「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吳則成為第一任館長。在他1967年11月就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時,吳已將「東亞藏書」轉變為美國收藏現代中、日資料的一個主要中心了。(按:吳文津先生就職哈燕圖書館館長時期為1965年10月。)就現代中國的資料而言,館中所藏之富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更是屈指可數。[7]
這一概括既客觀又公允,不過僅僅呈現出文津先生在事業方面的一個靜態輪廓。下面我要對他的動態精神略加介紹。

自1959年繼任中文圖書館館長,獨當一面以來,文津先生搜求資料的精神才逐步透顯出來。這個精神我無以名之,只有借用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事實上,無論是傅先生或文津先生,所發揚的都是中國史學的原始精神,即司馬遷最早揭出的所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文津先生只要聽說任何地方有中國現代研究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他便不顧一切困難,全力以赴地去爭取。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1960年他在台北拍攝了全部「陳誠特藏」的檔案。所謂「陳誠特藏」是指「江西蘇維埃共和國」的原始資料,1930年代初由陳誠的部隊在江西瑞金地區俘獲得來;運到台北以後,陳把這批資料交給下屬蕭作樑等人整理和研究。1960年4月有兩位美國專家專程到台北,希望獲得閱覽的機會。蕭請示陳誠,得到的批示是:「反共的人士都可以參觀」。但這兩位專家一向有「左傾」的聲名,蕭感到為難,因此求教於當時深受陳誠敬重的胡適。最後胡的答覆是「不妨寬大些,讓他們看看」。[8]
此事發生在文津先生赴台北爭取「陳誠特藏」之前6個多月,二者之間有內在的聯繫。文津先生認識到這批原始資料的重要性曾受上面兩位專家越洋「取經」的影響,這是可以斷言的。不但如此,文津先生也同樣得到胡適的助力。他告訴我們:
為此事1960年第一次來台灣。當時台灣的條件很差,據說攝製縮影微卷的機器只有兩部。一部在中央銀行,一部在中央研究院。那時胡適之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去請他幫忙。他一口就答應了。把機器與操作人員都借給我使用。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把這批將近1,500多種的資料照成縮微膠卷帶回美國……[9]
但是我相信胡適的幫助並不僅僅限於技術方面。上面提到他關於「不妨寬大些」的主張必曾對陳誠有所啟發,因而無形中也為文津先生開闢了道路。
在爭取「陳誠特藏」的整個過程中,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特別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初知台北藏有江西蘇維埃資料,但不得其門而入。稍後偶遇史丹佛大學地質系教授申克(Hebert G. Schenk),曾在台灣負責美援工作,與陳誠相熟。他便毫不遲疑地請申克教授介紹,終於得到複印的許可。可見他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中寓有一種「求道」的精神,不放過任何一點可能的機會。第二,他說爭取這一套極為珍貴的史料,最初是為了「加強胡佛對中共黨史的收藏」,這是忠於職守的自然表現。然而他對於研究資料卻抱著「天下為公」的態度,不存絲毫「山頭主義」的狹隘意識。因此他後來又取得陳誠的許可,「將這批資料再作拷貝以成本供應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以作研究之用」。[10] 他的職位在胡佛研究所,但是他同時也為全美所有東亞圖書館提供研究資料。

「三十年來你是發展現代和當代中國研究資料的中心動力……牢記中國的傳統價值,我們景仰你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抱負,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傳播與他人共用知識。」
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他在1960年代中期繼獲得江西蘇維埃資料後去爭取胡漢民1930年代未刊的來往信札事。早時,他得知胡木蘭女士存有她父親1930年代與中國各政要的私人手札。胡漢民為國民黨元老,且為華南地區舉足輕重之人物,這批資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與「陳誠特藏」一樣,他不得其門而入。後多方打聽,經友人介紹,得識胡木蘭女士及其夫婿。經數年之交往,來往美國與香港之間,得木蘭女士之信任,允考慮將胡漢民先生之信札寄存胡佛研究所,並開放予學者使用但不能複印,而個案研究則必須先得其批准。1964年文津先生受聘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1965年就職),胡女士得知後,頗為躊躇,因不知接任文津先生者為何人,乃建議將胡漢民先生之信札轉存哈佛燕京圖書館,由文津先生保管,使用條件依舊。文津先生喜出望外,欣然應允。於是這批2,700餘件信札遂寄存哈佛燕京圖書館。這一批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是研究民國史所不可或缺的;後經陳紅民教授編注,並得胡木蘭女士家屬的許可,於2005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15大冊,以惠士林。[11]
上述文津先生的基本精神稍後更得到一次大規模的發揮。1964年「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及「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下面有一個「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因為感到美國所藏當代中國資料之不足,決定調查世界各國的收藏狀況,以供美國參考。由於文津先生在這領域中的卓異成就,這一重任終於落在他的肩上;1964-65年期間,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全世界進行調查工作。他對這一件事,作了下面一段簡報:
調查一年時間裡,通過走訪西歐、東歐、斯堪的納維亞、蘇聯、印度、日本、台灣、香港的重要中國研究和圖書中心,還有美國本土圖書館,我發現蘇聯和東歐的部分圖書館,可以通過我們沒有的途徑從中國獲取原始研究資料,西歐和日本也有,但相對較少。大多數這些圖書館都接受與美國進行交換。所以在呈交給JCCC(按:即「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縮稱)的報告中,我建議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東亞圖書館服務中心來確定、獲取(通過館際互借和交換)以及複製分配那些無法獲取的當代中國書刊和只有少數美國圖書館才能擁有的稀缺研究資料。[12]
這一次調查旅行,地區之廣大和查詢之詳細,真正不折不扣地可稱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的報告和建議都是為全美各大學的現代中國研究著想,所以特別強調研究資料必須向所有圖書館開放。更值得指出的是:「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接受了他的建議,終於在1968年成立了「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這中心先後複製了無數難得的資料,不但遍及全美,而且流傳世界各地。正如文津先生所言,如果沒有這個資料中心,「各地圖書館現在是不可能擁有那麼多中文書刊的」。
總之,1964-65年文津先生的調查旅行不僅是他個人事業的不朽成就,而且也是美國現代中國研究史和東亞圖書館發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難怪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1988年頒發每年一度的「傑出貢獻獎」(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給文津先生時,獎狀中有下面的詞句:
三十年來你是發展現代和當代中國研究資料的中心動力……牢記中國的傳統價值,我們景仰你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抱負,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傳播與他人共用知識。本學會表彰如此傑出的事業生涯也是為自己增光。[13]
以上舉文津先生在史丹佛大學時代的幾個重要活動為例,旨在透顯他的獨特精神。通過這幾個事例,哈佛燕京圖書館為什麼非請他繼任第二任館長不可,便無須再作任何解釋了。

無論我們是要認識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歷史動向,還是想理解西方人怎樣研究這一動向,《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都能給我們以親切的指引。
文津先生到哈佛之後,雖然面對的具體問題與胡佛研究所不同,但他的精神則一仍舊貫。哈佛燕京藏書初以漢學取向,這一點前面已說過了。由於裘先生在這一領域已建立了規模,文津先生大體上蕭規曹隨,但始終維持著它的領先地位。我對此有親切的體會。因為漢學正是我的工作領域。我和文津先生共事10年,從來沒有感到研究資料方面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但在近代和現代中國的研究領域中,文津先生則將哈佛燕京的收藏帶到一個全新的境地。詳情不可能在此陳述,我只想提一下他在收集「文革」資料方面所費去的時間和精力比他走遍全世界調查現代中國資料更為艱巨,也更有成就。1965年他到哈佛的時候,正是文革前夕,但資料已極為難求,1966年文革起始後,中國出版界除《毛澤東選集》及《毛澤東語錄》等外,工作幾乎全部停頓。但各地紅衛兵小報遍起如雨後春筍,部分帶至香港經書商複印出售者為唯一可收購之資料,但供不應求,以致洛陽紙貴。當時美國國務院應學術界的要求,願意公開政府所收集的紅衛兵資料。於是上述的「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又邀請文津先生負起這一重任,到國務院閱讀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資料。他認為其中紅衛兵小報和周恩來等人與紅衛兵代表的談話記錄等都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因此建議國務院儘快公開於世。但1967年時「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尚在籌建中。於是哈佛燕京圖書館將最早從國務院收到的資料製成縮微膠捲,以成本計向各圖書館發行。這是他幾年前複製「陳誠特藏」的故智。直到1975年「中國研究資料中心」才出版了紅衛兵資料20卷,以後每隔幾年便續刊數十卷。我同意文津先生的話,這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公開出版的紅衛兵資料集」。[14] 最有趣的事是1980年5月考古學家夏鼐第一次訪問哈佛,也特別記下文津先生給他看的「紅衛兵各小報縮印本20餘冊」。[15] 我猜想夏所見的必是1975年「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的20卷本。
文津先生的精神一以貫之,此其明證。具此精神動力,所以他的成就特多,而為各方所推崇。上面已提到美國亞洲學會的「傑出貢獻獎」。先生1997年榮休時,哈佛大學校長魯登斯廷(Neil L. Rudenstine)在他的賀文中列舉先生對哈佛的貢獻之外,在末尾說:
我非常高興加上我個人以及哈佛全體同仁對他為哈佛作出的示範性的傑出貢獻致謝。文津,你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個更好的大學。[16]
最後,我要鄭重指出,這部文集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絕不可以一般個人的文字集結視之。無論我們是要認識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歷史動向,還是想理解西方人怎樣研究這一動向,《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都能給我們以親切的指引。
2013.10.17於普林斯頓
2016.1.6重新改定
[1] 參看本書所收〈裘開明與哈佛燕京圖書館〉。
[2]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5, p. ix.
[3] 陳毓賢,《洪業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159-160。
[4] 參看本書所收〈哈佛燕京圖書館簡史及其中國典籍收藏概況〉。
[5] 最早第一本書是2013年4月27日過世的費維凱(Albert Feuerwerker)的名著: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1958.
[6] 吳文津,〈美國東亞圖書館蒐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況〉收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書林覽勝》(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頁33-35。此文已收在本書中。
[7] Dongfang Shao in collaboration with Qi Qiu, “Growing Amid Challenges: Stanford University’s East Asian Library,” in Peter X. Zhou, ed., 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0, p. 182.邵先生寫此文時正在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的任內。
[8]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第9冊,頁3248-9。
[9] 同注6《書林覽勝》頁36。1960年11月10日他向胡辭行。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296。
[10] 同上,《書林覽勝》,頁36。參看本書所收〈《江西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陳誠特藏文件選輯解題書目》前言〉。
[11] 吳文津口述。
[12] 吳文津,〈北美東亞圖書館的發展〉,張寒露譯,《圖書情報知識》,2011年第2期,頁8。該篇英文原文“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載Chen Chuanfu and Ronald Larsen, e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Trends and Research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pp. 163-177.參看本書所收〈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資料問題〉,原載《書林覽勝》,頁87-89。
[13] 獎狀頒予1988年3月26日。此段原文為:“For three decades you have been the central dynamic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sources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Remembe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we admire you for the aspirations you inspire in others, for your achievements which benefit others, and your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shared with others. The Association honors itself in recognizing so distinguished a career.”至今吳文津先生仍為東亞圖書館界得此殊榮譽之唯一人物。
[14] 同注12。參看《文集》所收〈《新編紅衛兵資料》序〉。
[15] 《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8,頁426。按:夏氏當時還弄不清楚文津先生的姓名,只知道他是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四川人。
[16] 魯登斯廷校長賀詞結語的原文是:“I am very pleased to add my own thanks and the thanks of all of us at Harvard for his exemplary 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Harvard community. Gene Wu, you have made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and Harvard is a better university because of it.”
延伸閱讀:

啟蒙者、自由主義者、左翼作家、保守主義者相互鏈接,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思想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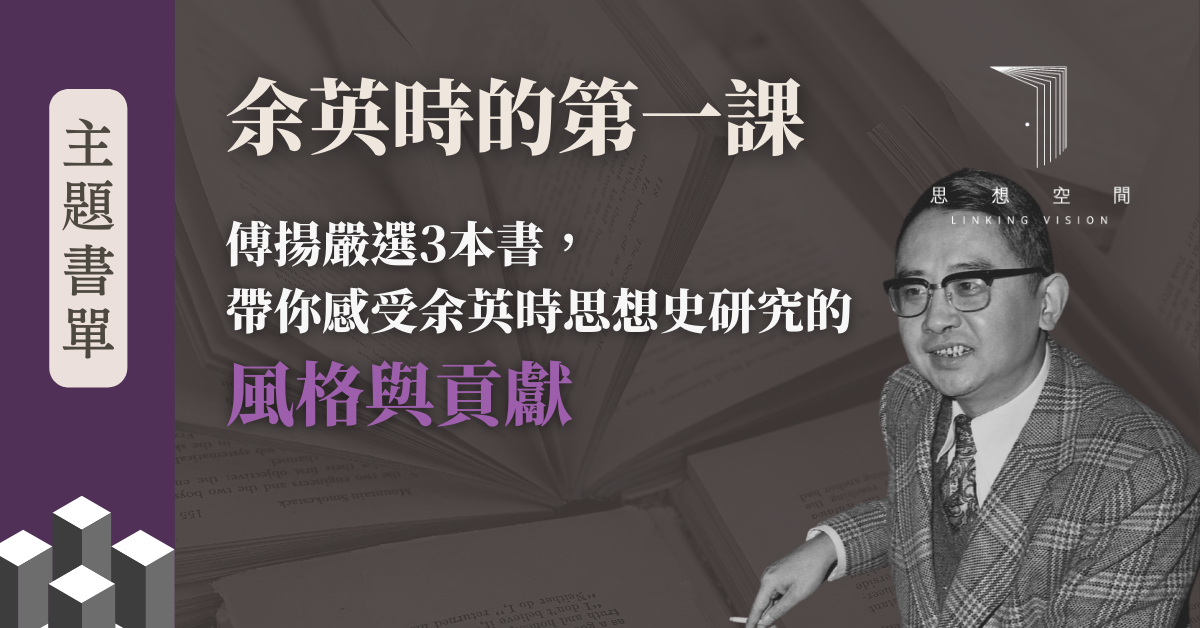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傅揚嚴選3本書,帶你感受余英時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與貢獻

容啟聰:第三勢力與冷戰:由余英時的《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1930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2014年榮獲「唐獎漢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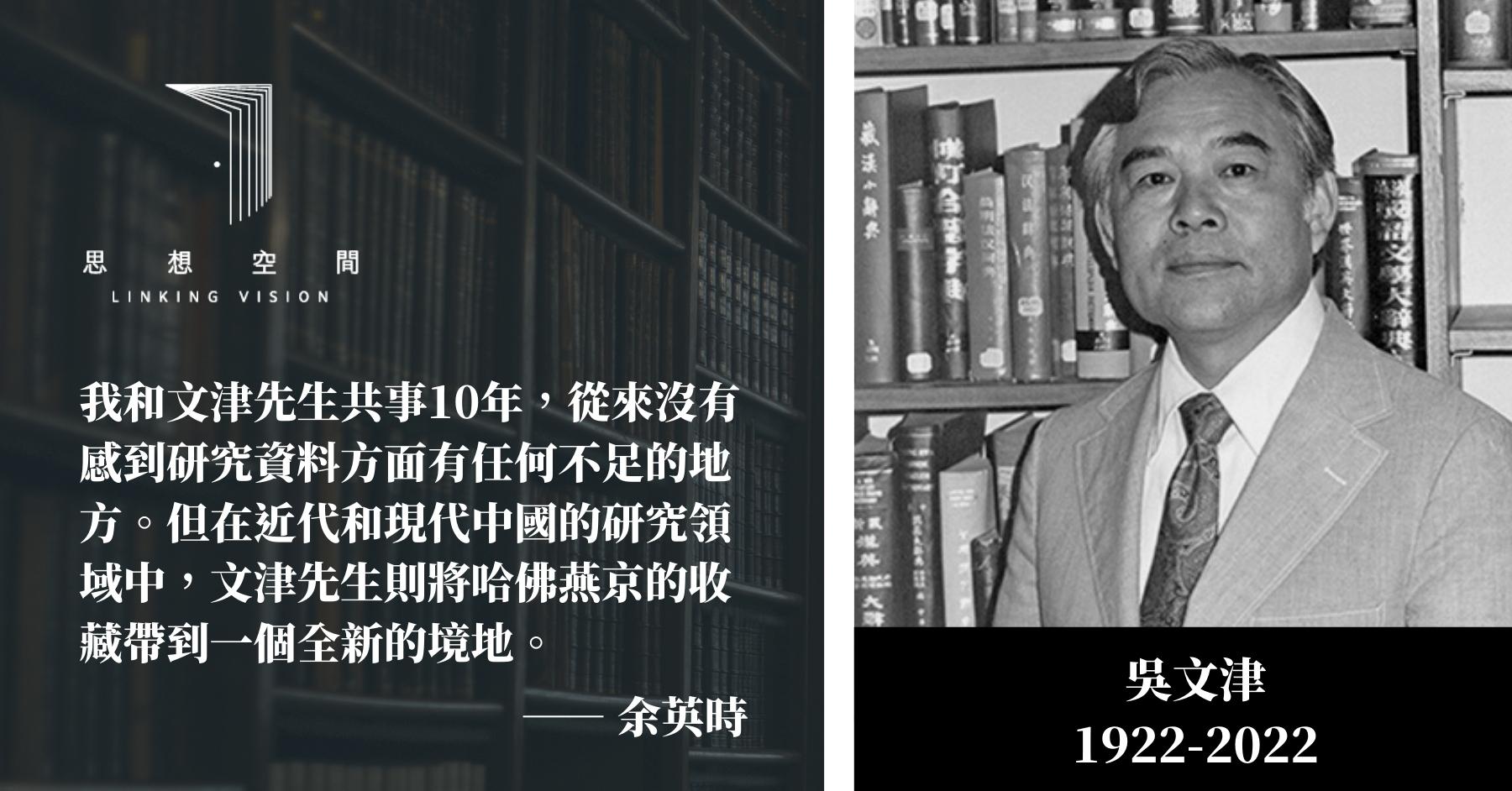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