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雪虹(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許多年前,我帶著我的丈夫夏木(當時我們還只是情侶,而且都是學生)回馬來西亞旅行一個月。我記得那是北京的盛夏,在馬來西亞正巧是伊斯蘭教徒的齋戒月。那是夏木第一次去馬來西亞。因為想看紅毛猩猩,所以我們從西馬飛到東馬沙巴州的山打根市。離山打根市中心大約二十五公里有一所人猿庇護中心(Sepilok Orangutan Rehabilitation Centre),據說那還是全世界最大的人猿保護中心。在山打根的那幾天,我們每天下午都去逛齋月的巴扎。齋月期間,馬來西亞各個城鎮每天都會有穆斯林的巴扎。穆斯林小販聚集在一起售賣各種清真食品,比如說糕點、椰漿飯(nasi lemak)、竹筒飯(lemang)、沙爹(satay),以及各種飲料。太陽下山後,齋戒了一整個白天的穆斯林恢復進食,因此所有人都趕在天黑之前到巴扎選購食物,以便及時吃上一頓豐盛的開齋飯(iftar)。
「那粉色的飲料是什麼東西?」夏木問我。
「喲,這麼多蒼蠅!」他又一次為著眼前陌生、新奇的景象而興致高昂。夏木當時在上人類學研究所,我經常笑稱他果然接受了正規的人類學訓練,對任何族群的文化或「奇風異俗」都能保持好奇心和尊重。
夏木說的粉紅色飲料是玫瑰露(air bandung)。不止粉紅色,我們還有艷紅色、淡綠色、奶黃色、白色、亮綠色、淺棕色和紫色的飲料。糕點的顏色也是如此。我們似乎很擅長在烹飪時使用食用色素,那些著色劑有的是人工合成色素,有的則直接來自植物的花或葉子,是大自然神奇的餽贈。
回想起來,十一年前的那場旅行於我而言是一條自我認知的分叉小徑。它引導我站在一個新的起點(視角)去觀望自己,或者說更全面地認識自己。此前我的生活環境所帶給我的是對身為一個華人這樣一種身份的認同,雖然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受到愛國教育的熏陶。但似乎由於華裔這個身份總是被凸顯,被視為更富有意義、更加重要,以及長久以來生活在多元種族的語境之中的緣故,像我這樣的華人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更在意自己的這個華裔身份。道理其實很簡單。在國內,族群議題經常是考量一件事的基礎點,人與人之間「對立」的地方是種族和宗教信仰;到了國外,人的身份轉換和更為多重,無論願不願意,將自己和他人區分開來的不再是或不僅僅是種族和宗教,而是一個人的國籍。
在許多華人眼中,一個華人皈依伊斯蘭教便意味著放棄華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變成馬來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族。
變成馬來人的華人,正在面對什麼?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旅途中,我和夏木的身份調轉了,他成了外國人,我們身處在我的國家,我以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向他介紹我的穆斯林同胞的宗教傳統和生活習俗。但很快我便意識到我能分享的大多是我和穆斯林的相處經驗和一些穆斯林的生活習俗,我對在這片國土上佔最大比例的穆斯林的宗教的了解並不深,儘管我每天生活在穆斯林當中,和他們的關係也非常融洽。
我的母親是一名裁縫,她的客戶絕大多數都是馬來人。她擅長製作馬來人的服裝,包括那些馬來新娘在婚禮上穿的精緻、華麗,經常帶有閃閃發光的金箔、假寶石或繡花的婚服。除了製作衣服,母親還曾經開辦裁縫課,學生也大多是馬來人。她和許多馬來人成為朋友,還認了一個年輕的馬來女子為乾女兒。
母親的裁縫鋪就在我們家的前廳,房子的後半部分則是我們的生活空間。但由於裁縫鋪裡經常開著空調,還有躺椅、電視機及冰箱,所以我喜歡待在那裡看書、休息。我經常看母親和顧客打交道,有時候也會幫忙招待客人。齋月是裁縫鋪最忙的時節,那些穆斯林客戶陸續來取訂製的衣服,有的還會帶自製的糕點送給我們。每年的那段時光總是和我們的農曆新年一樣令人難忘。
和關於開齋節的回憶聯繫在一起的還有我的大舅的婚姻。我的大舅是家裡的長子,教育程度也比較高。從本地的一所學院畢業後,他到一家手套廠當經理。他在工廠里結識了一個馬來女孩,不久兩人便結婚。根據伊斯蘭教法,穆斯林女子不許嫁給非穆斯林男子,所以我的大舅在結婚前便皈依伊斯蘭教。這件事在母親的家族中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許多華人眼中,一個華人皈依伊斯蘭教便意味著放棄華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變成馬來人」,背叛了自己的宗族。伊斯蘭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每天禮拜五次、齋戒、不吃豬肉,這幾樣足以讓華人覺得無法接受,更不用說不能像華人那樣在祭祖時執香跪拜,還有更換名字,起一個伊斯蘭名字。我的大舅後來確實換了個伊斯蘭名字,但仍然在新名字中加入自己的中文姓氏「鄭」(Tee)。這也意味著不管將來他有多麼「伊斯蘭化」/「馬來化」,人們還是可以從他的名字知曉他的種族。

我不經常回國,即便回國,也未必會見到我的大舅。他住在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而我們住在雪蘭莪州(Negeri Selangor),我們的家距離大約一百三十公里。多年以後,再次見到大舅時,我發現他的言談舉止和裝扮可以說是完全和馬來人一樣了。他的精神面貌和氣質也變了。也許這其中也因為逐漸年邁的緣故。他顯得更沉著和堅定,帶有一種虔誠的信徒(我願意視之為伊斯蘭教徒的敬虔)所特有的精神面貌,自律、自信、意志堅定,還有臉上的那撮山羊鬍子和頭上的那頂白色的塔基亞(taqiyah),那也是我們國家的(或許也是其他國家的)穆斯林男人的一個典型特征。
我最後一次見到大舅是在我母親的葬禮上。那是去年四月上旬。出殯當天,大舅領著母親的馬來男性朋友法益德(Fahyid)和他的妻子來到靈堂。那個馬來朋友是母親新認的乾兒子,看起來不到四十歲,在我家附近的政府機關工作。他聞到母親的死訊後趕來,想見母親最後一面。大舅在殯儀館外見到他們,便主動帶他們到靈堂。但棺木剛剛被釘上了。我觀察著法益德和大舅。雖然能看出他們兩人都有點焦急和遺憾,但昔日那種我所深刻感受到的屬於伊斯蘭精神的氣質仍隱約地彰顯出來。大舅和法益德站在母親的棺槨旁,兩人以馬來語談論母親和她的葬禮,他們語速緩慢,說話聲音不大,展露出內斂、溫文爾雅、親切的樣子。在整個出殯過程中,大舅的神態都是如此。
回到北京後,我和大舅開始在微信上聯繫。他詢問我父親的近況,還時不時給我發來一些視頻和他們全家到歐洲旅遊時所拍的照片。他後來不在工廠上班了,而是經營起超市的生意。他開了幾家連鎖超市,生意很興旺。我在臉書上還會看到他在他的社區裡參加宗教研習班和齋月時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衣著和身邊的馬來男人風格一樣,都是穿著傳統的馬來服裝,戴著白色的塔基亞(taqiyah)。我想這些照片或多或少都會喚起一個馬來西亞人在身處異國時的家國情懷,會令人感到親切,因為它們能在瞬間引起許多共鳴和回憶。
每年夏天,我和夏木都會去牛街散步……我只是從中尋獲一種屬於伊斯蘭教的情感和記憶,無關乎宗教,而關乎鄉愁。
在北京牛街,過穆斯林開齋節
除了大舅的照片,牛街(Niujie)是另一個能起到同樣作用的媒介。牛街是北京西城區南部的一條大街,同時也指牛街社區,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區。那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回民區,有自己的醫院、學校、清真商店、穆斯林餐館、菜市場及清真寺。牛街禮拜寺是社區的中心,是北京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清真寺。如今,它也是聞名於世的旅遊景點,同時吸引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遊客去參觀。來華訪問的伊斯蘭國家政要很多都曾參觀牛街禮拜寺,其中包括伊朗總統、沙特阿拉伯王儲、印度尼西亞總統,以及我的國家的最高元首[1]。這所清真寺始建於宋遼時期(995或996年),由一個阿拉伯篩海(Shaykh;傳教士)之子納蘇魯丁(Nazaruddin)奉敕所建,明朝時經過擴建、整修,清朝時再度大修。文化大革命期間,禮拜寺曾一度關閉,直至1980年才重新開放。不同於我們平時所見到的那種帶有大圓頂(在馬來西亞,我們戲稱為「大蔥頭」)的清真寺,這所清真寺採用了中國傳統的磚木結構形式,但又沒有傳統的龍、鳳、麒麟等動物的圖像,而是有著繁複、華麗的阿拉伯式花紋,只是那些漂亮的花紋、圖案早已因為歲月和塵土的侵蝕而不再熠熠生輝。
每年夏天,我和夏木都會去牛街散步。我們喜歡參觀禮拜寺,還喜歡那裡的石記餡餅、年糕及肉鋪。那裡使我有一種接近故土的親切感,雖然它其實和我的故鄉很不一樣。我只是從中尋獲一種屬於伊斯蘭教的情感和記憶,無關乎宗教,而關乎鄉愁。走在街上,我經常會留意某些事物,對比它們和我在自己的國家所見到的,並和夏木分享我的經驗。「我們那兒的馬來人也有類似的食物」,「我很少逛清真肉鋪,我們家不怎麼吃羊肉,更別提牛肉了」,我會這樣說。

今年,我選在齋月期間和開齋節去牛街逛逛。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過開齋節,過去的那些年,這個節日對我來說很遙遠,因為我再也沒有在齋月期間回國,沒有參加大使館舉辦的開齋節活動,身邊更是沒有一個穆斯林。我心血來潮,想感受牛街的穆斯林過節的氣氛。
牛街禮拜寺在齋月期間因為整修而關閉。門口貼了張告示,示意那些要做禮拜的穆斯林從北門進清真寺,非穆斯林則不被允許進去。我們只好在街上溜達,像往常那樣吃餡餅,排隊買白記年糕。大街上和商鋪內的情景和平時一樣,除了有一兩個興許是因為齋戒或熱天的緣故而打盹、無精打采的夥計外,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或能使我聯想到現在正是齋月。
「這裡齋月期間沒有夜市或什麼特別的活動嗎?」我問在路旁休息的環衛工人。
「啥都沒有。過節那天就會有,你們到時再來,從早晨七點多到上午十一點多,這條街可熱鬧了,賣好多吃的。」環衛工人指著清真寺對面的那條馬路說道。
兩天後,我獨自回到這裡,發現情況就和那個環衛工人說的一樣。這裡突然變得很熱鬧,終於有過節的氣氛。路上擺著許多白頂棚的攤子,賣著各種清真食品,醬牛肉、糖火燒、年糕、排叉、咯吱盒、馓子等等,其中有的還是北京老字號的食品。這條馬路人頭攢動,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在排隊買食物或看熱鬧。與此同時,馬路中央和路旁也有很多警察、城管和保安人員。他們有的負責實施交通管制,有的負責確保環境的安全,有的則負責走到餐館和藥房門口,驅趕那些在商鋪外販賣東西的店員。這次驅散行動有點突然,感覺只是在例行公事。十點二十七分,城管們開始驅散那些店員。所有人都是慢條斯理的,城管的態度堅決,但還算友好。我問其中一位城管開齋節活動是不是快結束了,她漫不經心地回答:「不讓在外面賣。」但不到半小時,那些店員又從店裡出來了。先前那些被搬進店內的桌子和食物又被搬出來了。

清真寺在這一天恢復對外開放了。我有點驚訝,兩天前它的大門還是緊閉的,而且還有兩個門衛站在外面,讓人有戒備森嚴的感覺。寺門口也搭起了棚子,不過那是安檢的地方。就像這十年來的北京地鐵站,所有進清真寺的人都必須通過安檢。清真寺對面的大馬路可以被視為牛街的中心,那裡掛了一條典型的紅色橫幅,上面印著「平等是民族團結之本,和諧是民族發展之魂」,而背後是一直以來就存在的中國五十六個民族的卡通形象。在橫幅後面的還有三個非常年輕的警察,他們圍成一個半圓圈,手持長棍或盾牌,表情嚴肅地站崗,看著來往的人群。
清真寺外有很多人在合影。一群巴基斯坦遊客正被幾個中國人包圍著。中國人紛紛拿出手機照他們。巴基斯坦遊客全都是男的,他們身穿風格簡約的傳統服裝,頭髮梳得很整齊,有的還戴著墨鏡。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們第一次這樣成為被關注的對象,不過他們倒是看起來很坦然、愉快,面帶微笑,表現得很從容。
深受歡迎的還有兩個英國女子。那是一個孟加拉後裔和巴基斯坦後裔,兩人都戴著眼鏡和頭巾,豐腴、年輕,看起來像是大學生。她們在清真寺的柵欄處被一個像是攝影師的中年穆斯林男人攔下,男人要求拍她們,她們欣然同意了。照完相後,男人還和她們合影,告別時大家拿出手機交換聯繫方式。就在這時,周圍的人也走上前,輪番提出合影的請求。英國女子很友善,答應每個人的請求,但很快她們就意識到情況不妙。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和她們合影,有的人還熱情地挽著她們的手。在照了幾張照片後,其中一個英國女子笑著向同伴喊道:「跑!」兩人便快步朝清真寺走去。


我們都是幸運的人,同樣享受著命運之神的眷顧,只不過我依靠的是民間團體(更確切地說,是華人團體)和中國政府,而她仰賴的完全是中國政府。
馬來女孩愛莎的幸運與哀愁
我盡可能地和所遇見的外國人交談。我發現我遇見的絕大多數都是巴基斯坦人。除了遊客,他們有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有的是在北京上學的留學生。愛莎(Aisyah)也是在這裡求學的留學生,不過她是馬來西亞人。她是我那天遇見的唯一的同胞。
其實我很早就注意到愛莎了。走在人潮中時,我突然瞥見有個戴棕紅色頭巾,身穿可巴雅(kebaya;一種起源於爪哇滿者伯夷國(Majapahit Empire)的女性服裝),膚色呈棕色的年輕女子。她身邊伴隨著一個中國女子,正在用英語向她介紹牛街的情況。出於某種直覺,我當時就猜這個女子應該就是馬來西亞人。這很有意思,我想起我的德國朋友漢娜曾對我說她總是能輕易地在人群中認出自己的同胞來(當然,這是在對方還沒開口說話的情況之下)。除了個別容易辨認的面貌特征之外,穿著和氣質自然也有助於辨認。
人群熙熙攘攘。愛莎和那位翻譯瞬間就消失在視線之外。我的注意力也很快被其他事物吸引。但過了一會,她們倆的身影又出現在我眼前。我尾隨著她們走了幾步。正當我準備拍愛莎的肩膀時,我看見她挎著一個黑色,印著「馬來西亞」字樣的布包。那是很典型的布包,價格不貴,經常能在旅遊勝地或超市裡看見,上面總是印著馬來西亞的象征物,比如說月亮風箏(wau bulan)、椰樹、犀鳥、木槿花或雙子塔(愛莎的布包上印的正是雙子塔)。
「你是馬來西亞人嗎?」我用英語問道。
「是。」
「我也是呢。」
我們倆很高興,還有點激動。在一旁的翻譯也有點驚喜。
「你也是馬來西亞人啊?」翻譯問。
「是啊。我看到她就猜她是馬來西亞人,走近了又看到她的這個包,所以就更確定了。你是她的翻譯嗎?」
「不是。我是記者,在地鐵站看到她,就和她一起逛了。」原來是《人民日報》的記者。
我和愛莎開始用馬來語交談。她告訴我她在去年來北京上學,還有一個多月就要回國了,機票也訂好了。
「你在哪間學校?北外(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嗎?」我們竟異口同聲地用普通話說出「北外」這個詞。愛莎有點驚喜。
像愛莎這樣來北京學習中文的馬來人其實有很多。儘管過去我知道有越來越多的馬來人來北京求學,但我和他們卻極少有交集。2007年至2010年,我在北京師範大學(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學習中國當代文學,當時我是班上唯一的留學生。那時候我學校的大馬人統共有十來人,而且全都是華人,分佈在不同的學院裡。據我所知,我們的馬來同胞都集中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上的是那種短期的中文課程或對外漢語專業本科班,而且全都領著馬來西亞或中國政府的獎學金。
愛莎也是獎學金的受惠者之一,她領的是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獎學金。愛莎今年二十九歲,從去年九月初開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中文,此時她已步入第二個學期的尾聲,並將在七月中旬回國。從牛街回來後不久,我給愛莎打電話,她將她的這段人生旅程對我娓娓道來,為我揭露一直以來我略有所聞,實際上卻不了解的事情。在聆聽愛莎述說她的故事時,我也從中發現我們命運的相似之處。我們都是幸運的人,同樣享受著命運之神的眷顧,只不過我依靠的是民間團體(更確切地說,是華人團體)和中國政府,而她仰賴的完全是中國政府。

大學畢業後,愛莎先後在日立集團(Hitachi)和葛蘭素史克股份有限公司(GlaxoSmithKline plc)工作。她主修的是工商管理專業的物流運輸方向(Business Administration-Logistics & Transportations)。後來,她漸漸覺得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點乏味,於是想在週末學點有趣的新事物。由於她一直都喜歡看中文電視劇,於是她突發奇想,認為學習中文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她很快就在家鄉淡江(Ulu Klang)找到一家華人創辦的語言輔導中心,每週回家度週末時順便到那裡學習中文。週一至週五,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兩年後,一天,老師突然在班上說如果他們將來想要到中國深造的話,那就必須先參加漢語水平考試(HSK/Chinese Proficiency Test),於是愛莎便前往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的孔子學院參加考試。孔子學院是中國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管理,為了向世界推廣漢語的一個非營利性機構,總部設在北京,中國境外的孔子學院都是其分支機構。在等待進入考場時,一個孔子學院的馬來職員走過來,和愛莎搭訕。
「你學中文,為何不直接去北京學呢?我們有提供獎學金。」那名職員說道。
「還有獎學金?我真的可以去嗎?」愛莎既驚喜又疑惑。
馬來職員馬上給愛莎孔子學院負責人的聯繫方式。幾天後,愛莎給那個負責人寫信,表示自己有到中國深造的意願。對方約愛莎在自己的辦公室見面。那是一個不會說馬來語的中國男人。他問愛莎想去哪所大學,同時還向她介紹申請方式。
愛莎最終選擇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畢竟是在北京,應該會比較好。」愛莎說。申請的過程很順利,那個負責人甚至為愛莎寫了推薦信。愛莎發現他在推薦信上寫到她曾經在孔子學院學了一年半的中文。這是申請獎學金的主要條件,只有在孔子學院學過中文的人才有資格獲得他們的推薦。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幫我,我並不是他們的學生。我覺得我佔便宜了。」愛莎說。
幾個月後的一個凌晨,愛莎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中國。她順利獲得孔子學院的獎學金,除了豁免學費,每個月還能有兩千五百人民幣的生活費。啟程那天,她的家人全都去送機了,父親甚至為了她的離去而流淚。愛莎是家中的長女,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這是她第三次出國,以前她去過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但那只是旅遊,這是她第一次要在國外生活,而且去的還不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她的朋友都不怎麼看好她的選擇,母親則因為擔憂她還單身而不太支持她出國。
「來中國後,我發現其實有很多人和我一樣,都還沒有結婚。我覺得這沒有問題。」愛莎坦然地說。
「以前在馬來西亞的朋友全都是馬來人。」她說。半年後,瑞士女孩回國,愛莎和一個波蘭女孩成了好朋友。她們倆都同樣喜歡韓國流行音樂。
愛莎的宿舍樓一共有四層,以前是專門提供給馬來西亞留學生的。但由於馬來西亞學生的人數逐漸減少,如今只有第三和第四層供馬來西亞學生住。有很多馬來西亞留學生都是馬來人,他們通過馬來西亞的人民信託局(MARA/Majlis Amanah Rakyat/Council of Trust for the People)或教育部的保送計劃來華攻讀五年制的對外漢語專業。根據合約,他們畢業後都必須回國當中文教師。
愛莎對讓所有大馬留學生住在一起這個安排不是很贊同,她認為馬來西亞學生最好不要全都住在一起。「難得來別的國家,應該多和不同國家的人交流啊。」愛莎用「交流」這個中文詞表述。
她確實做到了。她在北京交的第一個外國朋友是一個瑞士女孩,那也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個外國朋友。「以前在馬來西亞的朋友全都是馬來人。」她說。半年後,瑞士女孩回國,愛莎和一個波蘭女孩成了好朋友。她們倆都同樣喜歡韓國流行音樂。
「我昨天才從上海回來呢。我們去看黃子韜的演唱會了,棒極了!你知道黃子韜嗎?」愛莎說。
「我聽說過。」我回答。
「他原本是EXO(韓國男子組合)的成員,後來退出了。我是看了《夜空中最閃亮的星》才認識他的。那是最近播出的電視劇,愛奇藝上有。我每個月花九塊錢就能看各種節目。」
除了黃子韜的演出,兩個女孩還在去年冬天一起去香港看iKON(韓國男子組合)的演唱會。那趟旅途令人難忘。為了省錢,她們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去深圳,然後從深圳進入香港。回來時不幸只買到站票,只好時而站,時而坐在自己買的塑料凳子上。所幸她們坐在吸煙區裡,所以不斷有機會和在那裡抽煙的人閒聊,打發時間。
「我覺得這裡挺好的,和我之前所聽到的描述很不一樣。過去我經常聽到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現在我親身經歷了,發現情況不是這樣的。這裡的人對我的信仰也很尊重。在火車上,有人問我為什麼戴頭巾,我回答因為我是穆斯林,他們就沒有說什麼。有的人在一見到我就能猜出我是馬來西亞人,我很驚訝。中國人知道我的國家,我感到很自豪。」
「那你有過什麼不愉快的經歷嗎?」我問道。
「沒有。不過有一次一個男人在知道我是大馬人後問道:『你們的馬航飛到哪裡去了?』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好保持微笑。」愛莎有點無奈。
我們還談到了伙食和做禮拜。我原以為飲食和履行宗教義務會是愛莎和其他穆斯林在這裡面臨的難題,但看來並不是。
「在北京找清真餐館很容易,比香港容易多了。我在香港那兩天只能吃水果什麼的。」愛莎說。
愛莎永遠不會忘記她在中國的第一頓飯。抵達北京那天,辦完入學手續後,她已經飢腸轆轆。她獨自到附近的西部馬華餐廳(Western Mahua Restaurant),面對陌生、印滿漢字的菜單發怵。當時她已經餓得頭昏腦漲,就胡亂點了份皮蛋豆腐和一杯熱茶。那是她第一次吃皮蛋豆腐,雖然不怎麼喜歡,但還是吃下去了。後來,她逐漸熟悉周圍的環境,能找到越來越多的清真食物。
履行宗教義務比找食物容易得多。最初學校準備了一間祈禱室給穆斯林學生,但出於某種愛莎也不了解的原因,祈禱室在三個月前關閉了。祈禱室的門上僅貼著一張簡單的告示,通知所有人祈禱室再也不開放。愛莎認為這或許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允許校園內有任何宗教活動的緣故,對此她也只是表示無奈。她改為在房裡做禮拜,反正她也經常這麼做。
還有不到一個月,愛莎就要離開中國了。她已經計劃好回國前的最後一次旅行。她去過天津、杭州、上海、深圳、香港、澳门,接下來她會去桂林和張家界,然後到福州,從那裡搭乘飛機回國。當她如數家珍般告訴我她去過的地方時,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出「新馬來人」這個詞。這是我在奈保爾(V.S. Naipaul)的《不止信仰》(Beyond Belief)裡看到的一個詞彙。這部著作是奈保爾1995年在四個非阿拉伯國家——印度尼西亞、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旅行五個月後寫下的。它也是另一部著作——《信徒的國度》(又譯作:《在信徒的國度》)(Among the Believers)的續集,這兩部書談的都是奈保爾在這四個國家的見聞。在《不止信仰》中,關於馬來西亞的內容有一章被命名為「新楷模」,講述了一對年輕的馬來夫婦的故事。女主人公娜荻莎出身良好,住在吉隆坡,而她的丈夫則來自鄉下,他們的村子裡仍然沿襲著蘇門答臘的母系社會傳統。但娜荻莎看中的是丈夫的野心勃勃和實幹精神,認為他是新馬來人,是新楷模,所以即便兩人在許多觀念上有分歧,他們還是結婚了。後來,毫無意外,娜荻莎和丈夫離婚了,她最終認為丈夫其實一直以來都像隻「椰殼下的青蛙」(這是印尼和暹羅的諺語,和中國的「井底之蛙」有一樣的含義),和環境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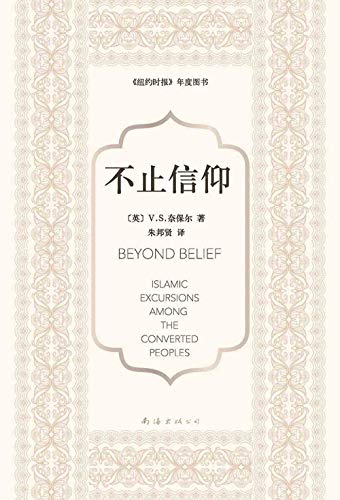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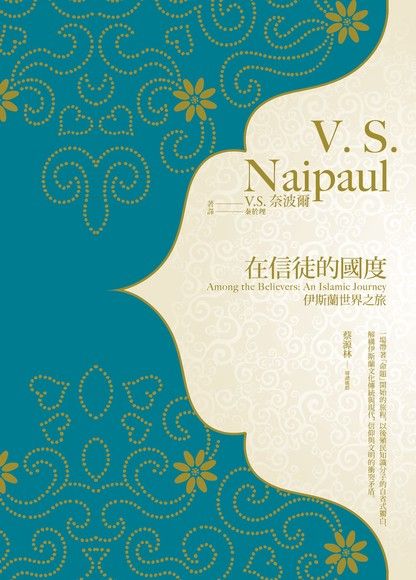
昔日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穆斯林堅定的臉孔再次浮現在眼前。掛電話後,我繼續讀奈保爾的《不止信仰》,並為之著迷。
那些新馬來人,已經擁有不同的面貌
印象中我從未聽過「新馬來人」這個詞。在查閱一些相關資料後,我發現「新馬來人」這個概念是在九十年代初由當時的雪蘭莪州州務大臣(Chief Minister of Selangor)莫哈末泰益(Muhammad Muhammad Taib)提出的。當時莫哈末泰益也是「宏願團隊」(Team Wawasan)的副主席之一。「宏願團隊」是時任副首相的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所領導組建的團體,旨在配合首相馬哈蒂爾(Mahathir bin Mohamad)在1990年提出的要在三十年內使馬來西亞成為先進國的宏願(Vision 2020)。「宏願團隊」在1996年瓦解,「新馬來人」這個概念也隨之消失了。
儘管「新馬來人」這個概念只是短暫地存在過,但放眼於今天的馬來西亞社會,它無疑還是被實現了。回望歷史,不難發現因1969年發生的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衝突——五一三事件(13 May Incident)而被推出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以及曾由安瓦爾·易卜拉欣領導的馬來西亞穆斯林青年運動(ABIM;Muslim Youth Movement of Malaysia)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安瓦爾與馬來西亞穆斯林青年運動反對政府所推行的偏愛馬來民族的施惠政策,但這個旨在淨化伊斯蘭教,深信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迫切需要的強心劑和淨化劑,深信伊斯蘭教能重新奠定馬來西亞的秩序的穆斯林青年團體也在以他們的理念和方式促進馬來民族的進步。
我想到去年春天我在大阪機場見到的那些馬來人。我和他們都準備搭乘亞航(Air Asia)的飛機回國。他們有的是舉家出遊,有的是朋友結伴出行。所有人的行李箱都是滿滿的(他們帶了很大的旅行箱!)。此外,他們還拎著大包小包的「戰利品」,其中包括日本的藥妝用品和點心。我當時對他們的購買力有點瞠目結舌,就像我看到闊綽的中國遊客時那樣。後來,我也從家人和朋友那兒聽說了類似的事情。許多華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馬來人變得越來越富裕,他們的經濟地位已經崛起了。有意思的是在提出這個看法的同時,華人們也提到了政府對馬來民族的施惠政策,並對此表示不滿或不屑。但無可否認的是政府的新經濟政策果然奏效了。大學學位固打制、獎學金固打制、土著房屋固打制等給予馬來民族優先待遇的制度無疑能使更多的馬來人擁有更多自我提升、階級上升的機會,也讓這個民族更加自信。
愛莎認為自己也是一個「新馬來人」。「我們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了,我們更開放,也更包容了。」她自信地說道。在北京的這一年,她確實見識了許多新事物,對自己的未來也更加有信心,但這一切並不主要有賴於我們的政府,而是源於中國政府輸出軟實力的政策。那些和愛莎一樣在北外學習中文的馬來青年,將來他們都會成為中文老師,這是我們的政府和中國政府所共同達成的共識,卻成為了許多馬來西亞華人的擔憂和不滿,因為在許多華人看來,馬來人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比華人更合格的中文老師。此外,有些華人也相信這是政府的陰謀,企圖以此威脅、取代華裔教師的地位。
「回去以後,我打算去新加坡找工作。」愛莎說。
「如果有機會在北京或其他國家工作,你願意嗎?」我問。
「願意啊。只要有機會,我願意嘗試不同的生活。」
「那麼移民呢?」
「可以啊。」
「國籍對你來說不是個問題?」
「嗯。」
「那麼嫁給外國人呢?」
「願意,」愛莎遲疑了一下,「不過對方必須是個穆斯林。」
突然有那麼一瞬間,昔日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穆斯林堅定的臉孔再次浮現在眼前。掛電話後,我繼續讀奈保爾的《不止信仰》,並為之著迷。那都是些關於信仰和人生的故事。倘若奈保爾還活著,我想他的這段旅行還可以繼續下去,因為二十年前他所寫下的那些新馬來人已經擁有不同的面貌,伊斯蘭世界的故事也更為複雜和豐富了。
[1] 伊朗總統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沙特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Abdullah of Saudi Arabia)、印度尼西亞總統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以及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端古·賈阿法(Tuanku Ja’ af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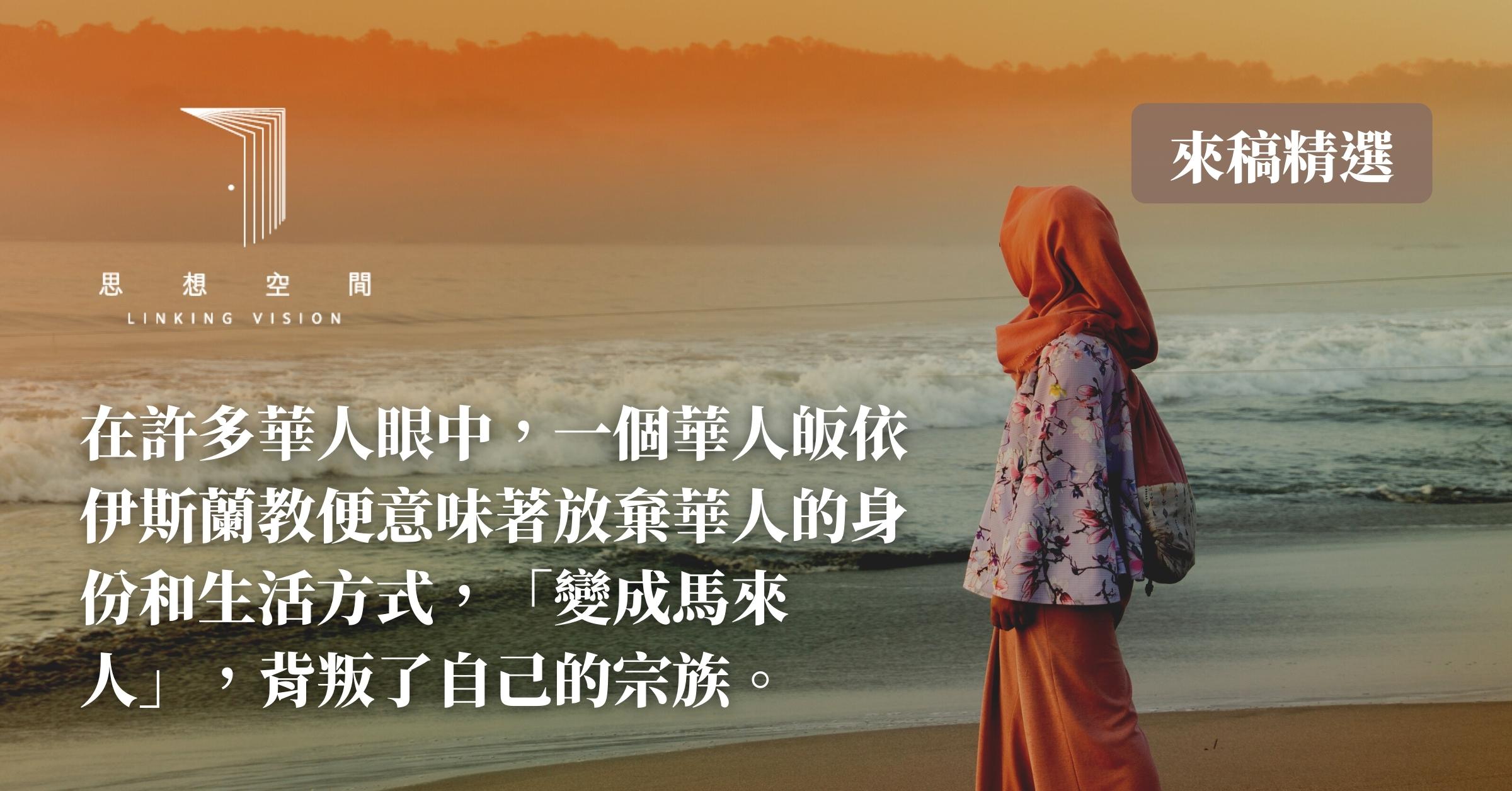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