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教授在9月5日余英時紀念論壇上的發言輯錄)
王汎森:「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我覺得這就是余老師讀書:他在讀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弱水兄、國翔兄、陳總經理,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主辦單位要我講余先生宋元明清以下的研究,但是因為我覺得余先生從先秦《論天人之際》一直到近代的著作太多,而且大家都有機會好好的讀,所以就避開了這個問題。最近中研院有兩個刊物要出余先生紀念專號,《漢學研究通訊》也有一個專號,我都答應要寫文章,所以現在就從這三篇裡面挑一篇〈余先生的讀書生活〉,講一下我所觀察的余先生讀書及著述。
今天在座幾位包括弱水兄和國翔兄,是比較少數能夠與余先生長期接觸的人,也常常有朋友跟學生問我這方面的問題。今天的主題既然是「史學家的耕耘」,就講一下我所觀察余先生的耕耘的實際狀況,給大家參考。當然我的觀察也只是一偏之見,因為我是余先生眾多學生中間的一個,也是跟他熟悉的眾多人中間的一個而已。我的觀察不一定正確,但是我希望對跟他不熟的人有一點用處。
關於余英時作為史學家的耕耘過程,我分成幾點來講:
第一點,從清代後期到民國時代乃至現在,很多人治學問都要先從熟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始,代表性人物如陳垣等。余先生對這部書的情形非常熟悉,我注意到他可能在某一個階段有個機會,非常廣泛地接觸到大量古今書籍,也對這些書的掌握非常(到位)。以前上課的時候,我常聽他提起這些書;他每次提到一本書的時候,都會比一下厚度,表示這些書他有接觸過。關於這些書,他大概有非常廣的提要性的瞭解和知識。第二點,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余先生提出史學家對時事要掌握得非常(精確),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地瞭解。第三點,我覺得余先生每天隨時都在思考。他有思索的習慣,有時候他眉頭稍微皺一下,你就知道他在思考各種問題。我在普林斯頓大唸書的時候,余太師母告訴過我,余老師在1957、58年左右,非常喜歡看當時流行的美國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梅》就是思考、偵查、破案。余老師好像在回憶錄裡也提到,他曾經讀過《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因此我覺得他對思考層層分析、解決疑難,以及思索的習慣,都是無時不刻在進行的。
另外,余老師讀書非常專注。我做學生的時代,常常會在報告前不久才把材料分派給大家。每一次余老師在看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在那個片刻,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跟那一頁書存在而已。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你做了小船登岸以後,這船就要燒掉了,永遠不會再看到它,因此要把整個文本「吃」下來;作告別計,好像讀完以後,這一生都不再看到它,可是它仍然在你腦海中深深地留存著。我覺得這就是余老師讀書:他在讀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
而且我注意到余老師在每個時代都有一些「總機性」的文本,從這個「總機」可以通向每一個人。我隨便舉一本,例如《胡適日記》——我留意到他對《胡適日記》非常熟,事實上余先生論及近代的很多文章,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兩條可能跟《胡適日記》有關。因為胡適接觸過的事情和人物太多了,因此可以從這一點,通向一件件個別事件。我想各位熟悉余先生著作、尤其是近代部分的朋友,應該可以瞭解我所講的。余先生對每一個時代(的研究),好像都有這種帶有總機性的文本,可以設立一個座標在那裡,通過一部總機連到各個人。
我從來沒有看過余老師動筆。余老師上課的時候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可是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腹稿」兩字也是他經常提到的。他長期在思索,一旦要動筆要寫的時候,會先把重要材料先看一遍,然後就放在一旁,啪啪啪地開始寫,因此讀余老師的論文,不會覺得引用史料非常繁重。而他動筆之後就沒日沒夜。我最近看到林載爵先生在一篇文章提到(余先生)一個月寫9萬字;而他在給一個老師的信中也講到,過去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的時候,曾趕稿趕到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其實除了傳統文獻以外,余先生也相當重視新材料,以及新材料在著述過程中的點化作用。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文物雜誌》好像是他很長時間都有訂閱(的刊物),後來他寫《論天人之際》的時候,也能力所及地用了很多新材料。在寫《論天人之際》的過程中,有幾次我們電話聯絡,他提到幾點我印象很深,其中當然包括「諸子是不是出於王官論」。我注意到,對這一問題他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寫,不過他說「諸子出於王官論」即使跟他寫的問題相干,也要重新說過。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他從70年代寫《中國上古史待定稿》那篇文章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醞釀。然而這裡面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每一關都要克服,所以已經想很久了,寫到後來,這(《論天人之際》)也成為他最後一本書了。我記得他提到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連柏拉圖也重讀了一遍。其他先秦史料,尤其是諸子,他都有重新再看,所以關於這個問題,他都想很久。余先生說其實亞洲很多後來的(觀點),都是從古代宗教、經過知識份子有意識的改造之後形成的。雖然余先生不專門做新材料,但我感覺他很留意新材料的點化作用。
另外一點我感觸比較深的,就是長期醞釀。余先生有兩種文章,一種是拿起筆來就寫的,非常快速完成;但大部分書、以及很多重要的文章,其實經過他仔細地追索痕跡,醞釀非常之久,就像珍珠形成的過程,要在蚌殼裡面不停的分泌、不停地摩擦。像是他的第一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就是由1957年交給楊聯陞的一篇研究生報告擴張而成的,後來他寫成了升等論文,出成一本英文書,這中間過了十年左右。像《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後來有一種感覺,這本書對商人的處理跟討論,早在他《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裡的若干章節跟注裡面,其實已經顯現出來了。像我們所熟悉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由一篇序變成1000頁的書,像幫顧喆剛日記寫成《未盡的才情》,本來也是從一篇序開始的……他把平常思考累積所得放在腹稿裡面,再將其擴充成一本書。
余先生曾經提到,在治學方面,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事實上,王國維非常用功的時間只有二十年,但他治學用力得當,就像下圍棋沒有廢子一樣,而成果如此之斐然。余先生做學問也跟下圍棋有一點相似,當然大部分人也有類似的過程:總是慢慢地從外面開始向中間包圍。所以余先生說他在讀很多書的過程中,慢慢形成問題,好像下圍棋一樣,慢慢包圍。
余先生的著作非常之多,我沒有力量在這裡做一個概括,也沒有按照總編輯後來給我的題目「宋明清以後」(來談)。以上將近十點,是我作為學生之一長期觀察的總結,謹在這裡整理出來作為大家的參考,謝謝。
陳弱水:「余先生對於各個時代文獻的鑽研,對各個時代問題的探索,往往有超過具體時代環境的意義,而涉及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段甚至是近乎本質性的問題。」
陳弱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主持人和兩位主講人,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好。我今天負責介紹余先生的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從先秦到唐代的部分。剛剛聽了汎森兄的發言,我的內容跟他可以呼應的地方相當多。
我要介紹的雖然是余先生關於早期中國史的研究,不過因為余先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所以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要先提兩點有關他的一般性認識:
第一點,余先生的首要身分是學者,是歷史學家,他絕大多數的思考跟著作都和他的學術生涯有關。可是余先生之所以對知識界有那麼深的影響,他的離世引起這麼大的震動,還是因為他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是先於他的學者身分而存在的。他在26歲的時候(1956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而在那之前已經寫了差不多60篇文章,很多都是涉及文化、政治、歷史的大問題,所以他的學術風格跟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是很難分開的。汎森兄剛剛提到余先生對商人的研究歷時很久——事實上,在余先生於1953年,還在新亞研究所唸書的時候,就寫過與商人有關的文章,寫中國歷代政府對商人的壓迫。所以余先生注意商人問題比汎森兄剛剛講的還要早,這只能說是出自公共知識分子的敏感度。
第二點,就是在學術研究上。余先生在很多領域當中都有原創性成果,他不但是多領域的學者,也是一個「通家」,通貫性的學者。我們因為讀了很多余先生的東西,可能有點習慣了,可是像他這樣又通又專的學者是非常少的。
余先生的歷史研究是從中國史的前半段起家的,更確切地說,秦漢史是他的第一個專業領域。余先生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1956),這是他在新亞研究所的研究論文,也是在新亞唯一正式的學術業績,我想這對他而言應該很有紀念意義。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學者,余先生在研究上取得突破,是他的第二篇論文〈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1959)。這是研究從東漢後期到三國士階層心態和思想變動的論文,體大思精,處理非常多的現象跟問題,有很多超越前人的看法,而且他用「群體自覺」和「個體自覺」的說法來做通貫性的說明,我個人覺得就研究水準而言的話,這篇可以說是體現了他超一流的學者品質。
從學生時代開始,余先生就一直從事漢史的研究,他在這個領域中也做了很多卡片,大概是唯一他做卡片的領域。1967年,他從密西根大學回到哈佛任教之後,研究重心才轉到明清思想史,特別是清代。比較特別的是,正如汎森兄提到的,余先生最大分量的漢史研究,並不是他投入最深的思想文化史,而是漢代的外族、外國關係,特別是匈奴。在這方面他最主要的著作是英文專書——《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原始譯名:漢代中外經濟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余先生研究漢代中國的對外關係,從博士生時代就開始,他選這個題目顯然和當時美國漢學界的主流問題意識有關。美國的中國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蓬勃興起,主流是中國近代史,一開始特別重視以清為代表的傳統中國的對外觀念和行為,以及中國的世界秩序觀,這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余先生的專書是對中國朝貢制度(tributary system)的起源的研究。余先生的最後一篇漢史論文,是1987年發表的〈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對於早期中國士人的性格以及儒家文化的傳播方式,有很具體、深入的揭示。
跟漢代研究的情況不同,余先生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全部屬於思想史的範圍。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宗教跟文學特別興盛,這裡宗教主要指外來的佛教和新興起的道教。就當時而言,宗教和文學興盛是重要的新現象,所以學者研究東晉以下的思想文化,重點大都在這兩個方面,反而忽略了士大夫原有文化傳統。這是新的傳統,受到玄學影響發生的變化,余先生的著力點就在這個地方,他由此對魏晉南北朝思想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80年代以前,余先生關於從古代到魏晉南北朝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就收集在聯經出版的《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余先生古代史的研究也是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余先生對先秦思想的興趣發生很早,不到二十歲就開始了。他不但讀先秦思想文獻,而且讀了近代有關先秦思想的經典研究,如章太炎、胡適、梁啟超等人的著作。余先生不但在先秦諸子及經書上下功夫,還注意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譬如對王國維、陳夢家、郭沫若的著作都很熟悉。先秦諸子思想,在某個意義來講,等於是他學思生涯的起步。結果沒有想到,因為偶然的因素,他最後一部主要著作也在這個範圍。
余先生最早的古代史論著是〈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1978),這是受中央研究院的「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計畫邀請所寫的,具有通論的性質。在論文當中,他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思想史問題,就是所謂「哲學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
「哲學突破」的觀念取自著名社會學家派森思(Talcott Parsons),指在公元前第一千紀中期左右,世界上幾個古文明都發生了一種突破。這種突破,可以說是精神覺醒的出現,也可以說是反省性思想的出現。就西亞、南亞而言,宗教的性格強(制度性宗教),就希臘、中國而言,思想性格強。簡單說,就古代中國而言,這是由政教不分的前思想過渡到具有獨立性的思想,也就是中國思想起源的問題。派森思這個觀念的來源其實是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但余先生當時並沒有清楚掌握。
余先生在〈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對「哲學突破」或「軸心突破」在中國的問題做了一些梳理。他後來一直注意這個問題,也成為最後一部主要學術著作《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2014)的主題。在〈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論文發表之後,余先生又陸續寫了幾篇關於先秦春秋戰國的士的論文,重點不在士的政治社會角色,而是在於士的精神文化。這樣做,是因為這部分對於往後中國歷史有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要談余先生的古代思想研究,無法離開他的《論天人之際》。這本書的出版跟我個人有關,我有情感投入其中。2004年的春天,當時中研院史語所的王汎森所長召集同仁,要編寫一套《中國史新論》,我負責思想史的部分。當時我的想法是,這一冊就以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作為主題,邀請學者就每一個重要的轉變寫一個涵蓋比較廣的討論;構想中第一篇論文的主題一定就是「思想在中國的出現」,作者非余先生莫屬。我擔心這個工作為他帶來太大的負擔,就建議他把之前寫的英文長稿轉化為中文,結果經過很複雜很長的歷程,成就了《論天人之際》這本書。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各種原因,余先生非常辛苦,我也是深感歉意。
這本書為什麼以「論天人之際」為題呢?是因為余先生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思想突破的基本路途,突破的方式是由商周的舊「天人合一」到諸子的新「天人合一」,孔子以下的各家學派,認為可以憑藉人自己的力量,特別是人的「心」,追尋到「道」,突破的資源則是原來禮樂傳統中的「巫」。這本書論證精妙,無疑是經典之作。
最後想提一下余先生跟唐代研究的關聯,在一般的印象中,唐代是余先生唯一沒有涉足的領域。其實余先生對於唐代的歷史跟文化,是相當有造詣和心得的。他在哈佛師從楊聯陞先生的時候,攻讀的就是從漢到唐的歷史,特別是社會經濟方面。他的第二篇英文論文,就是討論杜希德(Denis Twichtett)一本關於唐代經濟財政的名著。另外在余先生著名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一書中,也有關於禪宗跟唐宋之際佛教入世轉向的討論,雖然篇幅不多,但是背後有深厚的基礎。我在耶魯唸博士班的時候,余先生有一陣子一直在讀禪宗的「燈錄」,而且會跟我談他的心得。他對於唐代詩文的造詣更是不在話下,這方面我是有親身經驗的。
以上是我對余先生早期中國史研究非常簡單的介紹,在結束的時候我講兩點:
第一點,余先生的學問深而廣,可是他絕對不是炫學。他一方面不斷透過閱讀思考,累積自己的學問以及對各種人文問題的認識;他閱讀的範圍有很多還是西方著作,從柏拉圖、黑格爾一直到當代哲學。另一方面,他不斷在中國史的研究上,追索重要問題,很多探索都經歷了幾十年的時間。
第二點,余先生對於各個時代文獻的鑽研,對各個時代問題的探索,往往有超過具體時代環境的意義,而涉及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段甚至是近乎本質性的問題。他這樣做,除了是個人能力的積蓄之外,也跟中國史延續性高、在世界史上自成一格的特性有關,所以他做出來的不是黑格爾,也不是斯賓格勒或湯恩比的歷史哲學做法。以上就是我的發言,謝謝各位。
彭國翔 :「余先生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無論西方還是中文世界的中國史研究中,似乎呼應和繼承者已經寥如晨星。」
彭國翔(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
謝謝聯經的朋友邀請我參加這個活動,和王汎森和陳弱水兩位先生同場。剛剛得知余先生過世的消息時,王汎森先生和我,我想還有其他一些和余先生比較熟悉的朋友,都覺得非常的突然和震驚。因為我們一直認為,以余先生的健康狀況,至少壽過95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可惜的是,就像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死生有命」,也許每個人的壽命都是先天已有定數。當大限到來時,即使身體很好,也會遽然離去。不過,雖然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從情感的角度來說,余先生的離去還是讓人久久不能釋懷。8月5號和6號這兩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感受很強烈,卻完全不能寫通常意義上的紀念文字。我想,在遭遇重大變故,情感受到強烈衝擊的情況下,這種內心情感激蕩卻無法訴諸通常文字的情況,恐怕不是我個人特有的經驗。當然,「情郁于中,自然要發之於外」,或許只有「詩」這種特定的表達方式,才能使那種心情獲得釋放與安頓。所以,那兩天我先後寫了兩首七律和三首七絕。(編按:參考〈彭國翔:「鸚鵡濡毛平素志」——悼余英時詩五首〉)。當時的感受很奇妙,那些字句很自然地從我心中湧出,沒有經過刻意推敲,就把我20多年和余先生交往過程中的所思所感,一下子呈現了出來。詩裡展示的所思所感雖然未必完整,卻是最為直接和強烈的。
直到今天,余先生已經過世一個多月了。坦率地說,要讓我在一種平靜的心境之下寫一篇紀念文字,恐怕還是做不到。幾次坐下來,想在電腦上試試,每次都陷入恍惚之中。但我知道,我們必須接受余先生已經離去的現實,必須接受一個時代的結束,必須回到我們原本一直在行走的道路上。我想,雖然我們和余先生相識的機緣各自不同,卻是因為「志同道合」這個因素,才能夠讓我們在余先生生前,來到他的身邊,隨著他一起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回歸我們原本自己的道路,才算是接續余先生平生的「志」和「道」,也是繼續我們自己的「志」和「道」。因此,我之所以要感謝聯經,就不僅是因為邀請我參加這個紀念活動,更是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幫助我從恍惚中走出來、回到自己原來道路上繼續前進的一個契機。
聯經的朋友聯繫我時表示,希望我在這次的活動中,談一談余先生在宋明理學和儒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我想,這當然是出於對我專業領域的照顧。另一方面,在我尚未能從沉重的心情中完全恢復出來的時候,明確這樣一個主題和論域,也可以讓我在今天這樣一個以「史學家的耕耘」為題的學術場合,儘量克制自己的個人情感,不致陷入那種「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
余先生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這兩部書。但在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中,他為1983年臺灣水牛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辭典大全》這部辭書撰寫的詞條,包括「從尊德性到道問學」、 「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 「經學與理學」和「博與約」等,就已經屬於宋明理學和儒學的研究了。我雖然是在大學時代閱讀的這些詞條,如今已經年代久遠,但其內容以及余先生的主要論點,我至今記憶猶新。名義上,余先生撰寫的辭條是「清代思想史」的部分。但是,由於他採取的是觀念史的處理方式,而這些觀念很多都是在宋明理學中才得到充分討論的,比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從產生到發展,完全是在宋明理學的脈絡之中,所以,余先生對這些觀念的來龍去脈以及思想內涵的分析,對於宋明理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來說,都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並且,由於學界以往並沒有以這種方式去考察宋明理學以及儒學傳統中的這些重要觀念,余先生的研究,就是非常具有原創性的。他自己的謙辭,「事屬草創,前無所承」(《中國哲學辭典大全》,頁520),其實正是那種原創性的反映。我後來知道,余先生這一工作可以上溯到20世紀70年代,包括他1970年9月發表在《中國學人》的「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以及1975年12月發表于《中華月報》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的「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兩篇後來也收入了聯經1976年初版的《歷史與思想》。這樣看來,除了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在香港發表和出版的那些文章和著作之外,在余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對於宋明理學和儒學思想的研究,可以說是比較早的了。
當然,要說余先生對於宋明理學的最大貢獻,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2000年我在臺北第一次見到余先生時,就知道他正在撰寫這部大著。其中的緣由,我在聯經出版的余先生九十壽慶文集《如沐春風》 中有所交代,這裡就不多說了。由於我很期待拜讀,所以一直關注此書的出版情況。2003到2004年我在夏威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一聽說此書出版,便立刻在夏大的圖書系統裡查找。可惜夏大圖書館沒有第一時間訂購,要等我在2004年7月結束了夏大的客座轉往哈佛之後,才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讀到此書。有趣的是,當我查到此書時,它正在被人借閱。好在哈佛圖書館有這樣的政策,當有人預約某一本正在被借閱的圖書時,前一位借閱人需要在一定時間內歸還,以便預約者得以借閱。當然,歸還之後,可以立刻預約。這樣一來,前一位借閱人又變成了預約者。後來的借閱者也要按時歸還,如此前一位借閱人便可繼續閱讀了。如果後來的借閱者沒有看完或者還想再看的話,如法炮製,便會形成一部書在兩個借閱人之間被輪流閱讀的情況。我當時並不知道另一位借閱人是誰,但是我和另一位讀者輪流閱讀《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情況,卻持續了好久。直到2004年11月,我前往普林斯頓看望余先生,蒙他親手贈我新出的簡體字版,才結束了我和其他讀者輪流借閱的經驗。
余先生這部大著出版之後,立刻在學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對於一些評論,余先生本人也有回應。這一點學界的朋友都很熟悉,不必多說。我接下來要說的,是我個人對於此書的觀感。
我在很多場合都提到,從大學時代開始,海外華人學者中對我影響較大的有兩個譜系:哲學方面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史學方面則是錢穆先生和余先生。也許由於這一個人方面的原因,初次閱讀《朱熹的歷史世界》,我完全不覺得陌生,也絲毫不覺得余先生筆下的朱子和我以往接觸更多的哲學視角之下的朱子,彼此之間不能相容。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如果說以往我所瞭解的朱熹大多是哲學觀察所呈現的面貌,那麼,余先生的研究,就是別開生面,讓我們瞭解到了朱熹在其哲學觀念之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朱熹在整個宋代政治文化這一脈絡之中的思想和實踐。
在我看來,余先生的貢獻不僅在於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朱熹乃至整個理學傳統的認知,在以往理學家「內聖」的一面之外,讓我們充分地看到了他們「外王」的一面;還在於對應該如何理解這兩個方面之間的關係,做出了深入的探究。余先生的這一貢獻,在他的「內聖外王連續體」這一說法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事實上,「內聖」和「外王」,或者用理學自己的話語來說,「道學」和「政術」,原本是理學家們關心的一體兩面。可惜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哲學背景的學者只關注「內聖」,史學背景的學者只關注「外王」,兩者很少互動交流。而余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固然如其所說,是要在以往過多哲學角度的研究之外別開生面。但在我看來,其貢獻絕不僅僅是為朱熹以及整個宋明理學的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理解層面,更是在「內聖外王連續體」這一觀念以及圍繞這一觀念展開的基於堅實史料的細密論述中,指出了理解和深究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儒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取徑和方向。其實,古往今來認同儒學基本價值的士人或知識人,幾乎都有「內聖」(學術思想)和「外王」(政治社會的關懷和參與)這兩面,而且是連續一體的兩面。余先生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典範。
除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之外,余先生和宋明理學直接相關的專題研究,是隨後2004年出版的《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我最初看到這部書,也是2004年11月20號那次見面時,余先生親手送我的。由於前五章是《朱熹的歷史世界》的「緒說」,所以更具實質意義的,是其中第六章「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這一點,也是余先生贈書給我時特意指出的。對此,我記得很清楚。這一章佔據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見其內容的豐富。
《朱熹的歷史世界》處理的是宋明理學中「宋代」的部分,儘管其中已經不能完全與「明代」的部分無涉,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說,「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撰寫過程中,明代的對照不但已經時時往來胸中而且也偶然流露於筆端。」(《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頁6,自序)。但是,對於「明代」部分更為集中和深入的研究,或者嚴格地說,從政治文化這一角度對於以陽明學為主體的明代理學的探索,則是在「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這篇專論之中。
除了在史料運用和思想闡釋兩方面都有許多具體的精彩之處,我個人覺得,對於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這一專題研究,余先生最為突出的一個貢獻,是指出了明代以陽明學為主體的理學,在以往宋代理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得君行道」這一思想和實踐的取向之外,大規模地開闢了「覺民行道」的另一種取向。如果說「得君行道」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在於朝廷尤其是君主這一政治權力的最終來源,「覺民行道」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則顯然是在民間社會。與「得君行道」不同的是,「覺民行道」的目標不再是通過君主的支持和相應政策的實施來改善政治與社會的秩序,而是通過化民成俗、移風易俗,以淨化人心的方式達至社會的改良。在這個意義上,余先生提出的「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可以說是一個頗有啟發性和解釋效力的觀念架構。由此來觀察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儒學傳統的演變,可以讓我們看到哲學或史學的單一視角所難以顧及的側面和層次。
在我看來,余先生這一觀念架構的貢獻,和「內聖外王連續體」的觀念一樣,不在於對一些具體的現象提供確定無疑的定案,而在於抓住了宋明理學在政治文化的脈絡中發展演變的最為基本和重要的兩條線索。通過探究宋明理學內部「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這兩條路線的關係與互動,宋明時代的儒學、思想、政治以及社會的豐富性,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揭示。這一點,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從20年前,也就是2001年,發表在臺北《漢學研究》的文章「王龍溪的《中鑒錄》及其思想史意義——有關明代儒學思想基調的轉換」,到2019年3月在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所做的主題演講「陽明學的政治取向、困境和分析」,可以說都是在余先生這一觀念架構的啟發之下嘗試進行的思考。
《朱熹的歷史世界》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兩書,以及剛剛提到的那些文章,都是與宋明理學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我這裡只是以這些文字為例,對余先生在宋明理學和儒學研究方面所做的貢獻,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即便以宋明理學和儒學研究為限,余先生在史料運用和思想闡釋方面的精彩,還散見於他的其它各種文字之中。相信熟悉余先生文字的學界朋友,和我會有共同的感受。
除了「內聖外王連續體」的觀念以及「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的線索這些對於宋明理學與整個儒學傳統研究的直接貢獻之外,余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我認為同樣是巨大的貢獻。並且,由於遠遠超出了宋明理學和儒學研究的範圍,足以為從事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學者樹立典範,這一貢獻或許更有意義。相信這不是我的私見,而是很多專業同行的共識。既然如此,這一貢獻的意義如何呢?對這一問題,就讓我在最後表示一下我的看法。
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有人稱之為「心史」。這個詞不同的人也許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來,除了表示余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喜歡或者擅長透過史料去捕捉和分析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之外,這個詞也表明,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在一般史學家視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敘事」之外,還有一個探究人心所反映的各種觀念的部分。換句話說,除了把「事」說清楚之外,還要把「理」講明白。
余先生不僅可以從事極為精細的考證工作,這在其《方以智晚節考》和《朱熹的歷史世界》中都有鮮明的反映,同時又能夠在堅實的文獻考辨基礎之上,對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課題做出非常精確和恰當的分析與判斷。同樣是《方以智晚節考》和《朱熹的歷史世界》,其中一貫的特點之一,就是善於從文獻的字裡行間進入到研究對象及其所在的精神與思想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余先生是中國史學領域裡面最擅長談思想的一位。
我歷來認為,一個好的思想史研究,應該是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對於一個思想史研究,如果從史學的角度看,史料充分,證據確鑿,所謂「持之有故」;從哲學的角度看,觀念清楚,層次分明,所謂「言之成理」。這就可以說做到了既有歷史、又有思想。
對史學訓練的學者來說,做到史料充分和證據確鑿或許並不難,相對不太容易的,是觀念清楚和論證有力。我並不認為觀念清楚和論證有力一定需要哲學的訓練,但自覺經常閱讀哲學類的著作,至少不輕視哲學,顯然是有幫助的。在這一點上,余先生正是一個足以現身說法的例證。他長期以來對西方哲學重要著作和最新成果的主動閱讀和不斷吸收,熟悉他的人都很清楚,不必多說。這裡,我只想以我個人的親身經驗,為此再增加一個注腳。
2007年Charles Taylor的巨著A Secular Age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上市時,我正在哈佛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雖然我在哈佛廣場的書店見到後也曾翻閱過,但因為實在太厚,最初並沒有購買的打算。不料在書店見過此書之後不久,余先生在一次電話中,竟特意向我推薦此書。從他的話裡可知,余先生不僅已經買了這本書,而且已經讀過至少大半,書中的一些內容,引起了他強烈的共鳴。2008年1月,在給田浩的《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本新序最後,余先生花了整整三段的篇幅介紹A Secular Age裡的相關內容,引為自己關於朱熹、王陽明的專題研究的「空谷足音」(《會友集》上,三民書局,2010,頁216-218),這也是他那段時間認真閱讀該書的印證。我讀書一般儘量在圖書館借閱,那次正是由於余先生的鄭重其事,我才最終決定將那本書買下。
最後我要說的是,余先生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史研究裡邊,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國史學者中,似乎呼應和繼承者已經寥如晨星。這固然與「思想史」這一學科在西方史學界整體上的衰落有關,因為隨著史學研究取徑的日益多樣化,傳統的思想史與後起的文化史、社會史、地方史等之間的此消彼長,也是學術發展的自然之勢。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來說,既有歷史也有思想這種要求本身所構成的難度,恐怕也不能不说是研究者有意無意地棄思想史而取諸如社會史、文化史等其它取徑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如果中文世界的學者大都自覺不自覺地趨附西方學界的潮流,唯其馬首是瞻,那麼,當西方學者由於種種原因不欲從事中國思想史時,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在中文世界也被冷落,顯得似乎落伍,就好像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了。不過,這既不是思想史本身的問題,更不是既有歷史又有思想這一要求的不當。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反而益發顯示出余先生所代表的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的難能可貴。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固然不是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而無視西方中國史研究、西方史學乃至整個西方人文學的傳統及其最新發展,前面提到的他對於Charles Taylor新著的關注,即是鮮明的一例,但與此同時,余先生也時時提醒研究者不要盲目趨附西學的潮流,落入黃宗羲所謂「從人腳跟轉」的窠臼。比如,在他那篇膾炙人口的「如何讀中國書」中,他就告誡中文學界說,「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份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著外國調子起舞,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青年朋友們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同樣的話也見於《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自序」,三民書局,1995,頁9-10)「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
當然,這就涉及到中國人文學(Chinese humanities)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宗教、藝術等的研究應當確立怎樣的學術標準這一大問題了。這個問題超出了今天我要講的範圍,但面對余先生的研究所建立的典範時,卻恰好是無法迴避的應有之義。所以,我最後也順便提出來,也許大家有興趣思考。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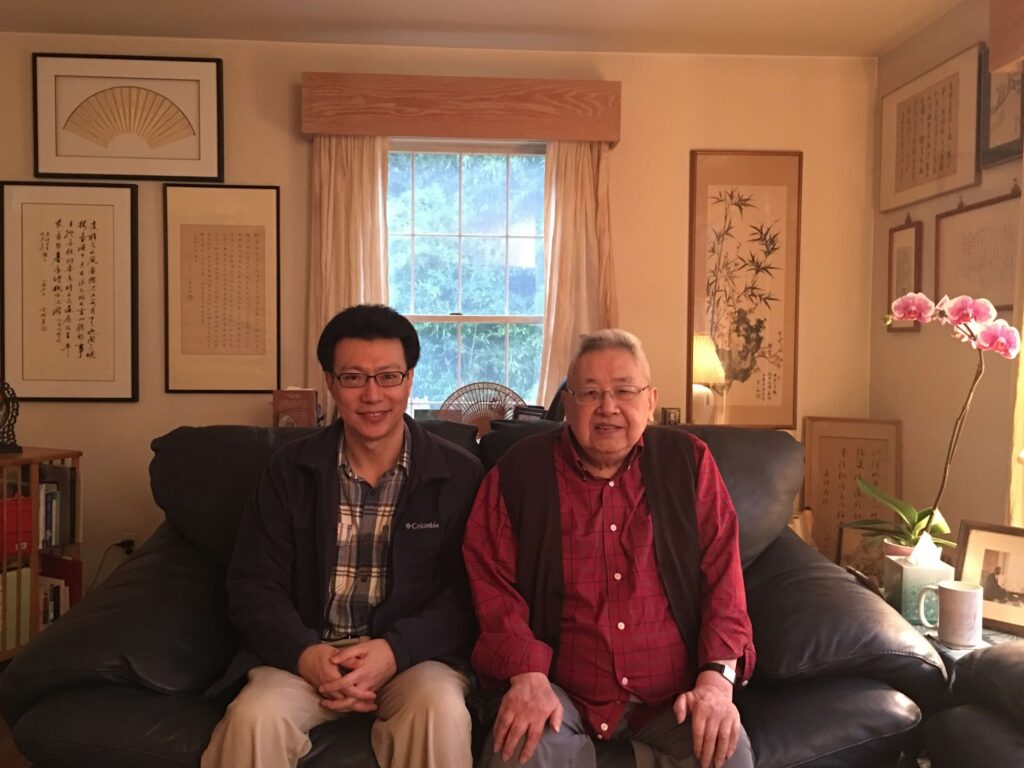
延伸閲讀
孫康宜:文學偵探余英時
葛兆光:余英時的通史視域與現實關懷
編輯部:在黑暗年代探尋勇氣和光——「余英時紀念論壇」問答精選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