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
編按:2022年11月26日,台灣將舉行「地方九合一大選」,同日亦將舉辦「18歲公民權修憲案」。究竟18至20歲的公民是否可以參與地方大選、修憲公投,擁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被選舉權?這又與我們的未來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關係?回顧當代道德暨政治哲學家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在《未來關我什麼事?》一書中對「未來世代」的描述與關注,我們看到自身與後代間存在著一種互惠關係,能為我們此刻的許多行動賦予意義;而我們此刻的許多行動也能確保後代生存的可能性,或是擁有更好的生存環境。(* 摘自《時代本位主義及其不滿》,標題為編者擬。)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對於人類未來的評價與討論,就和對於人類過去的評價與討論一樣乏善可陳。也許向來就是如此,而且近來也有不少學術風氣不再帶著敬意或崇拜來看待先人,不再認為他們立下了我們賦予其忠誠或是榮譽的理想標準。我認為這些學術風氣包括了傾向個人主義與宗教懷疑主義的風氣,再加上對於文化多元性的日漸讚許,卻同時對民族與種族組織的道德模糊性倍感不安。這些風氣破壞了以往我們認為歷史具備規範意義的概念,但是我們卻還沒能發展出另一套概念和態度能夠取代這些被拋開的部分。
我們在空間上愈來愈趨向世界主義,在時代方面卻愈來愈走上本位主義,倒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這種分歧的傾向可能有個共同原因,畢竟這兩者都是受到現代科學興起而產生的……
我覺得,我們對自身所處以外的其他時代的思考方式,以及對於自己所居以外地區的思考方式是一種有意思的對照。「全球化」與「全球整合」都在我們這時代最流行的字眼之列,大家都知道,科技的發展急遽地增加了全球交通與通訊的便利性,跨國界的社會與經濟互動也因而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而這又對許多人如何理解社會與自身地位造成無遠弗屆的影響,也帶來與日俱增的壓力,逼得大家必須發展與建構規範全球交通、通訊、貿易、金融等方面的跨國規範與機構。所以無論學界內、外,都迅速燃起了對於例如世界主義、全球正義、人權、國際法等「全球化規範」主題的興趣。
話雖如此,儘管我們在空間上愈來愈緊密結合,但是在時間上卻愈來愈受侷限、愈來愈深植於我們的這個時代裡、愈來愈不能透過豐富的價值與規範體系來看待自己與前人以及後代之間的關係。我們談了許多的全球整合與國際整合,卻很少想到時代整合與世代整合;我們愈來愈察覺到世界上不同地區人民的多元性串聯,但是對於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結感,和一些重視祖先、後代以及世系傳承等概念的傳統社會相比,卻是愈來愈弱。
到目前為止,我都是在大膽地說著我們在想什麼、我們的態度與信念,這樣肆無忌憚地使用第一人稱複數來談,可能會令某些讀者認為我偷懶或自大,只是把坐在安樂椅中的幻想偷天換日當成是普世真理罷了。不過我之所以用「我們」這稱呼,並不是出於放諸四海皆準的念頭;我在說我們的態度時,並非暗示這些態度就是每個人的態度,也不是預設那就是讀者的態度。事實上,我用第一人稱複數的方式來談,是為了表明我並非僅僅只是在描述我自己獨有的態度,而是試著刻畫出一些信念的類型,希望讀者會接受這確實就是當代思想與論述中常見的傾向(儘管未必普世皆然)。另一方面,之所以使用第一人稱複數的談法,意在強調當我提到這些思考模式有些缺陷或張力時,並未打算將自己撇除在批評之列以外。
我所描述的態度轉變並不是發生在一朝一夕之間。七十幾年前,T.S.艾略特(T. S. Eliot)就談到當時正興起一種所謂新的「本土主義」(provincialism):「這不是空間性的本土主義,而是時間性的本土主義。」艾略特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他在談到時間性本土主義時,最關切的問題是他見到當時社會上對於過去價值與標準的不當評價。不過,引起他關切的那些態度,也可能是一種普通現象的症狀,我稱這種現象為時代本位主義(Temporal Parochialism),包括了我們對於過去以及對於未來的這兩種態度。

我們很自然就會好奇,為什麼地理空間上的本位主義日趨萎縮之際,時代本位主義卻逐漸抬頭?答案乍看之下似乎一目瞭然。我先前提過,這幾十年來,全球交通、通訊、經濟活動急遽成長,而方興未艾的世界主義則是對這些事實的一大回應;不過,在時間方面卻沒有可相提並論的發展。想當然耳,跨越不同時代的交通、通訊或經濟交換並未增加;再說,有許多人已不再抱持著過去的傳統信念,不再接受過去對於世代之間聯繫的想法,即我們找不出可信的說法讓人看重對自己與祖先和後代的關係,讓人認為世代之間是彼此緊密結合的一體。由此來看,我們在空間上愈來愈趨向世界主義,在時代方面卻愈來愈走上本位主義,倒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這種分歧的傾向可能有個共同原因,畢竟這兩者都是受到現代科學興起而產生的:從一方面來說,科學使得世界各地人民的彼此關聯快速成長,促進了發展地理世界主義的傾向;相對於此,科學也破解了許多神話與故事,而這些神話與故事卻是在傳統社會中,世代彼此相連的信念之所繫。
不過,我們會有這種分歧態度也還有其他值得考慮的可能解釋,其中一種解釋涉及到時間形上學的信念變遷。說不定我們對時間的想法,已經從前人那種「永恆主義者」(eternalists)變成了「現在主義者」(presentists);說不定他們相信過去與未來的事物和時間,都與現在的事物與時間同樣真實不虛,但是我們卻只相信唯有現在的事物與時間存在。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雖然在地理上愈來愈傾向世界主義,卻也愈來愈擁護時代本位主義。當然,這種信念變遷本身也需要解釋,在許多人看來,既然這種信念改變得不到現代科學的支持,就更是需要好好說明。有人會很理所當然地說,假如我們比前人更願意接受現在主義,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再抱持著那種讓前人覺得自己與祖先和後代彼此相連的傳統信念了。可是如果這種說法沒錯,那我們所謂在時間形上學中的信念變遷,就不是解釋為什麼時代本位主義日益盛行的理由,反而成了得靠它來解釋的項目了。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則是訴諸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已經不同了。根據這種說法,我們現代人愈來愈重視的,是能夠追求當前的目標、試圖滿足當前慾望的那種自由,這會讓我們厭惡來自祖先與後代——活在過去與未來的那些人——以及來自我們現在無法接受的傳統所提出的要求。而這種只看重現在的自由概念,也可以相容於我們應將自由範圍延伸至全球而非僅限於國內的政治制度觀念。因此,就算我們的確有些接受某種時代本位主義的理由,這些理由卻未必要反對地理世界主義。當然了,對這種說法同樣可以再想想是誰來當解釋項,又是誰成了被解釋項。說不定日漸蓬勃的時代本位主義能夠解釋我們為何對只看現在的自由概念愈來愈看重,而非相反的情況。不過,我們對自由的理解有所轉變,確實是一種可能的解釋原因。
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政治原因。就我的觀察,地理世界主義的興盛不僅是一種道德進展,也是政治與制度的一大躍進。世界各地的人都處在同一套全球政治之中,在這座論述競技場裡,各種論證彼此辯駁、各家利益相互競爭,政策屢經爭辯,行動方不得不察覺自身行動對他人的影響及其可能的反應。就我們在地理空間上愈來愈世界化這件事來看,這多少意味著全球政治也正在擴張。全球政治愈來愈全面、愈來愈包山包海,制度上也愈來愈複雜抽象。當然,這些進展都十分複雜,而且也容有不同的詮釋。但是,無論如何詮釋,總會與時代問題形成強烈對比,畢竟世上現在既沒有任何跨時代政治,也不可能出現這種東西。我們既不會、也無法參與其他時代的人類所共享的那套政治,過去和未來世代也同樣無法在我們的政治中替自己的利益發聲。這並不是說某個世代無法影響後續世代的政治生活,這種影響無孔不入,也因而引起傑佛遜式的反駁看法,反對讓前人的亡者之手緊攫著活人不放。這裡的關鍵其實在於我們無法與生存時代和我們並不重疊的世代共同爭辯、思考與議論,在這種意義下,我們和他們並未共享同一套政治。除非我們選擇站在他們的立場替他們說話,否則他們干預不了我們的政治辯論與思考。再者,對我們同時代的人愈是包容,就可能對其他時代的人愈不包容,因為那些不同時代的人得與同時代的人一起競爭我們所能提供的有限時間、注意力與資源。這話如果沒錯,那也就難怪地理世界主義愈是日漸蓬勃,時代本位主義更會甚囂塵上了。
我們的時代本位主義其實不是真相的全貌,與更加傳統和宗教信仰更深的社會相比,我們對於世代關聯之間的理解可能真的薄弱膚淺得多。
我所提到的這些解釋彼此並不互斥,也並未窮盡所有可能,我也不打算對這些解釋做出結論,更不打算研議其他的可能性。更何況,我們之所以提到這幾種可能的解釋,並不是要誇大這些解釋試圖去解釋的那些態度。從一方面來說,我們的世界主義本身就是個還在發展中的立場,它表達出了當代思想與實踐中的一種重要傾向,卻也遇到(而且還會持續遇到)許多不同種類的強烈反彈。長期來看,世界主義的態度與觀念在政治與文化上要如何能夠得以確立,我們現在還無法完全弄清楚。至少就目前來說,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呼聲,以及國家和族群衝突的慘況,都讓世界主義的前景看來並不明朗——這還只是好聽的說法。相對於此——而且其實更直接與本書的主要論證有所關聯——我倒認為有很多人都對我們這種時代本位主義感到不安。我會舉一些證據來說明我們在對過去世代的態度上,普遍都對系譜傳承以及追溯個人家系頗感興趣。這份興趣的普及程度,表示出有很多人都十分渴望建立起與自己祖先之間的關聯感,將自己與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先人連結起來。這並不是對過去無感的人會有的念頭,而是渴求歷史的人才會有的想法。
至於對未來世代的態度,也有跡象顯示我們這種時代本位主義其實是導致焦慮的根源。比方說,原本就已經汗牛充棟的末日文學與電影愈來愈多,愈來愈多的小說與電影都在敘述地球毀滅的故事,描繪瘟疫、核子衝突、天體撞擊等災難事件,想像人類即將滅絕或已經滅絕,還有在發生這些事件之後的種種反烏托邦樣貌。說這些末日想像與反烏托邦故事是來自於擔心地球陷入重大危機、擔心後代的命運未定、擔心無力拯救人類未來的普遍恐懼,其實並不為過。這些並不是認為未來世代毫不重要的人會關心的事,而是對人類將來感到恐懼的人心中的擔憂。
我認為,對祖先系譜的興趣和末日文學及電影的流行熱潮這兩組現象所顯示出的不安,恰恰證實了我們對於自己在時間之中的地位,或是我們與生活在其他時代的人之間的關係,欠缺一套可靠、有條理的理解。這份不安也能解釋為什麼蘊含我們對過去或未來世代態度的公共政策,包括從歷史教育到環境保護等種種議題,會經常引發爭議、帶來激辯。這一切都指出,我們的時代本位主義其實不是真相的全貌,與更加傳統和宗教信仰更深的社會相比,我們對於世代關聯之間的理解可能真的薄弱膚淺得多。我們對這些關聯的思考,並未依據十分豐富或明確的價值體系而生,但是卻絕非對自己與先人後輩的關聯不感興趣。而這種對於自身在世系傳承中地位的貧弱思考,也有許多人覺得是個大問題、覺得是一份空虛欠缺,是需要設法解救的價值崩壞。


我至今所談的不只是我們對後代的態度,也包括了我們對祖先的態度。但是,我在這本書裡主要關心的問題還是我們對於未來世代的態度,所以不會再進一步談到關於對自己先人或對過去前人的態度了。這些題目也都很豐富有趣,但就留待他日再談吧。此外,我也不打算繼續追究如何解釋地理世界主義和時代本位主義之間的相互對照。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但是我在這本書裡想談的並不需仰賴這問題的答案,所以要將這個問題暫且擱下,專注在探討我們對待未來世代的態度所涉及的問題上。
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氣候變遷,就是蘊含了這種態度的大眾議題之一。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一派所持的主流觀點,是氣候變遷會對地球造成嚴重威脅,而人類受害尤深。儘管專家學者對於我們要花多少代價才能有效減緩或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意見分歧,但大多數看法都認為那恐怕在天文數字之譜。假設真是如此好了,而且再假設如果沒辦法採取這些減緩行動真的會導致一連串嚴重後果,危害到在我們之後才生活在這世上的人們。這些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後果有些目前就已經很明顯了,要是真的不靠大家通力合作,在我們有生之年恐怕就會遭受更嚴重的影響,在我們之後才生活在這世上的人所面臨到的影響,肯定會比我們所遭遇的更嚴重。到了最後,地球恐怕就再也不適合人居住了。事實上,就在我寫這一段文字的同一天,《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就引用了未具名科學家的說法,認為到這個世紀末,地球就不適合居住了。
如果這是真的,那我們就面臨一項抉擇:必須決定願意付出多少成本、願意改變多少目前的生活,才能遏止或延緩將來造成無數地球生靈落入生存困境、且最終恐怕導致人類滅絕的惡化過程。這項抉擇的具體樣貌,會因人們處於不同社會裡而有所不同,最富庶的國家一直都該為排放溫室氣體這個造成氣候變遷的人為主因負責,而生活在這社會裡的我們,也許就得決定要將生活水準降低到什麼程度。相對地,生活在開發中的社會裡、和我們一樣一心追求富庶生活的民眾,可能就變成要決定願意放棄或延後多少期待的報酬。但是這些選擇都有同樣的架構,富庶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一樣要決定現在的人準備付出多少成本、吞下什麼樣的苦頭,才能讓將來的人不用過得更辛苦,讓人類可以繼續在地球上生活下去。
如果我們問為什麼應該在乎未來的人類,或是我們對他們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可能很容易就會假定,唯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們該將他們的利益或福祉看得多重。
氣候變遷吸引了許多不同領域研究者的注意,其中哲學家更是對這議題所引起的正義與責任問題特別感興趣。按照世上各國各自不同的富有程度、人口多寡、發展程度、溫室氣體排放紀錄來看,各國要負擔何種程度的代價來避免或緩和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最糟後果才叫做合乎正義?透過現有的國家體制與國際組織能夠處理多少氣候變遷問題,而面對這個問題又需要發展新的全球管理架構到什麼樣的程度?這些新架構應該要是什麼模樣,才能夠滿足正義的要求?個人又該負起哪些改變行為與參與政治的責任,才能夠支持這些對抗氣候變遷的努力?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在此之前,還有些問題需要先處理。真要說到底,就是我們究竟為什麼應該要在意氣候變遷?尤其是為什麼應該關注那些在我們全都死了之後才出現的氣候變遷後果?如同先前說的,氣候變遷的後果已經清楚有感,而且在沒有通力合作的情況下,甚至即使我們真的共同努力,這些氣候變遷的後果在我們餘生中仍可能愈形惡化。大多數人都同意有理由關注氣候變遷對自身生活所造成的重大影響,而且說實在的,就是因為這些影響這麼嚴重,才更有可能驅使我們設法去處理。不過,假設即使氣候變遷的狀況繼續惡化下去,可是我們大多數人剩下的人生都不用面臨氣候變遷惡化所造成的苦果,還有理由去關心氣候變遷在自己死後對未來世代帶來的種種磨難嗎?如果答案仍是「有的」,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想我們要認真看待一件事,就是現在要談的問題是未來世世代代的命運。哲學家有時候會混用「未來世代」和「將來人類」,在某些脈絡下,這種用法也確實無傷大雅;但是世代這個詞有其特殊內容,而「未來世代」的普遍使用也有其重要意義。這個詞指出了一項事實:未來的人類——也就是現在我們要考慮其生存與繁榮的那些人——並不是只存在於我們思想中散亂無章的一群人,他們對我們來說,是按時間出現、受因果影響的人。我們所考慮的,是在時序上世世代代傳承的未來,而各代也同樣是因先前世代而孕育生出。當我們問為什麼應該為未來世代操心時,不只是在問為什麼應該在乎未來的人類能否存在,也不是問他們將過得如何;我們問的是儘管我們是藉由世代傳承而生,但為何應該關心這條時序上的世代傳承,是否要在更不利的條件下繼續向未來延伸?這些問題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問為什麼應該在乎未來的人類,或是我們對他們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可能很容易就會假定,唯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們該將他們的利益或福祉看得多重。我們可能不會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未來世代對我們來說之所以重要,可能就是在於他們是我們的後繼者,他們的存在是延續了我們共同身處其中的世系脈絡。所以光是用不同的方式形塑問題,就可能讓我們錯失答案中的重要部份。不過,如果那就是部分答案所在,它其實也近在咫尺,只要我們用到「未來世代」這個詞就看得見。
我想要問的其實是我們為什麼應該關心我們現在活著的人永遠見不到、永遠活在集體經驗界限之外的那些人會面臨什麼命運?
但是,究竟有誰落在這個詞所涵蓋的範圍裡頭呢?有一種我稱為無限制(unrestricted)詮釋的說法認為,未來世代包括了現在還沒出生、但將來某天可能在世的所有人,這就包括了我們還在世時就會出生的許多人。事實上,既然全世界平均每分鐘大約會有兩百六十七人出生,所以這說法在這一刻會包括你讀完這一章時出生的好幾千人,但是等到你讀完這一章時,他們又不算在未來世代之內了。第二種說法我稱為有限制(restricted)詮釋,認為未來世代這個詞僅指現在世上所有人死去之前都還沒出生的那些人。照這說法,在你讀完這一章剩下部分之前出生的人都不算是未來世代,就連在當下這一刻也不算。
當然了,這兩種詮釋都包含了像「現在」、「還沒」等指示要素(indexical elements),所以「未來人類」在這兩種詮釋中才會隨著這些指示詞所指稱的變化而不停變動。這也提醒我們「未來世代的傳承」這個概念,其實是過度簡化了更複雜的現實情形。新一代的人類不會同時出現,也不會一口氣替換掉先前的各個世代,而是像布萊恩.貝瑞(Brian Barry)所說的那樣:「『世代』是一種將人口替代的連續過程以抽象化表示的概念。」這裡其實有兩點不同,第一點是人類父母通常不會在孩子出生時就死亡,所以無論什麼時刻,人類人口組成永遠都包含了不同世代的成員。第二點在於人類世代脈絡終究是在個人層級上,由個人與其祖先和後代組成,但是這種個別繁衍脈絡並不會依照統一的時間表進行,所以屬於同一個世代的不同人群,往往也是在時間上交互重疊而非完全重合。但我在本書後頭會再強調,我們不能因為有這些差異,就推論說「未來世代」這個觀念的意義只在於當作一種純粹化約論式的理解。換句話說,我們不該假定自己對未來世代的關懷必須要真的關心到某支個別的繁衍脈系,比方說,關心我們自己這一家的後代。說不定,儘管未來世代是一種「抽象化表示」,卻也能出奇地成為我們關心的對象。意思是說,不管我們自己個人有無後代,把人類當作能夠持續繁衍後代的整體來看這件事,對我們來說可能都很重要。不過這裡我話說得有點早了,在後頭兩章會再回來談這一點,說說我自己認為我們確實重視、也應該重視未來世代的理由。

還有更直接相關的一點,就是在有限制詮釋與無限制詮釋之間的這層區別,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我所提出來的問題。如果我們採取有限制詮釋的觀點,那麼為何應該關心氣候變遷對未來世代有何影響這個問題就會顯得格外明確;反之,若採無限制詮釋,那我們在問這個問題時所涉及的對象,就有一些是我們可能會遇見、甚至是會與我們建立起重要關聯的人了。如此一來,在無限制詮釋底下,要回答為什麼應該關心未來世代命運這個問題的好答案,就必須考慮到(而且也勢必會影響到)我們可能終究會與屬於這些世代的其中一部分人彼此相連的這個事實了。不過,我想要問的其實是我們為什麼應該關心我們現在活著的人永遠見不到、永遠活在集體經驗界限之外的那些人會面臨什麼命運?為什麼應該為那些我們永遠不認識、身份永遠成謎的陌生人負擔起任何成本?等到他們活在這世上的時候,我們早就已經化為塵土了,那為什麼現在還要考慮他們的命運?為什麼應該為了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或避免其惡化,而要在自己的生活品質上有所妥協?說得更極端些,如果我們知道氣候變遷的結果是地球終將不適合人類居住、人類世系在我們自己和所有認識的人全都死光之後才會終結,我們又何苦為此煩惱?如果我們要問的就是這些問題,那麼對於未來世代這個詞的理解,就要採取有限制、而非無限制的詮釋了。
我想主張,對於思考人類未來這回事,我們所擁有的評價資源終究要比自己所了解的還多,而且我們要關心後人命運的理由,也比大家普遍以為的還要更強、更多樣。
不要以為只有道德懷疑論者才會提出這些質疑。對於想以較廣泛的人倫關係——也就是一套處理我們與他人之間關係的價值與規範——來思考道德的任何人而言,我們的行動在道德上對於我們與其他現存者都永遠不會親身接觸的那些人究竟有何意涵,仍是撲朔迷離。這些行動當然有某些道德意涵,打個比方,任何可信的道德觀點,都會認為在大量人口集中區設置一枚核子彈,並訂於兩百年後引爆,殺害一大堆現在還沒出生的人是件錯事。可是就這個情況本身來說,現在活著的人在核子彈爆炸時早就不在了,而且他們與到時候核爆受害者之間也不會有直接的人際關聯,則明確的人倫關係可能就未必是能夠明白認定這件事是錯事的判斷基礎了。說得更廣一點,當我們考慮自身行動對於現今人們永遠不會親身接觸的後人有何意涵時,處理我們與同時代人之間關係的道德規範能提供多少指引也尚屬未知。所以,就算我先前提那些問題的重點在於探索我們對於未來世代究竟有何特殊道德責任,也不一定要將其當作是一般道德懷疑論所提的質疑,這些問題反而可能反映出道德在延伸到後世時可能引發的實際難題。
在此同時,大家也要注意我在描述這些問題時,並沒有特別指涉哪種道德觀。這些問題問的是我們關心未來世代的理由,並未假定最後得出的理由一定會是道德上的理由,而且這也不是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可能解答時應該採取的預設。如果我們有理由替未來世代操心,那麼無論這些理由是否在道德領域之內,都仍然是一個理由。
其實,對於為什麼我們應該關心氣候變遷對未來世代的影響,或是關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人類滅絕危機,答案都必定要援引我在這章開頭討論的價值觀念。這問題的答案一定要引入某些價值概念或是人類存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說的沒錯,我們大多數人其實對這種概念都沒有一套穩定、完善的看法。我們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時代本位主義,可是我們在這套本位主義裡並不安穩。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彷彿都會執著於自己在整個世代傳承脈絡上的地位;而這種曖昧態度,也就證實了我們隱約體認到後人的命運蘊含著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至少在我看來正是如此。
因此,我這本書的目標就是要發掘出這種曖昧態度的根源。我想主張,對於思考人類未來這回事,我們所擁有的評價資源終究要比自己所了解的還多,而且我們要關心後人命運的理由,也比大家普遍以為的還要更強、更多樣。若我所料不錯,那我們在認識這些根源與理由時,也就增進了對自我的理解,能夠更明白我們自己是誰、更清楚什麼對我們來說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除此之外,我們也能有些實質的收穫。如果我們在思考人類未來時所擁有的評價資源真的比自己所了解的更多,那這些資源也就可能得以應用到當前會對未來世代造成嚴重威脅的種種情勢上,包括氣候變遷以及其他各種問題。
延伸閱讀:

理論思維的跨界形構和在地實踐——史書美《跨界理論》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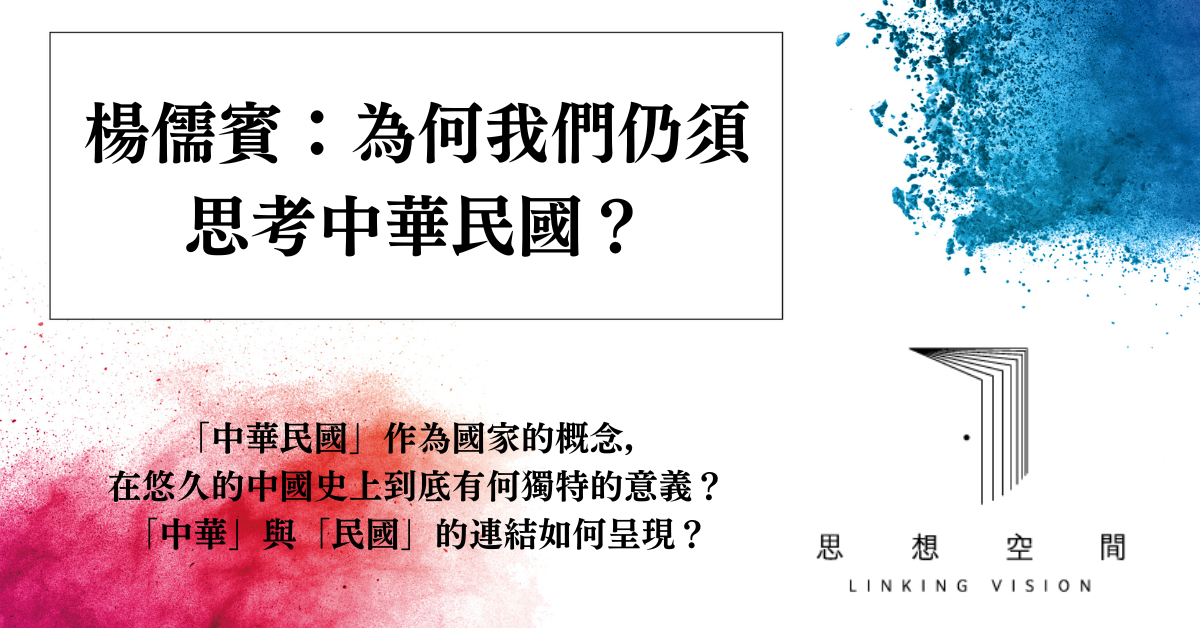
楊儒賓:為何我們仍須思考中華民國?

動物苦難與人類的反省:「人性之鏡」照出了什麼?
| 閱讀推薦 |

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當代道德暨政治哲學家。著作嘗試解決倫理理論的核心問題,探討的各式主題包括平等、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寬容、恐怖主義、移民、傳統和個人關係的道德意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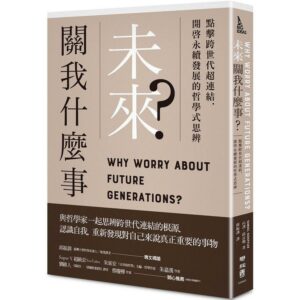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