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爾希.浦洛基 Serhii Plokhy(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烏克蘭史教授)
編按:今天的烏克蘭民族,是在各種帝國勢力與文明範圍交會之處,從各種瓜分與苦難中生長出來的。2022年9月,哈佛大學烏克蘭中心主任謝爾希.浦洛基的著作《烏克蘭》中譯本面世,其在書中深度剖析了這座「歐洲之門」兩千多年的歷史軌跡,並且從帝國大敘事的瓦礫堆中,挖掘出烏克蘭的複雜過往,重建這段被許多人輕忽或遺忘的歷史。在俄烏戰爭仍在延燒的當下,我們不妨從更深層的歷史脈絡中,瞭解烏克蘭的處境與現狀,從中理解烏克蘭人思考身份、尋找未來的方式。(* 本文摘選自《烏克蘭: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尋自我的荊棘之路》第二十五章〈再見,列寧〉;全文分為二篇,本文為二之一,標題為編者擬。)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烏克蘭和蘇聯其它加盟共和國的公民們,都緊緊盯著他們的電視機螢幕,每個頻道都在播放一條從莫斯科發出的消息:蘇聯領導人、眾多外國和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的莫斯科人都聚集在紅場上,送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個統治這個超級大國長達十八年的烏克蘭人。他身患慢性病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幾天前在睡夢中死去,許多從不知有其他領導人的電視觀眾難以相信「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為了世界和平不知疲倦的戰士」(這是官方宣傳機構對他的頌詞)就這樣走了。他的老人政治凍結了蘇聯社會向上爬升的空間,讓所有改變的希望破滅,似乎擁有讓時間停止的力量。對此,官方使用的術語是「穩定」,很快勃列日涅夫時代就將被人們稱為停滯時期。

激進的改革嘗試、急劇的經濟下滑和強大蘇聯在政治上的分崩離析都將在這個新時代出現。在這個崩解過程中,烏克蘭將走在前列,迎來自己以及其它那些較為猶豫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的二十年間,烏克蘭的年度工業增長率從百分之八點四下降到百分之三點五,而表現向來不佳的農業的增長率則從百分之三點二下降到百分之〇點五。這還只是官方數字,在一個充斥著虛假報導的時代裡沒有太多意義,現實的情況更為嚴峻。蘇聯愈來愈依賴其通過向海外出售石油和天然氣獲得的強勢貨幣,在七〇年代初,當蘇聯和西方的工程師們還在忙於修建將天然氣從西伯利亞和中亞送往歐洲的管道時,產自烏克蘭達沙瓦(Dashava)和謝別林卡(Shebelynka)的天然氣被運往中歐而不是國內消費者家中,以換取強勢貨幣。隨著這些氣田的枯竭,烏克蘭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天然氣進口國。
赫魯雪夫曾向蘇聯民眾承諾他們將會生活在共產主義時代,這一承諾從未變成現實,並已被當局的宣傳家們徹底遺忘。蘇聯人生活水準的下降有如自由落體,唯一讓下降減緩的力量是國際市場上的高油價。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時,精英階層和大眾都完全不抱有希望,不僅針對共產主義,也針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個詞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官方對蘇聯社會形態的定義。隨著勃列日涅夫的棺材被放進克里姆林宮圍牆附近新開掘的墓穴,克里姆林宮的鐘樓報出下一個時辰,禮炮也齊聲鳴放,宣布一個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到來。激進的改革嘗試、急劇的經濟下滑和強大蘇聯在政治上的分崩離析都將在這個新時代出現。在這個崩解過程中,烏克蘭將走在前列,迎來自己以及其它那些較為猶豫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
在那些站在列寧墓前的主席臺上、為已故的勃列日涅夫致禱詞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一個人顯得與眾不同,他就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弗洛基米爾.謝爾比茨基。此時是十一月,天氣寒冷,然而滿頭銀髮的謝爾比茨基為了表對對勃列日涅夫的敬意,一直沒有戴上帽子。謝爾比茨基在其政治生涯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代理人,因此有理由感到悲傷。在勃列日涅夫意外辭世之前,克里姆林宮內部已有傳言說勃列日涅夫會在即將到來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宣布辭職,將權力移交給謝爾比茨基,以此保證聶伯彼得羅夫斯克派在這個國家的領導集團中的優勢地位。謝爾比茨基是聶伯彼得羅夫斯克本地人,在被調往基輔前就是聶伯彼得羅夫斯克的共產黨領導人。然而勃列日涅夫死在了全會召開之前,新任的黨領導人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前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i Andropov)。安德羅波夫與聶伯彼得羅夫斯克派毫無瓜葛,很快就會對勃列日涅夫的黨羽們展開貪腐調查。


葬禮之後,謝爾比茨基將會返回烏克蘭,在那裡韜光養晦,以求平安渡過這段難以預測的時間。身體狀況良好的他此時才六十四歲,在政治局成員中算得上年輕人。他的直接競爭對手們年齡都比他大,健康狀況也不佳。此外,在他執掌烏克蘭共產黨最高權力的時期,謝爾比茨基已經建立起一個忠於自己的代理人群體。安德羅波夫於一九八四年二月 [1] 死去,而他的繼任者康斯坦丁.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死於一九八五年三月。謝爾比茨基活到了他們去世之後,然而此時他攀上莫斯科權力之巔的機會已經過去了。由尼基塔.赫魯雪夫建立、由勃列日涅夫加強的俄羅斯–烏克蘭上層間合作關係,此時幾乎已經蕩然無存。新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上臺。他精力過人,與烏克蘭共產黨機構沒有任何關聯。戈巴契夫的父親是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在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混居的北高加索地區長大,從小就對烏克蘭民歌耳熟能詳,然而他首先是一位蘇聯愛國者,對俄羅斯之外的任何加盟共和國都沒有特別的感情,並將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們在各加盟共和國創建的代理人網絡,視為對他的權位的威脅,也是對他上臺伊始就啟動的改革計畫的威脅。
那條在此前三十年中不斷將烏克蘭幹部向莫斯科輸送的輸送帶,很快就停止了運行。戈巴契夫從俄羅斯各地區調來新人,其中包括他後來的敵人伯里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戈巴契夫打破了自史達林去世以來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默契——每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領導人都必須是本地人,且須來自本地第一民族。他將俄羅斯人根納季.科爾賓(Gennadii Kolbin)「空降」到哈薩克,替換了忠於勃列日涅夫的哈薩克人丁穆罕默德.科納耶夫(Dinmukhamed Konayev)。與葉爾欽一樣,科爾賓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即今位於烏拉山區的工業城市葉卡捷琳娜堡)的黨組織培養出來的官員,與哈薩克從無關係,也不曾在那裡工作。他的任命讓哈薩克學生們走上街頭,掀起了蘇聯戰後歷史上第一次民族主義暴動。
這一天發生了風向改變,原本向北和向西的風向轉為向南,使輻射雲飄向烏克蘭首都,這座城市擁有超過二百萬人口,而輻射狀況正在發生快速變化⋯⋯
一九八六年四月,距基輔不到七十英里的的車諾比(Chernobyl)核電廠發生爆炸,在烏克蘭造成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科技災難。此後不久,莫斯科的新領導集團與烏克蘭領導層之間的裂痕就公開化了。提議將核能帶到烏克蘭的是烏克蘭科學家和經濟學家,而當時擔任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的彼得羅.謝列斯特希望為烏克蘭迅速發展的經濟提供新的電力,在六〇年代努力鼓吹這一方案。一九七七年車諾比核電站開始並網發電時,包括「六〇一代」領軍人物之一伊凡.德拉奇在內的烏克蘭知識分子都對烏克蘭進入核能時代表示歡迎。對德拉奇和其他烏克蘭愛國者而言,車諾比意味著烏克蘭向現代化更進了一步。然而,德拉奇和其他熱情的核能鼓吹者沒有留意到:這個專案的運行權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而電廠大部分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都來自烏克蘭之外。烏克蘭從車諾比獲得電力,卻對核電廠內部事務幾無發言權。與蘇聯其它所有核設施以及烏克蘭大部分工業企業一樣,這座核電廠歸屬蘇聯政府部門管轄。這座核電廠與在這裡發生的那次事故都以俄語對附近那座城市的拼寫命名,並為世界所知——即車諾比(Chernobyl),而非烏克蘭語的喬爾諾貝利(Chornobyl)。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於一次失敗的渦輪機測試,車諾比核電廠第四號反應爐發生了爆炸。直到此時,烏克蘭領導人們才突然意識到他們對自身的命運以及這個共和國的命運多麼缺乏掌控。一些烏克蘭官員被邀請加入中央政府負責處理事故後果的委員會,卻幾乎沒有發言權,只能聽從莫斯科以及莫斯科派出的現場代表的指令。他們負責組織核電廠周圍三十公里範圍內居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卻不被允許將事故的規模和它對自己同胞健康的威脅告知全體烏克蘭人。這個加盟共和國的政府對烏克蘭命運掌控權的有限程度在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早上變得昭然若揭,這一天發生了風向改變,原本向北和向西的風向轉為向南,使輻射雲飄向烏克蘭首都,這座城市擁有超過二百萬人口,而輻射狀況正在發生快速變化,考慮到這一點,烏克蘭當局試圖說服莫斯科取消原計畫的國際勞動節遊行,卻沒能成功。
車諾比核電廠第四號反應爐的爆炸和部分熔毀將約五千萬居禮的輻射量釋放到大氣中,這相當於五百顆廣島原子彈釋放出的輻射量,僅在烏克蘭就有超過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輻射汙染⋯⋯
五月一日,當黨的組織者們讓組成佇列的學生和工人走上基輔大街,準備開始遊行時,共和國領導人中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地缺席了,那就是弗洛基米爾.謝爾比茨基,這是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在五一節遊行時遲到。當他乘坐的豪華轎車最終出現在基輔的主要街道和遊行的核心路段赫雷夏蒂克大街時,烏克蘭共產黨的高層們發現謝爾比茨基流露出明顯的不安。「他告訴我:要是你搞砸了這次遊行,就請直接退黨吧,」這位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對他的幕僚們說。沒有人不明白這句話裡那個沒被提到名字的「他」是誰——整個國家裡只有一個人有資格威脅將謝爾比茨基開除出黨,那就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儘管輻射量正在快速上升,戈巴契夫仍舊命令他的烏克蘭下屬照常執行任務,以向全國和全世界顯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而車諾比的爆炸也不會威脅到民眾的健康。謝爾比茨基和其他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很清楚事實並非如此,卻覺得除了聽從莫斯科的命令之外別無選擇。遊行按原計畫舉行,他們只能將它從四個小時縮短到二個小時。
車諾比核電廠第四號反應爐的爆炸和部分熔毀將約五千萬居禮的輻射量釋放到大氣中,這相當於五百顆廣島原子彈釋放出的輻射量,僅在烏克蘭就有超過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輻射汙染,比整個比利時的面積還要大。光是反應爐周圍的隔離區面積就達二千六百平方公里。爆炸發生後一週之內,有九萬多居民從隔離區被疏散出來,其中大部分人從此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近五萬名核電廠建築工人和運營人員居住在普里皮亞季城(Prypiat),這座城市至今仍處於遺棄狀態,成為一座現代的龐培城和蘇聯最後歲月的紀念碑。在普里皮亞季城中的屋牆上,至今仍能看到弗拉基米爾.列寧和共產主義建設者們的肖像,也能看到讚美共產黨的口號。
在烏克蘭,有二千三百個定居點和超過三百萬人受到輻射塵的直接影響,因依賴聶伯河和其它河流水源而受到這場爆炸威脅的人口則有近三千萬。這次事故對烏克蘭北部的森林地帶也是一場災難,這裡是烏克蘭最古老的定居區域,千百年來當地居民一直在這裡躲避來自草原的入侵者。現在這些曾讓人們免於遊牧民族傷害,曾為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大饑荒倖存者提供食物的森林,卻變成了毀滅之源。樹葉成為了輻射源,而輻射這一看不見的敵人讓人無從躲避。這是一場世界級的災難,而烏克蘭是除了毗鄰的白俄羅斯之外對這場災難感受最為痛切的地區。
輻射影響了從黨的領導層成員到普通大眾的每一個人,因此車諾比核事故讓烏克蘭黨內和社會各界對莫斯科及其政策的不滿急劇增長。當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們動員烏克蘭人面對這場災難的後果,並打掃中央留下的爛攤子時,許多人不禁要問自己:為何他們要拿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來冒險?他們在餐桌旁抱怨中央的失敗政策,向他們信任的人吐露失望情緒。然而烏克蘭的作家們不願保持沉默,在一九八六年六月的一次烏克蘭作家協會會議上,許多在十年前曾為核能的到來歡呼的人開始將它譴責為莫斯科用來控制他們的國家的工具。伊凡.德拉奇(Ivan Drach)是引領這場攻擊的人之一,他的兒子是基輔一所醫學院的學生,在事故後不久就被派往車諾比,沒有得到充分的指示,也沒有防護設備,並因輻射而中毒。
車諾比的災難讓烏克蘭覺醒了,讓人們開始思考諸如加盟共和國與中央的關係,和共產黨和民眾的關係等這些基本的問題,並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多年死寂之後的第一場公共大討論——這個社會正在努力奪回自己的發言權。「六〇一代」站在了這場運動的最前列,他們中包括作家尤里.謝爾巴克(Yurii Shcherbak)。謝爾巴克在一九八七年末成立了一個環保團體,後來發展為綠黨。環保運動將烏克蘭視為莫斯科所作所為的受害者,因此成為戈巴契夫改革時期烏克蘭最早的民族動員形式之一。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不僅讓烏克蘭共產黨領導層與他疏遠,還讓擁有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充滿民族意識的知識階層動員起來反對身為統治上層的精英。結果證明,烏克蘭的這兩個彼此衝突的群體,即共產黨體制內集團,以及新生的民主反對派,將會在反對莫斯科統治集團、尤其是反對戈巴契夫中找到共同利益。
[1] 譯註:原文作十二月,有誤。
延伸閱讀:

葉浩談《到不自由之路》:民主跳級生為何要重新思考「不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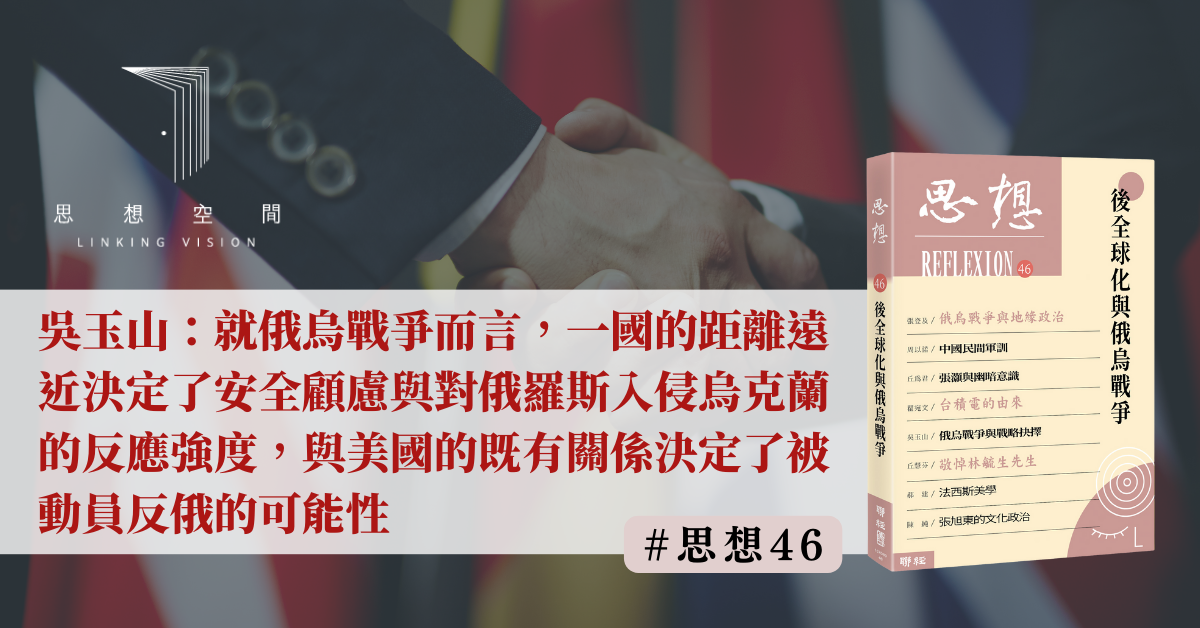
盤點各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站位——如何理解戰略抉擇?

【學人專訪】謝爾希.浦洛基:新的烏克蘭社會已經形成
| 閱讀推薦 |

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烏克蘭史教授,專長為東歐知識、文化、國際關係,研究主題包含烏克蘭史、俄羅斯民族主義、二戰與冷戰史等,2018年獲頒表揚對烏克蘭文化卓越貢獻的「國家謝甫琴科獎」。其著作《最後的帝國:蘇聯的末日》得到外交政策界重要獎項「萊昂內爾.格爾伯圖書獎」,《車諾比》獲得頒發給年度最佳英語紀實寫作的「巴美列.捷福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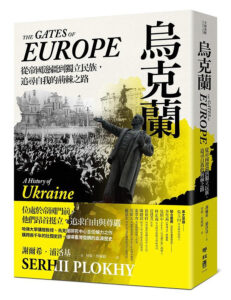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