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德維(費薩爾國王學術及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
無論是叮噹(ドラえもん)還是Doctor Who,任何時空穿越的故事中,都會出現「如果在那一天我轉向了另一邊⋯⋯」一類劇情。[1] 1979年,岡田英弘(1931-2017)《康煕帝の手紙》初版發行;直至2021年,八旗文化首次推出該書的華文譯本,將我們帶回了42年前一場史學革新的起點。
陳氏視岡田氏為「先行者」的原因,在於他認為現今「新清史」的學者擴大視角,以滿、蒙語文的史料觀察與分析大清帝國的歷史,而這正是岡田英弘在1970年代嘗試的方向。
岡田英弘,與「新清史」研究的先行者們
本書的中文譯名《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以下只標註頁碼),是根據2016年二版初刷時的書名《大清帝国隆盛期の実像――第四代康煕帝の手紙から 1661-1722》(中譯:大清帝國隆盛期的真象:自第四代康熙皇帝的書信所見,1661-1722)而立。在2016年的版本中,岡田氏曾直言,書名的改動是因為1979年在中公新書出版的《康煕帝の手紙》的內容大約只有2016年版的三分之一。
新版本中增加了岡田氏對大清帝國的概論,也包括他自1979年以來發表的六篇相關學術論文與五篇日譯蒙語史料;此外,再於1979年版的舊作正文添上資料在台灣出版的《宮中檔康熙朝奏摺》頁數作為出處說明,並另附人物與概念的解說,故不宜被視為同一作品。而作為藤原書店《清朝史叢書》的首冊,《大清帝国隆盛期の実像――第四代康煕帝の手紙から 1661-1722》亦有顧及21世紀初日本一般讀者的考慮,認為華語世界廣為人悉的康熙帝,在日本並非家傳戶曉的人物,故需要增添上迹鋪陳。(頁2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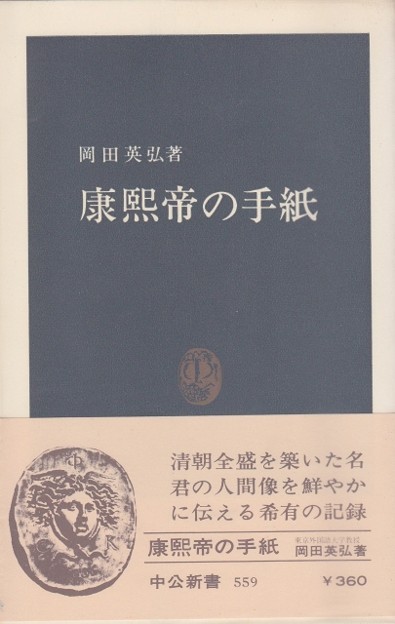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岡田氏並沒有將他對滿文檔案的研究定位為(當時尚未出現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作品,但為本書作導讀的陳國棟(1955-)卻徑然稱岡田為「『新清史』的先行者」。
陳氏視岡田氏為「先行者」的原因,在於他認為現今「新清史」的學者擴大視角,以滿、蒙語文的史料觀察與分析大清帝國的歷史,而這正是岡田英弘在1970年代嘗試的方向。1979年《康煕帝の手紙》初版面世時,岡田氏就曾指出:「要理解17世紀的東亞史,不只是中國的史料,還必須要利用以滿洲、蒙古、西藏等語言所書寫而成的史料,做出綜合性的判斷。」國立故宮博物院公開清宮檔案前,他就曾於1974年多次到訪台灣,閱讀康熙帝(1654-1722)在與準噶爾汗國對決時的滿文書信。(頁13-14)陳國棟的觀察,也為「新清史」的領軍人物、岡田氏的學生歐立德(Mark C. Elliot,1968-)所認同。歐立德認為「新清史」的苗頭於1970年代業已開展,在台灣、中國與日本多國同時發生。
陳捷先(1932-2019)與莊吉發(1936-)在整理與出版故宮博物院館藏檔案時,發現滿文檔案的數量遠多於漢文版本;而要探究這批新史料,就需要閱讀滿文的能力。1977年,陳氏與莊氏成功以《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九輯的名義出版了這批材料,引起多國史家的關注。同年,莊吉發轉抄及翻譯了部分滿文材料,獨立出版了《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主要內容圍繞康熙帝與噶爾丹汗(1670-1697)對戰時的滿文信件。在1977年版的序文中,莊氏感謝包括岡田氏在內的三位日本學者幫忙訂正其書。另外兩位學者,包括後來成為明治大學名譽教授神田信夫(1921-2003),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文化中心(ユネスコ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所長的松村潤(1924-)。兩位都在20世紀晚期成為重要的清史研究者。
兩年後,岡田氏的《康煕帝の手紙》初版問世,書中的關懷與觀點與莊氏類同。而陳捷先則前後出版了《滿文清實錄研究》(大化書局,1978年)及《滿文清本紀研究》(明文書局,1981年),都可以說是70年代故宮博物院整理及出版滿文檔案的直接成果。而參與其中的學者,亦成為了往後30年東亞最具影響力的大清帝國史學者之一。除了歐立德師從於岡田氏以外,莊吉發與Beatrice Bartlett(1928-)的常年通訊,也促成了80年代滿蒙語文應用於大清帝國研究的風潮,並且進入了北美洲的歷史學者圈子。[2]
回到滿文史料開發的起點,有別於莊吉發等學者,岡田英弘在抱有疆界與種族文化關懷的同時,還對滿洲帝王家族的私領域作出盡細的探索。
「新清史」研究的反思和挖掘
有關「新清史」的討論與批評,已在過去十年間廣受矚目。[3] 我們無意在這裡重複這些論述,但仍要提及其中一種觀點——2021年,學者楊斌(Yang Bin)指出關於「新清史」的討論不時都有「牛頭不對馬嘴」的現象——這一觀察甚具啟發性。
楊氏從史學史的角度解釋了:正是70年代北美洲與英語世界對中國史學界有著獨特的學術關懷,才在80年引發了日後被稱為「新清史」的研究範式。在他看來,北美的中國研究起源於20世紀中葉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一代的近代史學者。這些學者關心的問題,主要在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故論述多集中於思考中國的固有體制(Chinese World Order)「進化」為現代體制的歷史。這一世代史學者的成果,後來被費正清在哈佛大學的學生柯文(Paul A. Cohen,1934-)稱為「刺激——反應」範式(impact-response paradigm)。
到了80年代,柯文等學者提出希望美國學者可以揚棄西方/歐洲中心(Western-centric / Eurocentric)的論述方式,改為從中國的角度研究中國(尤其近代中國史)。這一觀點不論在北美或世界均得到不少正面回應。然而,由於「中國本位」模式(China-Centred Approach)的應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在處理各類議題之前,必須先處理「何謂中國」的前題。楊斌認為「中國本位」是美國中國研究的「阿克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其「左腳跟」是邊疆/疆界問題,其「右腳跟」則為族群問題——也就是分別在梳理「中國究竟有多大」的面積問題,以及「誰是中國人」的身份問題。楊氏認為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討論內在理路(inner logic),構成了「新清史」的基礎,在90年代後期將中國研究與內亞研究結合,用以對治中國邊疆和族群研究的問題。
在此視角下,我們看到研究大清帝國歷史的著作中,幾本被視為「新清史」系列(作者卻不一定承認)的作品都可說是在嘗試醫治「阿克琉斯之踵」。羅友枝(Evelyn Rawski,1939-)的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8)、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1955-)的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分別了處理了滿洲的族群文化與身份問題對帝國身份的影響;而米健華(James A. Millward,1961-)的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1998)與濮德培(Peter C. Perdue,1949-?)的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2005)則以多語言與多層視角,分析了大清帝國的疆界問題。[4]
當然,以上的研究關懷和進路也不限於北美的史學圈子。前文提及莊吉發的《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1977)也在回應類近的疆域問題。撇除與學術無關的「新清史」爭議,「新清史」也有不少地方尚待發展。例如,楊斌認為受「新清史」論述影響的北美與東亞的中國研究學界,無疑都將研究視角集中於中國與內亞的疆界,卻較少關心海疆(如閩廣、台灣)議題,也可說是合理的評價。[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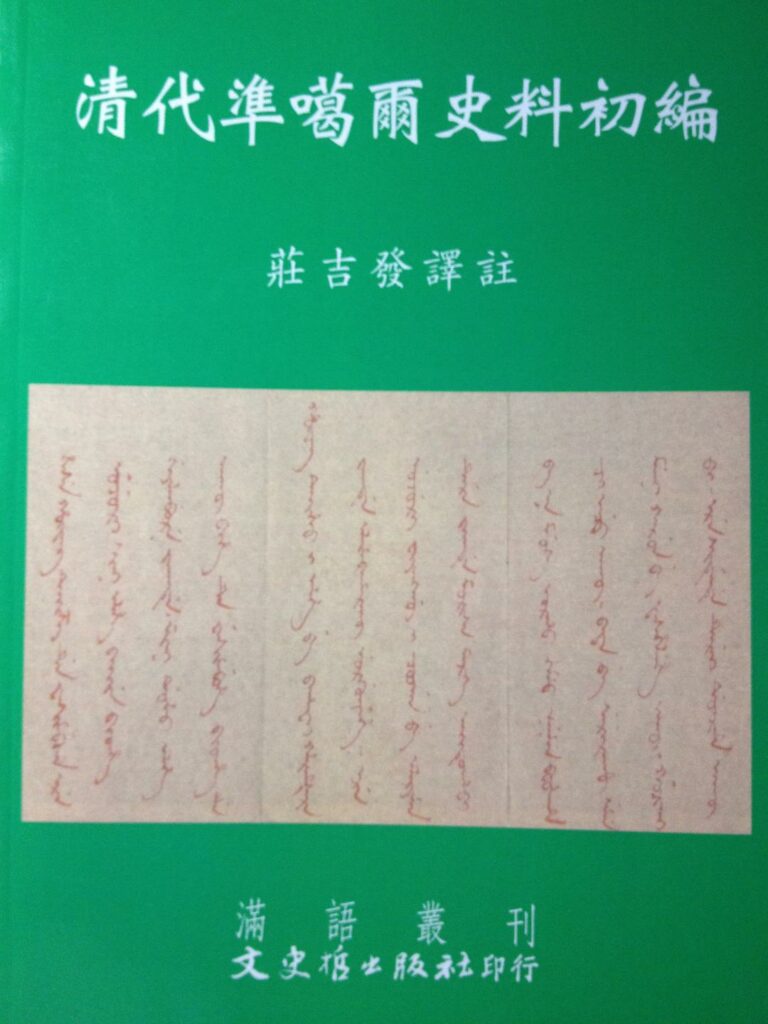
從研究者的學術關懷與問題意識的角度出發,楊斌以內在理路闡釋了北美「新清史」研究範式的起源與侷限,卻沒有提及70年代滿文檔案整理與出版對這一範式的啟動作用。綜合「內因」與「外緣」,滿文檔案的出版之所以促成了「新清史」的出現,還是在於研究者閱讀相關材料時、已怀揣著自身的關懷。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在1970年代研究者有其他關懷,滿文史料又會為學界帶來甚麼呢?」
回到滿文史料開發的起點,有別於莊吉發等學者,岡田英弘在抱有疆界與種族文化關懷的同時,還對滿洲帝王家族的私領域作出盡細的探索。《皇帝的家書》以康熙帝與準噶爾汗國決戰的期間(1690至1696年,此時康熙即將步入中年)與太子胤礽(1674-1725)的書信為基礎史料,關心的自然不只是疆界與族群問題,還有帝王的私人生活。這些討論從信件的行軍生活、飲食瑣事、對家人情感與期待,還原了康熙帝的「非公共生活」(non-public life)。[6]
岡田氏就在這段時間以檔案史料開拓了康熙帝在「非公共領域」的個人情感研究。關於疆界、族群與情感的研究,自然沒有高下之分……
兩個研究方向,開啟史料探索的新可能
自1979年《康煕帝の手紙》出版後,岡田氏針對這一批滿文史料的研究,就集中在兩個範疇。2013年,《康煕帝の手紙》以原書名再版時,新加入的五篇論文也展現了這些思考。首先,循著「非公共生活」思路的討論,岡田氏進一步以滿文史料探討了康熙帝的天文學知識(1981年以日文刊出,頁382-385)、以及他與耶穌會士互動過程(1989年以英文刊出,題為 “Jesuit influence in Emperor K’ang-his’s Manchu letters”,頁370-381),都是根據康熙帝滿文書信的史料進一部考訂而成。
滿文書信的另一種應用,是在原本依賴華文史料而生成歷史論述之外,提供了另一系統的歷史紀錄,以幫助考訂華文史料中的過失、或人為造成的盲點。如原刊於1983年的〈親征蒙古時的聖祖滿文書簡〉一文,就將滿文史料與《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及《聖祖實錄》對比,考訂了文本中互為矛盾的日期問題,以及事件發生的先後問題,可說是典型的文本比對範例。岡田氏在該篇論文最末整理了清準戰爭日程表,可說是現在重讀《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八、九輯時的重要參考材料。(頁308-342)在同類史料考訂、補充論文中,亦有對噶爾丹汗的死亡日期與形式(頁343-357)、格魯派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1635-1723)的生平(頁358-369)、以及開元城位置(頁386-398)等問題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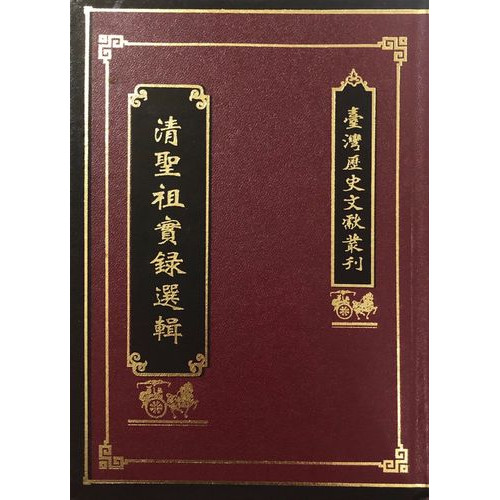
岡田氏的兩個研究方向,後者可說是典型新史料出現及普及後,史家與舊史料比對以反思既有論述的現象;而前者則是類同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史家所關心的「全體史」(histoire totale),亦即史學家的關懷超越傳統「理性」範疇、轉至其他因素與角度,如情感、兒童、家庭等等。值得點出的是,學者多將戰後情感歷史的研究與植根國家檔案的蘭克學派實証史學(histoire positiviste)相對立,但岡田氏對於康熙帝父子關係與感情的討論,也正正建基於70年代台灣與日本學者對大清帝國在台檔案的開發。[7]
當滿、蒙文史料(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後,被稱為「新清史」學派的北美學者,因循費正清、柯文等學者對於「何謂中國?」這一問題的關心,而將新史料應用於疆界與族群問題。這當然不是滿、蒙文史料的唯一應用方式,岡田氏就在這段時間以檔案史料開拓了康熙帝在「非公共領域」的個人情感研究。關於疆界、族群與情感的研究,自然沒有高下之分,但正如王汎森對讀者的提醒:20世紀史學中「人的力量」逐漸被「非個人歷史力量」(impersonal force)(如結構(structure)、系統(system)、模型(model))所取代。在以「新清史」學者主導滿文史料研究的20世紀,岡田氏閱讀康熙帝書信時呈現出的關懷,無疑開啟了詮釋與探索的另一種可能性。[8]
滿洲官員對穆斯林的態度與漢人官員的態度會有不同嗎?族群身份對接納或拒斥異教的決定有影響嗎?這些過往幾乎不能回答的問題,有機會可以從上述滿文與漢文夾雜的檔案中得到進一步分析。
當下的詮釋方法永遠不是唯一的路徑
黎志添在介紹宗教經典的詮釋方法時就曾提到,詮釋宗教經典是由「讀者」、「經典作品的結構」(即利科(Jean Paul Gustave Ricœur,1913-2005)所說的「論述形態」(modes of discourses),包括文類、風格、體裁、結構及組織等等)及「經典的意義世界」三者構成的、「一個複雜但具創造性的詮釋循環和事件」。[9] 同樣地,滿文檔案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亦自然視乎讀者/史學家的學術背景、個人關懷,乃至當下的非學術考量等因素,因此也具備很多可能性。

以筆者為例——筆者在東亞史的主要研究範疇,圍繞著近世官僚如何應對諸宗教共存的問題,因此也對官僚體制的能力與侷限多有留心。在康熙帝與兒子的書信往來之中,筆者可以感受到君主對某些事物尤其感到「驚訝」,並會專門記下、傳予在北京的兒子閱讀,更要求兒子傳閱給其他家人或高級官員。站在由大明帝國承繼的中國官僚體系的最頂層,康熙帝理論上具有接收所有資訊的權限,因而往往被假定能掌握治下領土的大部分知識。然而,從康熙帝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官僚體系明顯無法將所有知識帶給皇帝。
舉例而言,第二次親征時,康熙帝在書信中多次提及當地水草的肥美程度、動物的數量等等遊牧的知識,並假定在北京的太子和皇室成員無法知悉;行文中也反映出他「驚訝」於某地動物數量的多寡。我們大抵可以推斷,這一類型的資訊不會在漢人官僚、或蒙古人官員日常上報的傳訊渠道中有所提及。(頁181-225)如果說動物數量不為官僚體系所掌握仍在情理之內,那麼當皇帝對於大同到寧夏驛站數目是否充足、在領在行軍、寄信需要的時間多寡、地方最高官員身體狀況和樣貌都不甚了然,就足以提醒我們:不能將具量化管理能力(quantitative management)的現代化政府與近世的帝國相比。(頁235-253)如果能夠系統整理滿文的帝王私人書信,其中所反映的「知」與「未知」,相信能協助我們對官僚體系收集與發布資訊的能力有更深入的暸解。
除了岡田氏介紹的康熙帝書信,筆者在過去研究中,亦發現滿文檔案在宗教史的研究中可以具有重要的地位。五年前,筆者開始致力於整理大清帝國官方史料中有關穆斯林的記載,為有興趣從事東亞伊斯蘭教研究的學者提供更多有用材料。目前已完成1800年前漢文《清實錄》的紀錄,下一步準備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文本。在收集過程中,筆者發現內閣大庫檔案的文獻不時出現滿文與漢文夾雜的情況。在過去大清帝國伊斯蘭史的論述當中,一直隱然有「政府」/「中國」與「穆斯林」/「回民」對立的二元框架。
我們目前主要從70年代以來滿、蒙文檔案的發掘與應用中,認識大清帝國政府的多樣意見;那麼滿洲官員對穆斯林的態度與漢人官員的態度會有不同嗎?族群身份對接納或拒斥異教的決定有影響嗎?這些過往幾乎不能回答的問題,有機會可以從上述滿文與漢文夾雜的檔案中得到進一步分析。上述簡單的、不成熟的案例,旨在說明滿文檔案與史料的多種可能性。《皇帝的家書》就如「如果電話亭」一樣,提醒了讀者:當下的詮釋方法永遠不是唯一的路徑。如果今天有抱著不同關懷的史家,用時光機/Tardis回到1970年代與岡田氏一同開發滿文檔案,現在我們就會在平行宇宙裡、站在另一個巨人的肩膊上,遠眺史學前路。
(本文原題為《族群、疆界、非公共生活與其他:滿文檔案與史料的可能性》,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1] 參藤子・F・不二雄:〈もしもボックス〉[如果電話亭],《ドラえもん》[叮噹/多啦A夢],《小学四年生》[小學四年生],1976年,1月號;Doctor Who, “Turn Left,” Doctor Who Series 4, Episode 11, 50 mins, 21st June, 2008, BBC One。
[2]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卷24,期2,2006年,頁1-18;莊吉發:《清代準噶爾史料初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3),頁1-2。
[3] 有關「新清史」的簡介、討論與爭議,參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2004 (88), 193-206;黨為:《美國新清史三十年:拒絕漢中心的中國史觀的興起與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頁1-18;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劉文鵬:〈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歷史研究》,期4,2016年,頁144-159、192。
[4] 楊斌著;韓翔中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新北:八旗文化,2021),頁19-27;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Calif.;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楊斌著;韓翔中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頁25-26;值得提出的是,楊斌Laura Hostetler 以「內部殖民」的觀點分析大清帝國對西南邊疆族群的理解與治理,但重心在於帝國的殖民者的知識建構而非西南部自身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這類使用「重非公共生活」而非「私人生活」(private life)的原因在於康熙帝的書信同時涉及了個人情感與家人關係,但這些情感同時與帝國的政治糾纏一起,筆者難以將這些書寫理解為純粹的「私人生活」。然而,本書上述所介紹的情感,卻與帝國政治的公共討論無直接關係,故稱之為「非公共生活」。
[7] 王晴佳:〈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蔣竹山:《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9),頁57-69。
[8]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7),頁353-391。
[9] 黎志添:《宗教研究與詮釋學-宗教學建立的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3),頁37-59。
延伸閱讀:

蕭公權:二千餘年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起伏轉變

蕭公權: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是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二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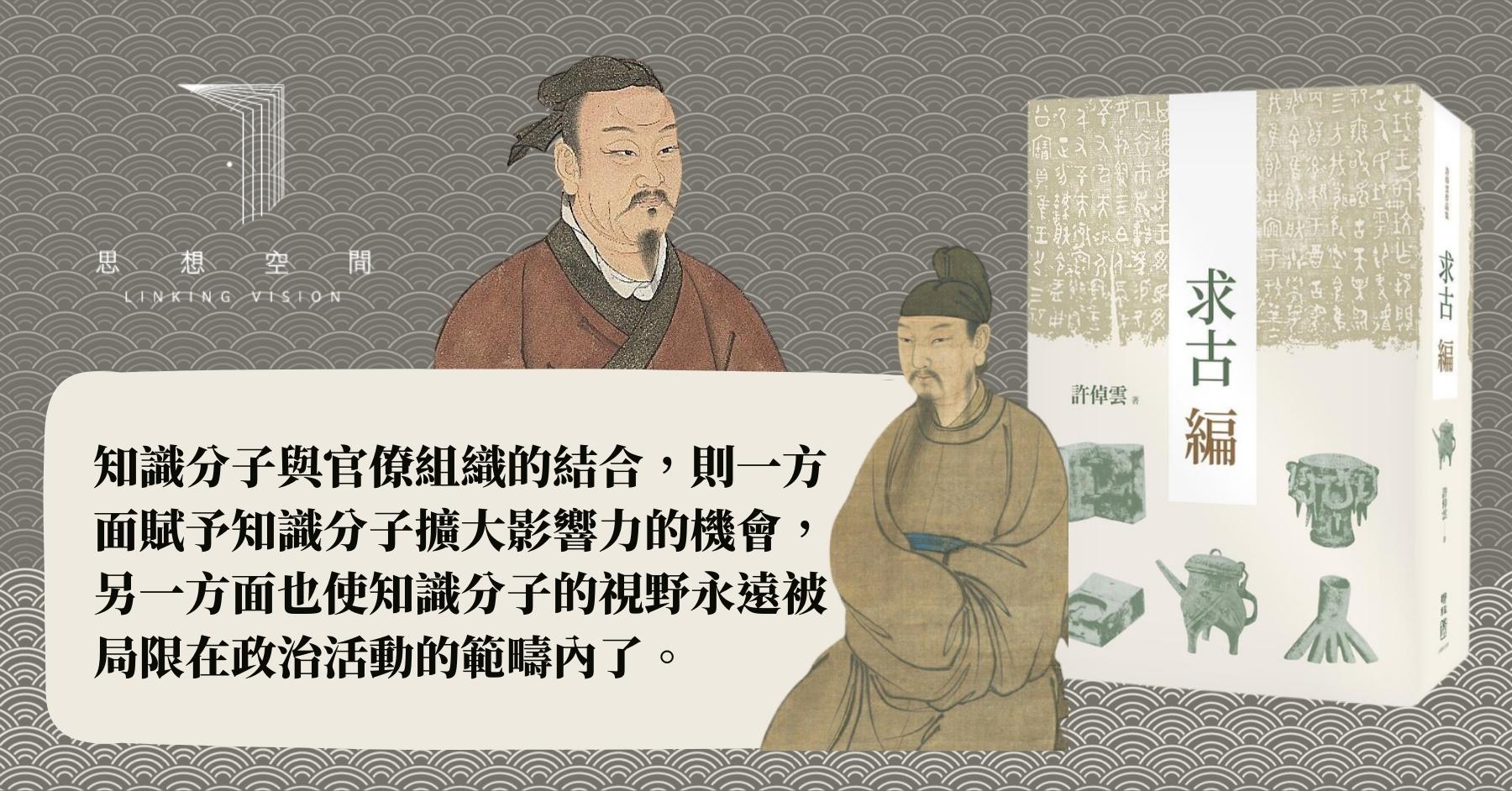
許倬雲:權威、理想、反抗、隱逸?漢代知識分子圖鑑

香港人,1991年出生,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大學中國研究博士。現任費薩爾國王學術及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訪問學人於中央研究院,並參與歐洲、海灣地區及東亞不同學術會議。現職沙特阿拉伯王國費薩爾國王學術與伊斯蘭研究中心研究員及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自17世紀以來東亞少數群體的研究,尤集中於小眾的宗教團體與政府及與主流社會的關係,主要包括中國的穆斯林及基督徒與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群。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