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上海,文學系出身,香港媒體人,關注兩岸三地政治、社會與文化研究,相信文字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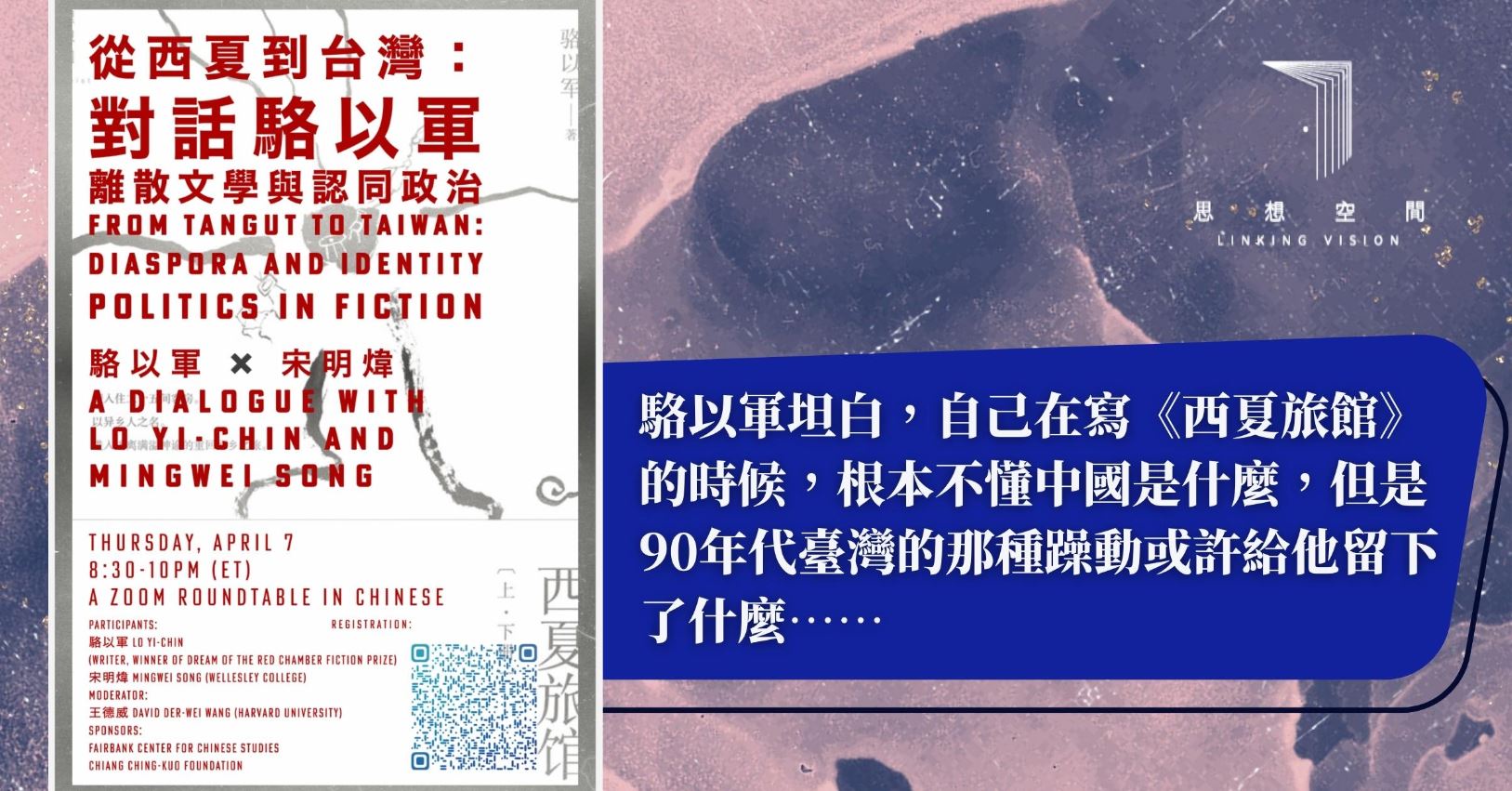
記錄/袁瑋婧
編按:2022年4月7日,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辦講座《從西夏到台灣:駱以軍談離散文學與認同政治》,由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擔任主持,邀請了美國威爾斯利學院東亞系副教授宋明煒與臺灣作家駱以軍展開對話。講座從駱以軍著作《西夏旅館》展開,並談及其小說創作中的離散與身分認同。
| 講者簡介 |
駱以軍,臺灣作家,1967年生,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編過年度小說選,常任各大文學獎評審。曾獲第五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首獎、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等。著作有《匡超人》、《小兒子》、《棄的故事》、《西夏旅館》、《遣悲懷》等。
宋明煒,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文化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文學,科幻小說。著有《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少年中國:青春文化與成長小說》等。
《西夏旅館》是駱以軍在2008年出版的長篇鉅著,一方面呈現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的最後逃亡史,另一方面以現代旅館為書寫的立身之所,在不斷造夢和洗夢的過程中,講述關於創傷與救贖、離散與追尋的故事,隱喻著臺灣外省第二代的命運與身分認同。
為什麼身在臺灣的駱以軍,會想到寫西夏這樣一個神秘、遙遠、不存在的國度?講座就從這個故事誕生的起源開始。

阿城一口咬定,駱以軍根本不是個漢人,而是一個胡人,是突厥混了一些中亞的血統。
《西夏旅館》的誕生起源
有一年,大陸的作家阿城來臺灣,阿城說自己當年在雲南流放時看過很多人,一看人的長相就知道你祖先的由來。那是阿城第一次見到駱以軍,看到他的臉,就說他在陝北的一個村子,每個人的臉都跟駱以軍一模一樣。阿城一口咬定,駱以軍根本不是個漢人,而是一個胡人,是突厥混了一些中亞的血統。
後來駱以軍有一次去寧夏旅遊,他在那裡看到李元昊的陵墓群,有個羅漢臉上帶著水漬,彷彿在流眼淚。在那個瞬間,他彷彿被西夏這個神秘的國度電到了。
那時他才大概30歲,還沒寫過長篇小說,對自己未來要寫的長篇小說懷抱著構建宏達世界的勁頭。
西夏是公元11至13世紀,中國西北方由一個叫党項羌的民族建立的政權,駱以軍說,以現在的話來說李元昊就是一個「西夏獨」,積極效仿宋朝方方面面,文字亦借鑑漢字,這些歷史文化當時震撼了他。
駱以軍本來想效仿《東京夢華錄》或《哈扎爾辭典》,全部虛構偽造一個世界,蓋一座東京夢華錄那樣過去時光的廢墟,後來在生了一場憂鬱症後,轉變心意。
在翻查資料中,他更確信自己跟西夏的緣分。他說,蒙古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時候,死於首都党項城那一戰,所以蒙古人在打下西夏之後大屠殺,這個民族整個滅絕了。可是據傳有一隻神秘飄忽的西夏部隊逃了出來。一直到了明末,還有一個安徽人寫了一本書,寫到他父祖那一輩,一些流離失所的西夏遺族男子移到山東、河南、安徽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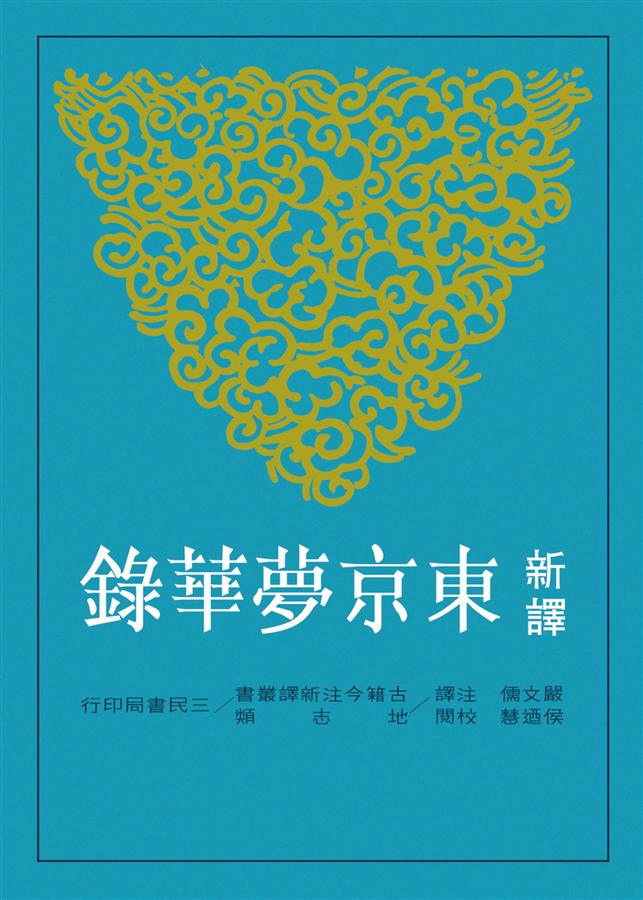

駱以軍覺得這很像當年國民黨被解放軍打到遊走臺灣,建立眷村。書中對這些男子的描寫,跟臺灣小時候記憶裡的父親及他的結拜兄弟們的印象非常相像。那本書裡寫到,這些西夏人非常高大,非常質樸重義,也娶不到漢人女子,因為他們是外來者,這都跟當時國民黨老兵非常相像,所以最後他們會互相送終,一旦有人過世,這些高大的男子都會嚎啕大哭。這和駱以軍從小聽父親講的南京老家的祖輩們也很像,他們都很高大,重情重義,「我後來就越看越覺得自己一定是最後一個西夏人,就寫了這本小說。」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可能他也沒辦法變成一個小說家,這種戰爭的體驗太恐怖了。這個弦的暴力震動,從一百年前持續到國共戰爭……
祖父輩的逃亡與離散
宋明煒認為,從《西夏旅館》開始,駱以軍的多部作品都在通過文本的方式回到過去,像《女兒》在對應《紅樓夢》和張愛玲的作品,《匡超人》是對應《儒林外史》,像是一種文本寄居的方式,其中又指涉多部文學作品,即將自己的寫作置於一個複雜的文本對話之中。
駱以軍講到,自己最近看了一個印度智者演講的視頻,他開口第一句話說:所有人的存在都是一個弦,是一個膜的振動,可能有千萬個多重宇宙在繁殖。這個印度人說,祖先就活在我們裏面,我們弦在共振的時候,裡面必然有一個很大的雜音。
駱以軍就想到,為什麼自己寫《西夏旅館》和之後的長篇小說時,要找到那個依傍和游離/背反。其實這個內在的磁場,非常混亂,又很尖銳。同時又很笨重,很像一百年的感覺。不管是跑到臺灣來的外省人,或者是臺灣本省人,這過去的100年,用波拉尼奧的講法是400年,這一切的故事是從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始,然後帝國主義開始侵略。
「這一百年混亂的感覺,裝進我父親的大腦,而我父親只是1949年時100萬人之一,」駱以軍說,「他當時所經受的恐懼,其實像現在烏克蘭300、400萬跑到波蘭、保加利亞的這些難民,幾乎就等於昨天才發生,淮海戰役時100萬共軍殲滅80萬國軍,身邊的人死亡,或流離失所。」駱以軍讀了父親的日記,當時他逃到了定海(位於浙江舟山),大批部隊都散亂了,他們都在等船。
駱以軍說,自從自己有記憶以來,父親都在講述逃亡的故事。後來到了學校,但凡遇到外省佬,他們也講述同樣九死一生的逃亡。後來他意識到,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可能他也沒辦法變成一個小說家,這種戰爭的體驗太恐怖了。這個弦的暴力震動,從一百年前持續到國共戰爭,父親也總是對駱以軍講述祖輩在南京老家的故事。到了他20歲開始讀西方小說的時候,祖先的故事和西方小說故事裂開成為兩個局域,變成兩個裂腦。
在臺灣,這種缺了「左腦」的創作者,長出像七等生這種小說家,缺了「右腦」的創作者,在臺灣長出了陳映真。
90年代臺灣文學繁華夢
在80、90年代的臺灣,青年開始閱讀川端康城、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卡奎斯、卡夫卡等等這些《新潮文庫》。駱以軍認為,大約在90年代初一直到上世紀末結束,臺北的現代小說力量呈現一種躁狂的創作力,充滿嘉年華歡會上濃郁的酒精。
當時身為一個小說學徒的駱以軍,沈浸在這濃郁的氣味之中,有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有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有王安憶的《小城之戀》、《長恨歌》,有韓少功、蘇童、余華、賈平凹⋯⋯而臺北也有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也有馬華的李永平,在他的心中成為臺灣和大陸兩隻小說隊伍,就像49年後硬生生切開的左腦和右腦。但是在臺灣,這種缺了「左腦」的創作者,長出像七等生這種小說家,缺了「右腦」的創作者,在臺灣長出了陳映真。


對90年代的文青來說,還有彷彿昨日還是禁書的魯迅、沈從文、老舍,駱以軍認為,他們像是現代主義小說語言的萬讀之綱。不僅僅是對於他而言,這樣的情況其實從五四以後就一直在發生,分左右兩邊各自殘缺的腦,一直產生對於古老中國的基因段,這些基因段產生躁動和疾病的隱喻,煮在一個大鍋裡,變成萬讀之綱,滋養了一代的小說家。
不論去依附西夏的歷史,還是依附明朝、《紅樓夢》、《儒林外史》,駱以軍形容這很像《牡丹亭》,就如同杜麗娘做了一個春夢愛上了一個夢中人,然後留下夢中男子的畫像,像是留給未來人的密碼。
駱以軍坦白,自己在寫《西夏旅館》的時候,根本不懂中國是什麼,但是90年代的臺灣的那種躁動或許給他留下了什麼,也許他就如同杜麗娘,先留下了那一張寫真。而他很多的感受,到後來的《匡超人》、《明朝》才慢慢填補了上去。


從在《西夏旅館》裡寫的「脫漢入胡」,到《匡超人》裡寫到西遊的概念,都有發生「脫華」和移動。但這不代表他本人的身分認同因年紀發生多劇烈的變化,而是觀測法不同時期的結果。
量子力學、波粒二象性與身分政治
宋明煒認為,駱以軍的小說裡離散的感覺非常強大,這些祖父輩逃亡的回憶貫穿在幾部小說裡,駱以軍不斷地回到那個時刻,那個時刻像一個黑洞,就像《匡超人》裡寫到的「洞」,都有歷史的指向。在《西夏旅館》裡,又隱含了很多對臺灣政治的描寫,在當時的歷史背景裡,隱含了陳水扁槍擊案,也提到蔣經國,有非常實指的一面。但小說的敘述又像一個夢境,裡面的人物撲朔迷離。
宋明煒提到書中最神秘的人物圖尼克,他把自己認同為最後的党項人,給自己編織神話;書中祖父和父親相遇,身分發生重疊,小說中的「我」和圖尼克亦發生很多身分的變化。書中還寫道一句話:「我」只是一個龐大信息海洋里,某一極短暫之時間截點。這句話彷彿回過頭看身分這樣東西,它變成了一個液態的、模糊的,可以時常、永遠處於流動之中。這是駱以軍小說中蘊含的身分政治。
駱以軍表示,從在《西夏旅館》裡寫的「脫漢入胡」,到《匡超人》裡寫到西遊的概念,都有發生「脫華」和移動。但這不代表他本人的身分認同因年紀發生多劇烈的變化,而是觀測法不同時期的結果。
駱以軍形容自己寫《西夏旅館》時是帶著情緒化的小孩子氣,「我覺得當初在寫脱漢入胡時有一種負氣,因為當時臺灣2008年前有一種粗暴的驅逐外省人的傾向,當時我在和太太結婚的過程中,發現他們澎湖家庭的婚禮非常嚴格按照古禮傳統,我就覺得你們本省人才是真正完整古老漢族傳承,而我是胡人,是我要脫漢入胡。」
而他的父輩經歷過五四,在上世紀20年代就經歷過對自己身體裡的古漢或古中國人命運的否決和摧毀。我們後來接收到的西方文學,都是30年代的人翻譯引入,包括大陸走到共產主義,其實都是胡人(西方)的東西。「我就覺得其實早被去中國化的人是我,你們才是中國人。你們生活裡的所有細節、信仰、祭祀,都是中國的。」
而在書寫《女兒》的時候,駱以軍閱讀了大量關於量子力學的入門書,但最影響他處理敘事結構的是波粒二象性。量子力學永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你永遠不可能既看見粒子長什麼樣子,又掌握它處於宇宙時空中的某一個動態位置。
駱以軍認為,像《儒林外史》和《海上花》,或者卡爾維諾的小說,就寫出了後者的這個狀態。裡面沒有一個面孔是清晰的,可是他有一個能力造景,把所有的人物狀態散放出去。而《儒林外史》可以全景呈現明代中葉文人之間的那一套虛以委蛇和繁雜的關係網絡,這就是波函數的概念。
駱以軍覺得,能同時做到波粒二象性的就是《紅樓夢》還有波拉尼奧的《2666》,既做到粒子態的微觀,最後又形成一個波函數全景動態的跳躍。
宋明煒指出,波函二象性和量子力學的比喻成為了對身分政治的一個破解,在這個情況下,過度強調身分政治,可能會帶來極端性表達。
駱以軍坦言,旅館是他沒有辦法不去蓋的空間。他也想寫出自己的一個大院,不是紅樓夢也不是大觀園,可是曾是一個女系家族裡最好的心靈,她們各自在做著什麼,也各自變化。
旅館空間的塑造與女性情感教育
談到《西夏旅館》所營造的旅館這個空間的結構時,駱以軍講述年輕時的自己讀到井上靖的《冰壁》、川端康成的《千羽鶴》,裡面所描述的不倫對於二十歲的他來講都帶來相當激烈的閱讀美感,給他帶來極大的震撼,駱以軍形容,他們筆下這些女人很像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女性降生在戰後的日本,某種心靈廢墟劇場,女人被懸吊在一個絕美的,卻又是像火燒女巫的刑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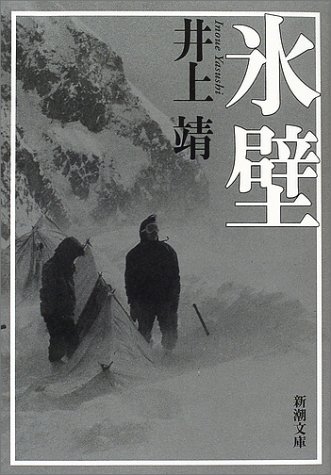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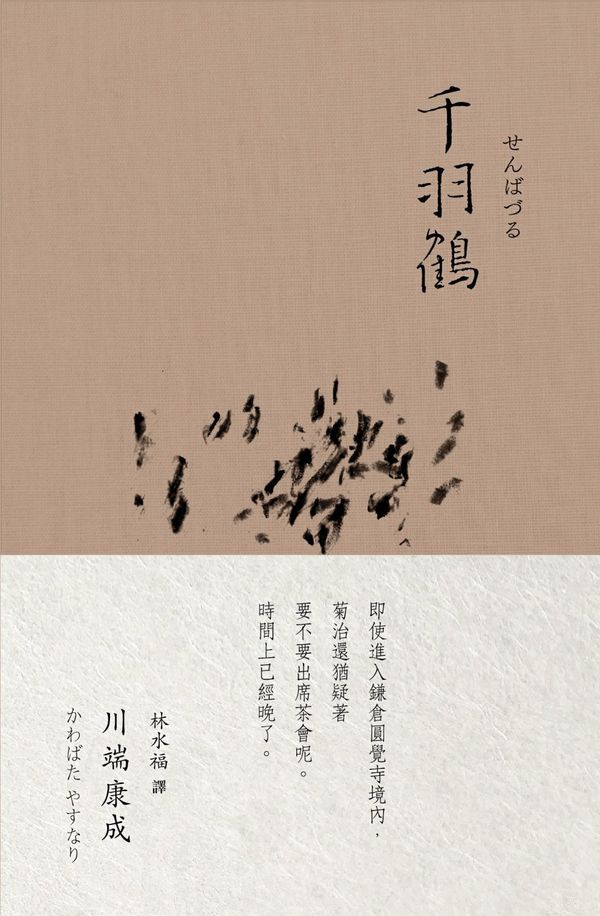
「她們的美以及病態、不幸,像對第一批從東亞男性秩序中,沒有潛力可循的精神孱弱男子,在靈魂上面對的原子彈。」駱以軍談到,這些小說帶來情感教育,但裡面還有一些東西需要更大的劇場才能以展開,所謂「人類感」的高貴,再多一點可能是恐怖與哀鳴,再多一點可能是無法無視窮人的痛苦,再多一點可能是每一種感覺的科學意義的投影。可是他後來發覺,不是這樣,不管在大陸還是臺灣,完整的愛的學習並沒有建立起來,「因為這個系統只花了一百年,如同是紙糊的,這一百年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暴力侵襲,摧毀了這個臨時系統」。
駱以軍坦言,旅館是他沒有辦法不去蓋的空間。他也想寫出自己的一個大院,不是紅樓夢也不是大觀園,可是曾是一個女系家族裡最好的心靈,她們各自在做著什麼,也各自變化。可是他感受到,這是不可能的。
最後,駱以軍也預告了自己將在今年6月底出版的最新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小說講述在瘟疫之下,臺灣最後倖存十個人躲進一個溪谷,像十日談一樣每天講故事,直到最後他們才發現自己並非最後倖存的十個人類,而是十個病毒。顯然,在這部最新的作品裡,最終也模糊了人和病毒的身分,呈現出身分的一種流動性。
延伸閱讀: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