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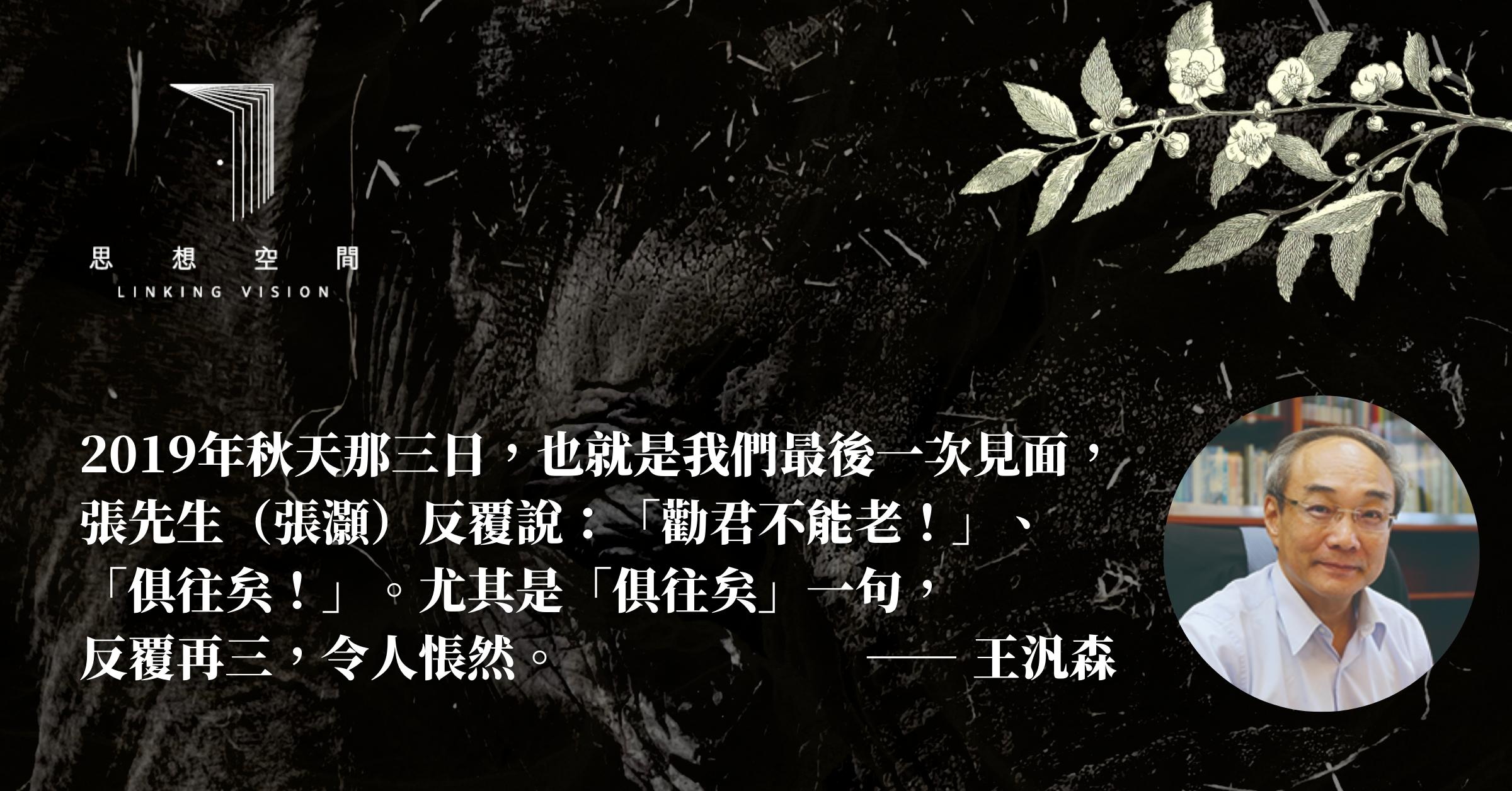
文/王汎森(歷史學家)
編按:著名歷史學家張灝先生近日在美國舊金山離世,享年86歲。張灝專長中國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著作頗豐,亦在海內外獲得許多榮譽。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收到訃告後深感驚訝,亦撰文悼念,一方面回憶兩人間的交往趣事,此外也與我們一道回溯張先生的學術生涯和人生經歷。
四月廿二日上班途中,突然收到余師母從美國打來的電話,我倉促接起,師母說:「張先生過去了。」因為車子剛開進隧道,有點慌亂,我忙問:「哪位張先生?」我之所以沒有馬上想到是張灝先生,主要是因為今年二月在國家圖書館線上捐書典禮中看到張先生時,覺得他的狀況還不錯,所以完全沒想到兩個月後,張先生便故去了。
過去兩年多,我經常想起《聖經》〈啟示錄〉中的「天啓四騎士」,他們總是聯手而來: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新冠病毒、烏俄戰爭、疫區封禁的飢饉,還有死亡。余英時老師、張灝先生的故逝,都來得令人驚愕萬分。因為疫情,我與他們兩位久不通問,然後某天醒來突然發現死亡騎士的身影居然悄悄出現在他們身邊。
張先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大師,他的著作具在,大家可以參看。倉促之間,我只能在此先談談我與張先生的幾次會遇。
我感覺張先生早期關心梁啟超及近代中國文明的過渡等問題,而在這個階段,則相當關心歷史人物的生命氣質、生命意義、存在感受以及社會秩序的問題。
(一)
仔細回想,我初見張灝先生正好是四十年前,也就是在1982年夏天,我尾隨中國時報棲蘭山莊會議的成員一路從台北台大會館附近坐車到宜蘭棲蘭山莊。記得遊覽車在北海公路上行駛,然後在一處風景點停泊休息,我聽到余英時老師盛讚這條公路的美,一如加州的卡邁爾公路(所以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一遊卡邁爾公路)。當人們紛紛從洗手間出來時,我主動上前向張灝先生請教了一個問題,當時年方四十五歲的張先生侃侃而談。我記得余先生開玩笑地說:「張灝又在吹牛了!」然後兩人相視大笑。
在整整四十年的時間中,張先生與我同在一地的機會很少,但是值得寫的東西應該很多,現在因為時間及手頭材料不齊,只能先寫幾件個人印象深刻的事。
張先生很少寫信,可是在我們初識幾年中,我好像收到過他幾封信。第一封信,大約是在1983年春他回我的信,詳細內容我不記得了,其中有一段是希望我精讀Max Weber的幾本書,記憶最深的是《宗教社會學》,張先生信末用了讀完上述諸書後「自然入港」四個字。
當時台灣刮起一陣韋伯熱,許多韋伯的英譯都有盜印本,而我在這股熱潮中如饑似渴地讀了所有能到手的韋伯著作,但《宗教社會學》(英文本)卻是陌生的。所以,我曾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軍官宿舍,每天晚上就著一盞黃燈閱讀《宗教社會學》。對我而言,這本書相當晦澀困難,將近一百天才看完。如今,書中的論點大多不復記憶了。
另一封信大概是在1985年,我將新出版的《章太炎思想》寄請張先生指正。想不到,張先生居然來了一封信祝賀。張先生非常大度,在他第二本英文書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一書中,曾多次引用《章太炎思想》一書的論點,使我受寵若驚。
在棲蘭山莊之會後的幾年間,張先生好像一直被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這本書稿牢牢糾纏住,拖了七、八年,遲遲未能完稿付印。張夫人警告他,如果不將這本書作一個了斷,將要如何如何!
我感覺張先生早期關心梁啟超及近代中國文明的過渡等問題,而在這個階段,則相當關心歷史人物的生命氣質、生命意義、存在感受以及社會秩序的問題。我記得張先生告訴我,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一書的副標,原來是想用beyond wealth and power,表示他不認為近代中國的轉型一切都是在追求「富」與「強」——這是史華慈成名作《嚴復》一書的英文標題: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同時也有生命意義,存在感受方面的激烈衝突。不過後來張先生還是把副標題換成了「尋求意義與秩序」。
生命的存在與意義關懷除了表現在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之外,也表現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一書,並有一部份擴散到「幽黯意識與民主傳統」的討論,「幽黯意識」一文首次發表便是在1982年棲蘭山莊那次會議中。
張先生是位沒有架子的人。我回國後在史語所工作時,張先生每次來台參加院士會議時,總會設法到我的研究室坐坐,看看我正在讀什麼書,並隨便聊幾句。
(二)
1987年,我到美國讀書。在美國留學期間,因為課程非常緊湊,所以我只在1991年第一次到美國中西部。翻查當時殘留的一個筆記本,我是在那年六月二日坐灰狗巴士(也是唯一一次)到匹茲堡先拜訪許倬雲先生及老友葉匡時,接著丘為君駕車載我到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Columbus)。晚上九時出發,十二點才到。如今,我還清楚記得車子奔馳於平坦且一望無際的中西部公路上的情景。張先生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三十年,這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在哥倫布市的家。
那一次拜訪,我們匆匆談了我的博士論文。張先生西方思想史的造詣非常深厚,我們的談論很快集中在實證主義對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影響,以及它如何改變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維的問題。
在這一次短暫拜訪張宅的過程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房子的壁紙是淡藍色的,還有玻璃屋式的大書房;匆匆一瞥,最顯眼的是一大套用舊了的四部叢刊。我記得張先生當天在一個餐廳設宴招待,席中他還說過「泡麵的味道真是過癮啊!」多年後,我在台北一個餐宴中引用這句話時,女主人相當不快地說:「王汎森,我請你吃這麼豐盛的菜,你居然大說泡麵。」
張先生是位沒有架子的人。我回國後在史語所工作時,張先生每次來台參加院士會議時,總會設法到我的研究室坐坐,看看我正在讀什麼書,並隨便聊幾句。
1999年,我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一個學期,由於張先生當時也正在香港科大任教,所以我們在香港清水灣曾經有兩、三次盤桓。談話中,我覺得張先生當時的學術關懷主要是「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當時張先生因為心臟手術,所以只能吃無油無鹽極為無味的食物。由於來往交通費時,所以每次總是來去匆匆。印象中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談及近代激烈思想的線索,張先生一再指出譚嗣同、李大釗這一思路的關鍵性。二是張先生希望與我合寫「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另外還有一件趣事。有一次晚飯之後,張先生突然表示,聽說你學過跆拳道,能否演示一下,我當即在他客廳踢了一陣。張先生很快便抓住重點:「你慣使右腳!」
詩人里爾克說:我與我的身體有神秘的契約,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神秘的契約可以維持多久。張先生的驟逝,令人「大悲無言」,思之慘澹不已。
(三)
2019年8月28日,張灝夫人病逝,我與內人決定趁去美國開會時,前往Reston探望張先生。當年9月23日傍晚,我們終於從普林斯頓一路摸到Reston。這也是與張先生最後一次的長談。從9月24、25日,我們都是早上十一點多去張府,然後一直談到吃完晚飯才離開,中間(24日)還在傍晚時一起去了Lake Ann遊逛多時。
這次談論,主要是張先生的人生經歷,尤其是張先生早年求學時期的趣事,以及張先生藏書將來的歸宿,此外還有三點:一、他說,他們一家是1949年到台灣,在台灣讀書十年,1959年到美國讀書,然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三十年,退休後到香港科技大學擔任八年講座教授,從香港回到美國之後,在Reston待了十四年。二、張先生說他到美國讀書之後,醉心於理論,到處聽課,深受Robert Bellah影響。他特別提到Robert Bellah是他當時求知的一個線索。在哈佛,他深受那一代活躍的幾位學者影響:Parsons、Robert Bellah、Shmuel Eisenstadt、Clifford Geertz(經Robert Bellah介紹)。張先生說,他的導師史華慈對他到處聽課有贊同也有保留。余先生曾經告訴我,張灝先生學生時代總是往哈佛的威廉詹姆斯大樓(社會科學)跑,有一次他問張先生,「你幹嘛老往那裡鑽?」張先生回答說:「這個我不管了!」三、在這一次談話中還提及他的父親張慶楨教授/立法委員。張先生說,他父親是芝加哥的西北大學法學博士。由於在學時間太短,所以他們心中對此常有懷疑。有一年,張先生與姊姊一起給西北大學寫信,要求確認父親的學位,張先生非常逗趣地告訴我,沒想到答覆是確定的。
除了上述之外,我們當然還談到許多往事,還有一、兩個學術問題,尤其是我多年來一直在試著梳理「清代統治的不安定層」的問題。這一次談論,雖然沒有得到確切的結論,但張先生也發表了一番意見。
張先生是殷海光的得意門生,但為人卻很有古意。張先生是名父之子,自幼生活優渥,父親對獨子寄望特深,所以經常帶他到處向長輩請教,其中包括程滄波。程滄波負文名,當時請教的範圍主要是古文,所以張先生能背古文,而且古文已經化成他血肉的一部分,日常談話之間,「爾公爾侯」之類的句子經常脫口而出。有時又雜以武俠小說中的「拳法亂了」之類的話。
張先生認為人與人交往,最好的境界是「相視一笑,莫逆於心」。所以不為時空所限,也不必拘泥於繁文縟節。在過去四十年中,我個人深受張先生的支持與照拂,到了不知如何言謝的地步。有幾年,我受困於某種病苦。張先生非常注意此事,在院士會議期間,急著找相關院士請教藥方,其情其景,如今仍然歷歷在目。
張先生欣賞的生命氣質是方重而帶有矯矯之氣。他幾度告訴我,他不喜歡秀麗的書風,偏愛方、硬,帶有碑味的書法,這其實也反映在他寫的硬筆字上。張先生連感嘆都有古典味。2019年秋天那三日,也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張先生反覆說:「勸君不能老!」「俱往矣!」尤其是「俱往矣」一句,反覆再三,令人悵然。詩人里爾克說:我與我的身體有神秘的契約,可是沒有人知道這個神秘的契約可以維持多久。張先生的驟逝,令人「大悲無言」,思之慘澹不已。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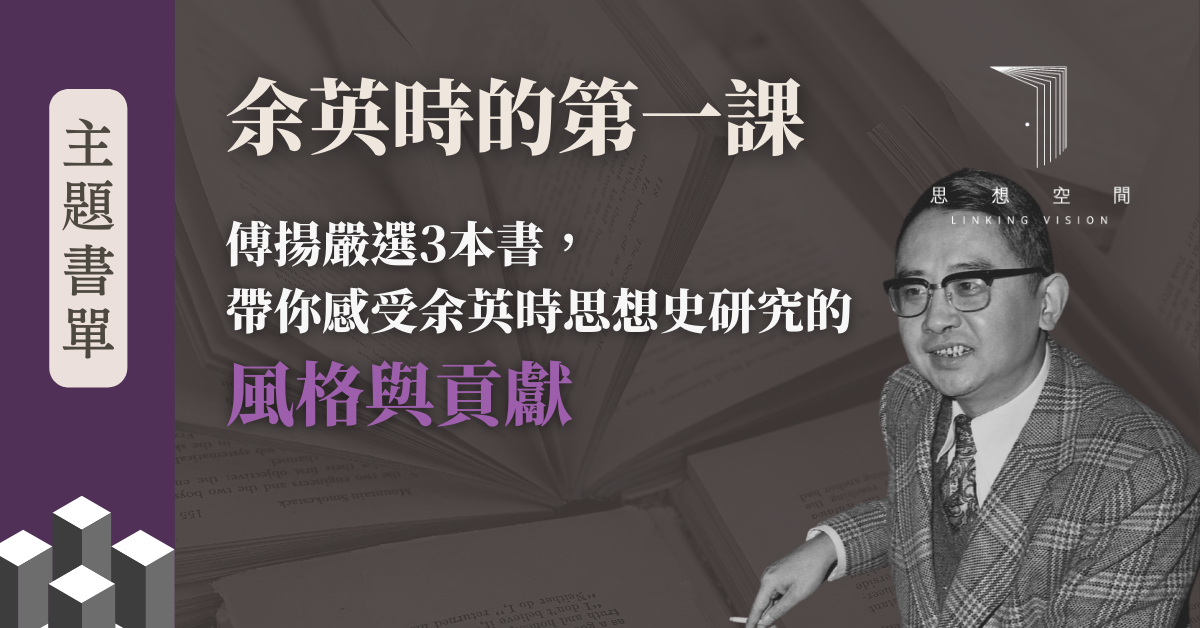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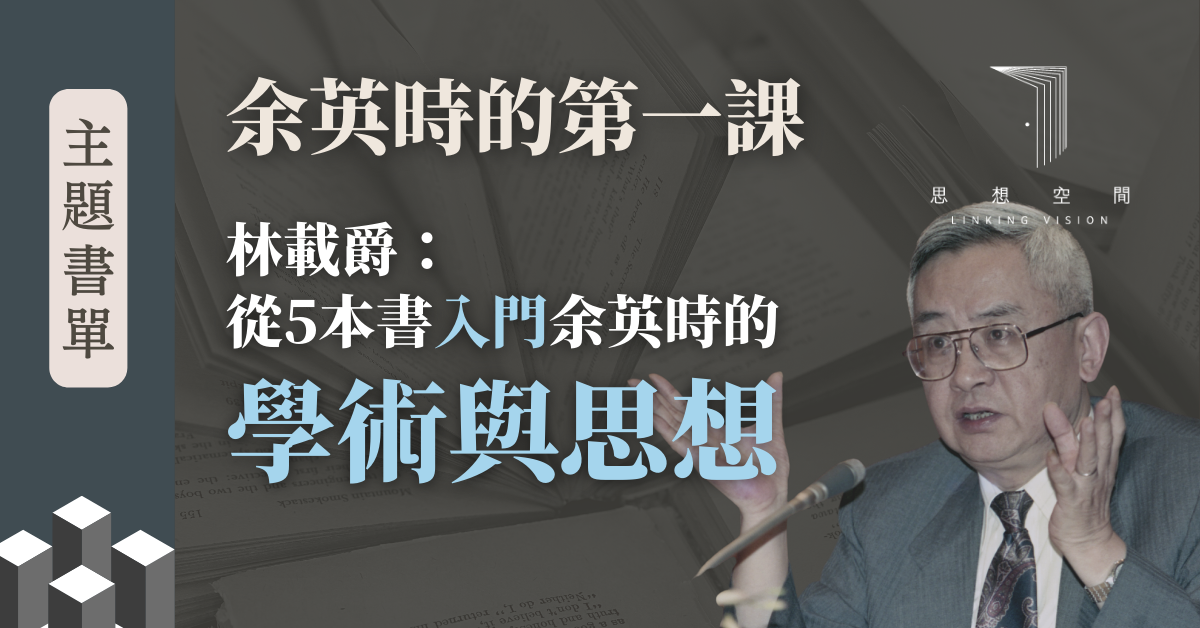

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書。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