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傑克
譯/彭依仁
編按:烏克蘭土地上仍然戰火綿延,戰爭發生至今,有不少畫面依然令人深刻。曾有一位烏克蘭老婦人,面對俄羅斯士兵時,將一把向日葵種籽塞進士兵的口袋中,並說:「當你們都死在這裡的時候,至少烏克蘭土地上還能長出向日葵來。」2022年2月26日,哲學家Michael Marder在「哲學沙龍」平台(The Philosophical Salon)發表文章談論這一幀畫面;其後,紀傑克(Slavoj Žižek)再撰文回應,用流行文化切入,討論混亂年代全球自由資本主義秩序的危機。
邁可.馬德(Michael Marder)在哲學沙龍發表了一篇妙絕的文字,是關於一位烏克蘭婦人將向日葵種籽拿給一位俄軍士兵的。我把這篇文字形容為妙絕,是因為它做了今日最需要做的事,就是為我們對今日烏克蘭災難的反應,加上更深刻的哲學維度。這起事件令我想起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瑪波小姐系列》的《黑麥滿口袋》,故事中一位名叫雷克斯.福蒂斯丘的倫敦富商,在喝完早茶後死亡,人們搜查他的衣服時發現夾克口袋裡有一堆黑麥。在小說中,黑麥在那裡被發現的原因,正是應驗了兇手提到的童謠中其中一句話「黑麥滿口袋」……這把我們帶回到烏克蘭,根據馬德的描述,有些出奇地熟悉的事情竟然在那裡發生,但不是黑麥而是向日葵種籽。在格尼奇斯克(Henichesk),這個位於阿速海濱的海港,當一名烏克蘭老婦人遇到一位全副武裝的俄軍士兵,她給他向日葵種籽並叫他放進自己的口袋裡——那樣它們就可以在他死的時候生長,他那腐爛的屍體在地球上仍可有用處:孕育植物茁長……
惟一讓我不安的是,這種姿態,對被派到烏克蘭進行軍事任務的一般俄軍士兵,缺乏同情,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輜重和糧食,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和為甚麼要去那裡,這些事例被報道為烏克蘭人給他們食物。這令我想起1968年的布拉格,我在蘇軍入侵前一天抵達那裡,在城市周遭逛了幾天,直至給外國人的運輸系統被組織起來。即時打動我的,是一般士兵的混亂窮困與高階軍官產生鮮明對比,與我們這些抗議的示威者相比,士兵似乎更大大地害怕他們。
我們錯在沒有從字面上去看普丁的威脅。我們認為他不會認真、而只是在玩一場策略調動的遊戲罷了。
即使在這些瘋狂的日子,我們也不應該恥於堅守常態的最後痕跡,並應該引用流行文化。所以,讓我提及克莉絲蒂另一部經典作品:《池邊的幻影》(1946),故事中,偏心的露茜 · 安卡德邀請了克利斯托先生(他名叫約翰,是哈雷街頂尖的醫生),他的妻子格爾妲,和她的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員一起,在她的別墅裡渡過周末。赫丘利 · 白羅留在他的村莊小屋附近,也被邀請共進晚餐。第二天清早,他目睹一幕奇怪地上演的情景:格爾妲 · 克利斯托拿着一把手槍,站在約翰的屍體旁邊,屍體的血流進泳池裡。露茜、亨麗達(約翰的情人)與愛德華(露茜一家的侄兒、亨麗達的第二個表弟)也同時在場。約翰最後發出急迫的請求——「亨麗達!」——然後就斷了氣。看來格爾妲很明顯是兇手。亨麗達上前拿走她手中的左輪手槍,但顯然笨手笨腳地把它弄丟在泳池裡,毀滅了證據。白羅看出,死者臨終時的那聲「亨麗達」,是呼籲自己情人保護妻子,以免因為自己的死而坐牢;缺乏有意識的計劃,整個家庭都加入了陰謀並刻意誤導白羅,因為他們知道格爾妲是兇手,並試圖去營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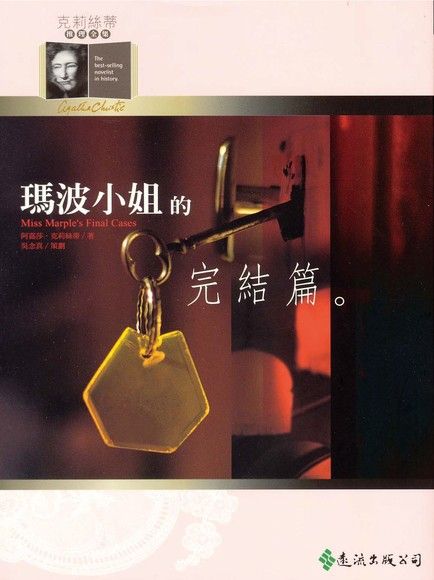


一次標準公式的逆轉(一場兇案發生了,一群嫌疑犯有參與動機及機會,甚至即使兇手看來很明顯,連偵探也發現了線索,那些線索卻是真正兇手為掩飾其痕跡而鋪排的兇案現場)在此出現:那群疑犯製造了指向他們自己的線索,以掩飾事實:真正兇手明顯是那位在兇案現場被逮到的,拿着手槍的人。那麼,犯案現場被佈置過,卻是以相反的形式呈現:欺騙存在於這樣一個看來被人工佈置過的事實,即:真相將自己偽裝成人工的表象,於是真實的膺品成為它們的「線索」——或者,正如瓊 · 瑪波在克莉絲蒂另一部經典《殺手魔術》裡說的:「不要低估那些顯而易見之物的力量。」
意識型態不也往往是如此運作嗎,尤其是在今天?它把自身表現為一些神秘之物,指向一個隱藏的底層,以掩飾它正在犯下或公開合法化的罪行。關於宣稱這種雙重神秘化,有一種人們喜愛的說法,就是「情況是更為複雜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比如說,野蠻的軍事侵略——透過喚起一句「其背景是更加複雜的情況」而變得相對化,這句話一如所料,令侵略變成防衛行為。這就是為何,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會忽略情況背後隱藏的「複雜性」,而只相信簡單的數字。
而現在發生在烏克蘭的不正是一樣嗎?俄羅斯攻擊它,但很多人在尋找它背後的「複雜性」。是的,可以肯定,這裡有複雜性,但基本事實是,俄羅斯做了那件事。我們錯在沒有從字面上去看普丁的威脅。我們認為他不會認真、而只是在玩一場策略調動的遊戲罷了。關於最高級的反諷,在此不能不提佛洛伊德引用的那個著名的猶太笑話:「當你真的要去利維夫的時候,為何你告訴我你要去利維夫呢?」在這裡,一個謊話以事實性真相的形式呈現:這兩位朋友已經建立了一套隱藏涵義的代碼,那就是,當你要去利維夫時,你就說你會去克拉科夫,倒過來也一樣,這樣,在這種空間內,說出字面上的真相意味着說謊。當普丁宣稱要進行軍事介入,我們不會在字面上認為普丁的聲明是要帶來和平及將整個烏克蘭去納粹化,而現在「深度」戰略家的責備如此:「當你真的要佔領利維夫的時候,為何你告訴我你要去佔領利維夫呢?」
在今日的烏克蘭,那些抵抗俄羅斯入侵的人具備行動自由,卻沒有自由權利。他們為自由權利而戰,而關鍵問題在於戰鬥後哪種自由權利將會更大。
那麼,然後怎樣呢?記得一、兩個月前,我們那些大眾媒體的大新聞項目,仍是關於瘟疫的消息嗎?現在瘟疫完全消失了,而烏克蘭上了頭版。而且,如果有的話,恐懼現在正變得更大:幾乎是對過去兩年抗疫美好光景的懷念。這種突然的轉變展現出我們的自由界限:沒有人選擇了這種變化,它就是發生了(除了那些陰謀論者聲稱烏克蘭危機是建制了為繼續緊急狀態,並繼續控制我們而寫的劇本)。
要掌握瘟疫和烏克蘭危機之間的差異,我們需要分辨兩種自由:「行動自由」(freedom)與「自由權利」(liberty)。讓我冒險地把這對立設定在黑格爾所稱的抽象自由與具體自由之上。抽象自由就是一個人想要無視社會規則或習慣,及違反這些規則和習慣的能力,正如在一種起義或革命處境中完美體現出「激進否定性」的爆發。具體自由是透過一系列規則和習慣維持的自由。對於反對接種疫苗人士來說,接種疫苗與否的自由,當然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然而,這是為了有效抗拒因為接種疫苗、而很可能導致我的實際自由及其他各種自由被限制。在實際方面,我的自由只像在一定社會空間內被規則或禁制所管轄的自由那樣。在一條繁忙的街道上,我可以自由地行走,因為我可以合理地確定街上其他人會以文明的方式對待我,如果他們攻擊我、羞辱我之類的話,就會受到懲罰。我可以行使與他人談話及溝通的自由,只要我遵守共同建立的語言規則,連帶其所有含糊的部份,包括其言外之意的不成文規則。當然,我們所說的語言,並非在意識型態上中立:它包含很多先入為主之見,使我們無法清晰地表達一些不常見的想法。思想經常以語言來出現,它也帶來常識上的形而上學(現實觀),但要真正思考,我們必須運用與這種語言截然不同的語言來思考。語言的規則可以被改變,以打開新的自由,但政治正確的新話(newspeak)所帶來的麻煩,則清楚地顯示,要直接實行一種新規則,可以導致語焉不詳的後果,並萌生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更為微妙的新形式。
然而黑格爾很清楚,抽象自由總會在危機的時刻介入。在1944年12月,尚—保羅 · 沙特(Jean-Paul Sartre)寫道:「我們沒有任何時候比在德國佔領下更自由。我們失去了一切的權利,首先是我們的言論自由權,他們從我們臉上羞辱了我們……那就是為何抵抗運動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對士兵來說,正如他的長官一樣,一樣的危險、一樣的寂寞、一樣的責任,以及在紀律下一樣的絕對自由。」這種充滿焦慮和危險的境況,就是行動自由而非自由權利,後者在戰後正常秩序回歸的時候建立。而在今日的烏克蘭,那些抵抗俄羅斯入侵的人具備行動自由,卻沒有自由權利。他們為自由權利而戰,而關鍵問題在於戰鬥後哪種自由權利將會更大。普丁的宮廷哲學家阿歷山大 · 杜金,為歷史主義的相對主義加上後現代的粉飾(阿歷山大 · 杜金原文):
這裡接下來的問題是:對敍利亞和烏克蘭的人民來說會是怎樣?他們能否也選擇他們的真理/信仰,抑或他們只是那些大「老大」及其鬥爭的遊樂場?某些左翼人士甚至視杜金為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反對者,以及族群—文化認同不可化約多樣性的倡導者。但杜金所倡導的多樣性是一種建基於族群認同的多樣性,不是基於族群內部的多樣性,那就是為何「只有戰爭能真正地決定」。基要主義族群認同的興起,最終只會是全球市場的另一面,而不是其對立面。我們需要更多全球化,而不是更少,如果我們要認真對付全球暖化,我們比任何時期需要更多的全球團結和合作。
吉爾伯特 · 基思 · 卻斯特頓寫道:「除去超自然以後,你所剩下的只有不自然。」我們應該贊同這個命題,但是在相反的意義上,而不是卻斯特頓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們應該接受自然是「不自然的」,是一場被缺乏內在節奏的偶發性干擾的怪誕秀。在2021年6月底,一場「熱穹」(一種由高壓脊聚集及壓縮暖空氣,推高溫度並烤熱該地區的氣候現象)出現在美國西北部及加拿大西南部地區,導致氣溫高達攝氏五十度,甚至令溫哥華比中東地區還要熱。誠然,「熱穹」是一種地區性現象,但它是全球氣候類型受干擾的後果,這明顯地由於人類介入了自然循環,我們已全球性地對它產生作用。
當我們真的要對抗普丁時,我們必須集結勇氣以帶判批地反躬自身。
想一想在戰爭爆發頭一、二天,普丁在電視上怎樣呼籲烏克蘭軍隊推翻澤倫斯基政府並且接管它,聲稱這樣會更容易與他們進行和平談判。或許俄羅斯本身能提供如此發生的事件,就像在1953年,朱可夫元帥曾幫助赫魯雪夫扳倒貝利亞。那是否代表我們就應該妖魔化普丁?不是。當我們真的要對抗普丁時,我們必須集結勇氣以帶判批地反躬自身。
在過去幾十年間,到底自由西方與俄羅斯玩着甚麼遊戲?它如何有效地把俄羅斯推向法西斯主義?這裡只消想想他們在耶爾欽年代向俄羅斯提供的災難性經濟「建議」⋯⋯是的,普丁很明顯對這場戰爭籌備多年,但西方知道這一點,所以這場戰爭絕對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震撼。我們大有理由相信西方是有意識地將俄羅斯逼入絕境。俄羅斯對被北約圍堵的恐懼遠非迫害妄想症的想像。沒有人比維克托.歐爾班說這番話的時候,更接近真相的時刻:「戰爭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陷入了地緣政治主要對手的交火中:北約向東擴張,而俄羅斯對此感到越來越不舒服。俄羅斯人提出了兩項要求:烏克蘭宣佈中立,而北約不再接受烏克蘭加入。這些安全承諾並沒有給予俄羅斯人,所以他們決定透過武力去取得。這就是這場戰爭的地緣政治特徵。」當然,這小小的真相,掩蓋了一個大謊話:俄羅斯正在進行着一場瘋狂的地緣政治遊戲。
對於當前的狀況,不應該有所禁忌。明顯地,烏克蘭一方也不能完全信任,頓巴斯地區的情況仍遠遠不明朗。再者,對俄羅斯藝術家的排斥浪潮跡近瘋狂。米蘭比可卡大學將保羅.諾利教授的杜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課程延期,其論據是非常普丁式的:這只是一種讓情況平靜下來的預防姿態⋯⋯(在一段日子後,延期被取消。)但現在與俄羅斯的文化接觸,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還有允許烏克蘭人,而不讓目前身處烏克蘭並設法逃避戰火的第三世界學生及工人,從烏克蘭進入歐洲的大醜聞呢?還有在西方的爆炸性種族主義呢?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特派員查利 · 達加塔,在上星期曾說過,烏克蘭「是一個不像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樣,得到應有尊重的地方,那裡已經被衝突肆虐了幾十年。這是一個相對文明,相對歐洲化的(我也必須小心選取那些詞語)城市,是一個你不會預料,或者不希望刻下事情發生在那裡的地方。」一位烏克蘭前任副檢察長告訴英國廣播公司:「這令人非常激動,因為我看見,每天都有金髮碧眼的歐洲人被殺。」法國記者菲利浦 · 科爾貝斷言:「我們不是在討論逃避普丁支持的敍利亞政權轟炸的敍利亞人。我們是在討論像我們般駕駛汽車逃生的歐洲人。」誠然,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衝突肆虐了幾十年。但我們在這些衝突當中的複雜性又如何?今日,當阿富汗真正成了伊斯蘭基要主義國家,誰仍記得三十年前,那是一個帶有強烈世俗化傳統的國家,包括一個獨立於蘇聯地奪權的強大共產黨?但是,自此以後,首先是蘇聯,然後是美國介入,就變成現在那裡的模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恐懼並不限於第三世界,它們也不只是我們在螢幕前舒適地觀看的東西,它們也可以在這裡發生;所以如果我們要安全地生活,就必須在任何地方和他們戰鬥⋯⋯
我們的特派員和評論員對現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感到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非常地模棱兩可。它可能意味着:我們現在看到的恐懼並不限於第三世界,它們也不只是我們在螢幕前舒適地觀看的東西,它們也可以在這裡發生;所以如果我們要安全地生活,就必須在任何地方和他們戰鬥⋯⋯但它也可能意味着:讓恐懼留在那裡,遠遠的,就讓我們保護自己免受他們傷害。普丁是個戰犯——但難道我們現在只發現這一點?難道多年前他就不已經是個戰犯,那時候,為了挽救阿薩德政權,他讓俄軍戰機轟炸敍利亞最大城市阿勒頗,而且是以比今日他們在基輔野蠻得多的方式?當時我們就知道這個,但當時我們的憤慨是純粹道德上和口頭上的。我們對「酷似我們」的烏克蘭人更大地感到同情,顯示了費特力克.洛爾頓嘗試以斯賓諾莎的跨個體「情感模仿」維持「歸屬感」,以為解放政治奠基的局限。我們必須與那些並沒有與我們享有情感歸屬的人團結起來。
當總統澤倫斯基將烏克蘭的抵抗稱為對文明世界的捍衛,這是否意味着他把不文明者排除出去?那麼在俄羅斯因為抗議軍事介入而被捕的幾千人又如何呢?那麼納粹主義在體現歐洲最高文化的國家裡當權的事實又如何呢?就在那裡,金髮碧眼的歐洲人幹着殺戮的事。如果我們只是「捍衛歐洲」,那麼我們就已經在用杜金和普丁的語言來說話:那是歐洲真理對抗俄羅斯真理。文明與野蠻的界線在於文明內部,那就是為何我們的鬥爭是普遍性的。今日唯一真實的普遍性,就是鬥爭的普遍性。
烏克蘭在前蘇聯國家裡是最窮困的。即使他們——希望如此——打贏了,對他們來說,他們的防衛勝利對他們來說也會是一個真理時刻。他們將必須要認識到,僅僅趕上西方是不夠的,因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本身正陷入深重的危機。關於烏克蘭正在進行的戰爭,最可悲的是,當全球自由資本主義秩序正在多層面上陷入危機,現在的情況再一次被錯誤簡化成野蠻極權對抗文明西方⋯⋯而對全球暖化視而不見。如果我們跟着這條路,我們就輸定了。當下的時刻並非真相時刻,當事情水落石出,而基本對立明顯時。這是最深的謊言時刻。如果一個排除了「不文明者」的歐洲贏了,那我們就不需要俄羅斯來毀滅我們,我們自己就可以成功達成任務了。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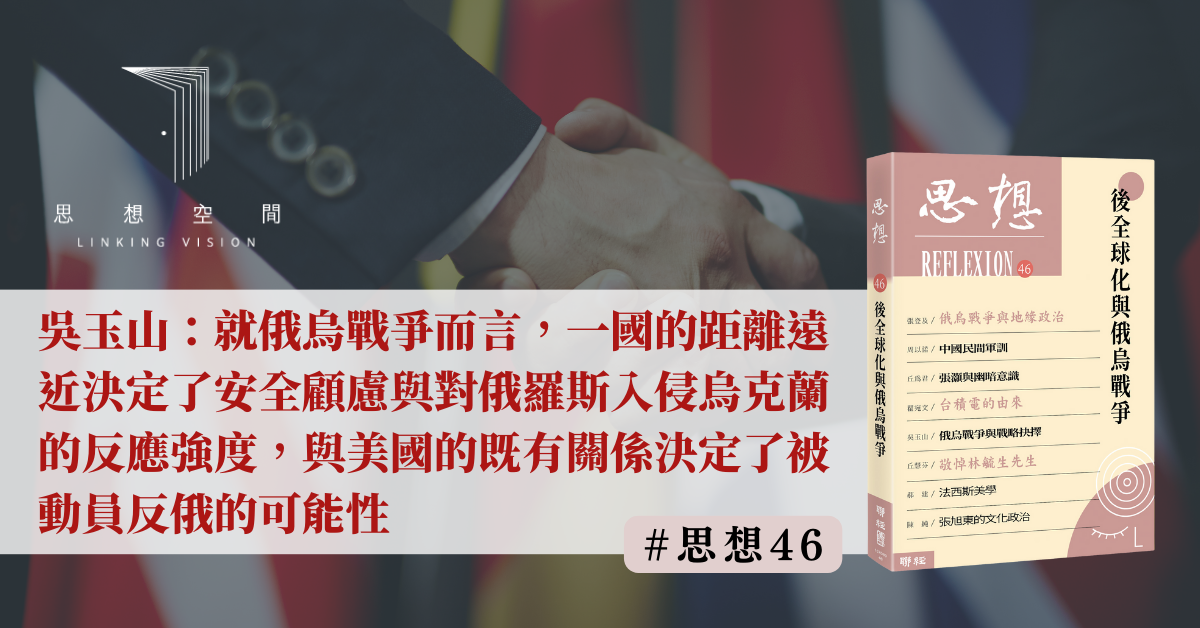
盤點各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站位——如何理解戰略抉擇?

【學人專訪】謝爾希.浦洛基:新的烏克蘭社會已經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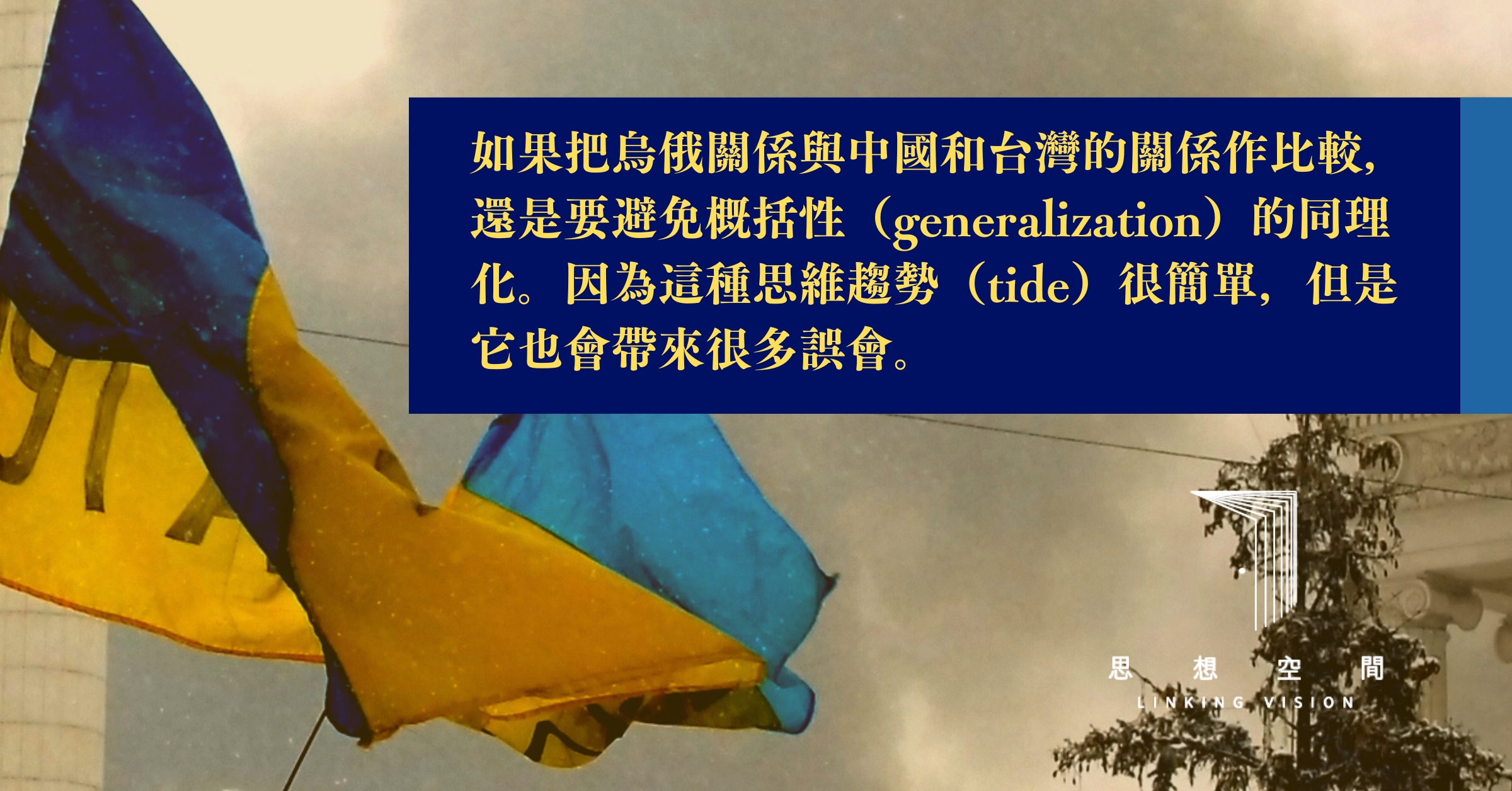
Mariana Savchenko x 涂豐恩:我們為何會低估烏克蘭人的力量與反抗?

斯洛維㫐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及文化評論家,是我們時代其中一位最傑出的思想家。紀傑克在1989年以英文出版了其第一本著作《意識型態的崇高客體》,獲國際承認為社會理論家。他也是報章如英國《衛報》、德國《時代週報》或《紐約時報》的定期撰稿人。他被有些人標簽為「文化理論的貓王艾維斯」,並且是大量紀錄片大和書籍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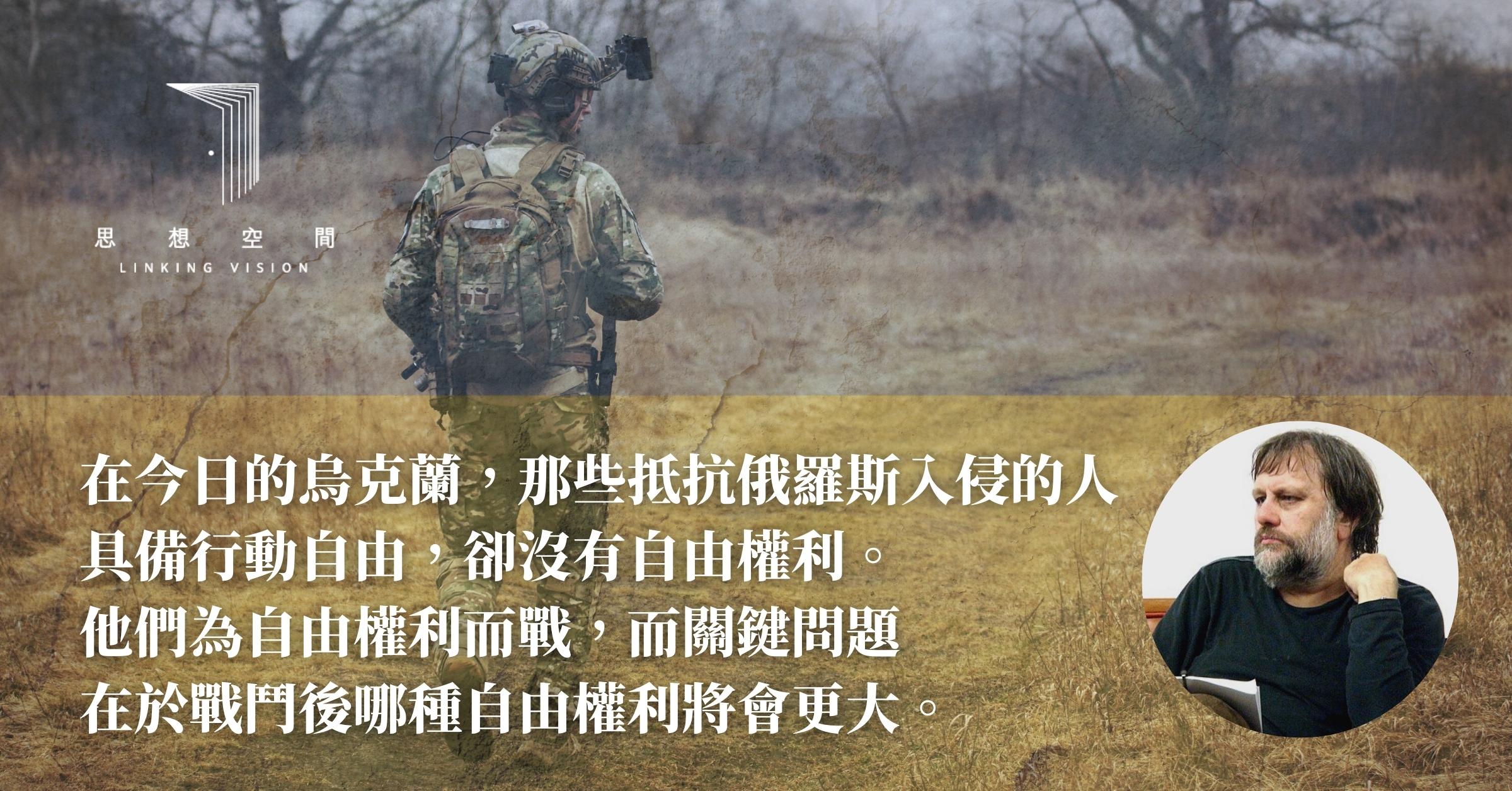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