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自官大偉「今晚我想來點民族學」系列,感謝作者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擬。本文為第二篇,上篇為〈今晚我想來點民族學——從蔡元培到費孝通,民族學脈絡爬梳(二之一)〉。
對於殖民地人類學,除了要有批判性的解讀外,我個人的經驗是,必須看到不同尺度下的不同作用因素。
殖民地人類學
台灣的原住民各族甚至不同的地域群體,都有自己對人群的分類方式、對於人群關係的理解,而在殖民接觸後,也進一步產生了對於墾殖者的認識和稱呼;另一方面,不同時期來到台灣的墾殖者、傳教士、博物學家、政府官員,也留下了對於台灣人群的描述和紀錄。
1895年日治開始,日本政府啟動對於台灣人群有系統的調查與分類,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以受雇於政府之業餘人類學家的身分,來到台灣進行調查。1909年總督府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由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36人,完成了《蕃族調查報告書》8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8冊、《臺灣蕃族圖譜》2冊、《臺灣蕃族誌》1冊、《台灣番族慣習研究》8冊等一系列的報告(陳奇祿1974)。
自1895年到1928年之間的調查與研究,都具有直接的統治目的。這個時期,人群分類是主要的工作之一。伊能嘉矩批評清治時期的生/熟分類,是以政治上之歸化與否為劃分,而非科學的依據,也批評馬偕曾做過的分類局限於北部的經驗。經過四次在台灣的旅行(包含半環島、環島、外島)踏查後,他以體質、風俗、思想、語言、歷史口碑等「客觀」標準,提出了四群、八族、二十一部的分類方式,並解釋人群的地理分布和進化程度的關係。
之後,與伊能同期來台,但較晚展開調查的森丑之助,則批評伊能大多依賴官署記錄以及通譯,且缺乏對山區全面性的研究。在深入山區調查後,森提出了泰雅、鄒、布農、排灣、阿美、雅美的分類。然而,不論是馬偕、伊能或是森,都不脫一套以科學為宣稱,將人類至於自然史分類方式的種族知識架構(陳偉智2009)。雖然殖民統治者已經離去,但這樣的分類,至今仍影響深遠。
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土俗人種學講座」(英文名稱為Institute of Ethnology,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由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移川子之藏主持,他雖然研究民族史(完成了《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但也帶入美國文化人類學式的研究旨趣(Van Bremen 1999:369 ),例如,移川對於原住民族時間觀的研究、他的學生馬淵東一對於原住民族地理觀的研究等等。除了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以及合著「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的宮本延人之外,這個時期和原住民之研究相關的學者還有,岡田謙(社會)、古野清人(宗教)、小川尚義(語言)、淺井惠倫(語言)、鹿野忠雄(地理、博物)、奧田彧(農業)、千千岩助太郎(建築)、金關丈夫(體質人類學)、國分直一(考古)等人。
相較於前一個時期,這一階段(1928-1945)的學術活動重心,從過去以東京人類學會為中心的往來,移轉到台北帝大,研究者有較專業完整的訓練,而學術研究的內容也較不受限於統治的目的(劉斌雄1975)。但也有後世學者提醒,這樣的將「文化」「袪政治化」的典範,看似是學術和政治脫離,但卻也是研究者對被研究者在現實中遭遇的壓迫視若無睹的一種「暴力」(丘延亮1997)。
上述日治時期的調查紀錄與研究,在戰後許多譯者的努力之下,大多已經逐漸翻譯成中文,對現今的讀者有很大的便利性。雖然,毫無疑問的,這些著作都受到其殖民背景的影響,但如何批判性的解讀、善用,則是今日學者的責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2016年「伊能嘉矩全台調查120週年特展」的座談上,台大人類系的童元昭教授,就說道:這些殖民時期的調查和研究,當然有它們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無法看到這些殖民背景和侷限性,那就是我們的問題。
對於殖民地人類學,除了要有批判性的解讀外,我個人的經驗是,必須看到不同尺度下的不同作用因素。舉例來說,研究者在其研究歷程所累積出來的對人、對地,和對物的情感,往往不是殖民剝削可以完全解釋的。
北科大建築學系黃志弘教授,在2012年與政大合作的「千千岩助太郎台灣高砂建築踏查特展」中,曾經口述過一個千千岩助太郎的故事。九族文化村的原住民族建築,是依照千千岩助太郎所做的高砂族家屋測繪紀錄所重建的。在興建的時候,基於慎重起見,請了千千岩助太郎來監工,並且特別找了一批經過日治時代的老工匠來施工。當這些家屋全部在園區中興建完竣,園方特地把老先生再從日本請來驗收。老先生到達完工現場,整個工班戰戰兢兢,排成一列迎接。他繞了一圈,表情嚴肅,不發一語,大家面面相覷,深怕哪裡出了差錯。老先生走著走著,走到一個棵大樹下,坐在樹下的石頭上,然後脫下帽子,大哭起來。原來,他沒想到,有生之年,能有機會再親眼看到,這些幾十年前他在台灣山中看到的美麗建築。
若要論及對於殖民地人類學作品的翻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有系統的翻譯了很多調查報告,但楊南郡先生的貢獻更是不可抹滅。楊南郡先生翻譯過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鹿野忠雄、馬淵東一等人的許多重要著作。這些人物中,他最鍾愛鹿野忠雄的博學、奔放與自成一格。2016年,在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譯作的發表會中,他以鹿野忠雄為例,鼓勵後進,要把握人生的黃金時期,只要全心全力投入,就能有驚人的成就。
當時楊南郡先生已經身體有恙。三個多月後的某天,我一大早要搭第一班飛機前往台東,登機前,在機場收到他的女婿雅柏甦詠的簡訊,楊南郡老師與世長辭。我坐在飛往台東的飛機上,從高空看著窗外清晰起伏的台灣山脈和海岸,感受到這個島嶼上累積了不同時代的足跡。昔人已遠,但這些足跡,已深刻的留在這個島嶼上。


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也是早期隨國民政府遷台之學者逐漸凋零的階段,新一批在歐美接受人類學訓練的學者返台,帶入新的研究氣象。
戰後的機構與學科發展
一、從民族學研究室、台大人類學系到各人類學相關系所的建立
1945年,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改制為文學院歷史學系下的「民族學研究室」。在1945年至1949年之間,台大留用了一批日籍學者,包括宮本延人、國分直一,以及在醫學院但致力於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金關丈夫,成為戰後初期延續相關研究之主力(歐素瑛2005:174)。
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民族學者、考古學者來到台灣,台大文學院中增設考古人類學系,「民族學研究室」從歷史學系併入考古人類學系,而留用的日籍學者則因為政治氣氛的轉變,回到日本(歐素瑛2005:181-184)。1949年考古人類學系設系後的第一任系主任,由和移川子之藏同樣師承於哈佛大學人類學系Roland Dixson的考古學者李濟先生擔任,他引入了美國人類學式四大分支:考古學、民族學(在此分類下視為等同文化人類學)、語言學及體質人類學的課程設計(台灣大學人類學系2018)。
隨國民政府遷台而任教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學者有凌純聲、芮逸夫、衛惠林等。台大考古人類學系1953年培育了第一屆畢業生——李亦園、唐美君,是為戰後本土第一代人類學者。兩位先生分別出生於福建、浙江,先後在1948年、1949年來台求學。考古方面的本土先驅宋文薰先生,則是竹東出生,少年赴日,1951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宋文薰先生、李亦園先生皆是畢業後在考古人類學系任助教。唐美君先生畢業赴美國加州大學留學,之後亦返系任教(唐美君:123)。和宋文薰先生同系同學,亦曾受教於國分直一者,還有畢業後任職於省立歷史博物館的劉斌雄先生。出身台南,留學日美,並曾擔任台大歷史系助教的陳奇祿先生,則是1953年自美返台後,擔任考古人類學系講師。
在戰後初期留任的日本學者、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學者,以及初萌芽之本土學者的傳承下,人類學在台灣逐漸開枝散葉。1982年,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改名為人類學系。台大之外,清華大學在1984年由李亦園先生籌創人文社會學院,隨之在1987年成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1998分出人類學研究所)。暨南大學在2003年設置人類學研究所(2014年改為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在考古方面,則有成功大學於2015年設立了考古學研究所。此外,東華大學1995年成立的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台東大學2003年成立的南島文化研究所(2011年改為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還有交通大學2004年成立的人文社會學系、2008年成立的族群與文化碩班,雖然不是以人類學為名,但人類學的教學與研究,在這些系所都扮演著重要的地位。
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5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學籌備處,籌備處主任為凌純聲先生,而李亦園先生則被聘為助理員 (之後在1968年擔任副所長,1970年接任所長)。1965年正式設民族學研究所,但考古的部分則是維持在歷史語言所。
直至1960年代初期,中研院民族學籌備處的調查,以描述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的歷史文化為主。包括:1955年在排灣族來義鄉的調查、1957年在蘭嶼的調查、1958至1959年之間在馬太鞍與秀姑巒阿美族地區的調查、1960年至1963年之間在南澳泰雅族的調查、1963年至1965年之間的大港口阿美族地區調查。1960年代初期,還展開了馬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台灣民間信仰、彰化泉州厝、龜山島漢人社區等漢人社會的研究(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2015)。開啟了日後的台灣漢人社會、宗教與文化研究的方向。
1970年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參與跨學科的大型台灣本土研究「濁大計畫」。這個計畫結合台美資金,由當時任教於耶魯大學的考古學者張光直主持,聯合考古、民族、地理、地質、土壤、動物、植物共七個學科,調查研究濁水溪及大肚溪流域的長期人地關係變遷。這個計畫培育了新一代的學者,像是陳茂泰(1975)泰雅族果樹經營的研究、黃應貴(1975)布農族經濟變遷與調適的研究,都是結合了碩士論文研究及計畫參與。這些研究不同於前一階段的社會歷史文化描述,為當代原住民族社會變遷研究奠定了基礎。
作為國家體制中的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肩負協助國家政策發展的任務。1980年代,有省政府民政廳委託的「山地行政政策評估研究」(李亦園1983)。2010年,則有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的「臺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研究(黃樹民、莊英章2010)。另外,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自2007年開始推動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計畫」,則是支持人才投入原鄉小型的公共服務與發展計畫(余舜德2018),進行由下而上的社會實踐。
三、研究趨勢概略
如前所述, 196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在原住民族社會之外,開展了漢人社會的研究;原先描述台灣原住民族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也轉向探討現代化、工業化後之社會變遷、影響與調適。李亦園先生稱這樣的轉變,是從民國時期民族學南派(重歷史)的取徑,轉向北派(重當代社會)的方向(李亦園1993)。從另一個角度來看,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也是早期隨國民政府遷台之學者逐漸凋零的階段,新一批在歐美接受人類學訓練的學者返台,帶入新的研究氣象。
1980年代中,胡台麗(1984) 拍攝了首部有聲彩色影像民族誌紀錄片。台灣解嚴後,人類學對於新族群現象與公共議題之關注進一步浮現(參見黃應貴1999),例如,謝世忠(1987)的《認同的污名》一書,對於原住民族運動就有重要的影響。2000年之後,與原住民族相關的研究,也涉及更多公共性的議題。另一方面,原住民各族之本民族學者增加,原住民族研究(indigenous studies)做為一種方法論,和人類學的對話也增加。
中國研究的部分,1960年代以前,多是以1930年代至1950年代收集的資料進行書寫;1970年代以後,中國改革開放,台灣的學者也陸續入境中國,進行第一手資料的調查,而有一段蓬勃發展的時期(參見何翠萍1999)。2010年代後期,中國進入到政治權力更集中、緊縮、保守維穩的階段。外國學者要進入中國做研究的難度日增。未來變化與影響,值得持續觀察。
太平洋的部分,早期凌純聲(1956、1957、1958、1967)曾有一系列比較台灣、太平洋地區、中國東南的研究。透過歷史文獻考證,這些研究試圖論證台灣、太平洋地區之文化和中國的關係。太平洋地區的研究,早期還有張光直做過貝珠錢的考古分析。1970年代吳燕和老師做過巴布亞新新己內亞的調查。1980年代末期童元昭老師在法屬玻里尼西亞做研究,其研究初始從太平洋地區的華人移民切入,逐步開展出整個太平洋的視野,也為之後新一代直接以太平洋島民和文化為對象之研究者奠定了基礎(參見Guo 2005)。2000年之後,因為台灣的南島論述和政治實踐,人類學的太平洋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國際關係研究,也在南島的架構下有所交會。


一方面,民族學、人類學在不同的年代/區域,都有不同的差異,但許多時候彼此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題也相互滲透和影響;另一方面,不同機構的不同傳統,也會展現在當前的發展上。
從邊政到民族
1955年,也就是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學籌備處的同一年,在台北的另一端,政治大學於在台復校,復校時設置的五個學系之一,即包含邊政學系。
一、邊政學興起的背景
相較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之美國人類學式四大分支的架構設計,政治大學的師資組成和教研取向,顯得很不一樣。雖然有衛惠林所教授的民族學,但亦有胡耐安(第一任系主任)的邊政通論,蔣君章(地理學者,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的邊疆地理,以及札奇斯欽(蒙古族、歷史學者)的民族語言、歷史等課程。這樣的設計中,除了反映著重文獻檔案、從民族史建構民族間往來互動關係之民國時期南派民族學的特色之外,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等多學科的匯集,更反映了其延續邊政思維中培育「邊疆」治理人才的邏輯。
「邊政學」於1930年代至1940年代在中國興起,有著中日戰爭下鞏固國族、以釐清政治與文化邊界,來映照國家主權範圍的歷史背景。吳文藻在《邊政學發凡》一文中,指出所謂的「邊疆」的意義,包含有政治上的邊疆與文化上的邊疆,邊政學在理論上是要將西方人類學、政治學、史學、地理學及社會科學諸多學科進行整合,實務上是要將其運用在實際的邊疆政治中。當時不同學科的學者,都在「鞏固大後方、團結各民族、一致抵禦外侮」的民族主義旗幟下(黃樹民 2011:182),投入這樣的打造工程。除了吳文藻為邊政學定義之外,包含之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民族學者,例如,凌純聲、芮逸夫、衛惠林、都是邊政學會的重要成員,也都曾在南京中央大學的邊政學系任教,而凌純聲還曾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汪洪亮2010、馬玉華2012)。
二、從邊政學系到民族學系的轉型
1955年在台復校之政治大學的邊政學系,英文系名為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胡耐安先生於政大《邊政學報》創刊號中論及,培養邊疆治理人才,需注重民主、自治之涵義,亦需對人類社會文化的辨識和理解,同時考量課程安排與畢業生發展,乃採此英文系名(胡耐安1962)。1960年,劉義棠先生(民族史、維吾爾研究)畢業留系擔任助教;1961年,歐陽無畏先生(藏學)加入任教。1969年,和劉義堂先生同為本系畢業生的林恩顯先生留日學成返系任教,同年,邊政學系改名為民族社會學系,並成立邊政研究所,從事台灣原住民族之民俗學研究的阮昌銳先生亦在此年加入。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民族社會學系逐漸增加社會學相關師資與課程。1981年,民族社會學系改名為社會學系,原先和邊政相關的教研,完全移轉到邊政研究所。
民族學與社會學的分家,同一時期(1980年代)亦在中研院民族所發生。政大民族社會學系改名的同年(1981年),在台的中國社會學社社員大會通過促請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學研究所,而中研院的專案小組1988年擬訂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要點,1995年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並有11位民族所中社會學專長之研究人員轉入社會研究所。
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之間,台灣內部經歷了民主化、本土化,外部則面臨中國崛起後的新地緣政治格局勢。此時,傳統邊政研究中所謂邊疆治理的目標也已不符時空條件,但新的時空條件中,也有著新的發展可能。1990年,邊政研究所(當時所長為唐屹先生)在滿州、蒙古、西藏、新疆之外,增設台灣山地組(林恩顯1999:4-5),同年邊政研究所改名為民族研究所。1993年,政大設民族學系;1996年系所合一;2001年設置博士班。這樣的發展,也帶來對於學科定位的進一步討論。
三、學科的定位
在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關係上,張中復於1999年「胡耐安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座談會」中就以〈從邊政到民族〉一文指出,政大的民族學應該超越過往以「中央——邊陲」所建立起來的邊疆觀,邁入以「人群與文化」為中心的民族觀,同時他也認為,狹義的民族學,是一門認識人群文化的學問,這部分和人類學是相同的;廣義的民族學,則有民族間的關係、民族與國家之關係的政治與政策應用面向。因此,民族系學生需要認識人類學的理論,但非將其奉為唯一圭臬(張中復2019)。
此外,趙竹城(2014)則提醒,將臺灣的民族學建構在西方人類學的學術發展傳統,是「後製化」的結果,並憂其將導致學科原本的「公共性」與「政治性」之消失。他認為既然民族問題是人類社會眾多問題之投射,要面對民族問題就需要跨學科整合能力。同時,他也主張,在維持民族學跨學科整合的性質的同時,應超越傳統邊疆治理邏輯,進入到國家、超國家組織、社區、第三部門、跨域治理等層面的應用及參與。
在方法論上,林修澈(2006)綜整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代中期之間,政大民族系及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投入民族認定、族語復振等計畫之經驗,以「採蜜」與「養蜂」做比喻,指出過往對於原住民族的研究,經常是只重研究材料的取得(像是採蜜一樣),而未必在意該民族是否存續,但若以民族本身利益為思考,則民族的生存發展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因此其主張,研究者是要以學術之能力,投入和民族生存發展相關事務之探討,並影響政府政策之制訂,以期為原住民族之生存發展帶來正面的效益。這樣的主張,固然用了一個相當本土、淺顯的比喻,但是卻和西方社會科學中的行動取向研究方法論相契合。
四、小結——善用自身特色、創造學術與社會貢獻
德國民族學和英美人類學有不同的傳統,而中國之民國時期民族學同時受到德國民族學與英美人類學的影響。戰後台灣的人類學,繼受了日治殖民地人類學的遺產,也在民國民族學者的啟動下建立機構、培養本土的人類學者,並逐步在一批批赴歐美受人類學訓練學者返台後,和歐美人類學有更緊密的銜接。以民族學為名的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同樣是朝向與歐美人類學高度結合的發展,但因為機構的特性,同時肩負著政策相關調查研究的責任。
政治大學的民族學系,若以其演變來看,此一支的「民族學」並非只是美國人類學式的四大分支下的文化人類學,而是有著德國民族學之自我國族建構色彩,以及民國時期民族學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發展出之邊政學強調公共性、政治性的傳統,並且在台灣經歷民主化、本土化後,累積出實證之民族事務研究與實踐經驗。
一方面,民族學、人類學在不同的年代/區域,都有不同的差異,但許多時候彼此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題也相互滲透和影響;另一方面,不同機構的不同傳統,也會展現在當前的發展上。舉例來說,同樣是人/地相關學科的科際合作,在台大,有著人類系和地質系、地理系合作的「地質考古學」與「人文地理資訊科學」課程教學,以及考古遺址分析的研究計畫。
在政大,民族系和地政系之間,則長期有原住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相關的研究合作,近年並合作設立「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培育同時具備貼近原住民族土地文化,以及與國家政策制度對話之能力的人才。這兩種人/地相關學科的跨域合作模式都很重要,關鍵就在於善用自身特色,創造對學術與社會的貢獻。
同樣的,延續長期以來累積對中國少數民族及其周邊民族研究之資產,提供台灣社會面對當前地緣政治格局時,應有的族群關係視野,相信也會是政大民族學系很重要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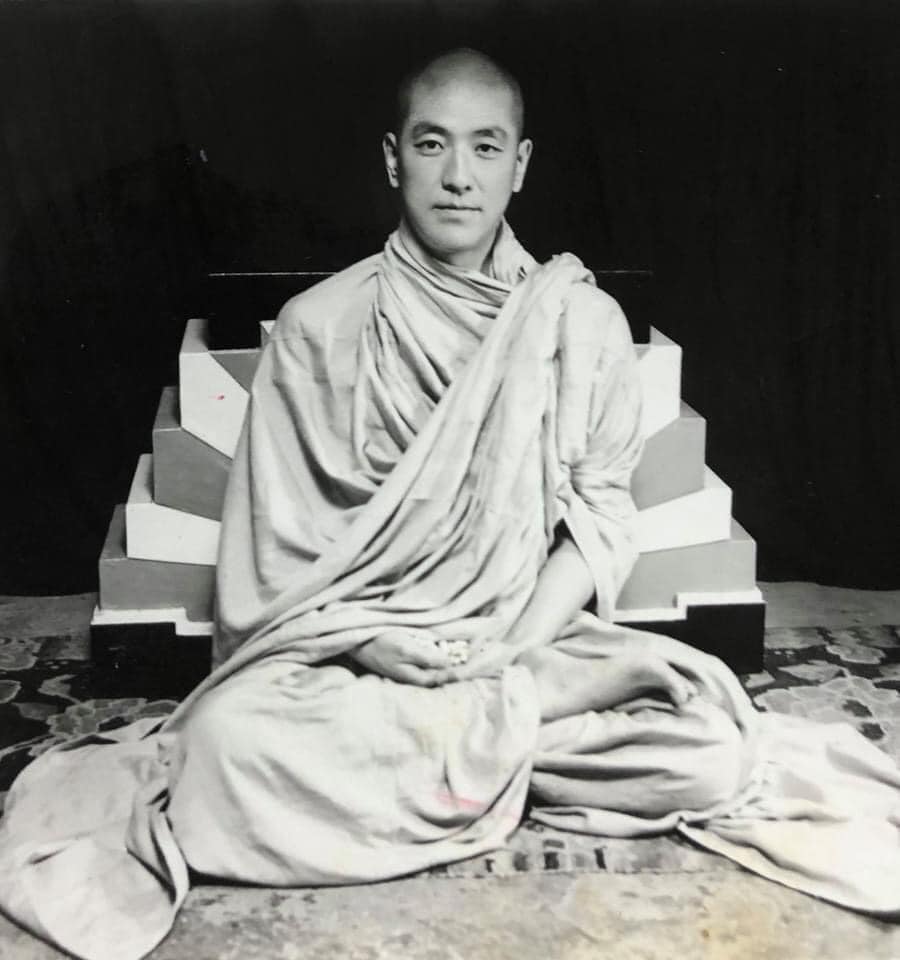

延伸閱讀:

官大偉,泰雅族,美國夏威夷大學地理學博士,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研究教學領域為:民族政策、民族地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原住民空間研究、原住民社區製圖、社區自然資源管理等。致力在原住民族土地議題上結合學術研究、教學與社會實踐,有許多和部落合作進行土地調查與發展計畫的經驗。近年來亦嘗試在文化生態、土地政策等主題上,進行台灣與菲律賓、紐西蘭、夏威夷等地區的比較研究。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