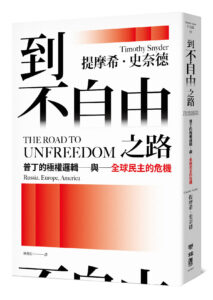文/ksiem
編按:2022年3月,烏俄戰爭爆發,至今已經兩年有餘。在動盪的世局之中,學者對於現代極權的觀察與分析,也愈漸受到大眾的關注,著名歷史學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就是其中之一。史奈德的經典著述包括《黑土》、《暴政》等,已廣為華語讀者所認知;去年七月,他的新書《到不自由之路》中譯本由聯經出版,更是嘗試從思想史的脈絡裡著手,談當今極權現況,以及眼下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全球政治危機。
聯經出版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以「在幻象、機器人與網軍的年代裡,民主該何去何從」為題,就最新翻譯出版的《到不自由之路》一書展開討論。誠如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在開場時點出,本場講座不僅談到了史奈德作為歷史學者如何梳理普丁極權背後的種種脈絡,更連繫到台灣的當下處境與歷史問題,從而引發我們重新思考「自由」、「民主」、「極權」等耳熟能詳的概念。
難以抗衡的永劫輪迴
專研西洋政治思想的葉浩,卻選擇從百年前的一則歷史事件開始說起。1925年,來到台灣的日本殖民者發現了布農族特有的「繪曆」傳統 —— 分佈在台灣各處的布農族人,會按照自己居住的地方、根據山和太陽的位置,來繪製一整年的勞作計畫。「繪曆」的出現讓殖民者們深感驚訝,打破了布農族人在他們眼中非常前現代、且毫無時間概念的既定印象,也引發了一系列爭辯;而這些爭辯,也關乎史奈德新書中所提到的兩種史觀之間的分野。
葉浩歸納了這兩種時間史觀的概念,其一是指向進步的線性史觀,另一種則是源自於尼采「永劫回歸」的「永恆迴圈」,也就是循環史觀。所謂線性史觀,是假定人類歷史的進步不可避免,認為如若反對人權、法治、自由貿易等理念,都會造成人類歷史進步上的阻礙。「永恆迴圈」則與之全然不同,而普丁政權運用的正是後者:「2013年普京訪問基輔時,就不斷重提1025年基輔大公改信基督教的事情,他說『我們(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在上帝的照顧之下,是同一個民族,靈魂是環環相扣的』,這也成為了普丁統一烏克蘭與周邊國家的重要理由。」
普丁呼喚「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復興,其背後的思想支撐,是長期仰賴著哲學家伊林的想法;而習近平卻把自己當作哲學家來塑造,宣揚一己之思想,意欲成為「哲君」。
普丁所說的民族統一,乍聽之下你是否既覺得似曾相識、又有種怪異感?那或許是因此類「統一」的想像,實際上是與現代國家的共識有所違背的。葉浩指出,早在1648年時,西方已經有一套新的主權國家體制;從西發里亞條約開始,慢慢產生了以領土為範圍的國家概念,直至20世紀時成為世界上普遍的民族國家體制。然而俄羅斯卻不承認西發里亞條約的基本精神,因此在其「統一」論述中,直接繞過了以領土實際掌控範圍為核心的國家概念。
「聽起來你就知道他跟中國很像,在這個脈絡底下,俄羅斯和中國都是反西發里亞條約、反現代國家體制的國家,所以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時間想像往前延伸到任何時間點,宣稱『自古以來就是同一個國家』。」葉浩不僅指出了俄羅斯與中國的相近之處,更看到兩者現況的分別 —— 普丁呼喚「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復興,其背後的思想支撐,是長期仰賴著哲學家伊林的想法;而習近平卻把自己當作哲學家來塑造,宣揚一己之思想,意欲成為「哲君」。因此,要與後者相抗衡,難度恐怕也會更高。
線性與循懷之外,可有新故事?
在闡述史奈德的主要論點之餘,葉浩也點出了書中未盡細緻的地方:「他(史奈德)只簡單區分了線性跟循環,可以例如在我們這個島上,卻同時擁有好多個線性史觀和循環史觀。」
如果從現實案例介入討論,會發現這兩種史觀的內部也有不少分支 —— 例如史奈德提到了美國特殊主義,卻尚未區分「舊約版」與「新約版」兩種不同取徑。葉浩詳細解釋了兩種路徑的相異之處:「舊約版」是指築起城牆自我保護的、相對孤立的政策;而「新約版」則著重萬國傳教,希望把美國的生活方式、民主價值、自由貿易等一切向外廣傳。「這也造就了美國內部的兩股不同力量不斷在輪替。」葉浩總結道。
而循環史觀也一樣,既可以用人類整體的角度來思考,但還有一種獨特的循環史觀,即是「天朝」。「朝代史觀是個典型的循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的循環史觀還要加上這一層意義。而俄羅斯的循環則是『我們曾經是一個國家、自古以來都是血肉相連,我們統一起來之後,可以成為上帝使命的行動者⋯⋯』在他們的循環中,除了時間面向,還有一重神學向度,是伊林整套神學支撐著普丁的外交政策。」
「我們認為彼此還活在同一個故事底下,扮演不同角色,而且新世代也可以增添新的故事情節,後代也可以不斷重講前代人的故事。只要仍然相信當初的奠基者,那我們就活在同一個故事;反之,如果已經不相信、不認同了,那也可以創造另一個新的故事。」
由此可見上述循環史觀,可以隨意穿梭在時間長河之中,任選時間點來進行闡述;且在這漫長的想像時間裡,只存在一個主體,且永恆不變 —— 「它叫俄羅斯,或者叫做中華民族,看你怎麼想像。」葉浩補充說,「由於這樣的史觀是徹底違反西發里亞體制的,它假想了一個在時間當中永遠不會變的主體,這個主體必然是一個虛構。只有循環史觀,才能夠預設一個永遠不變的主體。」
這也迫使我們回過頭來思考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國族?葉浩羅列了目前談及國族主義時,最主流的三大理論,也就是分別從血緣、文化、現代性觀點出發。而至於民族國家,除了上述三種起源,還衍生出「原生的國族主義」以及「公民國族主義」 —— 前者強調同文同種的一群人就應該成為一個國家;後者則更留意共聚共居的一群人之間,一同創造出公民精神。
而從古至今,凝聚社群的方法亦有多種,包括西方的聖愛,或分化敵我,或高舉友誼、正義、互惠互利的旗號,這些都在當今社會中屢見不鮮。然而葉浩卻對上述種種方式抱持懷疑,因而提出了新的「敘事共識性」:「簡單來說,就是我們認為彼此還活在同一個故事底下,扮演不同角色,而且新世代也可以增添新的故事情節,後代也可以不斷重講前代人的故事。只要仍然相信當初的奠基者,那我們就活在同一個故事;反之,如果已經不相信、不認同了,那也可以創造另一個新的故事。」
台灣的多重時間宇宙
當近年的戰火打破了我們對於「和平年代」的想像,人們愈發感受到當今世界充滿張力。葉浩引用了史奈德在探討歐洲、美國與俄羅斯時提出的雙螺旋結構來談這點:「其實台灣乃至全球,也都在兩種不同的時間想像中不斷交錯,它會構成人類的錯亂。一方面是經濟一體化、全球化、以新自由主義為主;但另外一面,二戰之後前殖民地都解殖、慢慢獨立了,所以又有民族自決的原則。這兩股勢力是同時進展的,像兩個螺旋狀會互相扭轉對方,直到有一天可能會爆掉。」
緣此話題,葉浩直接指出,其實在台灣也有著非常明顯、且十分嚴重的雙螺旋結構。「那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除原住民之外,台灣有一波一波的移民,可是最奇怪的是,來到這一片土地上的人,卻都帶著自己舊有的時間想像和史觀。大部分人移民後會想找方法融入當地,而不是一直在想著『我的根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葉浩看來,其中隱含著一種時間性的異化:「西方思想一次一次移入,不管是大清民政、日本殖民、三民主義,或是之後接受了美國的冷戰佈局⋯⋯我們可能在二十世紀的某一點,接受了別人在十九或十八世紀的思想,然後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時間想像的斷裂,最後造成的就是時間性的異化。」諸如此類的情形,也造成了這片土地上的族群異化:「我們沒有同一個民主觀,也沒有同一個時間想像,更沒有同一個時間上的政治想像。因此有人想要往前獨立,有人希望向後回歸或統一。」
「任何一個新興民主國家一定有三種人。第一種人,是仍然活在威權體制下,追隨領導者、想要救世主。第二種人,從小到大就沒經歷過威權,覺得自由很自然、民主很正常,正因如此,他們也會覺得自由沒有那麼珍貴。另外一個族群,他們從威權時代學到了民主自由的概念,也曾徹底反對過,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有轉身過的人。」葉浩所指出的這三種人同時存在,也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存在的異化,而異化很可能就成為極權介入的罅隙:「因為民主具有開放性,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居住自由、通商自由,可以允許別人進來,可是對方卻是封閉的。這是一個徹底的權力不對稱,但我們沒辦法對他們改變,他們可以永遠利用這種開放性,對民主國家徹底介入。」
「個人的生命記憶不等同於集體記憶,集體的記憶也不等同於歷史的真相。我覺得我們只是沒有現實感、沒有時間感,又愛談歷史、愛談民主,但是不知道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民主跳級生的必修課
作為「民主跳級生」的台灣,對於上述的介入及其方式,或許仍然知之甚少;而不太遙遠的威權經驗,卻又讓我們常常將所有事情的矛頭直至當權,從而造成更多縫隙。「我們就是在一連串的勒索當中,不斷奉行新自由主義,讓資金一直外流,而流進來的資金再重新回頭控制我們的房地產、金融、地方派系。何去何從?」
葉浩提出了現今難題,並接續強調:「許多人說『轉型正義是最後一哩路』,騙你的。因為那就是一種線性時間概念,他告訴你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問題是,你要的是哪一種民主?對於民主的真正的內在與工具價值,我們甚至都還沒辦法弄清楚。」
當下生活在台灣的我們,或許也該捫心自問,是否真的思考過什麼是民主、為何要自由?甚至在街頭高呼口號理念時,是否對於那些美好詞彙本身的意義,仍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們對台灣的歷史不夠認識,我們對世界的歷史不夠認識。我們缺乏現實感,活在想像跟幻象當中,而且我們不在意真理、不在意事實。我們對抽象真理也毫無興趣,對事實沒有興趣,以史觀代替真正的歷史。然後,我們失去了現實感、失去了時間感,我們喜歡談歷史但不符合歷史,有人擁有五千年的長期記憶,然後沒有五十年的短期記憶;有人永遠活在1947年,有的人活在1895年⋯⋯」
在講座尾聲,葉浩總結到:「個人的生命記憶不等同於集體記憶,集體的記憶也不等同於歷史的真相。我覺得我們只是沒有現實感、沒有時間感,又愛談歷史、愛談民主,但是不知道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當我們成為了內心空洞的器皿,極權就得到了介入的空間,可以填塞各式各樣的內容進來。「這是我們的很大的困境,而這些的困境本身與不認識思想、不認識民主有關。這也是因為我們太幸運了,因為我們是民主的跳級生。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跳級生的結果通常不是非常美好,因此他或許要去補課,尤其要去補人生的基本常識。」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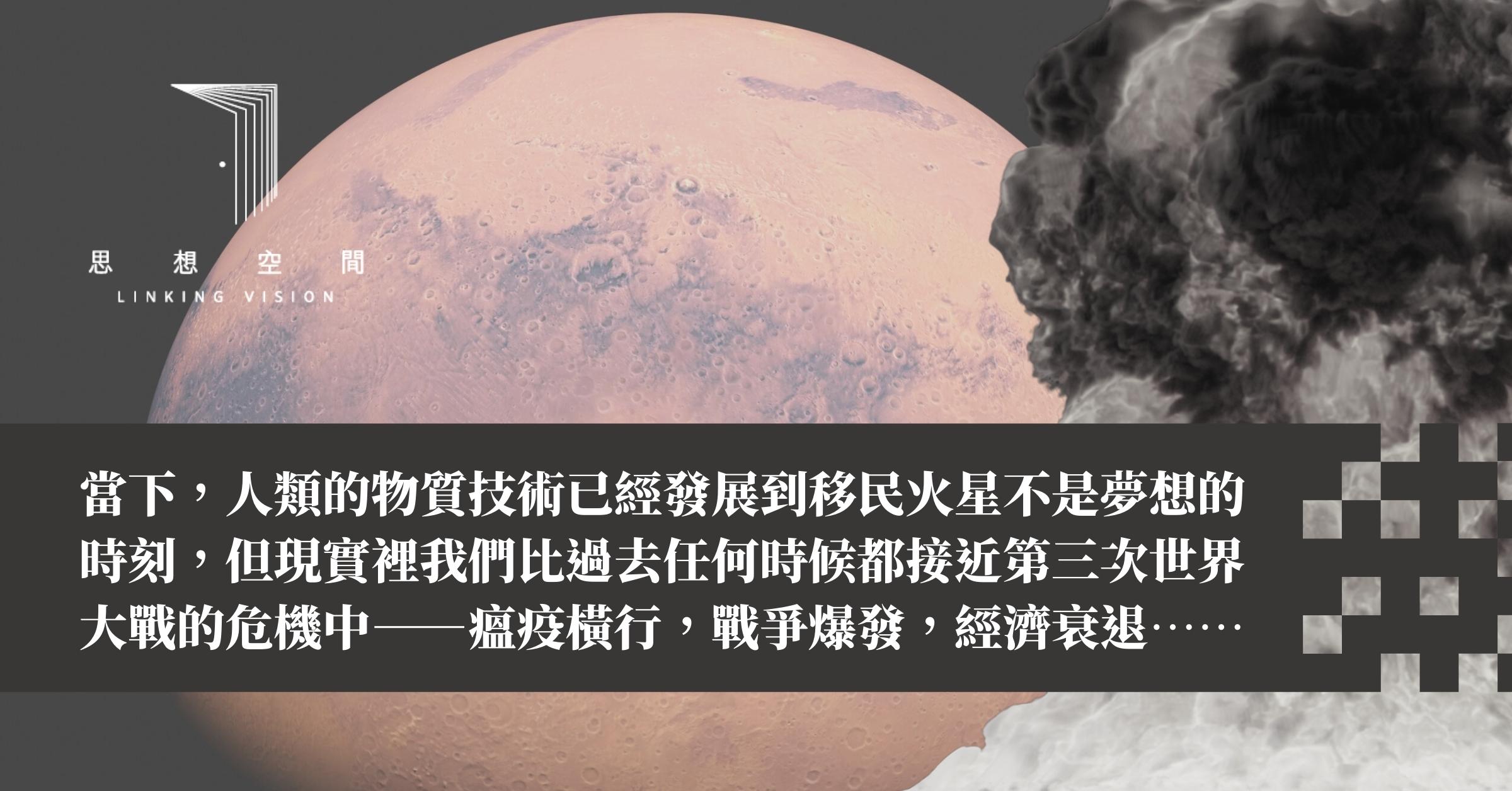
丘為君:歷史的機遇與危機

陳方隅×趙怡翔×邱師儀:戰略清晰抑或模糊?大膽想像台美關係

王宏恩:身為小國民眾,我們沒有缺乏國際觀的本錢
| 閱讀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