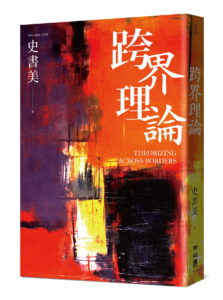文 / 史書美(Shu-mei Shih)
這本論文集收入了我數年來有關文學和文化理論的論文,大部分原先以英文寫成,在美國和英國出版,小部分原先由華文寫成,在台灣出版。因為希望這些論文有機會和華語語系各地區的讀者們交流,藉著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華人文化講座」的邀請,我把它們整理出來,用華語做了四場演講,外加一場相關的和本地學者的座談會,並在此把全書七章收集成冊,呈現給讀者。雖然,每一章有它寫成當時特定的訴求和對話對象,這些論文也表達了我一貫思維的某些共通性。
第一,讀者們可以發現,我在理論方面的思考,從來沒有背離實踐的前置性,所有立論都有所指,也就是說都是有話要說才說。第二,我從來不以為批評本身就是目的。學術界有些學者,為了批評而批評,我認為是一個有問題的作法。因為沒有理論或論述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找到別人論述裡可以批評的地方非常容易,所以批評別人的著作只為了表現自己的批評能力多麼犀利,我認為是一種膚淺的、片面的作法。況且,很多時候,這樣的批評常常是批評錯對象、誤讀、或對象不值得批評,欠缺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目的。筆者的一貫做法是,需要有所批評的時候,只批評最大或最重要的對象,因為這些對象值得批評,也擔當得起批評,所以絕對不是為了吵架或自以為是而批評,而是嚴肅地看待和處理對方的觀點,並同時建議一些新的或不同的想法以為糾正和抗衡。第三,筆者認為沒有理論建樹的批評是無用的。如果批評的目的,只是表示對對方的一些想法的不滿,那大多只是浪費時間。沒有用的想法或概念,自然而然會被讀者們淘汰,也許並不值得我們去批評。實質的批評,即使是負面的,仍然是一種給批評對象的恭維,因為,妳即使有不同的意見,對象值得批評而給予批評,仍然是一種對對方的重要性的認可。這個應該是對話的起頭,不是終結。同時,批評必須要有實質性的內容,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建樹性。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提供對象理論缺失如何可以改進的進一步的思考,形成與對方真正的對話,並把對話向前跨進一步。
同時,這本論文集雖然題為《跨界理論》,這裡每一章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在地實踐,大部分在筆者熟悉的兩個語境中產生—美國和台灣—而在這兩個語境中又有同時和相疊的對話對象,像一個維恩圖(venn diagram)一樣,有分別的語境和重疊的語境。更關鍵的是,這兩個語境又同時存在於世界這一個大語境中。由於美國和台灣各自都不是孤立形成的,所以對我來說,理論思維在踏實的在地上出發,必須同時注意這個在地的跨界性,以及在地和跨界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美國身為世界上文化和政經的大帝國,它的存在本身無疑同時是在地和跨界的,它在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在國內的定居殖民主義在在牽涉到世界所有的國家和人。至於台灣,我一向的做法是把台灣看作是世界系統的一員,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島國,因此其思想層面也需要如此看待,不應屈服於小國的偏見而認為在大世界的領域裡自己無足輕重。
我一直堅持,台灣研究應該放在世界的語境來進行,正是這個意思。台灣和美國都是定居殖民地,兩個政體都剝奪了原住民的土地和主權而存在,卻以移民社會自居,代代的定居殖民者把自己描述成移民,取代了原住民變成了「本地人」,成為人口多數。「移民」在所有的定居殖民地,包括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紐西蘭等,事實上只是定居殖民者的誤認和一種脫罪的自我認同。台灣是這個世界性的定居殖民歷史過程的一員,不容忽視。如上所述,我所有的思考自然而然是從美國和台灣這兩個分開卻相互交錯的語境中折射出的一個關係網中產生,而這個關係網又是世界性的,兩者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參與世界歷史的進程和建構。在這個關係網中,我汲汲發掘並批判不同層次的權利關係和各種階序(如種族、殖民、性別、知識等)的運作,以及以這樣的批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希望有創意、符合本地社會文化實況,又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理論思維和概念性的東西,最終的訴求是反叛西方中心和殖民者中心的理論的霸權,不僅擺脫知識殖民的迷障,更以創新的思維超越這個迷障,對理論有所創思和建樹。
因此,對筆者來說,理論從在地出發但也同時是跨界思維,它的在地實踐同時也是跨界實踐。如果台灣論述的跨界層面,常常不被認可,被歸類於邊緣化的場地,那是來自世界格局當中由政經階序所主宰的認可機制(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和認可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運作而來。所謂的在地可大可小,並不代表小的地域就缺乏意義。況且台灣的面積,事實上比英國還大。如果說英國在世界史上舉足輕重,那是因為它不光榮的全球殖民史。台灣也比希臘大,而希臘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一個國家的大小,因此和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無關。台灣的重要,在西方的學術界常常被忽略,也正是認可機制和認可政治的問題。本書的第一章爬梳在世界文學的領域裡,哪些認可機制使少數、被邊緣化、第三世界、小國、小語言、非白人的文學被擋在所謂的殿堂外,並且分析這些機制運作的模式。這一章的特色是它的批判性,揭發西方中心的文學殿堂論,為一種自我反射(self-referential)的滔滔邏輯(tautology),以支撐西方的優越感。為了批判而批判,如前所述是不足夠的。
因此,本書的其他章節接著提出不同相關領域當中創建新的理論的可能性。配合第一章對世界文學認可機制的批判,筆者在第二章進一步對世界文學的形構提出一個不同的方法,提供替代西方中心機制的另一套觀點。這裡,筆者從世界史出發,把世界文學界定為文學參與世界史、為世界史的一分子,並對世界上的某些重要事件提供不同認知的載體。因為世界史是一個關係的場域,所有文學,不管是西方或東方、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大文學或小文學,都是這個關係網的一員,也是形成這個關係網不可或缺的行動者。這樣的世界文學的概念,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學,同時給予了小文學、非主流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原住民文學等被邊緣化的文學同等的存在價值。而用這樣的方法去研究世界文學,很明顯是在比較的領域上,因此世界文學方法論其實也是比較文學方法論,我稱它為「關係比較學」。就此,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姊妹篇,第一章開啟的思維,由第二章完成。第一章以批評為主,第二章則提出一套新的理論取代第一章批判有關世界文學的思維。
同樣地,第三章開啟另一個對筆者一貫關注的領域的批評—所謂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首先揭發它自以為的普遍性,實為一個特殊性的包裝。在「理論之死」論到處蔓延的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回顧批判理論,並提出一個新的認知批判理論的模式。筆者和長期以來的合作者李歐旎(Fransoise Lionnet)所共同撰寫的這一章,企圖把批判理論落實到不同在地的語境中,並主張最能夠對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世界擴展以降的世界有普遍性和說明力的批判理論,事實上來自曾經被西方殖民過的國家,如加勒比海諸國等。所以,我們所謂的批判理論是由一個永不止息的混語創建(克里奧化〔creolization〕)的過程產生。雖然這一章沒有提到台灣,我們可以想像,在中華帝國霸權的陰影下,對經歷過東西方諸國連續殖民的、也是現在進行式的定居殖民地的台灣來說,批判理論也必定是在殖民混語化的境況下產生的。
因此,為了呼應第三章對批判理論的思考,第四章就直接了當地進入對台灣理論的一些提議。這兩章因此也是姊妹篇。第四章提出以下問題:立足台灣的批判理論是什麼模樣,它在什麼樣的歷史境況形成,而它可能提供的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理論概念又有哪些可能呢?雖然看起來第三章的論述架構是跨界的(歐洲、美洲),而第四章是在地的 (台灣),但是兩者同樣在世界性的語境中產生。不論是第三章批判的法國批判理論,提出理論混語創建的概念,或第四章分析台灣在全球定居殖民史上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於美國主義在台灣至高無上的地位,導致的華/英混語創建的理論概念等(如上面提到的「滔滔邏輯」,或謂「套套邏輯」),台灣理論在此如同第三章提到的加勒比海理論,是一種混語的理論(creolized theory)。另外,這一章其實有更踏實的在地層面。這是筆者和廖朝陽、梅家玲、陳東升合組的「知識台灣學群」的成員們討論之後寫下的我在這一方面的報告。我們合編的幾本書,都是著眼於抗衡第一章所談的理論境界的認可機制的壓迫、第三章西方中心的批判理論之死之後,如何對台灣理論的建構有所建樹性。
接下來第五章,沿著批判理論在地化的路線,討論女性主義理論在台灣的演繹和混語化,尤其是當台灣的主流女性主義面對外來的理論權威時的尷尬,牽涉到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問題,更落實在一個真正發生的事件上。當在美國執教的一位印度裔的、後殖民理論的頂尖學者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到了台灣,竟然能發生什麼事呢?她如何和本地的女性主義者們對話?一向自以為是西方理論下游的台灣,和美國來的大理論家對話有可能嗎?而這個(沒有真正)對話的邂逅代表了什麼?台灣為定居殖民地的這個事實,又如何將這個邂逅多加了一層其他重要的意義或缺失?這個(沒有真正)對話的邂逅與缺席的原住民女性主義者有何關係呢?筆者在在關注的是「(不可)通譯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問題,因為這也是跨界相遇的最大絆腳石或最大的潛能所在,但看相遇時各方的態度和對在地的訴求度。史碧娃克和台灣主流女性主義者們之間有(不可)通譯性的問題,台灣主流女性主義者們和原住民女性主義者們也有(不可)通譯性的問題,那史碧娃克和台灣的原住民女性主義者之間大概基本上是完全不可通譯的吧?因為後面兩者其實連見面都沒有,可能互相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如果台灣一直只是被動地引進和運用西方理論,那史碧娃克在台灣的角色很明顯地有問題。她是一位理論大家,因此台灣的女性主義者們,只有被動地聽她說的選擇嗎?史碧娃克有沒有任何基本應該認識台灣的責任?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在加州大學歷史系的同事,也是英國新馬的領導人物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到台灣訪問時,他為了準備,讀了大約十多本有關台灣的書,後來也寫出了一篇非常犀利的有關台灣的文章出版,讓我非常佩服。史碧娃克好像並沒有任何對台灣的關注,很難說她連一篇有關台灣的文章都看了沒有,難怪根本沒有和主流以及原住民女性主義者們對話的空間和可能。付出需要是雙方的,批評也應該是雙方的,而這個批評為的是擴展對話的空間和策略性合作的可能,這就是台灣原住民作家阿所說的「相互的批評」。
在「批評加立論」的思維邏輯下,第六、七章延續之前的篇章,把空間(space)的跨界性落實在地方(place)的跨國性,提出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的概念,以及把跨界本身即是比較的思維落實在種族的概念中,提出全球語境下的種族論述,必須以比較的方法進行分析。這裡比較的意義,如同第二章所述,不是比較兩個或多個不相關的論述或文學,而是把世界各地相關的論述用關係學的角度串聯起來。如同由上而下地、由國際資本掌控的跨國主義,由下層的、弱勢的群體齊集起來的弱勢跨國主義,也需要用比較的、關係性的、跨界的思維去建構。而種族(race)這個概念在西方被發明,並以其名強行設立世界各民族國家和人種的階序,原來也是關係性的、比較視野的產物。如果沒有比較、就沒有階序。權力即是一種關係,而沒有空間或在地是權力的真空。因此,跨界和在地的思維最終都是比較的思維,使有關比較方法論的探索更為緊要。以此為序。
——史書美於美國洛杉磯
延伸閱讀:

理論思維的跨界形構和在地實踐——史書美《跨界理論》自序

陳力深:不只是「約砲神器」——交友軟體的政治性

戴遠雄:耕植一種「去歐洲中心」的跨文化論述——讀史碧瓦克《在其他世界》
| 閱讀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