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雪虹(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我們沒有自己的房子。我們一直住在租來的房子裡。那是別人的房子。沙發是別人的,馬桶是別人的,做愛的床也是別人的。對一個有潔癖的人來說,這是很難受的。你得花上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這樣的生活。需要拼命地打掃房子,需要花心思佈置房子,需要讓整座房子充滿自己的氣息。這就是安頓下來的意思。好在你總能做到。
先前我們住在金台西路的一座老公寓裡。它和這個國家一樣老。因為住在一樓,所以我總有一種錯覺,以為我們住在一棟小平房裡。房子後面有一座荒涼的院子,那裡長滿了野草,還有一棵石榴樹和幾棵青菜。房子前面有一個絲瓜棚,夏天會長出黃色的花朵和彎彎的絲瓜。清晨,月亮還在,清道夫竹掃帚寂寥的唰唰聲就會在窗邊盤旋,那個時候我就不敢再睡下去了。
然後是廣順南大街。公寓有三十層,對面是新世界百貨和索尼大廈,從早到晚都會有憤怒的汽車鳴笛聲,深夜辦公樓總是燈火通明。時間長了,這一切都使人感到壓抑和疲憊不堪。所以我們常常到旁邊的小河散步,雖然冬天河流乾涸、爛泥淤積,夏天河水渾濁,水面上漂浮著密密麻麻的青苔。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周圍的人是怎麼買房子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人人看起來都像能幹又獨立的中產階層。
我們從來沒想過要在這裡買房子。即便想買,我們也負擔不起。曾經夏木的父親會為房子的事顯得憂心忡忡。他慨歎自己沒有能力給孩子買房。不過他自己也沒有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房子。他的父親把房子和拖拉機給了其他兒子。偶爾他會建議我們去住公租房,說公租房的租金很低,可以節約不少錢。我不知道公租房長什麼樣子。不過現在他也沒再提房子的事了。
我的姐弟們都有自己的房子。那些房子是他們自己掙錢買的。我們的父親不會給兒女買房子。他說一個人一旦成年了,就不應該從家裡拿東西,哪怕是一卷衛生紙。父親住的房子是用爺爺的遺產換來的。他應該會一輩子守著那座房子。死後好歹留下一座房子,不至於敗光祖輩的財產,這是他的執念。
忽然從某一天起,我們身邊的朋友都陸續在北京買了房子。後來甚至有人在希臘買房子。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我和夏木開始參加暖屋派對,我會站在書櫃前看朋友喜歡讀哪個作家的書,會看墻上掛的照片和海報,會看衛生間的洗漱台上擺著什麼護膚品。我當然不會碰那些東西,因為我也不喜歡別人碰我的東西。
耐人尋味的是有的人把房子租了出去,然後出國深造或工作了。他們的房子在他們離開後成了一個又一個北漂族的棲息地。我們在露露去巴黎前和她吃了頓飯。飯桌上,她對我們說她剛把房東的房子買下來了。「我無法像你那樣,為了寫作而忍受貧窮。」露露對我說。我暗暗吃了一驚,因為那時的我對自己的處境或未來並沒有看得很清楚,想的盡是「有花堪折直須折」。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周圍的人是怎麼買房子的。我在馬來西亞的親友對此也感到納悶。偶爾我會從朋友那兒或網上聽說各種買房子的故事。我還聽說了「六個錢袋子」。那都是些令人嘖嘖稱奇的事。大多數朋友都是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人人看起來都像能幹又獨立的中產階層。
去年春節,我和夏木去小馮家拜年。小馮和妻子都是北京人。他們剛把一居室的房子賣了,然後買了一間兩居室的公寓。我們難得聊到了房子。
「這孩子還沒長大就已經有三套房,」小馮指著他的兒子說,「所以他壓根不需要打拼。」三套房指的是小馮夫婦的房子、孩子爺爺的房子及姥姥的房子。
「所有父母都會支持孩子買房,這是理所當然的。你的錢不留給孩子,還能給誰呢?」小馮說。
「這也是一種投資。」我們的另一個朋友說。
和漢娜在一起時,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光景。漢娜是我們的德國朋友,這些年來在不同國家當駐地記者,一直沒有買房的念頭。「我們有的是自由!」她調侃道。不過她已經有足夠的存款了,說不定將來回德國後,她會給自己買一間公寓,從此安度晚年。
其實此時此刻我最想去的是法羅島。那是我能想到的最遙遠的天涯海角了。遠離中心。「法羅島」在哥特蘭語是「旅人的島嶼」的意思……
我讀傑西卡 · 布魯德的《無依之地》時,心裡想的是約翰。約翰是我朋友露西亞的兒子,也是我從前的學生。高中畢業後,約翰沒有像他的同學那樣上大學,而是選擇加入美國海岸警衛隊。這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岸警衛隊的格言是拉丁文Semper Paratus,意即「隨時準備」。為了實現理想,約翰在畢業前幾個月就努力地減肥,最終成功減去大約三十磅。他已經準備好離開父母,在美國過一個成年人的生活。這將是他第一次正式在美國生活,因為他從兩歲起就定居國外——塞內加爾、洪都拉斯和中國。夢想成真後,約翰將自己的制服照設置為臉書頭像。照片中的他看起來健碩、穩重和自信,他再也不是從前那個臃腫、不著邊際的男孩了。露西亞為兒子感到驕傲,偶爾她會給我看約翰的工作照。約翰到過的最遠的地方是美加邊界。眺望著遼闊的湖面,他躊躇滿志,堅信這只是美好生活的起始。
只是短短幾個月,約翰就險些被一場意外擊垮。在巡邏船上,他不小心摔斷了四根肋骨,出院後不久合同就被解除了。他被迫從宿舍搬出來,父母在美國沒有房子,他只好寄居在密歇根的叔叔家。新冠爆發後,在醫院當清潔工的嬸嬸介紹他到醫院工作。我一直不清楚約翰的職業是什麼,只從露西亞那兒聽說他除了每天都要替人測體溫之外,還有機會學習放射學技術,未來也許可以成為放射技術師。他們一家始終對那場意外耿耿於懷,露西亞認為約翰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海岸警衛隊的做法過於殘酷。約翰變得鬱鬱寡歡,體重又恢復到從前的樣子了。
「他差一點就無家可歸。」某個冬日午後,我和露西亞走在路上,又聊到了約翰的近況。我們設想了各種可能性,包括鼓勵約翰來中國上大學。
「他還得先學好中文。」露西亞意興闌珊地說。
所有建議或想法似乎都瞬間被推翻。和從前一樣,這場對話最終以沉默告終。風越吹越烈,我們匆匆走進一家韓國進口超市裡。
無家可歸。露西亞用的是Homeless這個詞。我腦海中浮現出電影《無依之地》中,芬恩對從前的女學生說的那句話:
「我不是無家可歸,我只是無房可歸。」
在另一張飯桌上,也是一次暖屋派對上,小馮對我和夏木說:「該輪到你們買房了。」那時我才意識到在場的所有人都擁有自己的房子,他們正饒有興味地聊著房價、設計草圖和家具。
「我就是個無房可歸的人。」也許我應該這樣自嘲。
這個夏天我們就要離開北京了。我已經沒法在這裡生活下去了。我們打算搬到天津,租一間更小的房子,過更清靜、簡樸的生活。其實此時此刻我最想去的是法羅島。那是我能想到的最遙遠的天涯海角了。遠離中心。「法羅島」在哥特蘭語是「旅人的島嶼」的意思,那也是一個在其他地方不怎麼受歡迎的人(這說的不就是我麼?)的聖地。
多年來,我總是被「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這樣的話深深觸動。我想我從來沒有認真思索關於「家」和「房子」之間的聯繫。畢竟要憂慮的事情已經足夠多了。我的父親在他步入中年後一直都被各種與房子有關的事困擾,母親則終其一生都受困於房子(有形的房子和無形的家)之中。諷刺的是,她卻沒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這是她臨終前最後,也最卑微的願望。
也是這些故事和經歷讓我在讀《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時有了更深切、痛苦的感受:
「如果這個時候沒有房子該是多麼淒慘啊:他將會死在圖爾斯家的人旁邊,死在那個巨大的支離破碎的冷漠的家庭裡;把莎瑪和四個孩子留在他們中間,留在一間屋子裡;更糟糕的是,虛度的一生都不曾努力讓自己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活著和死去時都像一個人被生下來那一刻,毫無意義而且無所適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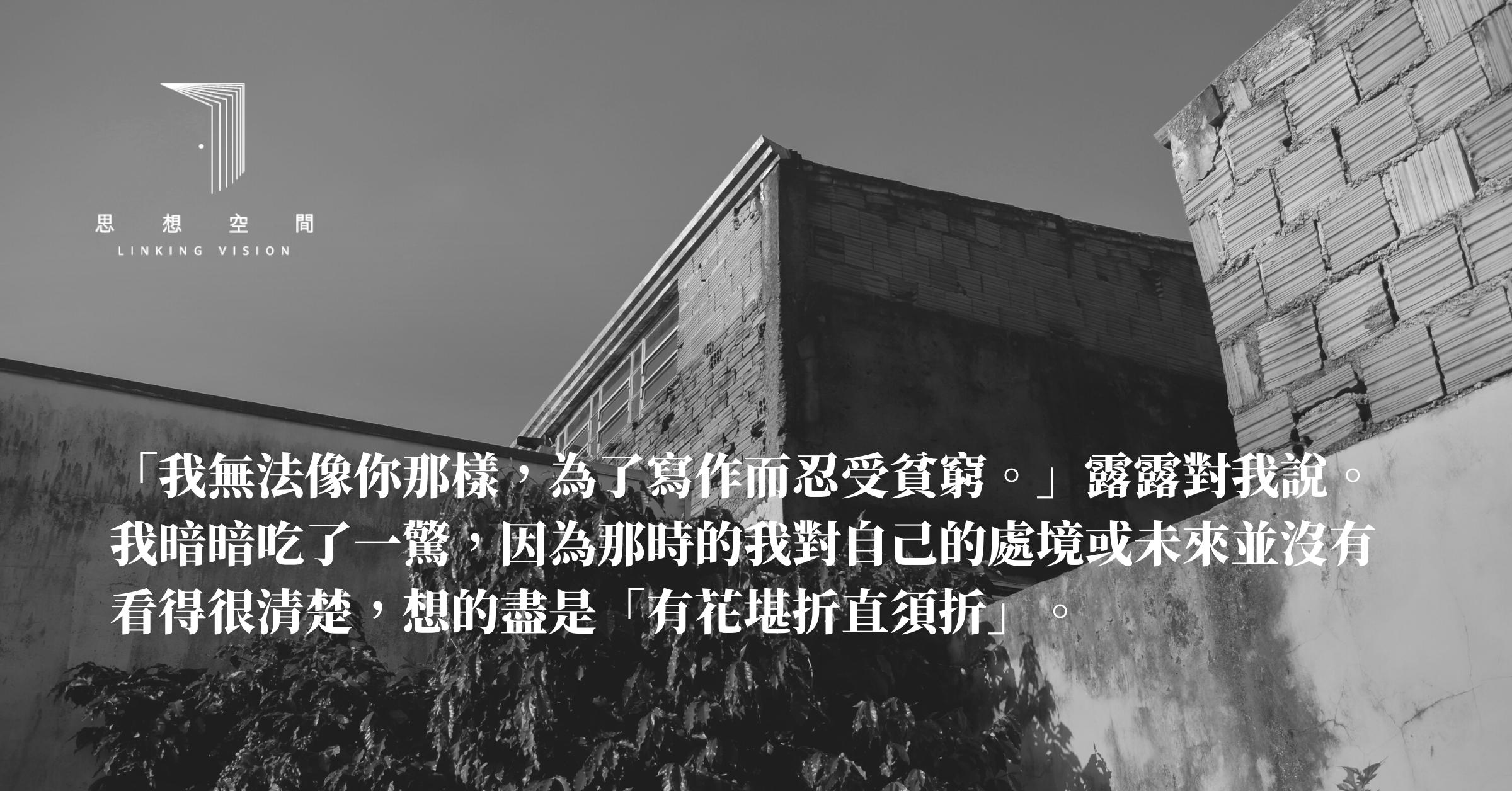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