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雪虹(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在廣場舞盛行以前,這裡的女人跳的是交誼舞。男人也跳,他們牽著女人的手,挽著她們的腰,和她們一起在公園的樹蔭下扭呀扭,轉呀轉。
我的房東吳阿姨每天晚上都在北土城公園跳舞。她的房子就在公園後面,從公園的最深處沿著斜坡走到盡頭就能看見。那是軍隊幹部休養所,吳阿姨的先生是軍人,已經逝世多年,她繼承了他的房子。房子陳舊又黝黯,瀰漫著隔夜菜和舊物的氣味。最令人沮喪的是那間浴室。浴缸經常堵塞,一把已被遺忘的木刷底下爬滿了不知名的細小蟲子;門邊放著洗衣機,導致門永遠半敞著;沒有可以放置衣服的地方,而且還得小心翼翼地,以免撞倒吳阿姨的東西或不小心碰掉掛著的衣服(骯髒透頂的瓷磚地板!)。我討厭在那裡洗澡。
吳阿姨把三間臥室租給我們這幾個女孩,自己在主臥吃飯、睡覺和看電視。我的室友艷艷是技術工程師,對面的女孩分別是攝影師和影視化妝師。她們都是北漂族。在搬到這兒之前,艷艷住的是半地下室。後來我的導師也說我是北漂族。他是對另一個教授說的,恰巧被我聽見了。
那時我還在上研究生院。不上課或不打工的日子,我就待在房裡。吳阿姨會進來找我聊天,或是在我經過她的房間時叫我進去看《北平往事》。她喜歡邊看邊評論女演員的相貌和衣著,還喜歡慨歎自己韶華已逝。「還很年輕呀」,我會笑著說。
她確實不老。她早早地就結婚,女兒妞妞已經上大學了。眼下她沒什麼可愁的,租金足以使她吃飽穿暖,所以她可以把心思放在跳舞上。她也真的這樣做了。
她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講述她在舞會上的見聞。不是對其他女人評頭論足。她眼裡好像並沒有其他女人。她聲稱自己是舞會上最漂亮的女人。
她似乎無時無刻都不在為晚上的舞會做準備。她買新裙子和中跟鞋,花大量時間在洗秋衣、胸罩和試衣服上。穿好衣服後,她會在過道上走來走去,偶爾還會在鏡子前走舞步。「阿姨漂亮嗎?」她喜歡這樣問我。那時候她的眼神會很嫵媚,眼角擠出一堆魚尾紋,笑盈盈地等著你讚美她。
廚房裡永遠有一堆雪梨。吳阿姨每天都燉銀耳雪梨湯。從舞會回來後,她會到廚房喝一大碗雪梨湯。她興致勃勃地對我們講述她在舞會上的見聞。不是對其他女人評頭論足。她眼裡好像並沒有其他女人。她聲稱自己是舞會上最漂亮的女人。也許這是真的。有幾次我去看她跳舞,她的確是最令人矚目的。看得出來她精心裝扮過。她那粉色連衣裙的裙擺在晚風中搖曳。她的舉手投足都在為了呈現自己完美的一面。抬頭挺胸,輕輕晃動長長的馬尾辮,矜持的笑容,雙眼要時不時望向遠處。還有恰到好處的沉默。
白天,吳阿姨會請舞伴到家裡來。最常來的是那個高挑、拘謹的王叔叔。在王叔叔來之前,吳阿姨會穿上粉色的裙子,裙子下面是粉色的秋衣,一會兒檢查睫毛,一會兒梳理劉海。「王叔叔帥嗎?」她會這樣問我。王叔叔不會逗留很久,因為他們要去舞廳跳舞。我總覺得那是個神秘、奇妙的地方,因為我不知道哪裡會有這樣的地方,外面是光天化日,裡面是夜色溫柔。這樣的地方使我想起漠河舞廳,多麼地孤獨和憂傷。
吳阿姨一直想再婚。和舞伴去舞廳對於她是一場約會,晚上的公園舞會只是相親,是正式約會的前奏。她沒有想很多柴米油鹽的問題,她要的是可以一起玩樂的伴侶,最好是一段浪漫的愛情。她和那個軍人的婚姻來得太突然,她甚至沒能來得及品嚐愛情的滋味。「我太年輕了,才十八歲,一個外地女孩在北京打工,什麼都不懂。」她感慨道。那是一段帶有性暴力、誘騙和權力壓迫(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階級壓迫)的意味的婚姻,令人不免聯想到《雷雨》或阮玲玉的故事,震驚、不可思議,但時過境遷之後,留下的卻只有寬恕、淡然和懷念。
軍人氣急敗壞,先是窘迫地往後退一步,然後又逼向吳阿姨。他們這樣一來一回,像是在跳一場滑稽、蹩腳至極的圓舞曲。
這個小區其實一直隸屬於部隊,只不過當時我並沒有太在意。我不知道這可能意味著不自由和壓制。你只知道門衛室裡永遠坐著兩個沉默的軍人。那又怎麼樣呢?畢竟那是你當時所能找到的最便宜、合適的房子了。一個寒冷的初春,三個軍人來到吳阿姨的房子,聲稱他們發現了我這個外國人的存在,命令我立即離開那裡。所有人都大驚失色,只有那三個軍人仍然緊繃著臉。
「她必須馬上搬走。這裡有國家機密,不允許外國人進來。」軍人指著我說道。
「你們就不怕萬一我出什麼事嗎?我可以去大使館告發你們。」我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
「這我管不了,總之你現在就得離開。」
一番爭執之後,那個年紀較大,官階較高的軍人有點不耐煩地對吳阿姨說道:「其實這兒根本就不允許你把房子出租,你這是違反規定。」
吳阿姨跳了起來,衝上前,聲嘶力竭地哭喊著:「你們就只會欺負我這個寡婦!我沒有錢,我們母女倆怎麼活下去?你們就是看我沒男人,所以都來欺負我……」她一邊叫嚷,一邊向前逼近,穿著粉色秋衣的身體抵在軍人的胸口上。軍人氣急敗壞,先是窘迫地往後退一步,然後又逼向吳阿姨。他們這樣一來一回,像是在跳一場滑稽、蹩腳至極的圓舞曲。
這當然是一場無望的反抗。在三個軍人的監視下,我匆匆收拾東西,離開了吳阿姨的房子。往後的那幾周,我住在不同朋友的房子和公共浴室裡,直到找到新住處。我後來有回去取剩下的東西,並向吳阿姨告別。她還繼續參加公園舞會,依舊穿著粉色的裙子和梳著高高的馬尾辮。但我再也沒有去公園看她跳舞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差點就忘了它。不過我想我知道為什麼我會那麼在乎浴室的整潔,會羨慕那些擁有寬敞、乾淨的浴室的人。許多年後,我和一個馬來西亞的老同學見面,驚訝地發現這件事已經被蒙上了諜戰片的神秘色彩:
「我們還以為你被中國共產黨懷疑是間諜了呢!」同學神秘兮兮地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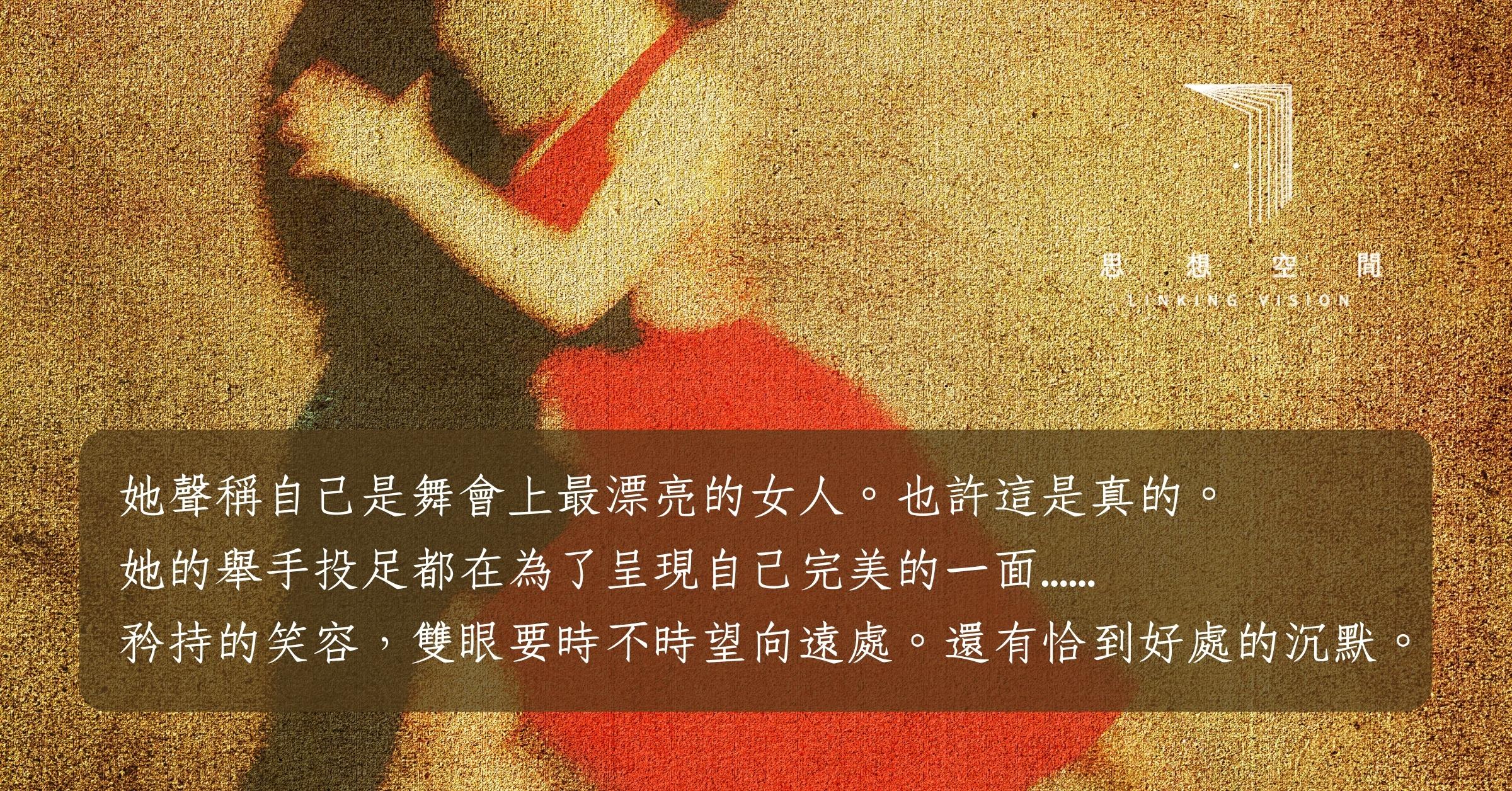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