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為桃園學研究中心於2021年11月24日主辦之「日治時期風景的移植、創造與在台日本人——以台北行道樹栽植為例」講座內容紀要。
| 講者簡介 |
主講:顏杏如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
主持:鄭政誠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
為甚麼要大規模種椰子樹呢?這與台灣作為日本的南方想像甚有關係。台灣正是類似日本南方想像的實驗場,於是移植的另一義,即為想像的移植。
樹木是我們生活常常遇到的背景。走在台北的街道,乘搭公車的時候,我們都會看到一棵一棵的樹木在視線中出現與消失。但如果我們誤以為那些樹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同一個樣子,這個講座就在翻轉我們的認識。
行道樹,被移植到台灣的南方想像
顏教授從行道樹窺見整個殖民都市工程的展開與變化,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以小見大的研究。事實上,「自然」跟「人工」在都市空間並不是二元對立的,從都市中放置象徵「自然」的樹木,給予空間色彩與變化。早期日治時代台灣都是以政府鼓勵、民間栽植的想法執行。自1901年起,官方才開始介入,在中山北路栽植的相思樹,理由是防風、枝葉繁茂,主要是功能性為主,以容易取得為優先。相思樹則是其中一類容易取得的樹類,北台灣的一些淺山丘陵特別容易看到相思樹。這些植樹以記念植樹為主(天皇生日、逝世) 。
1910年拆掉台北城建立三線道路,並在路旁立下植樹帶。顏教授考察並比對了三線道路的樹種、樹的數量與擺置方法,並引用日文材料,如田代安定在台北總督府任職所寫的《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一開始的特徵是台灣原生種比較多,以混植為主,比如蒲葵與洋紫荊,花朵鮮豔。然後在1936年之後,即日治後期,則有整齊、劃一和井然有序的追求,北三線(蒲葵)、東三線(大王椰子)、南三線(茄苳)、西三線(楓香)都是單一樹種的,常見的榕樹則去掉了。
這些樹種植模式的變化首先來自管理機構的變革,從沒有專職管理行道樹的部門,到後來庶務課,再後來(1926)土木水道課接管,然後1932年行道樹開始被納入都市計畫中,配置了技術員。另方面是跟人們心中何謂都市美有關,植木者對於原來混植的狀態感到不滿且作出了批評。因此,對於甚麼是好的都市想像,可以用從實用到美觀來概括。但甚麼是美觀?這又可以從南國想像與台灣風景兩方面來談起。
前者值得注意的樹種是大王椰子。為甚麼要大規模種椰子樹呢?這好像跟行道樹的遮陰功能沒直接關係,這卻與台灣作為日本的南方想像甚有關係。甚至可以說,台灣正是類似日本南方想像的實驗場,於是移植的另一義,即為想像的移植。這個南方性並非內在固有在台灣,而是相對於一種殖民現代的彷效或競逐心理,日本自我期許為大東亞中最為先進發達的國家,於是想要學歐洲在東南亞各國的殖民地的植物。因此摩天大樹的視覺觀感便容易滿足所謂壯觀景色的需求。
此外,出身地域對於都市植木者的南方想像有著質的差別。比如在鹿兒島(九州地帶)成長的田代安定,趨向於往外找熱帶風景,他的熱帶是更「南方」的。對於山形(東北地區)的芳賀鍬五郎而言,台灣本身的樹木就很熱帶了。熱帶有著多種的可能性,所以說南方作為一個意符脫離不了身心對空間的體察,在想像之外仰賴實際感受。
樹種的選擇與觀看風景的視線包裹著個人、時期的差異而變動。而在時代心理的構成方面,則具有眾多的自我/他者在拉扯,西方文明、南國想像、母國懷思與台灣風景共冶一爐。
熱帶風景的文化論述
誠如前面提到,在日本正在冒起的帝國時期,熱帶風景是可欲的,熱帶風景以植樹為具體呈現。然而熱帶風景並不足夠滿足人們內心的渴求,由於鄉愁懷思在日本本土植物所形成的風景得到內化,也難怪他們想要隨著季節變化的樹木顏色。而最常見的榕樹消失的原因也在於此,楓香就變成了新的寵兒。
對於榕樹的評價變化,從被稱讚雄偉、四季常綠的優點,到後來一些主觀的批評也是針對此特徵:榕樹常綠使得台灣的風景缺變化、讓世界很陰暗使人厭倦。甚至其時有種對此而來的優生學想像,說樹色不變導致灣生的感受力變鈍。有著熱帶的精神衰弱等。這也隨著越來越多兒童出生,人口增長與分佈改變了人看待樹的思維。如此種種,表面是自然環境與人類不協調,在深入探討下卻看到是文化的作用。
在另一邊廂,接近二戰的時段,在台日人也開始思考甚麼是台灣獨有的風景,從模仿西洋近代風景到建立大東亞風景,把往外尋找轉而向內凝視,在此過程中把「台灣性」納入考慮之中。這個追認台灣風景是官方/民間的集體性呈現,可以從上至徘句、民謠,下至小學生的作文。把殖民地放進國族打造的歷程。當中包括定義甚麼是原生種。楓香樟樹也是這樣順著這個潮流逐漸為人所喜愛,因為他同時滿足了「日本想像」與「台灣獨特性」的條件。
行道樹除了作為文明都市的象徵,也可以作為常民記憶的地標。常民記憶看重的,本身可能跟官方所欲望的現代與南國風情有所不同。在把相思樹與榕樹撤換的時候,有些在台日本人有保留原風景的呼聲。顏教授展示了一個大正町(雙連跟中山站附近)的集體繪圖,是戰前日本人的聚居地。這幅地圖也同時提醒了我們,地圖除了呈現「客觀」的地景,實則傳遞了畫的人看到了甚麼,他關心或側重了甚麼,戰後返歸日本定居的人回想戰前居住的地方,隨著記憶流逝,作為生活背景的榕樹/相思樹竟成為了一個記憶點。行道樹好像就是那些過去時間的錨一樣。
由此可見,顏教授的研究針對在台日本人的體驗,其實也是在反思後殖民研究的一些盲點。若然將殖民關係是把殖民者簡化為壓迫者,與被殖民者作為受害者,那其實有許多人的經驗並不是那麼極端。在台日本人就是台灣的生活經驗與日本經驗的並存,在台日本人包括公務來台、旅居、定居、考察的人,也有灣生,是一個帶有高度流動性的異質社群,他們這些人跟日本本土的心理跟經驗距離不一,可以看到殖民連帶的群體多樣身分。當中的焦點是,在台日人蘊涵了遷移者的向度,所以那個再造也不只是風景的再造,同時是身分的再造與存在感受的再造。特別是日本人的在台意識,也說明了台灣意識的概念不只是被一般而言「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所主導,據顏教授的話來說,從溫帶到(亞)熱帶的遷移經驗,是他們一連串協商跟適應的過程。
在這個演講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轉譯的過程,都市綠化是殖民地的統治政績的再現,不過對於樹的理解則不限於殖民者的評價。綜合而言,樹種的選擇與觀看風景的視線包裹著個人、時期的差異而變動。而在時代心理的構成方面,則具有眾多的自我/他者在拉扯,西方文明、南國想像、母國懷思與台灣風景共冶一爐。此外,實物與想像的互動亦不容忽視,在實用性以外還兼及生活、追求美學的面向。這些面向都不能不與打造理想的殖民與政體的焦慮一起思考。在台日人本身混雜而多變的植樹追求,更多是和台灣風景互動、對話的結果。對於這個論題的延伸思考,顏教授提到他研究的時間段是日治時期台北地區的行道樹,至於國民政府來台後為甚麼繼續沿用日治時代的樹種的原因,倒是值得進一步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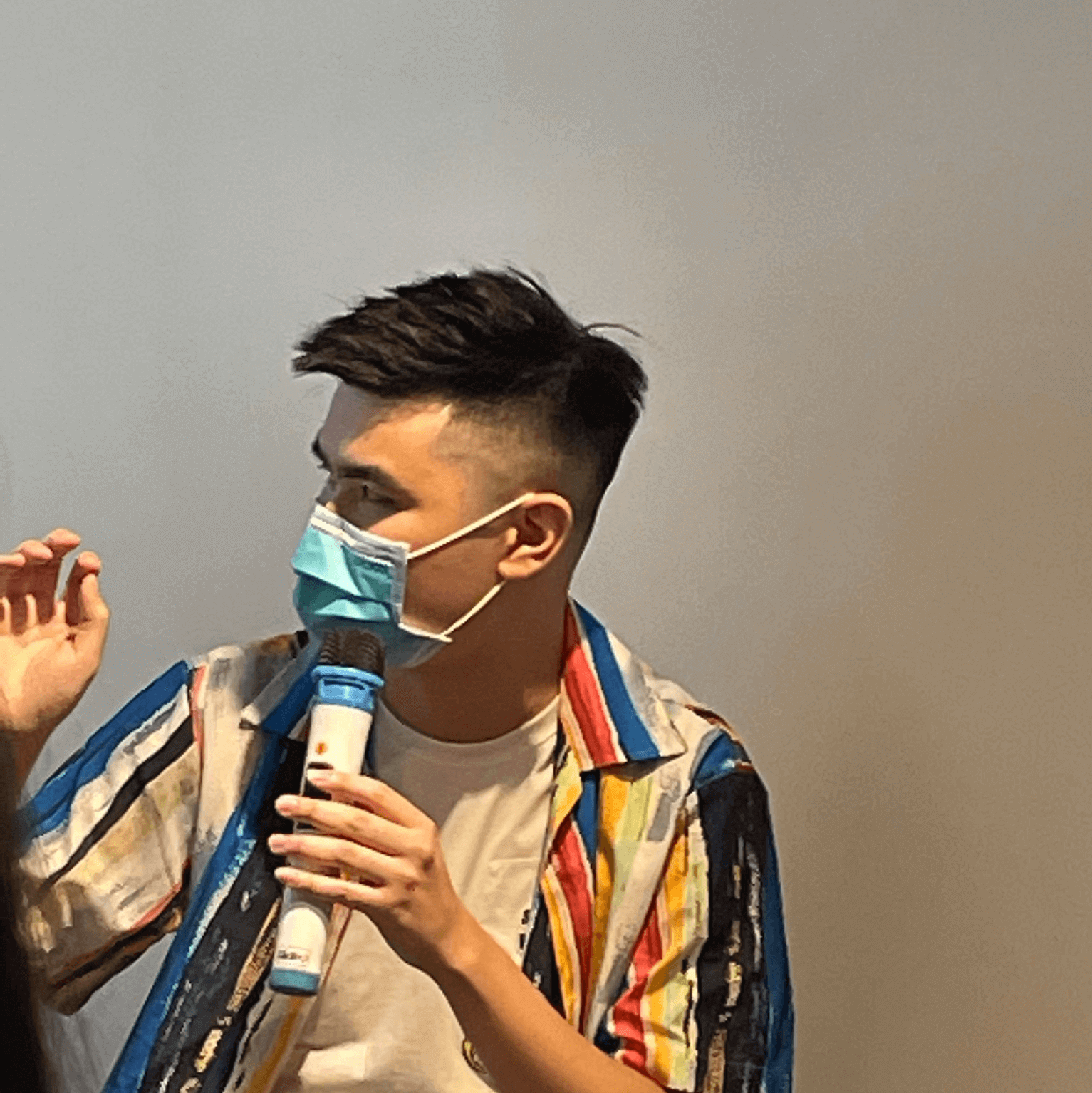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