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編按:有關時代劇《茶金》「4萬換1塊」事件的史實討論,正正昭示著現今台灣的政治處境之下,台灣史討論的風氣與風險,而台灣史研究者許雪姬也早在其梳理文章中提出了這一趨勢。我們隨著許雪姬的視角,回到台灣史研究日漸成為顯學、而漸漸又顯現出險學一面的過程之中,再探風險何在、研究者何為。
本文節錄自《思想16:台灣史:焦慮與自信》,2010年10月出版。原文題目為〈台灣史研究三部曲: 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共分為三篇,本文為第三篇,標題為編者擬。 前兩篇內容請參考——許雪姬:那些為台灣史研究播種的人(三之一)、許雪姬:學門路漫長——從民間跨入學院的台灣史研究(三之二)。
以政治立場論釋歷史所造成的不同調,在台灣複雜的政治情況持續下,恐怕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十一、台灣史研究所成立
如果說以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政大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成立,做為台灣史成為顯學的指標,那麼2004年這一年是值得大筆特書的一年。
中央研究院做為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在學術研究上扮演著領航的角色。早期院內對台灣史的研究,除了上述郭廷以、黃嘉謨出版專書外,並無一人從事專業台灣史研究。中研院最早聚焦在台灣,從事跨學科的研究,則始於1971年由張光直院士所帶領的「濁大計畫」。這計畫分成六組,其中雖無歷史組,但有陳秋坤、林滿紅兩位加入,尤其陳秋坤的加入,更是研究台灣區域史的學術先鋒。濁大計畫的影響如何,張光直在1995年撰文時曾說,以台灣為區域進行研究,是「台灣史在戰後的台灣,第一次明目張膽的進行,對今日台灣史之成為顯學,起了開山的作用。」
張光直院士復於1986年決定負起由中研院推動台灣史研究的學術職責,向國科會申請了台灣史田野研究工作計畫,並在1988年由院方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會」,由史語、近史、社科、民族四所聯合進行,設定之後即全力投入資料的搜集,發行《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27期)並出版《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下)及相關書目的編排,如《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台灣漢人移民史研究書目》、《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等。1993年6月成立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正式確認了台灣史學門,而國科會在填寫專長項目時,也不再將之歸入中國地方史內。
吳大猷院長、李遠哲院長共聘12位學術諮詢委員,來協助台史所籌備處,並以黃富三為第一任籌備處主任,陸續聘用專業研究者,學科專長有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學、建築學等,使台史所具有學科對話和科際整合的條件,並進而凝聚出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環境史等幾個研究方向。在籌備處期間,發行機關刊物《台灣史研究》(目前已發行到第17卷,自第15卷開始改為季刊,2008年已被評比為國科會歷史學門第一級刊物,並被2008年IHCICore收錄,此誠為長年努力的成果),並召開多種學術研討會,發行論文集,並出版史料,尤其是日記與古文書,亦即台灣史作為一個專門的歷史學門,必須有豐富的史料做基礎,這是該所研究人員在撰寫論著之餘的另一工作重點。2004年7月1日台灣史研究所正式設立,此後台灣史研究又進入另一時期。
2004年以後台史所的研究以五大領域設群,奠立了三大研究取向:1.基礎學科研究:以歷史學為基礎,結合相關學科之理論與方法,從事貫時性實證研究;並廣泛調查蒐集國內外官方及民間台灣資料,建立台灣研究的史料學;2.區域比較研究:重視台灣內部的區域差異,並注意台灣與南亞、中國大陸與大洋洲等區域的歷史文化交流,探討區域之間人群來往、互動與認同等關係;3.整合性研究:對於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推動跨學科、跨區域和長時期的整合型主題研究計畫;以擴大台灣歷史的研究範圍和理論視野,進而建構台灣歷史學社會發展的系統知識。
除了中研院設台史所外,政大也設台史所,以研究日治、戰後為主軸,並在2006年設立博士班,是第一個台灣史博士班,每年招收5名博士生;此外師大也設台史所,較偏向區域發展史、科學史,近兩年來由於師資結構的改變,日治、戰後亦在推展中。兩個所的發展是否能各有特色、做良性的競爭,尚有待觀察。
中研院台史所與這兩個台灣史研究所的互動自2008年開始,藉由《台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7),由三所合作進行該年台灣史研究的評介,中研院負責總類、經濟類,台師大負責社會文化類,政大負責政治類,動員幾十位台灣史學者、研究生共同來思考過去一年的研究狀況,會中提出的研究結果與方向有如下結論:
1.就研究的時代而言,以日治、戰後近百年研究為主,清代研究減少。清史研究減少,一方面是日治、戰後研究的增多,另方面是清史的題材較少有到國外交流的機會。跨朝代的通論性論文,較難掌握史料與史觀,較少人從事,亦勢所必然。
2.就論文性質來看,以社會文化史占多數,其外在原因是歷史學門跨出邊境,大量將其他學科有時代縱深的文章也列為台灣史的論文,其中包括不少台灣文學史,這和國內有十個台灣文學系所產出不少論文有密切的關係。
3.就傳承而言,王泰升、吳文星、施添福、黃秀政指導下的學生在台灣法律史,日治時期的各類學術史、教育史,歷史地理,方志學方面,都能集中在某一領域而有所突破,漸漸看出有異於早期楊雲萍、方豪、王啟宗、李國祁等所形成的學風,亦為可喜的現象。
4.台灣史研究範圍的擴大,由原來屬人擴充到包含屬地,亦即在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史,也將生活在該時期的日本人包括在內,正如戰後外省人與本省人共創戰後台灣史一般。此外,台灣史也能利用社會科學、文化理論增益歷史學科的不能,因而能和文學、經濟學、社會學、體育學等學門的研究者對話、互相學習,因而擴大研究的範圍。
5.史觀的問題仍難取得共識:這也是台灣史學界最吊詭的現象。亦即對日本統治(甚至荷、西時期)時期的台灣史解釋,有明顯的分歧,有人大力批評「皇民史觀」,有人認為日本人是「現代化的奠基者」、「文明的傳播者」。在二二八研究中最能見到針鋒相對的論點,甚至歷史事件的重塑只成為個人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歷史本來就有多面觀察的傳統,本不足為怪,但以政治立場論釋歷史所造成的不同調,在台灣複雜的政治情況持續下,恐怕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6.史料的刊布、數位化,對研究起了正面的作用:自《熱蘭遮城日記》、《荷蘭台灣長官到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一)1622-1626》、《艾爾摩沙島事務報告》的中譯出版後,對荷西時期的研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灌園先生日記》的刊布,對日治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自不待言。但近來資料的方便使用,也造成了只用關鍵字搜尋的資料、依時間順序排比成文,而造成零碎化、偏狹化的現象值得注意。
相對於中研院、台大的努力,地方上、民間也同步在進行各自的地方學研究,如宜蘭學、澎湖學、淡水學、台北學等。而這些「學」的產生,與早期文獻會與今日文化局的推動關係密切。
十二、史料的發掘、編輯、翻譯與數位化
史料是研究台灣史不可或缺的資源,但是台灣數百年來的歷史分別由不同的政權統治,所留下的官方檔案大半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來看,缺少發自民間的史料,因此在推動台灣史研究的過程中,搜集家族、私人資料成為相當重要的事。相對於《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數位化工作(由中研院與台灣省文獻會合作完成),中研院台史所除將309種《台灣文獻叢刊》數位化外,也積極建立台灣日記資料庫。目前將已出版的兩部大部頭日記放入,即《水竹居主人日記》(共十冊)、《灌園先生日記》(共27冊,已放入16冊),另《黃旺成先生日記》(二冊),以及前述《台灣文獻叢刊》309種中有關的日記如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啟》、蔣師轍《台遊日記》;也得到國史館林滿紅館長同意,提供《楊基振先生日記》,這些日記資料將使民間對當代的看法得以顯現。
此外,也盡力協助或獨力將官方檔案數位化,如將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的紀錄、土地銀行、林務局、最高法院檔案的資料數位化,甚至建立台灣史資源網,希望能成為豐富而獨特的資料庫以方便研究者。中研院史語所在2009年1月1日起開放其資料庫免費供外界使用,其中如善本書的傅斯年圖書館人名權威資料庫、明清檔案的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目錄、全文影像);此外台大圖書館對淡新檔案、岸裡大社資料、古文書、圖書也有重要的資料庫可供使用;另日治法院檔案的發現,進行數位化工作,也在王泰升教授與台大項潔教授的努力下完成,而於2009年3月21日召開「日治法院檔案與跨界的法律史研究」。這一切都可知,自1993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的這16年來,在台灣史資料庫、數位化上,已做了極大的努力。
相對於中研院、台大的努力,地方上、民間也同步在進行各自的地方學研究,如宜蘭學、澎湖學、淡水學、台北學等。而這些「學」的產生,與早期文獻會與今日文化局的推動關係密切。各地的文獻會成立是在第二任省文獻會主委黃純青大力推動下於1952年成立,之後展開第一波的修志熱;然而各縣市文獻會因政府的不重視,而後逐一停辦,只剩台灣、台北、高雄三文獻會,已如前所述。到了80年代修志風又起,主要是在內政部鬆綁,不再先由台灣省文獻會審查,再經內政部複審後,才能出版方志。此一鬆綁不僅使各縣市急於修志,連全台309個鄉鎮也都躍躍欲試,由於過去仰賴修誌的學者專家、文獻委員有限,因此文化包工公司出現,橫行方志界,以得標為目的,其內容與品質未盡妥善。民選台灣省長由宋楚瑜當選後,1997年成立文化處,極力推動修志工作,不僅補助,還由王良行教授編訂出所謂「六篇體」的修志規範。2001年文化處結束業務,但各地方的修志工作仍持續進行,修志熱迄今未退潮,至於台灣文獻館主持的《台灣全誌》更是修方志中的集大成者。
除方志外,口述訪談工作的進行也不遑多讓。口述訪談成果的出版在近20年達到高峰,舉2007年一年來說,就有國軍(陸、海、空)眷村口述歷史系列、國史館有兩本佛教人物訪談二冊,還有作家的訪談。中研院台史所舉辦第11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以「口述歷史週」的型態出現,其特色為對台灣大專院校中「口述歷史教學」的座談,以及與日本、中國的口述歷史界進行經驗的交流,同時也編製《戰後台灣口述歷史書目》。2009年成立「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同年也出版《台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1953-2009》,共收5,005條書目。
方志、口述史外,圖像資料的刊布(加上說明)也是目前出版界的寵兒,有以個人為主,有以家庭為主,有以地區為主,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的《日治時期的台北》都是。其中圖像以資料庫呈現、較大規模的有國立臺灣博物館、台大、中研院台史所、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等。
方志大抵以鄉鎮為最小的單位,台灣一度也盛行大家來寫村史,以每一村為單位來進行,但能具體落實、且品質好的,並不多見。主要原因在於不是人人都具備書寫的能力,而村史也必須有一定的內容與嚴謹度,而非發出多元的聲音即為「民主」,大家都來參與就可以達成共識。更慘的是文化包工仍舊出現,這一來,文建會的美意也在人去政亡的情況下只維持一個短的時間。
在研究上,台灣史的邊界雖然向外延伸,有容乃大,但被跨界研究擠壓,也不能不熟悉各種理論,發揮論述的能力,而後史家最重要的技藝——史料的考訂,是否會在其他學科的浸淫下,變成以論代證?
十三、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
由於台灣的政治情況特殊、統獨的拉扯,史觀的難以取得共識,因此研究台灣史原本可視之為國史,也可視為鄉土史的,是很自然而然發展的一個學門,卻被賦予廣泛的政治性。這當然與早期政府漢賊不兩立、反攻大陸的意識型態,使台灣只能是個「反攻復國的基地」、只為中華民國而生有關。戰後自大陸遷來的人不是台灣人、本省人,而是外省人,因此台灣當然不能是台灣人的台灣,因此台灣人自然不能研究台灣史,因而有當時的學子只知道黃河、長江,從不知台灣有淡水河、濁水溪的怪現象。不論你以鄉土史視之,以區域史、以國史觀點來看,都不能「忽視」台灣史的研究,也不能完全由中國立場,台、中關係史來看台灣,畢竟在現實的歷史發展上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過程是不相同的。由戰後楊雲萍等人提倡台灣史,到1983年我取得台大歷史系的博士學位時,居然是全台第一本歷史所台灣史博士論文。文化大學和台灣大學都在1967年成立博士班,卻要到1983年才有第一本台灣史博士論文出現,中間經過17年。
1993年到2004年這12年光陰,台灣史研究可謂「顯學」,因為歷史學博碩士論文中,台灣史論文達到四成上下,與1966年才有兩篇台灣史論文相比,當然是快速成長。然2004年雖然有三個台灣史研究所成立,但是政局的變化、中國強大的磁吸,以及台灣史研究老被認為與政治難脫關係,使學生裹足不前,都使台灣史的研究似有消沉之勢;而且面對中國以大量人力編製《台灣文獻匯刊》、《館藏台灣研究檔案》,要超越《台灣文獻叢刊》的大部頭數百冊的文獻資料,以及厦大、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武漢等地有關台灣史的任務性研究,都有步步進逼本地台灣史研究的趨勢;再加上厦大台灣研究院培養一大批三年即可拿到博士學位的台灣學生,而這些學生大半是考遍台灣各研究所難被錄取的,長此以往僅受短暫的訓練、卻又人數眾多,若政府再承認其學歷,排山倒海回台求職,台灣自己訓練的學生找工作更雪上加霜,學台灣史不是「險學」嗎?
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落實在本土性的研究,因此早就以台灣做為研究場域,和台灣史研究在1993年前的鮮學狀況不能相比。而到2006年底台灣公私立大學之台灣文史系所共有23所,大半為語言、文學、文化系所,台灣歷史所只有2個,何況只有台灣歷史所而沒有系!在學門上歷史系有被社會科學、文學瓜分、入侵之虞,歷史學也成為「險學」。在研究上,台灣史的邊界雖然向外延伸,有容乃大,但被跨界研究擠壓,也不能不熟悉各種理論,發揮論述的能力,而後史家最重要的技藝——史料的考訂,是否會在其他學科的浸淫下,變成以論代證?又對某些概念、理論的快速借用、囫圇吞棗的結果,也許會增加「可讀性」,但史學的基本要求安在?長此以往史學雖擴大範圍,卻會被跨學科的專史研究壓迫得難以喘氣,形成「險學」的局面。
近年來人文學科的研究已由後殖民理論進而談到現代性,或以東亞的詮釋框架來思索研究的徑路,日本帝國下殖民地的比較研究、日本殖民地主義與歐美國家(尤其英、法)的比較、殖民地前後政權的比較,都是可以展開國際對話的主題,如何培養、訓練年輕的研究生具有更充實的研究能力,更是刻不容緩的事。
我參與了影響中學台灣史教科書最大的《認識台灣》的編纂工作,曾被極右派人士包圍編譯館抗議,由於我衣著簡便未被視為「教授」,因而輕易突破重圍……
十四、結語
我自1975年進台大歷史所碩士班後,並未以研究台灣史為志業,而是以研究汪精衛為目標,但方豪教授的當頭棒喝使我從事台灣史的研究,經歷了台灣史的鮮學時期。我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有一整年(1982年)都在故宮文獻處看檔案,我所提借的檔案,故宮博物院都要有專人先行「審查」後,沒有問題我才能看,這是現在萬萬想不到的事。
當我進入中研院近史所時,據聞我的審查報告中有位審查人說我在《書評書目》評論過德馨室出版的《王詩琅全集》,是在評論「漢奸」的作品,是不合宜的;也有我母校政大歷史系的教授致電呂實強所長,千萬不要讓我進近史所。當我終於審查通過,第一天上班,近史所同仁奉另一審查人之命來勸我說,從此不要再做台灣史了,這是1984年2月的事。
1991年1月我被行政院成立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成員挑選加入「研究二二八工作小組」,之所以需做這些苦差事只因當時是「鮮學」時代,專業台灣史研究者不多,而我又在1989年升等為研究員使然。由於參加二二八,打亂了我的人生規畫,也使我成為政治事件受難者的訪談者,被我訪談過的有數百人。在這一年撰寫報告期間,必須由口述歷史作起方能完成報告,其中的艱辛難以為外人道也,如在零下6度、耶誕節前後獨自一人在南京二檔看二二八資料;又如受到一位姓龔的先生長期寫信來騷擾,即使我不回信也不斷寫來,最終他向當時的所長張玉法告狀……,不斷接莫名其妙的電話……那一年如何熬過來,到今天已難回想。
在研究院期間,經歷了中研院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到台史所設籌備處、設所,乃至於任所長,這一切的過程。在院外,我參與了影響中學台灣史教科書最大的《認識台灣》的編纂工作,曾被極右派人士包圍編譯館抗議,由於我衣著簡便未被視為「教授」,因而輕易突破重圍;也參加了新台幣改版設計的委員會,今天新台幣五百元的鈔票,以棒球為主,即出自我的點子;後來更成為「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董事(迄今8年),協助「白色恐怖」的補償工作。
我自198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迄今已27年,經歷了鮮學後半期(可以1965年台大召開「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座談會分為前後期),到1993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當時我是「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執行小組召集人,帶領室中成員寫了設所規畫書,為該籌備處的成立盡一分心力。1993-2004年台灣史成為顯學,台史所成立。翌年我被病魔侵襲,足足半年才痊癒,病中李遠哲院長勉勵我接下台史所的重擔迄今。這一路走在研究台灣史的道路上,時而在眾聲喧嘩時欲「去」之而後快,時而踽踽獨行,回顧茫然無友朋,終於走到了今天。也無歡喜、也無憂。
延伸閱讀:
| 閱讀推薦 |
| 新書快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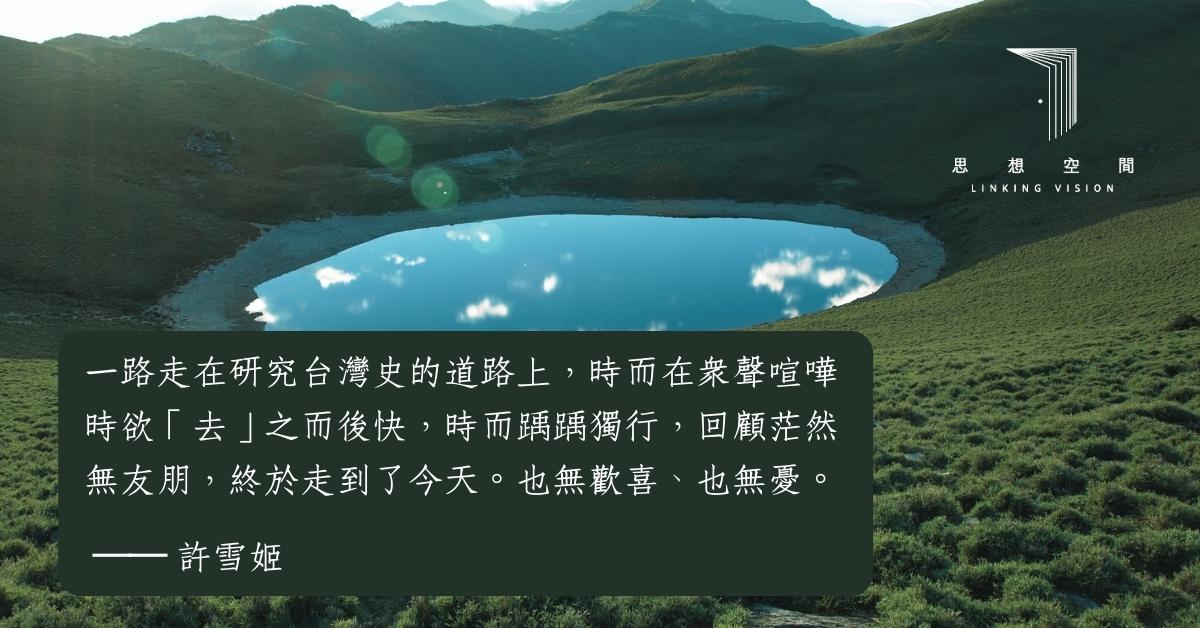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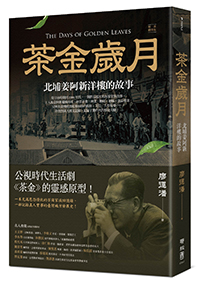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