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社會固然還沒有將這些事件完全消化進它們的公共文化之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事即使發生在中國,它們也不會引起同樣的爭議。
2017年10月,數十名好萊塢女星指控知名製片人哈威.韋恩斯坦曾對她們實行性侵,隨後,同樣受到過韋恩斯坦性侵的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在推特上呼籲受過性騷擾的女性用#MeToo標籤,講出自己的遭遇。這就是全球#MeToo運動的由來。2017年底,南昌大學前國學院副院長周斌被學生提出涉嫌性侵的刑事指控,這是中國大陸的第一起#MeToo案件。在接下來的一年裡,無數的中國女性在#MeToo的旗幟下站出來,講述自己遭到性騷擾的經歷。
#MeToo從一出現就爭議不斷,一些支持這個運動的人認為質疑者來自父權制的擁護者,或者來自守舊勢力,但在歐美,從其中影響較大的幾次批評來看,批評者本身就屬於女權主義者的陣營。在中國,情況更富有戲劇性。三波針對#MeToo的批評,批評者都越來越接近運動的核心。這迫使我們放棄「進步/守舊」的二分, 直面#MeToo內部的複雜性。本文嘗試通過分析國內外針對#MeToo的批評及其背後的邏輯,重構#MeToo的敘事,闡明「公共文化」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相互作用。與一些支持者不同,我認為這些批評根植於社會原有的公共文化之中,因此它們的出現具有某種必然性,#MeToo運動如果要真的改變社會的性別觀念,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它就無法跳過,也不應該跳過這些批評及其背後的公共文化。
一、公共文化與國外對#MeToo的批評
早在2018年年初,當中國才剛剛爆出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多名女學生的事件,法國主流報刊《世界報》就刊出了一封由一百位作家、演員、學者和商業精英連署的公開信,對#MeToo或#BalanceTornPorc進行抨擊,說這是一場新的清教主義運動。這封公開信的連署人全部是女性,她們認為:「男性對女性的調情,對性自由而言不可或缺。」「強姦是一種罪行,但不論手段是否笨拙, 是否窮追不捨,追求並不是一種冒犯,更不是一種大男子主義式的侵犯。」她們不僅認為一些指控有失實和小題大做之嫌,而且也提出這樣的運動對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產生了不良影響:它打擊了男性對追求女性的積極性,甚至助長了「宗教極端主義」[1]。
在這裡,一百個法國女性和#MeToo 運動的支持者就西方公共文化中的性自由產生了分歧,兩邊都認同性騷擾傷害了女性的性自由,但是前者認為應當允許男性有更大的試探的空間,這樣女性更能享受兩性關係帶來的樂趣,而後者認為男性應該等女性明確表示同意再展開調情和追求。我們在這裡說的「公共文化」,指的並不是簡單的流行文化,而是一個社會深層的理念、價值、原則、記憶、想像、思想結構,有點類似於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說的「公共理性」和加拿大哲學家查理斯.泰勒所說的「社會想像」。公共文化中的理念、價值、原則、記憶、想像和思想結構,不一定為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接受,但當一個人在公共討論中提出這些觀念時, 別的人能夠(在同等條件下)合乎情理(reasonably)地去理解,並表達贊同或異議,常見的異議包括對該觀念提出不同的詮釋、對其適用範圍表示質疑,或者訴諸其他觀念。並非所有人的觀念都全部來源於公共文化,但很少有人的觀念和公共文化沒有一點重合。公共文化的存在,使得某種程度的社會共識得以可能,不至於呈現為永恆的意識形態的大混戰。
性騷擾所涉及的公共觀念,西方世界出現的情況還可以更複雜。《紐約時報》8月刊登了一篇名為〈當女權主義者被指控性騷擾會如何〉的文章,提到紐約大學德語和比較文學教授、著名的女性學者艾維托.羅內爾被她以前的博士生尼姆羅.賴特曼指控性騷擾, 而羅內爾堅稱她和賴特曼之間的關係完全出於雙方的自願。紐約大學經過十一個月的調查,認定羅內爾的性騷擾程度足以「影響賴特曼的學習環境」,但否認了賴特曼所提出的「性侵犯、跟蹤和報復」等指控。今年春天,五十餘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給紐約大學寫了一封聯名信,抗議紐約大學對羅內爾所做出的處理,其中第一個簽名者就是女權主義理論家裘蒂斯.巴特勒。信中如下寫道:
儘管我們沒有看到保密的案卷,但我們都在羅內爾教授身邊工作了很多年,都見證了她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我們中間的一些人還認識那個對她發起惡意攻擊的人……我們可以為羅內爾教授的優雅風度、敏銳的智慧和對學術的熱忱投入作證,並請求給與她體面和尊嚴,這是任何像她這樣擁有國際地位和聲望的人所應得的。[2]
這封信被在網上公開以後,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人指責以巴特勒為首的女權主義學者,在受害者是男性且被指控者是女權主義者的時候,採用了不體面的「雙重標準」。8月20日,巴特勒通過電子郵件發表公開信,為自己先前的「背書」道歉,承認連署人不該「歸咎於投訴人的動機」,也不該「暗示羅內爾的地位和聲譽可以獲得任何形式的差別待遇」[3]。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為羅內爾背書、但對#MeToo一直持保留態度的左翼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在巴特勒發表公開信的前一天,依然堅持羅內爾的行為沒有什麼不妥,並說受害者「現在如願以償,享受媒體對一個模仿受害者的關注,這個位置給了他(和他的支持者)所有實際的社會權力,將艾維托這個『權貴』人物推向社交失能和被排斥的邊緣。」[4] 這種一般被稱為「譴責受害者」的言論,因為齊澤克是在幫一個女權主義者、酷兒理論家說話,似乎受到的批評也不甚嚴厲了。麗莎.達根也以「酷兒理論」來為羅內爾辯護,她認為不能從傳統的異性戀同性戀親密關係的眼光來看待酷兒親密關係,「酷兒不明確將友誼和愛情分開,不將伴侶關係和浪漫的友誼分開。」[5]
聯繫起#MeToo最早的發聲人,義大利女星艾莎.阿基多被小她22歲的年輕演員和音樂家吉米.本內特指控性侵一事,#MeToo 在西方的公共討論中所牽扯到的價值和原則已經極其複雜:是將「性自由」理解為擁有更豐富性體驗的機會,還是個人身體不可冒犯的權利?當受害者身分和被指控者身分不符合「擁有權力的男性性侵處於弱勢的女性」的刻板故事時,女權主義者是否會遵從「對事不對人」?酷兒實踐與性騷擾之間的界線在哪裡?儘管我們不懷疑會有女權主義者就上述事件給出一套融貫的說法,但要在原則前後一致、不歪曲事實、不損害#MeToo運動和女權主義的聲譽的前提下這麼做,恐怕難度不小。歐美社會固然還沒有將這些事件完全消化進它們的公共文化之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事即使發生在中國,它們也不會引起同樣的爭議。並不是說在中國沒有女性認為#MeToo運動妨礙了她們的性自由,也不是說中國的#MeToo運動中站出來的受害人和女權主義者不可能成為被指控者,但難以想像在中國的語境下,會有這麼多女性主動站出來維護男性調情的自由而不被輿論進行惡意解讀,當下的中國人更加不可能接受酷兒理論作為公共理由來為任何逾越常規的親密實踐和性實踐辯護。這充分說明在#MeToo這件事上,中國和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公共文化背景。
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社交平臺上的一些帶有國族主義傾向的輿論,一直將#MeToo渲染成一場由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主導, 旨在對中國各行各業的男性精英進行打擊的運動。
二、第一波批評
如果說,在上文的三個事件中女權主義是一個基本共識,只是詮釋不同,那在中國,針對#MeToo的討論並沒有一個女權主義的共識背景,有的人甚至認為中國根本不存在「公共文化」,只有價值觀的「諸神之戰」。
說中國不存在公共文化,可以有兩點理由:1. 中國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而公共文化的形成需要保證每個公民都能真誠地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充分的論述而不受到來自公權力的懲罰,否則這些表達出來的觀點很可能是受到操縱的:2. 中國只有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存在任何廣泛意義的「共識」,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呈現「同溫層效應」,不同的同溫層之間只能進行功能性的溝通, 無法進行深層次的對話。
這兩種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針對第一個理由,我們可以如下回應:中國雖然沒有作為「權利」的言論自由,但卻有事實上的、量化意義上的言論自由,這並不是說雖然中國政府沒有尊重憲法裡的「言論自由」這一條款,但中國公民可以隨便說話不會受到公權力的懲罰。「因言獲罪」的事當然時而有之,但由於管控技術的有限和管控成本的考慮,中國政府不可能對所有的公共言論都進行管控,就算存在管控,大多也以刪除為主。退一步說,即使有可能因言獲罪,許多中國人還是願意在公共討論中真誠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且許多公共言論本身並不涉及中國政府所認定的「敏感內容」, 它們本身可能是「政治中立」的。就這些方面而言,中國的公共文化,其公共性雖然是有局限的,但卻不是完全不存在。
第二個理由誤解了「公共文化」與「社會共識」。在中國,社會觀念的分裂狀態確實顯著,但這和公共文化是否存在沒有必然關係,因為公共文化裡面的諸多觀念不一定要被社會所有的人接受, 一個人很可能只接受公共文化中的其中一部分觀念,而不接受另外一部分觀念。如果一種觀念在公共討論中頻繁出現,且存在多種對它的不同詮釋,還經常被人引用作為對自身與他人行為之解釋,那我們可以說這種觀念處於社會意識的深層結構,也就是說,它屬於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公共文化內部,也不是一個融貫的整體,裡面可能存在著互相衝突的公共觀念。因此我們可以說,公共文化只是社會共識的材料,但卻不是社會共識本身。
正如我們考察國外對#MeToo的批評,可以看到西方的公共文化如何應對這場運動,我們也可以考察#MeToo在中國所遭受的批評,來觀測一些公共觀念如何從公共討論中湧現並接受#MeToo的衝擊。中國的公共觀念中最突出的一種,大概就是「國族主義」。中國的國族主義並非簡單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還包含了一點國家主義(statism)。不是說在中國就不存在單純的民族主義, 但由於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建構的含混,以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公共論述裡難解難分,所以大部分中國人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都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國家主義,因此我們用「國族主義」來替代,以區分西方意義上的「民族主義」。
針對#MeToo運動的第一波批評,正是來自國族主義。從羅茜茜舉報陳小武開始,就有來自體制內外的聲音認為,這背後一定有「境外勢力」興風作浪。2018年3月,微信公眾號「酷玩實驗室」發表了一篇〈收外國男人的錢,騙中國妹子的炮?天朝竟有這樣一幫「女權組織」〉,對女權組織「女權之聲」和青年女權行動者鄭楚然進行污蔑,同樣也是以「與境外勢力勾結」為罪名6。
文章稱,「女權之聲」收取境外組織福特基金會的贊助,鄭楚然與支持港獨的境外學者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密切往來,這些都說明,中國有一批女權主義者是受著境外勢力指使的。她們對中國男人進行討伐,目的就是將中國女人賣給白種男人。這篇顛三倒四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點名#MeToo,但是從其發布的時間、針對的對象(在#MeToo運動期間,女權之聲和鄭楚然的社交平臺帳號都發布了大量相關內容)以及所扣的罪名來看,可以說就是衝著#MeToo去的。
4月份,在美國衛斯理安大學東亞研究助理教授王敖和其他北大中文系95級同學的檢舉下,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主任、長江學者沈陽當年在北大性侵女學生高岩的事遭到揭露。北大的一些在校學生向北大校方申請,要求公開當年的相關資訊。北大外國語學院的大四學生岳昕因此遭到校方的多重脅迫,並由於她本人的出國經歷,被懷疑受到「境外勢力」的唆使。
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社交平臺上的一些帶有國族主義傾向的輿論,一直將#MeToo渲染成一場由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主導, 旨在對中國各行各業的男性精英進行打擊的運動。很快,#MeToo 在新浪微博上便成為敏感詞,無法發起帶著這個標籤的話題,也無法進行搜索。
嚴格意義上,這一波對#MeToo運動和女權主義的「批評」, 被稱為「攻擊」或「汙名化」也許更為恰當。它集中體現為「#MeToo 運動受到境外勢力操縱」這個說法。它主要來源於:1. 體制內的單位或人員;2. 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作為假想敵的反西方主義者;3. 國際關係的陰謀論者。從邏輯上來說,它的荒謬之處是顯而易見的, 比如它忽略了#MeToo運動在西方的起因,比如它建立在一些沒有根據的猜測之上,但它依然吸引了大量的信奉者。對於體制內的單位或人員來說,接受「境外勢力操縱」的說法,為他們打擊當事人、推卸責任提供了許多便利;對於反西方主義者來說,「境外勢力操縱」無疑是一次戰鬥的號角,他們可以將無形的恨發洩在有形的運動者身上;對於陰謀論者來說,這最能解釋同時有多個案件被曝光的巧合。上述三種立場都屬於某種意義的國族主義。除此之外,考慮到49年以來「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就一直被中國人掛在嘴邊,「#MeToo運動是境外勢力的操縱」這種國族主義表述是這個國家針對#MeToo最自然又最本土的反應。
然而,這一波對#MeToo的「批評」或「攻擊」除了將#MeToo變為敏感詞,吸引了來自體制的敵意,並沒有對運動造成實質損害。5月以後,儘管「境外勢力操縱」這樣的說法在公共討論中出現得少了,但也沒有完全消失。毋寧說,由於國族主義者對#MeToo運動缺少觀察分析的耐心,國族主義本身和#MeToo運動的邏輯也格格不入(7月底倒是有體制外的人認為#MeToo背後是政府借機來搞「自由派」),所以國族主義難以再在與#MeToo有關的公共討論中發揮重要影響。此外,由於#MeToo針對的對象以體制內人員(高校教師)為主,#MeToo的支持者又與體制發生過激烈對抗(岳昕事件),「境外勢力操縱」這種說法,反而對團結起所有對大環境不滿的人起了一定的作用,#MeToo所獲得的支持愈加廣泛了。
(本文摘錄自《思想》第38期,原題為〈從對#MeToo在中國的三波批評看公共文化的生成〉,標題為編輯所擬。)
參考資料
[1]Shu,〈維護男士「調情權」,法國女士譴責「#metoo」太過分〉,
https://mp. weixin.qq.com/s/wCtqzd9qeSzj1x1h_2gtZQ
[2]張之琪,〈當女權主義者被控性騷擾:是權力濫用,還是非常規親密關係?〉
[3]裘蒂斯.巴特勒,王芊霓(編譯),〈裘蒂斯解釋為何給羅內爾背書:羅內爾不該獲得差別待遇〉
[4]齊澤克,盧南峰(譯),〈齊澤克力挺羅內爾:一封事後的短箋〉
[5]皮晨瑩,〈紐約大學教授羅內爾性騷擾學生事件中不性感的真相: 權力〉
[6]酷玩實驗室,〈收外國男人的錢,騙中國妹子的炮?天朝竟有這樣一幫「女權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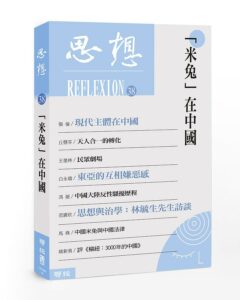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