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弘祺(國立清華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編按:19世紀的中國出現一個轉化基督教教義而成立的政教政權:太平天國。一個落第秀才自稱上帝之子,在長期累積大量民怨的社會氛圍中一擊中的,以天父為名的農民動亂,遂蔓延成這股野火燎原般的「長毛之亂」……2022年10月,德國作家施益堅新作《野蠻人之神:太平天國》面世,小說書寫近代東亞史上慘烈的歷史景況,試圖開啟另一種思辨且富人性化的想像空間:無論是大英帝國的外交特使額爾金伯爵、滿清帝國湘軍首領曾國藩將軍,或是太平天國的理想主義者「干王」洪仁玕,時代英雄也可能是千古罪人。在急遽變化而失去方向的世界態勢中提出深刻批判與反思:相互指謫迥異之人的野蠻與傲慢,其實乃為一體兩面之事?(*本文摘錄自《野蠻人之神:太平天國》導讀,標題為編者擬。)
施益堅(Stephan Thome)博士是德國出名的小說家,已經出版了五本小說,其中三部曾經被著名的德國圖書獎提名並入圍,可見他在小說著作上的成就。這本書使用小說的方式來描述十九世紀中葉,非常複雜的中國內政及外交的演變:集中在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跟這些歷史演變的重要人物:從洪秀全(以及洪仁玕)到曾國藩到英國外交代表額爾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全名中譯為「第八代額爾金伯爵,同時也是第十二代金卡爾丁伯爵」,頁六三)等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因此它可以歸類為「歷史小說」,而重要性就不僅止於文學,更在於作者所要演繹的歷史的本質和解釋。讀這本「小說」的人除了可以欣賞文字魔力的引人遐想之外,更能從它看到人類歷史的繽紛多彩。這本書在這兩點上都有出色的表現。再因為它所觸及的「事件」和人物是我們大部分人所非常熟悉的,因此自然地會引起中譯本的讀者們的感動。他們可以經過認同,反思和印證書中的故事,產生一種情感的過濾和昇華。

西方人對太平天國史的興趣則主要是在於洪秀全和洪仁玕的基督教信仰;即使到今天,也還有很多西方學者逃不離從宗教的本質來探討太平天國的束縛。
本書從太平天國講起,到英法聯軍簽訂合約為止。作者借用一個虛構的人物(菲利普)來交錯編織書中的情節。這個虛構的人是一個不很老實的基督徒:他喜歡浪跡天涯,不尊崇傳統,借用傳教士的身分,遠走中國,結果見證了太平天國的動亂,中英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當然,這個人的所見所言就是作者的觀點和聲音。
作者借用的是歷史的想像,透過文字的精彩來表達他對這一段中國歷史的看法。
首先,施益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擁有柏林自由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他熟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這點在書中到處可見。我敢說華人對十九世紀中國史的瞭解如果僅限於大學的程度,那麼他們很可能還比不上施博士,因為十九世紀的中外關係的歷史記載不只限於中文圖書,許多紀錄還存在於英、法、德,乃至於俄國的資料當中。因此一位能具備宏觀視野的歷史學者一定要能參考中外史料。施益堅在中文之外,還能參考上述語言所記錄的史料,因此他所掌握的視野遠遠勝過即使專門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中國史學家。這本「歷史小說」因此可以在研究這段歷史的眾多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
太平天國的歷史定位在清朝滅亡以前當然是負面的,因此也說不上有什麼合乎我們現代人所說的歷史敘述或客觀瞭解。清朝滅亡後,我們才進入一個可用批判眼光來探究它的時代。二十世紀大部分中國人對於太平天國的定位受孫中山先生的看法所左右,大多認為它是一場民族革命,要推翻滿清外族的統治。不過這樣的解釋在國民黨當政期間,並沒有得到大力的鼓吹,基本上到抗戰前夕,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對它抱持的是相對正面的印象。
第一個對太平天國做出有系統研究的無疑是簡又文。 [1] 他的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國史的學術地位。他更是孫中山的看法最好的詮釋人。因為他曾經在耶魯大學與芮瑪麗(Mary C. Wright) 及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交流論學,並在那裡出版得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1973),因此對西方學者如何透過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待太平天國有相當的影響,即使他的史學(基本上反對所謂的「農民革命」或「階級革命」說)缺乏一貫性也缺乏系統性。羅爾綱比簡年輕一些,對太平天國的研究也做出重要貢獻。他主張太平天國是一場「貧農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式的立場;整體來說,他還是採取正面的、屬於民族主義的態度來處理太平天國的歷史。總的來說,中共對太平天國的態度顯得較為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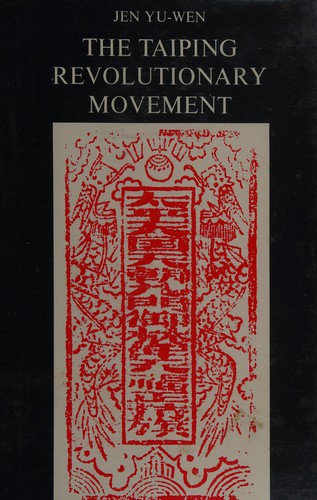
我認為國民黨的態度模稜兩可,主要就是因為如果過分地強調民族革命的色彩,那就會很難客觀解釋曾國藩的角色。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蔣介石要利用曾國藩的思想來充實中國民族思想的內容。蔣介石認為曾國藩的「名教」思想比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信仰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於是國民黨的太平天國歷史變成了曾國藩(和湘軍)平定動亂,保護中國歷史文化的鬥爭。尤有進者,國民黨在台灣更需要用曾國藩的思想來提倡中國人的傳統價值,因此不能過分提倡太平天國批判或反對中國文化的主張。
西方人對太平天國史的興趣則主要是在於洪秀全和洪仁玕的基督教信仰;即使到今天,也還有很多西方學者逃不離從宗教的本質來探討太平天國的束縛。二〇〇七年出版的《 太平天國:叛亂與對皇朝的褻瀆 》(Thomas H. Reill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bellion and the Blasphemy of Empire)也還對於太平天國的政治思想如何受到《希伯來聖經》(通常稱為《舊約聖經》)「十誡」影響的研究,而二〇一六年出版的《太平天國的神學,基督教在中國的地方化》(Carl S. Kilcourse: Taiping Theology: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843-64)更直接討論基督教思想的中國化問題。在他們看來,太平天國的政治乃至於神學思想基本上還是能從基督教的觀點處理。不過,總體來說,自從施友忠[1]和簡又文的書相繼出版之後,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對太平天國的寫作從此可以擷取前此比較少人看到的中文資料,開拓了新頁。史景遷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上帝的中國兒子》(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按:此書中譯本,譯為《太平天國》) 可以說是一錘定音之作。它的重要性除了有系統地使用不少英國國會圖書館的外交檔案之外,更成功地對太平天國史做出全面性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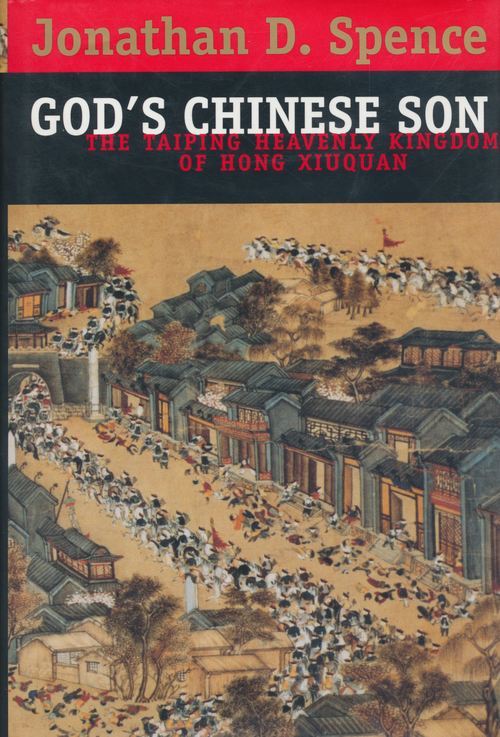
施益堅生動地描繪駐扎在極樂寺的額爾金如何中夜夢醒,深度反思中國人不能理解西方進步觀念的心理做了一種對位式的剖析。
史景遷的中心課題就是想要瞭解洪秀全為什麼會變成這麼一個動亂的領袖:他的思想、他的歷史背景,還有他令人著迷的毅力。史景遷指出這些東西不幸卻加增了中國的混亂和明顯的沉淪 ,而西方人因為宗教緣故,不知不覺地捲進了這個他們完全不瞭解的紛爭。難怪史景遷會把英國最受尊敬的外交官額爾欽說成「不對的人」(the wrong man)。西方的宗教和東方人對太平天國的錯誤——或至少是誇張的——瞭解,也造成了一種不可原諒的歷史錯誤。
史景遷文采出色,因此能用詩意的文字化解一般歷史敘述的乏味,使得太平天國的研究在西方又產生新一輪的興趣。施益堅所推崇的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就是一個例子。他寫的《天國之秋》(The Autumn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2012)將太平天國所帶來的動亂和影響寫得非常徹底,可算是一種新的「戰史」。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洪秀全的基督教信仰有了比較持平或寬容的認可,甚至於認為西方記者把太平天國的基督教過分渲染醜化,致使洪仁玕近代化的憧憬沒有實現的機會。之所以如此,有兩點:一個是西方記者集中在上海,聽到的主要來自官方說法,因此產生「太平軍是一群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野蠻人」想法。其次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基督教還是保持排斥非信徒的傳統,只要有絲毫與正統教義偏離的想法就被視為異端。在裴士鋒看來,這兩者都造成後人對太平天國極大的誤會。
施益堅對基督教的立場是開放的,他認同英國傳教士會的說法,主張拜上帝會的教義不外是所謂的「亞流派」(Arianism)的想法(頁二二〇——二二二)。因此他和裴士鋒一樣,明顯對太平天國的宗教觀有相當的同情,這就好像近年來西方基督教會不再隨便指摘在中國產生的靈恩教會是異端一樣,兩人對於過往基督教會的態度並不認同。更進一步來說,施益堅也不認為西方人對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有真正的興趣。他們不支持洪秀全,一言以蔽之,就是經濟的利害關係。施益堅在小說中(頁三八六)借用額爾金的話說出英國攻打北京,並放棄支持太平天國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和貿易的考慮。額爾金作為英國的貴族,擔負重要的外交任務(他的弟弟當時也帶兵在北京),他的考量當然是英國國家的長遠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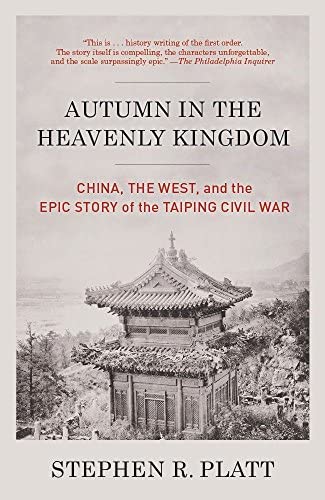
說到額爾金伯爵,這個人在施益堅的眼光中,雖然是對中國文化缺乏認識,但卻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英國紳士(雖然系出蘇格蘭)。施益堅把他描寫成一個懷疑亞羅號船上並沒有真的懸掛英國國旗,並且為英國出兵感到羞恥的人(參看頁六五)。他也不再提額爾金縱容士兵進入圓明園搶劫的這個說法。最後這點現今一般認為是法國官方的決定。有的史家更根據王闓運、李慈銘的記載,指出其實中國人比法國人還早進去破壞,因為咸豐皇帝逃亡之後,守衛人員散逃,於是附近的窮旗人就進去擄掠。法國軍隊還是在獲得長官許可後才跟隨進去,已經比難民晚了一步。無論如何,法國人放火,畢竟不是光彩的事。施益堅也提到,即便西方人也對法國軍隊的行為做出激烈的批判。
施益堅技巧地引述了額爾金的父親在希臘的醜事來襯托圓明園的破壞(參看頁七三——七四)。額爾金的父親就是早年把雅典眾神廟的大理石浮雕拆下並運回英國的人。這些大理石雕刻品構成了大英博物館非常重要的展覽品,去參觀的人絕對不會錯過它們,也是現代英國人感到心理上非常矛盾或曖昧的「收藏」而希臘政府積極追討希望可以要回去的寶藏。所以拜倫對他父親的指責自然地在額爾金心中不斷地激引他作為一個文明人的深沉反思,在夢中迴響。當他想起雨果的指摘,內心不禁有萬分複雜或羞慚的思緒(頁四五一——四五三)。
施益堅在書中幾度透過反省的語氣來探討十九世紀的「進步」觀念(參看頁七一)。本來小說裡面並不適合討論這類思想的問題,但是額爾金不是一般人,他生活的世界不是世俗的賺錢糊口的世界,他要的是文化藝術的熏陶,嚮往的是一種克服或超越物質的境界。在他看來,這才是所謂的進步。所以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不要將進步理解成軍事力量的增加。當一個國家能不再只是斤斤計較物質的條件時,國家才會強大」(頁三四〇)。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中國缺乏那種追求精神自由的精神理念(頁九〇)。
對比額爾金來說,曾國藩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施益堅對曾國藩也採取了同情的瞭解,寫出一個中國傳統讀書人看待非中國宗教的態度和方法。施益堅對中國思想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例如他在描繪曾國藩說明為什麼要討伐太平天國的時候,引用了孟子的惻隱之心(頁一七六——一七八)。施益堅也對王夫之的思想有相當的認識。他屢次提到這位曾國藩的鄉親,用以說明曾國藩所發揚的華夷之辯 :華夏文化很自然地必須要消滅蠻夷粵匪,因為它是發自內心的惻隱。
一般華人對於曾國藩的認識如我在上述所說的,主要是受到國民黨的影響。毛澤東基本上也對曾國藩抱著正面的形象。兩個近代中國的領袖都一樣認同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提出「名教」的觀念。名教觀念其實與曾國藩對現代世界的瞭解是互為表裡的。在這本小說所處理的年代中,曾國藩是把西方國家當作是中國名教的敵人,而極力反對。施益堅說法是對的。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前的中國;就是他並不太喜歡的李鴻章在這個時候也對近代武器和科技只有粗淺的興趣,更說不上對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礎有皮毛的瞭解。再過幾年,他們(加上稍後的張之洞)就要做出更進一步的反省,並開始推動同治中興。要曾國藩不從名教的基礎來思考拜上帝教,這是何等的困難!相比於黑格爾和額爾金,這些中國讀書人就真的注定要像「薛西弗斯的世界精神」一般,不斷地回到原點(頁一〇一,並參考頁九〇——九四)?施益堅生動地描繪駐扎在極樂寺的額爾金如何中夜夢醒,深度反思中國人不能理解西方進步觀念的心理做了一種對位式的剖析。
一部成功的歷史小說應該盡力遵守歷史專業研究的成果,而用文學的方式和筆調來演繹他對歷史的感受,從而提出他的解釋。
我已經寫得夠多了。就此打止。讓我在結束之前,就這本書作為「歷史小說」的意義和重要性發表我個人的看法。首先應該說,這是一本不斷讓人驚奇的歷史小說。裡面的人物透過作者的想像可說是栩栩如生(例如曾國藩背部的皮癬,額爾金的優柔寡斷,羅孝全的投機),不斷地把我們帶進他們的世界,讓我們瞭解超過一個半世紀前的中國如何在尋找或者不尋找一個合乎歷史邏輯的發展途徑 ——一個在中國人想像的世界裡是合乎理性(是的,這是黑格爾也常常說的一個字,參看頁一三八,二六三,二六五)的制度或目標。
在歷史小說的畫布上面,不是每一點,每一畫,或每一個細節都必須正確地畫出那所要呈現的對象。小說家要的是他對整體的瞭解,是要引導人們活進去小說的世界,產生一種心靈的昇華。讀者自然不會強求每一個細節都和歷史記載完全吻合。可以說,歷史小說是要用文學的手法將一個故事鋪排出來,好超越一般史學家光靠堆積史料的枯燥記事。
許多歷史小說因為需要而杜撰人物,但是歷史人物就必須與歷史的真實相符合。這是歷史小說的基本原則。如果杜撰的人物或事情只是作為表達他自己的思想或道德信念,不能產生真實發生的事實感,那麼這一定會成為失敗的作品。嚴格的專業歷史家對這一類的小說當然會嗤之以鼻。簡單地說,一部成功的歷史小說應該盡力遵守歷史專業研究的成果,而用文學的方式和筆調來演繹他對歷史的感受,從而提出他的解釋。所以《三國演義》是典型的歷史小說,《水滸傳》近似,而充滿虛構的人物和想像的情節。而《西遊記》和《紅樓夢》就不是歷史小說,雖然四部小說都反映了作者對人生的命運或冒險患難的想像。相同的,《雙城記》一般也說是歷史小說,但是它充滿了虛構的情節和人物;比起《戰爭與和平》,那麼後者就更接近我們可以想像的歷史小說。兩者都處理大時代的動亂,但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對於歷史事實和哲學的興趣就不如他對小說的文學性的關心。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文學素養當然不亞於狄更斯,而他對歷史的本質與意義顯然勝過狄更斯。
施益堅這本歷史小說非常合乎歷史小說的理想。我相信他的文字造詣一定是卓越的,讀中譯本都可感受得到。更重要的是作者盡量地忠實於歷史背景,用它來闡述一個複雜的時局,並透過重要而出名的中西人物來點出人與人之間因為文明的阻隔而難以溝通的困窘,也刻畫人與責任的需求(甚至於命運)之間的神祕而弔詭的關係。
作者的細膩非常值得欽佩,而譯者的功力也十分稱職。我相信西方人已經從這本書更進一步地瞭解了其實拜上帝教的信徒,乃至於他們的領袖們,對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是用心在揣摩甚至於憧憬的,其實值得西方人反思和同情。相同地,中文的讀者們應該能透過這本忠實可靠的翻譯而進一步把太平天國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裡,才能更中肯地,更理性地審視歷史的複雜與多元,知道文化是需要不斷改造,重新發明的過程。這樣才能把十九世紀西方人所憧憬的進步放在理性的視野裡。
——壬寅年夏初,於華萍澤瀑布
[1] 當然,蕭一山、鄧嗣禹等人也都有相當的貢獻。施友忠(Vincent Y. C. Shih)用英文寫的有關太平天國意識形態的書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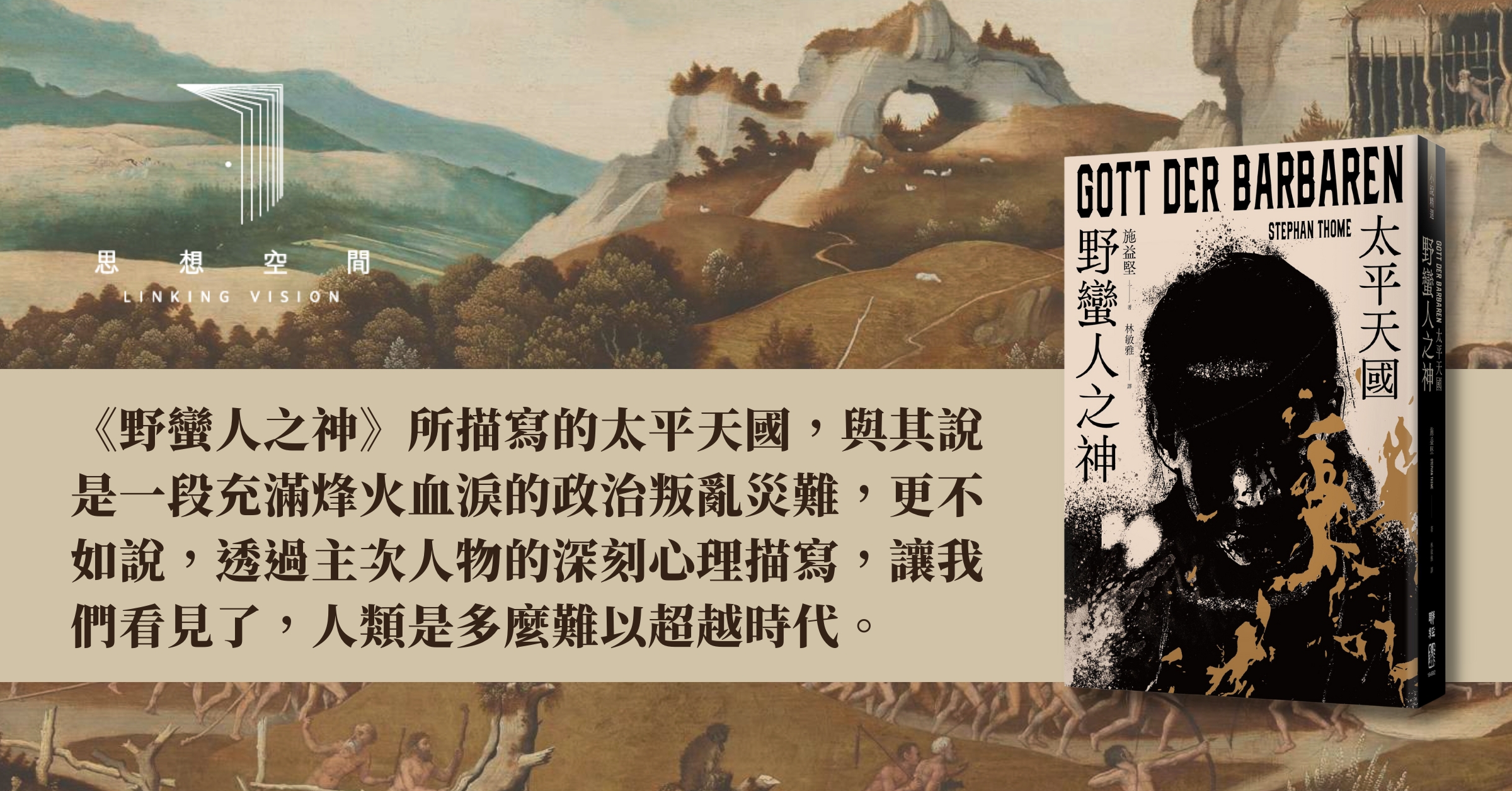
林運鴻:啟蒙一塊沒有光的大地,得比上帝更加顛狂:讀《野蠻人之神》

【森鷗外逝世百年】鄭清茂:超越東西方對立,從容漫步的文學異端

蔡詩萍x林載爵:新世代如何閱讀老靈魂?歷久彌新是高陽
| 閱讀推薦 |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