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編按: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其間不少學人故友、後生晚輩撰文懷念與先生之間的交往,也憶述先生帶給他們的學術啟迪。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曾在學術研究與日常交往中,都感受到余先生如沐春風的溫暖;在先生逝世後,唐小兵寫下情深意重的篇章,從初讀余英時、到認識「文化遺民」精神譜系中的余英時,與讀者們一同懷悼這位對後世影響深且巨的思想大家。(* 本文原刊於《思想》45期,經作者授權轉載。)
真正的史學,必須是以人生為中心的,裡面跳動著現實的生命。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
2021年8月5日對我是晴天霹靂的一天,剛到辦公室沒多久接到一個友人電話,告知余英時先生於8月1日凌晨於普林斯頓在睡夢中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一歲。放下電話,與余先生有關的各種記憶與細節紛至遝來,萬千心事誰訴?我不能自已而致痛哭失聲,恍恍惚惚中度過一整日。窗外綠意蔥蘢,濃陰匝地,在幾乎空無一人的暑期校園裡,陽光穿越濃密的樹葉灑落在地,斑駁的光影彼此錯落,不遠處是如茵草坪及靜靜矗立的第一教學樓。這靜謐悠遠的場景都讓我不斷回想2018年7月15日在普林斯頓余府周圍的草坪與陽光,也是一樣的綠意彌漫,陽光溫煦,仿若世外桃源,更像是新冠疫情來臨之前的黃金時代的最後一刻。我當時在先生家逗留的兩個小時,會在今後的人生不斷被細細回味。我發了微信朋友圈哀悼後不斷有朋友勸慰我不要太難過,都說余先生是高壽且無病無痛夢中離世是有福之人,而且他一輩子著作等身影響華人學界至深且巨,精神生命早已永恆。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仍舊覺得心裡面彷彿突然崩塌了一大塊,空空蕩蕩茫然無歸。余先生活著,我們的心裡就會有一個遙遠的掛念,同時也是一種巨大的安慰,這些年每次跟他簡短通話都會讓我感受到鼓舞,那種潤物無聲讓人如沐春風的溫暖,是只有真實接觸過先生的人才能真切感受到的。如今,春風遠矣!
余先生學問如大江大海,我和學生能夠從中汲取滄海一粟管中窺豹,也足夠滋養一生了。
說實話,不像我的一些同齡人尤其同門學友很早就接觸余先生的作品,我是很晚才開始閱讀余先生的著作。我記得應該是2002年的上半年,因偶然機緣與許紀霖老師通信,新聞系本科畢業在一所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書的我,無知者無畏,向許老師提了好些關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如何融合的大而無當的問題。許老師在回信中建議我除了李澤厚,要多閱讀錢穆、余英時等學人的著作來深度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從那一刻起,余先生的名字就開始在我的心靈裡扎根,我也有意搜求余先生的作品來閱讀。等我2003年秋天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讀研,余先生的作品就成為我們這些研究現代中國思想史的青年學子的必讀作品。我還記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版後,在許老師的課堂上我們專門討論過一次,此外,在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課堂上,我們也跟隨著許老師深入研讀和討論過余先生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余先生的治學兼有考證細密和義理豐贍的特質,而其史學語言又清雅曉暢,要言不煩,節制表達中自有一種綿密的引力,自然最能夠讓我們產生強烈的共鳴。
從研究生時代起,余先生就成為我高山仰止的學界前輩,其學術、思想與踐履型人格都成為我輩楷模。不過,儘管如此,我從未想像會有跟余先生私下交流的緣分。他是遠在大洋彼岸普林斯頓小鎮的一代史學宗師和人文巨匠,而我則是一個藉藉無名的青年學生(後來留校任教成為青年教師),我們之間橫亙著千山萬水的距離。我追隨著先生的腳步,讀他的新作、新的文章和訪談,也常常從師長輩那裡聆聽關於先生行止言談的吉光片羽,常常為之會心愜意並深受啟迪。
2011年12月17日是余先生曾經專門研究過的民國知識分子領袖胡適(見《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誕辰120周年的日子,那一年我愛人從湖南初到上海,任職於《東方早報》文化部,深度參與了胡適紀念專輯的採訪與寫作。當時報社部門領導提出要訪問余英時先生,初到上海工作的她自然沒有門徑去採訪先生,不得已從之前訪問過余英時先生的友人李宗陶處找來先生的電話與傳真號提供給她。我們將擬好的採訪問題傳真給余先生,年事已高的余先生潛心學術寫作,一般不接受訪問,但一來因為與《東方早報》專刊「上海書評」有深厚的情緣,二來也因為擬定的問題激起了他老人家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談談對他影響深遠的胡適的興趣。他作了詳細的書面回應並傳真給我們。一來二去,甚至可以說張冠李戴,我就與余先生算是有了一些「緣分」,偶爾也會打電話問候和請教於他。儘管從未謀面,他對於我卻極為親切和信任,常在電話裡跟我談治學之道、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狀況和家國天下情懷。我記得有一次他推薦我要做好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就得認真研讀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
2009年博士畢業留校任教,根據系裡安排,我講授了一門面向歷史系學生的必修課「中國文史原著講讀」,所用的參考書就是余先生先後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通釋》,學生從書中獲益良多,可惜2014年秋天後余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全面下架,我的學生也因緣際會而擁有了「禁書」,這是讓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擁有」。一扇從余先生的作品去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視窗就此關閉了,但有心求知向學的年輕人總會想方設法,突破文網去尋找余先生的作品和文章來研讀。去年秋天,我給研究生開設「中國文化史專題研究」的選修課程,與近二十位同學共同梳理了從錢穆先生的著作到余英時先生的作品再到王汎森、羅志田等前輩著述的學術脈絡和方法傳承,推薦學生精讀了余先生《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等作品,也可謂從學生身分到教師身分,對余先生所傳承和發揚光大的中國思想文化史學術傳統的自覺接近。余先生學問如大江大海,我和學生能夠從中汲取滄海一粟管中窺豹,也足夠滋養一生了。
讓我極為感動的是,余先生、陳老師為我們一家人分別準備了禮物,給小兒明峻的是余先生晚年長期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吉祥物⋯⋯
2017年秋天,我獲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機會,剛到波士頓就跟余先生通了電話,他很高興我能夠到其曾經任教過的哈佛大學訪學,並歡迎我去他家做客。因為獨自帶著小兒明峻訪學,他又在公立小學上學,很多假期哈佛燕京學社都有周密而妥帖的安排,再加上我初次到美國,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大通,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一直遷延到第二年夏天返回中國之前,我才得償所願攜家人終於踏上了通往普林斯頓之路。不過,在那之前,我常有機會與先生通電話,談天說地信馬由韁,但其實往往不脫治學與家國,這種常常是隨性所至卻每有創獲的交談,成了我在波士頓最珍惜也最奢侈的精神生活。
2018年7月15日的下午,依照約定時間我終於可以去我心目中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鎮普林斯頓拜訪先生,心情自然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歡愉與忐忑。我記得從新澤西住所出發去普林斯頓的那一個午後,是朋友Marvin駕車帶我們全家去的。路上風雲突變,大雨滂沱,車子是從一片水霧迷濛中前行,前行的道路依稀難辨,路途之中接到余先生的夫人陳淑平老師的電話,囑咐我們注意安全,晚一點到達也沒有關係(之前約定了下午三點登門拜訪,余先生一般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而下午接待訪客),這讓我們特別感動。這種細節之中的真誠關切,最能彰顯民國文化滋養出的一代知識人待人接物的溫情與周到。
等我們快到普林斯頓小鎮時,天色為之一變,雨後天晴風和日麗,藍空如洗,綠草盎然,那一刻真感覺有如神啟般的感恩與驚異。我們兜兜轉轉終於找到了幽靜如桃花源的余府,陳老師早已站立在草坪上等候我們了。我們一行五人,除了我們一家三口,還有同在哈佛燕京訪學,早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且此時正好又回到了普大短期訪學的徐蘭君教授,以及紐約的朋友Marvin。神清氣朗穿著短袖淺藍色襯衫的余先生在門口等候我們,我終於見到了先生!那一刻的心情難以言表,既興奮、歡欣又充滿著珍惜之情。我深知有太多的人想拜訪余先生,而余先生年近九十,仍舊筆耕不輟,新作不斷,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彌足珍貴,而他願意拿出一個下午來跟我這個從遙遠的故國來的青年學者漫談,這是一種怎樣的信任、關切和提攜後學的長者情懷!
門外草坪上是一個養著金色鯉魚的小水池,陳老師引導我們短暫駐足,觀看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魚兒,也告訴我們附近時常有鹿兒出沒。落座後,我們就跟余先生自然地交談起來,陳老師也端上了精心準備的茶點和茶水。讓我極為感動的是,余先生、陳老師為我們一家人分別準備了禮物,給小兒明峻的是余先生晚年長期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吉祥物——一隻棕黃色的毛絨小老虎,給我愛人的是一個印著“Knowledge is power”字樣的青白相間精緻瓷碟,而給我的則是余先生親自為我撰寫的一幅字,抄錄的是陳寅恪先生1964年給其晚年最器重的弟子蔣天樞教授新著寫的序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講述了歐陽修撰寫五代史記而改變了五代十國那種澆漓士風,讓士大夫重返一種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的醇正風氣中,並重申了文化比權力更有尊嚴、學術比政治更有生命的主旨(余先生曾經在一個訪談中提及,作為一個畢生致力於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學人,他寧可出現在他人嚴謹學術著作的註腳裡,也不願意出現在某一天報紙的頭條中。這透露了余先生的出處與取捨,也是他一生能夠給後世留下如此博大精深的學術成果的奧祕)。當陳老師將這個條幅在我們面前展開時,我內心極為感動,甚至羞愧於自己何德何能,哪配德高望重堪稱士林領袖的先生花費如此精力和心血寫下這一幅字?!那一刻,我分明感覺到了先生對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學人的期許,字裡行間都是一生為故國書寫歷史的余先生的文化關切與淑世情懷(我不由想起余先生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脫口而出的一句經典名言:「我在哪裡,中國歷史文化就在哪裡!」)。
幸虧錢永祥先生臨時給我安排了這個任務,讓我得以在余府寒暄之外,可以用一個小時的時間集中地向先生請教關於五四百年的歷史源流與因果流轉。
這一次拜訪余先生本來是完全隨意無目的的,直至到了啟程拜訪余先生之前不久,台灣《思想》雜誌錢永祥先生得知我有這個計畫,特意囑咐我對余先生做一個關於五四百年的訪問,並言《思想》雜誌雖然每一期都刊登對兩岸三地乃至歐美華人學者的訪問,但創刊至今尚未能夠有幸訪問余先生。我因為研究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與知識分子史的緣故,之前讀到過余先生關於五四的多篇名文,深感先生對於五四精神與歷史內涵的闡發,常別出心裁而又深具史識且能開闢出一些可以深耕細作的研究新論域。作為《思想》多年的作者和讀者,受惠於這本雜誌的思想與學術啟迪很久,自然應當飲水思源義不容辭。匆促之間,我連問題都沒來得及好好準備事先提交給先生,而且是到了新澤西之後才跟余先生電話中提及這個臨時多出來的訪問計畫。余先生稍一考慮就爽快答應了。如今追憶,幸虧錢永祥先生臨時給我安排了這個任務,讓我得以在余府寒暄之外,可以用一個小時的時間集中地向先生請教關於五四百年的歷史源流與因果流轉。[1]
預定兩個小時的拜訪時間匆匆消逝,我們不想讓先生太疲憊,就決定辭別了,在余府門口,我們一行與余先生、陳老師合影,留下了美國之旅最珍貴的影像記憶之一,我也請余先生在我從中國帶過去的先生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扉頁上題簽。在辭別之際,余先生很鄭重地告誡我不管時代如何巨變,世道如何艱難,都要將真正的知識與文化傳遞給下一代,用他廣為流傳的話來說,就是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這一情景與他寫的陳寅恪先生贈蔣天樞的條幅彼此交錯疊加,我深切地感覺到了中國讀書人守先待後薪火相傳為中國文化託命的「學脈」之真義。如今面對書架上對我微微笑著的先生的照片,我想起先生已經遠行,再也不能當學術與人生遇到難題時可以請益他時不禁悲從中來。話雖如此,臨別時余先生的贈語如醍醐灌頂更如空谷足音長久迴盪,人之相交,貴在知心,真誠所致,念念不忘。
等我歸國之後就著手整理訪談錄音,並傳真給余先生。這一次余先生再一次讓我震撼,不會使用電腦的他密密麻麻地手寫補充、完善我傳過去的文稿,整整達到了30頁,分成幾次才成功地傳真過來。對於我所提的關於五四啟蒙與戊戌啟蒙的關係、啟蒙與革命、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等問題,余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都給予了獨特而深刻的詮釋,尤其是對於五四的歷史意義的層累形成、五四在空間和地方上的差異化傳播等問題都別有洞見。這篇訪問記在台灣《思想》雜誌刊登後也引起了較大的學術和社會反響,我猜想應該是余先生晚年接受的最後一次學術訪問。念及於此,我就深深感動於余先生對待學術與思想的執著與熱忱,對歷史認知的通透與深邃,以及對人文與理性之中國的期許。他在傳真紙上的書寫和細微處的修改痕跡,以及每次傳真前附頁的文字說明,都在此時無聲勝有聲地傳遞著一個人文主義史家的學術情懷。如今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更是感歎於造化因緣的奇異,讓我能夠在新冠疫情全球爆發之前有機會赴美拜會余先生,並留下這一心靈和學術對話的記錄。
余先生代表了二戰結束以來華人知識界的典範人格,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有真切深入的了解與研究,並能堅持一種「反思的平衡」之價值立場⋯⋯
余先生去世之後,諸多師友紛紛在微信朋友圈紀念,可以說是近些年去世的老一輩知識人中間最受兩岸三地學人和文化人愛戴的一位了。《財新週刊》也突破封鎖,在網路上發表了余先生的老友陳方正先生的追悼文章和秦暉教授的紀念文章。之後在與台灣錢永祥先生通話中談及余先生一生之志業和學術文化貢獻時,我們都認為余先生代表了二戰結束以來華人知識界的典範人格,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有真切深入的了解與研究,並能堅持一種「反思的平衡」之價值立場,但又不像其老師錢穆先生過度浪漫化中國的文化傳統,對於西方文明中所蘊藏的基本人類價值持一種開放接納的態度,試圖將這套現代的價值系統接引到中國的現代文化傳統之中,實現中西文化之間良性的互動交流。余先生既是一個學術人(可是從無學究氣,更無學術權威氣),又是一個公共知識人(但從不因為對政治的關切而損害了學術的創造,更不會因此而損傷了自我的心靈生命,政治關切始終是他學術生命之外偶爾的興趣,是踐行一個現代士人公共關懷的職責而已)。更為難得的是,余先生的學術與人格如月印萬川,交相輝映,其學術與思想在很多方面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論域,可以說從堯到二十世紀中國,他都有涉獵而且是專精的涉獵,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空間裡,余先生待人友善,為人親切,尤其樂於提攜年輕知識分子和學人。這些精神人格的特質無需我多言,從早幾年台灣聯經出版的紀念文集《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的字裡行間,亦可處處感知到先生的風采與精神。
余先生已經遠行,再也不能聆聽其爽朗的笑聲和親切的教誨,此時此刻,除了追憶和哀念以及傳承先生遺志,我也由先生一生的學術寫作與教書育人之幾近功德圓滿,而想起自己去年底在香港《二十一世紀》發表的〈二十世紀中國精英文化的花果飄零〉一文,在該文裡我慨歎民國一代培養的人文知識人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運動中的身世與命運,進而感歎造化弄人讓諸多具有天分也有良好學術訓練的知識人,不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最後都是如余先生論史家顧頡剛所言是「未盡的才情」。若以顧頡剛、何兆武、瞿同祖、巫寧坤等1949年之後或留在大陸,或歷經千辛萬苦回到中國的學人之命運及著述而論,余先生真是一個歷史的幸運兒,也正因為這種幸運與自身的沉潛學術,而得以實現了最高的學術理想與人生目標。由此,我想起了台灣詩人瘂弦在回憶錄的序言中提及的一個命題:人生完成度。他如此寫道:
到了我這個年齡,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其實是沒有完成自己。記得楊牧詩中有一個句子,大意是:在維也納郊外的墓園裡,躺著一個完成了的海頓。是啊,完成了的海頓!弘一法師用「花枝春滿,天心月圓」來形容完成的感覺,最為貼切。是啊,完成很重要。而我就是一個沒有完成的人。[2]
他們在戰爭歲月留學,後來大部分基於家國情懷和對新中國的憧憬回國報效,結果成為了未能人盡其才甚至顛沛流離吃盡苦頭的一群人。
我在想,余先生也完全配得上「花枝春滿,天心月圓」這八個字。讀過先生回憶錄的人都熟知一個影響余先生人生走向的關鍵細節。1949年底,正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余先生,利用寒假去香港探親,看望移居香港的父母等親人。父親余協中教授希望他能夠留在香港跟隨其時在港篳路藍縷創辦新亞書院的一代史學名師錢穆先生讀書,也可以作為長子順便照顧兵荒馬亂中的家人。余先生一則不願捨棄學業,二則作為當時的進步青年也不願長久滯留殖民地香港,所以還是決意回燕大繼續學業。火車到了廣州因故障短暫停留於一個叫做石龍的小站達四五個小時,余先生也因此沒法當天坐車北上,只能等待第二天的火車,彼時彼刻,余先生也面臨一個類似於王陽明龍場頓悟那樣的天人交戰,去還是留,成為一個何以安身立命忠孝難以兩全的生命抉擇。余先生在回憶錄中坦承了思想大轉折的心路歷程:
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絕對不願在這種情況下棄父母於不顧。但在理智層次,我始終不能接受香港這個殖民地可以成為我長期居留之地,我當時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學術研究則是我最為嚮往的人生道路。……總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國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無可動搖的一大信念。……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也是過重外在的形式而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幾個月來一直深深困擾著我的「天人交戰」,突然消逝不見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靜與和暢。[3]
余先生這個從顧念家庭的小我視角出發的考量,最後成就的卻是現代中國人文傳統在北美的一脈相傳(後又回饋給兩岸三地華人學術界),並開花結果形成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學統。一個細小的決定,對於余先生的人生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假若他當年回到北京,朝鮮戰爭爆發,香港與大陸隔離,出身於上流知識分子家庭的他估計只能在檢討與悔罪中白白耽誤青年甚至中年時代,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為海內外矚目的學術成就。余先生的回憶錄最後一章寫到了兩代哈佛中國留學生的命運,前者是1920年前後竺可楨、趙元任、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李濟、洪深、梁實秋、梅光迪等群星閃耀的一群人,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文化與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自然這個貢獻主要是在1949年之前做出);後者是指抗戰後到哈佛留學的楊聯陞、週一良、吳於廑、任華等一群青年,他們在戰爭歲月留學,後來大部分基於家國情懷和對新中國的憧憬回國報效,結果成為了未能人盡其才甚至顛沛流離吃盡苦頭的一群人。如今細想,余先生的回憶錄收束於對兩代哈佛留學生命運的慨歎,又何嘗沒有一點對自身因緣際會得以留學哈佛任教於美國學府,進而得以避免在新中國歷經磨難的感歎呢?他自然沒有絲毫的自矜與慶倖,而是深深惋惜於一代代天賦異稟才華橫溢的知識人的生不逢時造化弄人。
對照之下,我不由得想起前不久去世的何兆武先生。他出身於西南聯大,學術訓練充分,又天資過人,可是在1950年代之後等待他的只能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的折磨,在一個將意識形態當作治國綱領的社會,獨立於權力的學術與文化只能奄奄一息。幸虧他晚年留下了口述史《上學記》、《上班記》,讓我們得以管窺民國時期西南聯大那樣一個天才成群結隊地湧來的象牙塔,那種自由而多元且富有原創性的人文主義傳統後來自然是被腰斬。何先生半為戲謔半為自傷地說過,他們是報廢的一代人!「報廢」兩個字隱含著何等的傷痛與惋惜!1950年代初,當余英時先生決定放棄燕大學業留在香港時,巫寧坤卻放棄了在芝加哥大學即將拿到的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應大學時代的老師趙蘿蕤的盛情邀約回到燕京大學任教,等待著他的命運是他被劃為右派經歷了九死一生之後提煉的人生三部曲「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而在學術生涯早、中期就寫下《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等經典的瞿同祖,1965年從加拿大回國後也基本上是無所作為度過後半生。他在晚年接受一個青年學者訪問時愴然涕下言及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代,學術生命自然無從施展。這樣的人生故事,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上俯拾皆是,讓人不勝唏噓,還有更多的歸國科學家的故事,可能因為史料、知名度等各種原因尚未進入公共記憶的範圍,至今仍處於被遺忘和被遮蔽的境地。
楊瀟的重走歷史旅途也是在對自我展開尋找,余先生的回憶錄也同樣是對自我的生命之路的奧祕在進行鉤沉。人生何以完成?如何在一個動盪時代保持個體心智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完整性?
行筆至此,想起7月下旬,颱風煙花肆虐江南的時刻,我在杭州南高峰下的六通賓館給一個暑期學校修和書院授課(余先生生前曾應邀為書院題署校名寄意深遠)。因主事者裕榮兄之介紹結識了紀錄片《西南聯大》和電影《九零後》的導演徐蓓,在風雨蒼茫的午後,我們一見如故,談及她採訪過的許淵沖、馬識途、楊苡、巫寧坤這群西南聯大老人的生命歷程與人生際遇,對於這群知識人在天旋地轉的二十世紀中國雖然飽經滄桑,卻終究能夠有所作為,為文學、學術與歷史留下見證而感懷不已,更多的有才華也有抱負的讀書人卻尚未開花就已經永久地沉沒到歷史河流的底部而湮沒不聞。我也熱烈地談及所注意的哈佛這兩代留學生的生命走向,並熱切地希望徐導能夠將百年前這群哈佛留學生的生命故事以影像記憶的方式呈現給今天的00後一代。我們也不約而同地提及今年出版的非虛構寫作作品《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這是我們一個共同的青年朋友楊瀟所撰寫,他通過四十六天的徒步,沿著當年長沙臨時大學從湖南到貴州抵達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的足跡重走了這條歷史之路,並以縝密的考證、紮實的田野和優美的敘事,將歷史寫作與旅行寫作近乎完美地結合了起來,呈現了歷史敘事所能夠包含的精神力量與人文之美。

無論是紀錄片也好,還是非虛構寫作也好,其實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從歷史深處生長出來的問題:西南聯大這一代人或者說哈佛幾代留學生的人生完成度跟歷史、政治、時代與個人的心性之間的關聯究竟如何?在面對一個給定的政治框架與時代格局時,作為個體的知識人該如何在時代巨變中錨定自我的歷史方位,以一種既有韌性也有智慧的方式來突破處境的限定而盡最大可能完成自己?面對一個可能不斷下沉的世道與衰敗的文化,讀書人又應該何以自處才能既不憤懣而陷入政治性抑鬱又不自憐自傷?有時候,刻意的啟蒙可能會因菁英的姿態而疏離了被啟蒙的對象,而在天地玄黃中能夠盡可能完成自我,活出一種生命的豐厚與承擔來,這種人格的感召力恰恰是這個虛無而亢奮的時代所亟需的。
你拚盡全力有尊嚴地活過的一生就是你的終極作品。從這個意義而言,其實楊瀟的重走歷史旅途也是在對自我展開尋找,余先生的回憶錄也同樣是對自我的生命之路的奧祕在進行鉤沉。人生何以完成?如何在一個動盪時代保持個體心智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完整性?余先生多年前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訪問時就曾經以一種平易的語言表達了對這個所謂「人生完成度」問題的思考:
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權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麼環境,儘量做自己該做的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4]
楊瀟在經歷了艱辛而漫長的重走旅途,以及對歷史世界中的西南聯大人的生命故事的追索之後,如此對他自己其實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進行反省:
有時候我會想我們出生於1978-1985年這一代人漫長的、好像永遠也不會終結的青春期。有好幾年的時間裡我的身邊滿是懸置著、漂浮著的朋友們,相信一切還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種可能性,其實自己已經老大不小。現在看來只是我們恰巧趕上一個國家的上升曲線,勢比人強,卻讓我們誤以為一切可以持續,遲遲不肯降落,以致浪費了太多的時間——不要誤會,我仍然認為無休止的旅行、觀影、清談和漫無目的的閱讀是珍貴的,可倘若我們真的想要「創造」出什麼,想有屬於自己的「一生志業」,那需要強烈的信念感、長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來的心力。[5]
我寧可將余先生對年輕一代人的告誡和楊瀟在歷史行走中的反省看作是兩代人之間超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和心靈契合。而作為一個從事人文學術研究和寫作的人而言,更為重要的是需要進入歷史的精神譜系,尋找到能夠激勵自己前行的典範人格和思想資源。余先生曾經在跟一個陷溺在茫然與憤激中的學者蘇曉康的談話中如此開示:「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6] 我想,余先生早已超越了有限的此生,而融入了「文化遺民」的精神譜系之中。
2021年8月6日至9日初稿、修訂
謹以此文紀念我永遠追懷、敬仰的余英時先生
* 作者按:本文〈二〇二一,春風遠矣:敬悼余英時先生〉初稿完成於余先生去世之後,後因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為中研院《中國文哲通訊》組稿專輯紀念余先生,為篇幅和主題所限,將論文的前半部分交付發表,現交付《思想》雜誌發表的是文章全文,比較完整地呈現了我對余先生及這一代知識人的學術與人格之認知與敬意,特此說明。
[1] 請見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思想》37期《「五四」一百週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139-151。訪談請見同期唐小兵,〈「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頁153-174。
[2] 瘂弦,《瘂弦回憶錄》,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序言,頁2。
[3]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8,頁96-97。
[4] 李懷宇,〈余英時: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時代週報》,2011年2月9日。
[5] 楊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頁559-560。
[6] 蘇曉康,〈忽到龐公棲隱處〉,載台北《印刻文學生活誌》,2018年10月號「余英時回憶錄專輯」,頁82。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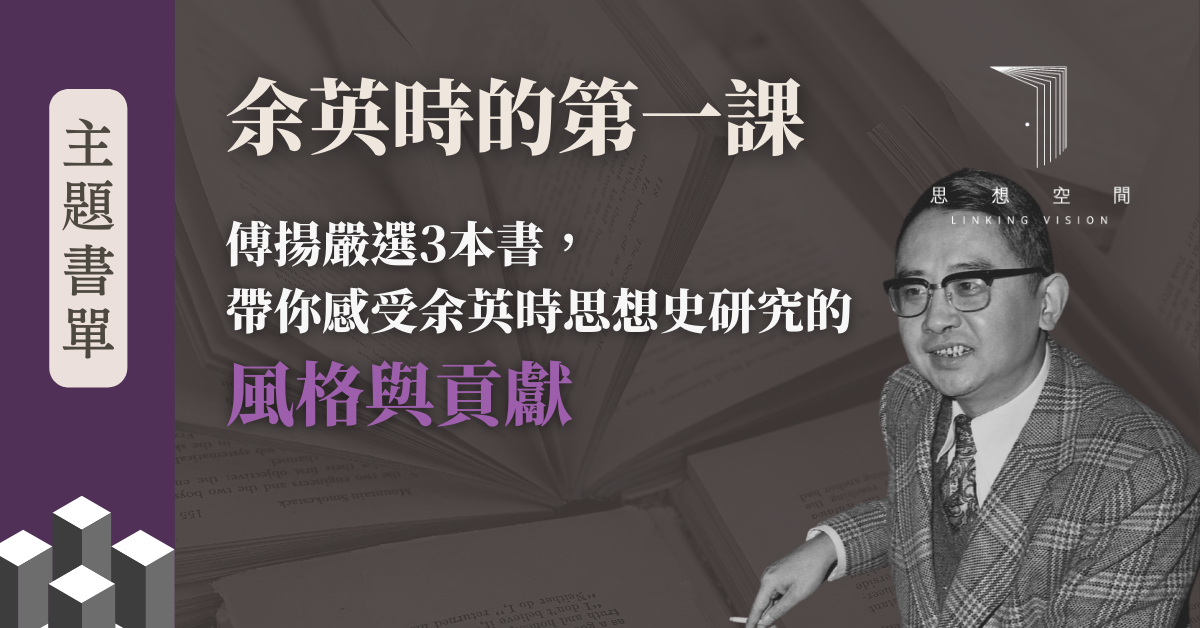
【主題書單:余英時的第一課】傅揚嚴選3本書,帶你感受余英時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與貢獻

容啟聰:第三勢力與冷戰:由余英時的《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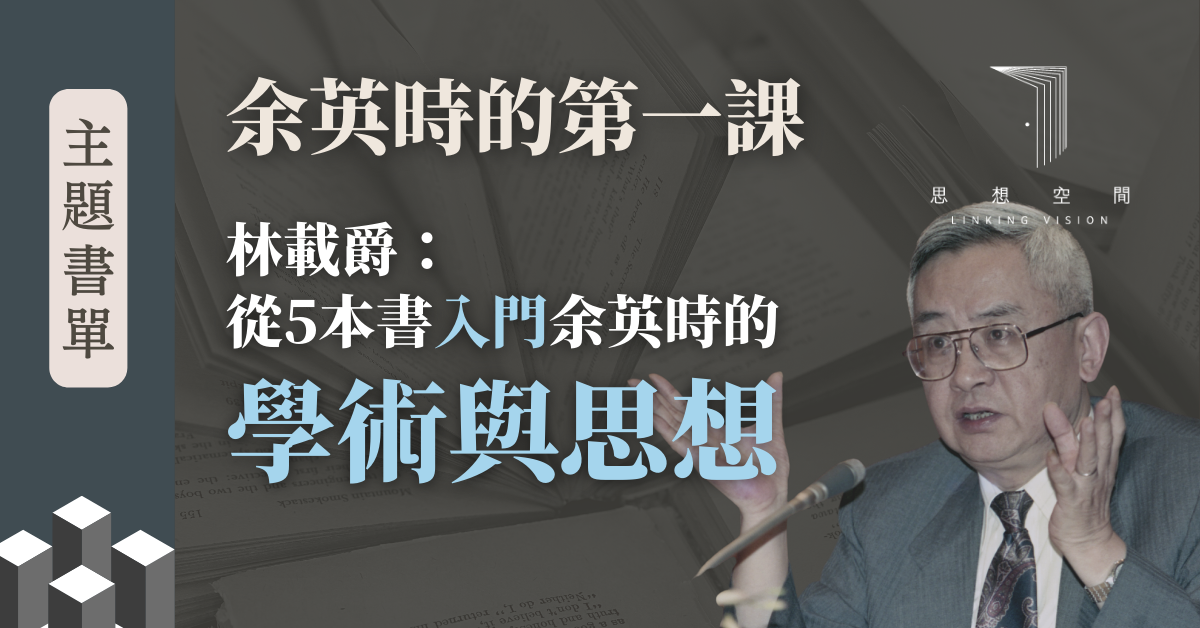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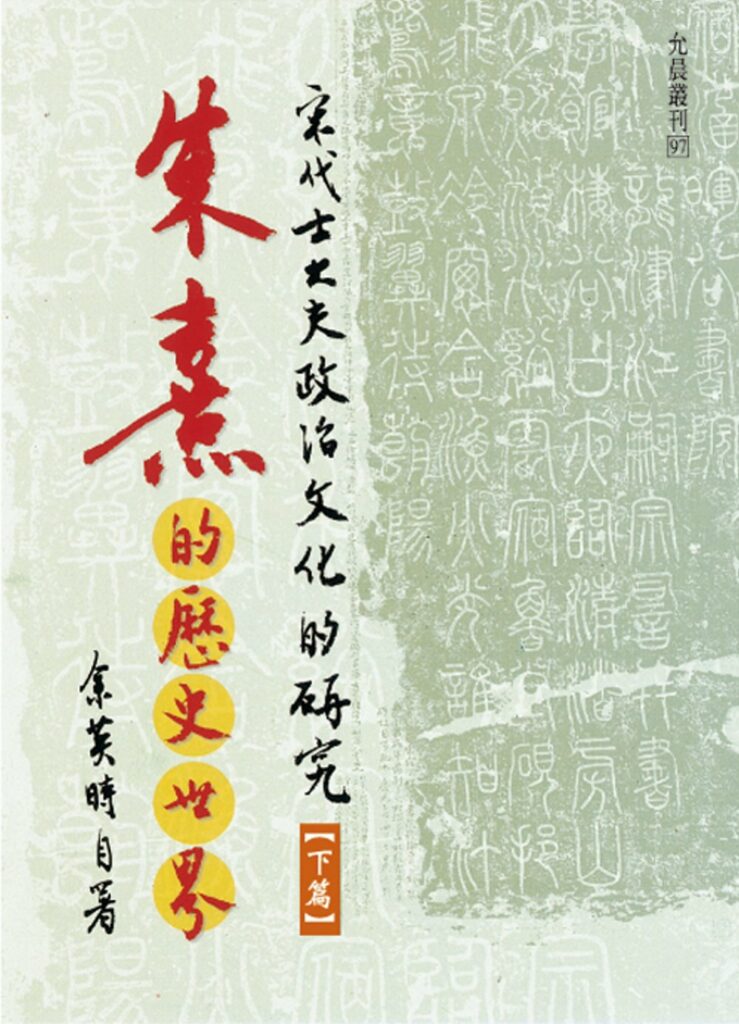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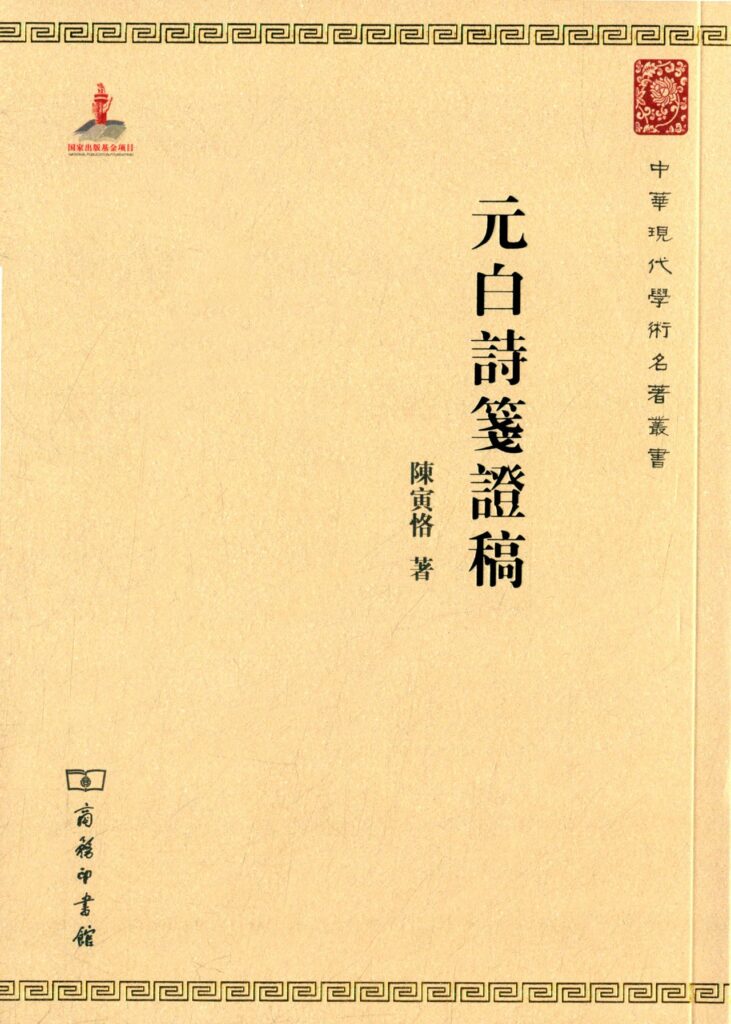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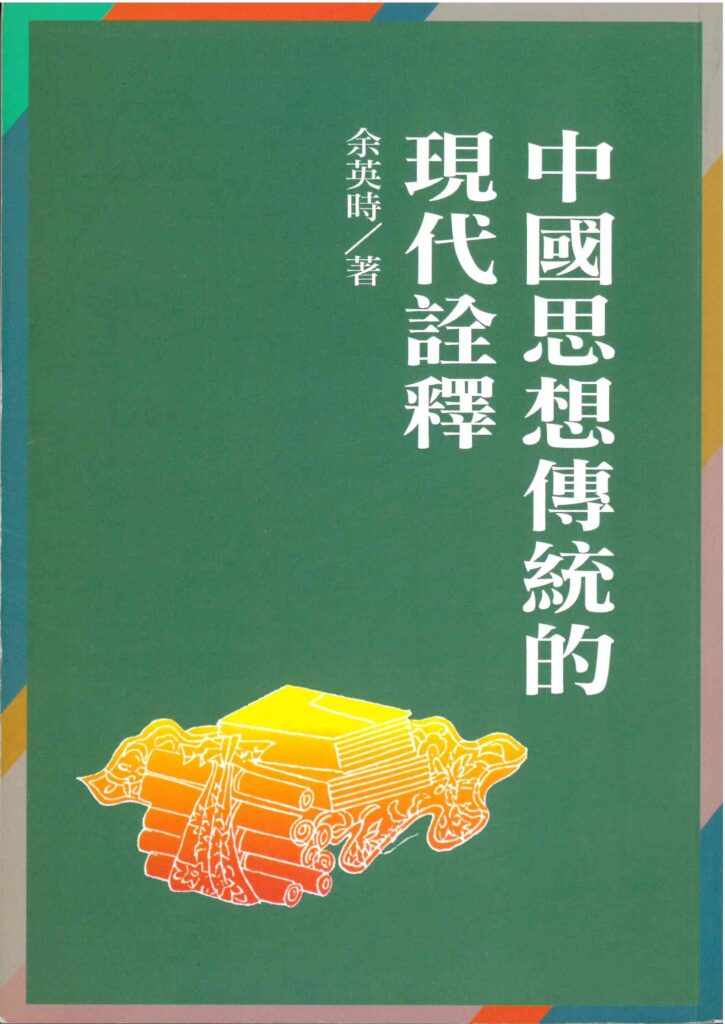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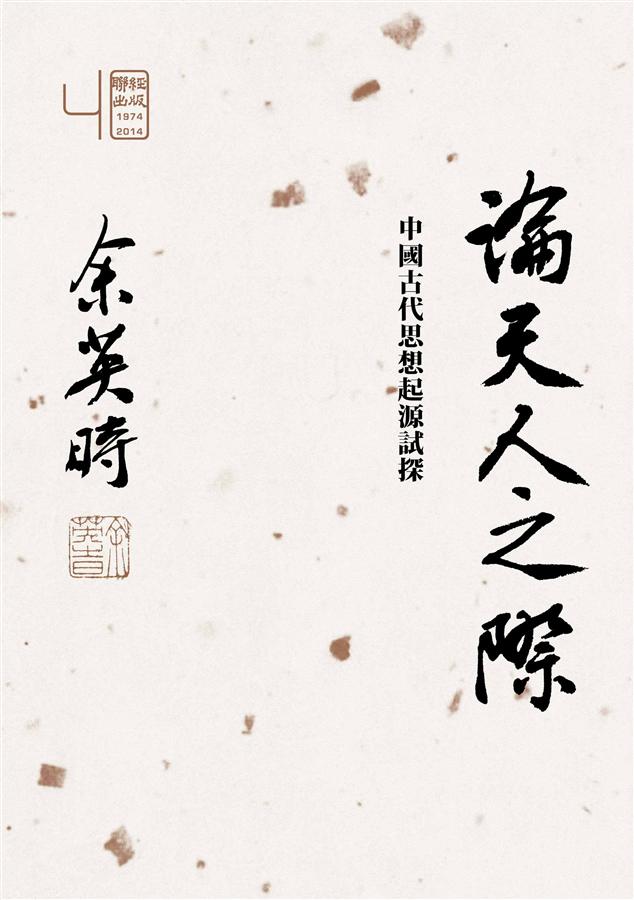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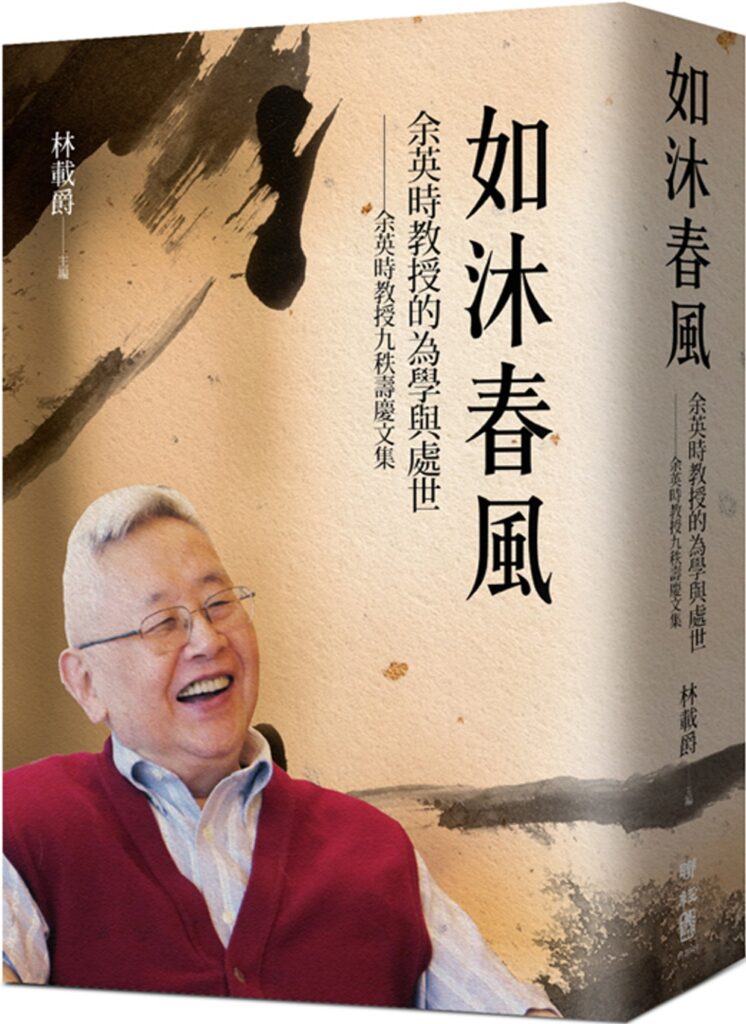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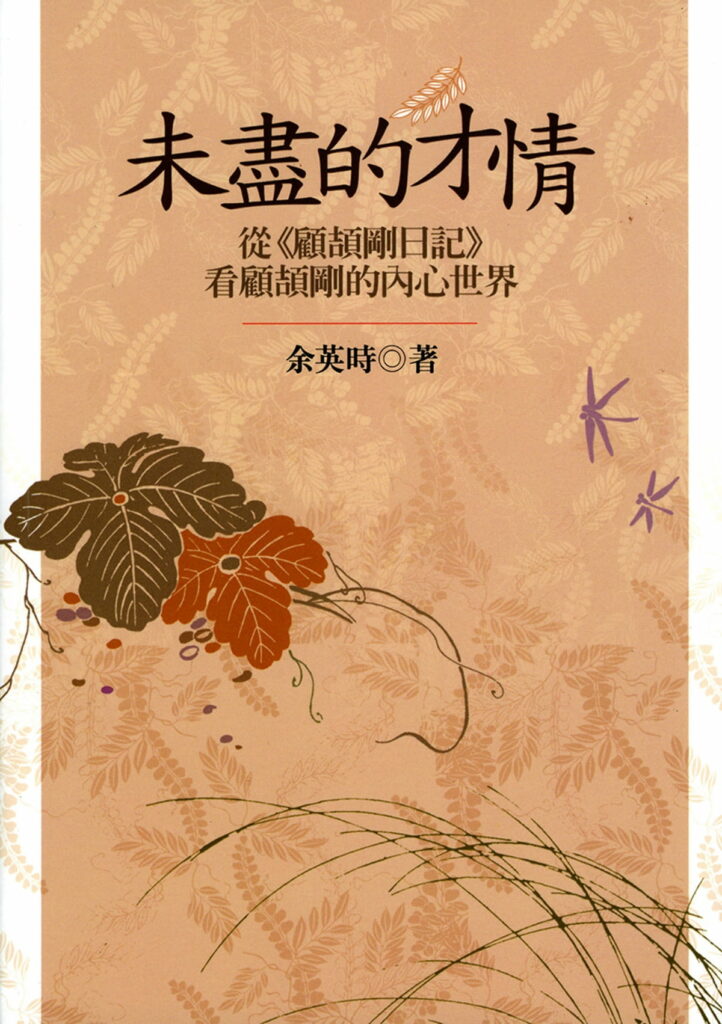





Be First to Comment